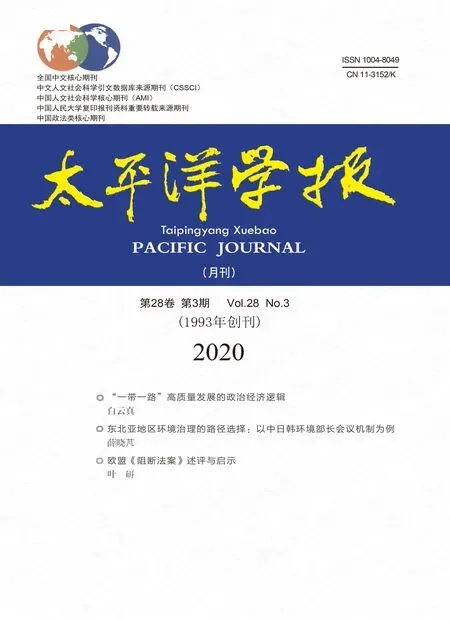澳大利亚对南极条约体系的影响:基于历史与现实利益的分析
吴宁铂 [澳]马科斯·哈沃德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 201620;2.塔斯马尼亚大学,霍巴特 7001)
澳大利亚的南极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一百多年前的“英雄时代”(1)1895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6届国际地理大会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认为南极地区是目前地理探险最重要的目标,国际科学界应当在本世纪结束前开展相关的探索与研究工作。从1898年至1922年,以英国为首的10个国家响应号召共计派出了17支探险队伍。由于当时交通与通讯技术领域尚未取得变革性发展,南极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也十分有限,加之恶劣的气候状况与复杂的地质地貌,使得探险队员往往面临着常人所无法忍受的生理与精神极限考验,但即便如此仍然涌现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伟大发现和人物事迹,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为“英雄时代”。(Heroic Era)开始,澳大利亚一直是南极探险与科学考察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之一。道格拉斯·莫森(Douglas Mawson)等人取得的业绩和对英国“南极领土”让与的国内立法为澳大利亚近6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领土主张提供了支持。但在南极恶劣的气候环境、偏僻的地理位置、得不偿失的经济开发价值和两极格局制衡等因素的影响下,澳大利亚选择与十一个国家共同签署《南极条约》,并在以该条约为基石所形成的南极条约体系的完善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学界对澳大利亚与南极条约体系关系的研究视角过于宏观,多为政策解读和事实陈述,鲜见理论与实证结合的深层次分析。澳大利亚提出南极领土要求的历史渊源从何而来?二战结束至1959年《南极条约》诞生期间,澳大利亚对南极国际治理的立场出现反转的主要客观因素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澳大利亚自认为对《南极条约》谈判起到了关键作用?澳大利亚在推动南极条约体系内部发展和迎接外部挑战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面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未来走向,澳大利亚的南极政策与立法将何去何从?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关注和解答,将对我国在南极治理中明确法律适用、参与规则构建和作出利益抉择等提供有价值的指引,为我国南极事业建设注入更强大的助推力。因此,本文将结合澳大利亚的相关南极活动,介绍澳大利亚在《南极条约》缔结前后政策转变的背景,探讨南极条约体系不同历史时期内的澳大利亚南极利益重点的形成、确立与转变的原因,分析澳大利亚促成《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马德里议定书》和南极条约秘书处和应对外部挑战的动机,评估南极条约体系对澳大利亚南极利益的保障效果。为我国在南极事务中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维护南极权益与彰显大国责任的均衡性,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一、澳大利亚在“前南极条约时代”的南极活动
早在18世纪末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伊始,在丰厚商业利润的驱动下,作为其支柱行业的捕鲸业逐步将捕猎范围深入到本土以南广阔的高纬度寒冷海域,形成了澳大利亚与南极地区最早的联系。随着1820—1821年南极大陆的发现,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等国以澳大利亚南部的悉尼、霍巴特等港口为后勤补给大本营,于19世纪中期相继组织了对这片未知区域的官方探险活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地理发现。将南极视为自己“伟大冰雪近邻” (Great Frozen Neighbour)的澳大利亚不甘充当他国进入南极的跳板,开始致力于本国的南极科学研究和考察。1886年澳大利亚南极探险委员会(Australian Antarctic Exploration Committee)在墨尔本创立;1898年来自塔斯马尼亚的物理学家路易斯·伯纳基(Louis Bernacchi)成为首个登上南极大陆的澳大利亚人;1907—1909年,澳大利亚地理学家道格拉斯·莫森、埃奇沃思·戴维、伯特伦·埃米蒂奇、利奥·卡顿以及约翰·金·戴维船长参与了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Shackleton)对南极的远征并首次发现了南磁极的位置;(2)“Australian Antarctic Expedition 1911-1914”, Australia Antarctic Division, Dec.15, 2017.1911—1914年道格拉斯·莫森领导了澳大利亚独立后首次南极探险与考察活动,揭开了澳大利亚自主参与南极事务的序幕并成为澳大利亚所谓“南极主权”确立的基础;(3)“Australia in Antarctica: Building on Mawson’s legacy”, Australia Antarctic Division, Dec.17, 2017.1928年,澳大利亚探险家乔治·休伯特·威尔金斯(George Hubert Wilkins)成为驾驶飞机飞越南极半岛的第一人;1929—1931年,道格拉斯·莫森率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联合考察队对东南极进行了勘测,其所取得的丰硕科考成果戍为澳大利亚进一步对南极地区提出领土主权要求的依据;1933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发布一项枢密令(Order-in-Council),将原英国主张的南纬60°以南、东经160°至东经45°之间除法国要求的“阿德雷地” (Adelie Land)之外约占南极大陆总面积42%的土地移交澳大利亚联邦所有,即“澳大利亚南极领地”(Australia Antarctic Territory, 简称AAT)。澳大利亚进入初步巩固和控制其 “南极领土”的时期。从那时起,澳政府开始尝试通过多种途径向国际社会展示其对所主张的南极区域拥有主权的依据,包括经谈判取得法国和挪威对彼此“南极领土”边界的承认,公布道格拉斯·莫森两次远征南极所收集的科学数据,出动飞机在其“南极领土”的多个地点投放澳大利亚国旗,着手绘制全面的南极地图以及计划派遣更多的探险队以寻求建立起永久控制等。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在所有南极主权要求国中态度最为积极,活动最为频繁。但随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波及,澳大利亚被迫暂时中止南极活动,全面转入战时轨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趁着英国陷入战争泥潭无暇顾及南极的时机,智利和阿根廷根据南美大陆与南极半岛地质上的亲缘关系、有效占领理论以及西班牙原来所宣称的对“南极领土”要求的继承,相继宣布对南极半岛及其邻近地区享有主权,造成了与英国主张区域相互重叠的争议状况。二战结束后,英国势力重返南极,与阿根廷、智利两国在所涉“南极领土”归属与划分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加剧,南极安全局势陡然紧张。为了避免三国冲突损害自己苦心经营的全球战略同盟及国家利益,1948年,美国向争议各方提议,应当建立一项南极国际化的制度以确立起对该地区的共同管理。澳大利亚虽然表态愿意通过合作寻找解决方案,但对南极问题国际化的必要性提出质疑。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埃瓦特(Evatt)表示,澳大利亚基于不放弃其“南极领土”内的矿物和其他资源权利的立场,不支持任何将澳大利亚“南极领土主权”与其他国家的主张合并的观点。(4)“Letter from H.V. Evatt to J.B. Chifley (8 February 1949)”,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1838/2, Item 1945/18/2.
二、澳大利亚与南极条约的缔结
2.1 南极国际治理:从抵制到接受的转变
进入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气氛日渐浓厚的大背景下,苏联试图涉足南极事务引起了英、法的恐慌。两国敦促美国尽快出台旨在限制苏联在南极活动的宣言。在参考了智利法学家埃斯库德罗早些年有关南极中立化的设想后,美国提出冻结南纬60°以南的所有领土主权要求5~10年、科考自由、成立协商委员会等建议。(5)Neal H. Petersen, John P. Glennon, et al.,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50,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ume 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807-809.对此,澳大利亚仍坚持其维持南极现状的立场,担忧成立协商委员会将为苏联开辟一条轻易控制南极的捷径:苏联或其他非缔约国在“冻结期”内的实际控制和活动将构成领土权利而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因此,澳大利亚坚持维持南极现状,反对南极问题国际化,美国的提议再次搁浅。(6)Marcus Haward and Nicholas Cooper, “Australian Interests, Bifocalism, Bipartisanship, and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Polar Record, Vol.50, No.1, 2014, pp.3-4.
随着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简称 IGY)的到来,局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先前提出国际共管南极建议两度遭遇阻挠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科研名义获得了一种以不直接威胁澳大利亚“南极主权”要求的方式来涉足南极治理领域的机会,拥有丰富极地研究经验的苏联以类似的理由加入也显得顺理成章。美苏两国在南极组织大规模考察活动,在澳大利亚“南极领地”的内陆战略要点兴建科学考察站,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南极科学竞争热潮。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理查德·凯西(Richard Casey)意识到:美苏以科考为名介入南极事务的局面已成既定事实,为避免构成对澳大利亚“南极主权”的承认,美苏不可能在澳大利亚“南极领地”内建立科考站前事先寻求澳大利亚的许可。为了在重申主权的前提下体面地解决这个敏感问题,凯西采取了一项重要的外交活动:公开发表声明欢迎国际物理年的各参与国,并愿意为那些希望在澳大利亚“南极领地”范围内从事科学研究的国家提供帮助。(7)“Australian Claims in the Antarctic”,1956,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1838/283, Item 1495/1/9/1(Part 1).就像他在日记中写道的,“如果我们不能阻止美苏等国,那就最好坦然去接受。”(8)Marcus Haward and Tom Griffiths, Australia and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50 Years of Influenc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11, p.73.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澳大利亚被迫调整了原先立场,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以适应冷战环境下的国际新秩序。
令澳大利亚稍感安慰的是,由于智利、阿根廷同样担忧苏联可能利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活动所确立的实际存在提出领土要求,这两国牵头提议,各国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活动都不得对南极主权问题产生任何影响。(9)Walter Sullivan, Assault on the Unknown: The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McGraw-Hill, New York, 1961, p.293.此举得到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12个南极利益相关国的一致赞同,从而达成了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不去进行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争论,以便保证使那些科学研究计划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的“君子协议”。(10)陈力等著:《中国南极权益维护的法律保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这也使澳大利亚能够与各国在南极安心进行科学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而不必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同时为《南极条约》的缔结奠定了政治基础。而通过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的调研,澳大利亚认为当时阶段南极矿产资源尚无开采价值,因此不值得为维持这片冰雪覆盖的贫瘠土地的领土主张付出过多外交和经济代价,这为其支持《南极条约》第四条“冻结条款”埋下了伏笔。(11)Alessandro Antonello, “Australia, the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and the 1959 Antarctic Trea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ol.59, No.4, 2013, pp.532-546.
2.2 助推南极条约谈判顺利进行
美国因其在构建南极治理规则与解决“南极领土”纠纷当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而扮演着《南极条约》设计师的角色。澳大利亚则因与南极相对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和对苏联觊觎其“南极领土”的警惕,积极在《南极条约》酝酿与具体条款磋商中充当起美苏之间的撮合者,在相当程度上促使条约谈判朝着本国预期方向发展。澳大利亚先是在谈判酝酿的初始阶段反对美国撇开苏联单独控制南极的安排,保证了《南极条约》最终的完整性;后又在谈判因草案内容争议而停滞不前时,协调各方立场,说服苏联接受《南极条约》第四条。所以,澳大利亚官方和民间长久以来都认为,相比于美国,本国对《南极条约》的历史贡献也是不遑多让。
(1)反对美国排斥苏联,避免南极问题的两极对立
在有关南极的国际治理问题上,美国最初的设想是“7+1”模式,即由美国组织其他七个主权要求国就争议问题展开谈判。在这七国中,智利、阿根廷是美国构建的泛美联盟及其互助条约中的重要盟友,英国、法国、挪威是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中美国的保护对象。所以美国确信,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由美国及其盟国单独控制南极的局面将更易于解决彼此间存在的争议。澳大利亚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苏联以科研名义在澳大利亚主张的南极领土范围内建立了若干科考站和后勤基地,已经形成了实际存在的局面;苏联必然会拒绝承认任何没有其参与的对南极的国际安排;由此,苏联甚至会趁机提出领土要求并单方面采取实际控制措施,冷战两极对抗格局又会在南极上演。总之,澳大利亚认为,苏联介入南极事务的既定方针无论外界态度如何都无法更改,解决南极问题完全排斥苏联是不现实的。解决南极问题的途径是在不放弃主权的前提下由包括苏联在内的各相关国缔结一项致力于南极科学合作与非军事化的协定,以免在“冻结”南极法律地位时影响到各国在该地区的后续活动。(12)“Memorandum of Conversion between Daniels(G), Wilson(ARA) and Booker(Australian Embassy), Border (Australian Embassy), 5 February 1958”, Department of State, Central Files, 702.022/2-558.
1957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四国会议上,澳大利亚会同新西兰和英国向美方表达了上述立场。这使得美国在综合各方情况后对其南极政策作出了重新评估和调整。(13)“Memorandum no 1150/57, 23 October 1957 ”,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1838/2, Item1495/17/1.195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赞成通过建立一项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制度来和平解决南极问题。同年5月,美国邀请包括苏联在内的十一国政府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解决南极问题的会议。6月,上述各国陆续接受美国邀请,《南极条约》谈判的序幕正式拉开。
(2)敦促苏联转变立场,消除条约谈判的最大障碍
南极条约谈判从1958年6月开始。至1959年3月中旬,与会各国就条约前三条的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即南极仅用于和平目的、科学调查自由与促进国际合作,但对条约其余九条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保留和疑虑。其中最主要的争议集中在第四条有关“冻结”南极法律地位现状的讨论。其中苏联的立场最为激进,提出“搁置领土要求和政治纷争最佳途径是在条约中不要提及它们。”(14)Suzanne E. Coffman and Charles S. Samps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United Nations 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 Matters, Volume 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fice, 1991, pp. 539-547.美国等国与苏联在是否接受第四条内容的问题上分歧严重,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在会议召开之初就强调:“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争议扰乱南极的和平。”他也承认未对南极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保留其立场的权利不应被缔结的条约所削弱。《南极条约》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力消除彼此之间的猜疑。凯西与苏联副外长费德林就南极问题交换意见时,阐述了关于冻结南极主权要求的观点,并确信美国等国对苏联的立场可能存在根本的误解。为此,澳方支持设计一项条款,规定搁置所有悬而未决的领土主权问题,并由领土要求国与非要求国以及尚未在南极开展活动的国家,在条约生效后创设一项法律制度以维持各国对南极的主权或权利要求现状。凯西确信,华盛顿会议所正在探讨的将要起草的第四条可以实现上述目标,并且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美苏这两个对南极保持浓厚兴趣的非声索国的合理利益。他还解释道,如果无法实现该目标,缔结一项条约将毫无意义。如果苏联对这方面所建议的文本内容有任何疑虑,澳大利亚政府将提出任何可供替代的草案。(15)Hayton and Robert, “The Antarctic Settlement of 1959”,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54, No.2, 1960, p.357.
凯西与苏方代表建立的良好沟通渠道发挥了作用。1959年4月,苏联谈判代表团团长菲利波夫向美国国务院代表丹尼尔通报,苏方正在重新审议第四条内容。美苏代表随后通过多轮会议就各自分歧交换了意见,最后达成共识:双方的争议焦点仅仅局限于条约加入方式和争端解决形式,在《南极条约》的内容上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久,费德林在给凯西的信中证实:“在华盛顿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已得到指示,同意《南极条约》第四条草案。”(16)“Cablegram from Australia High Commission in London (9 June 1959)”,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A1838/2, Item 1495/3/2/1/4.1959年6月13日,苏方将该信提交给在华盛顿的各谈判国代表,宣布苏联接受有关《南极条约》第四条的内容,标志着围绕《南极条约》第四条“冻结”现状的争议所形成的谈判僵局已经被打破。澳大利亚说服苏联重新考虑对第四条的态度并改变立场,为《南极条约》后续谈判扫除了主要的障碍,被本国学者盛赞为是整个谈判进程中关键的转折点。(17)Marcus Haward and Tom Griffiths, Australia and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50 Years of Influenc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11, pp.84-86.
三、澳大利亚对南极条约体系发展的影响
1961年生效的《南极条约》除第九条第一款f项“保护和保存生物资源”外,本身并未对人类在南极的所有活动形式,如海洋生物资源捕捞、矿产资源开发等作出明确规定,更谈不上建立起详细的规则与机制来分配这些权利。《南极条约》以“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治理形式在南极事务中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显然不利于澳大利亚南极活动的进一步开展及其南大洋渔业与“南极领地”开发与保护的协调。有鉴于此,凭借《南极条约》缔约国身份,完善和扩展南极条约体系并引导南极国际治理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维护本国南极权益的选择。
3.1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澳大利亚的全方位支持
澳大利亚通过广泛参与南极事务巩固其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支持,这种参与对南极条约体系发展以及应对内部外部挑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南极条约体系能够有效维持的重要因素之一。澳大利亚对1980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以下简称CCAMLR)诞生所作的工作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谈判过程中,澳大利亚反对苏联、日本以渔业捕捞为主的意见,坚持应当以“养护”(Conservation)为公约根本宗旨的立场得到了参与国家的普遍赞同,从而一致通过了其关于建立一项能够兼顾南大洋生物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系统保护的特定管理制度的倡议,填补了《南极条约》在南大洋商业捕捞管理上出现的法律适用空白。(18)Marcus Haward and Tom Griffiths, Australia and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50 Years of Influenc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11, pp.166-168.谈判结束后,澳大利亚举办了各缔约国的最后会议,成为CCAMLR的公约存放国,向公约秘书处提供重要支持,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总部选址在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由澳大利亚人戴瑞·鲍威尔担任首届执行秘书。
澳大利亚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预防、阻止和消除CCAMLR适用海域内的非法、未报告及未管制捕鱼(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简称IUU)的养护措施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CCAMLR阻断非法、未报告及未管制捕捞渔获物在缔约国港口上岸或转运路径的最主要养护措施——《关于犬牙鱼类的捕捞文件计划》(Catch Documentation Scheme for Dissostichus spp.,简称CDS)的雏形来自澳大利亚的一项行动方针草案,该草案最初建议引入一项数据文件计划来追踪犬牙鱼的国际交易。(19)CCAMLR, “Report of Seventeen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Hobart,1998, p.17.澳大利亚联合美国、乌拉圭等国实施船舶监测系统(Vessel Monitoring System,简称VMS)数据分享试验所取得的成果,被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作为修改和细化船舶监测系统安装规则的首要参照指标之一,(20)CCAMLR, “Report of 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Hobart,2003, p.55.较好地弥补了船舶监测系统启用初期暴露出的易被伪造或篡改方位的缺陷。2011年,在CCAMLR各缔约国就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应当遵照的指导方针、寻求的目标宗旨和参照的科学数据指标等基础问题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以澳方提案为基础制定的《关于建立CCAMLR海洋保护区的总体框架》及时消除了各方分歧,初步建立起一项所有国家都能够接受且遵循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正式法律文件,避免了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进程的无限期拖延。
3.2 《马德里议定书》制定中澳大利亚的改弦易辙
澳大利亚对南极条约体系发展的另一个贡献是促成1991年《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Protocol 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 the Antarctic Treaty,以下简称《马德里议定书》)的诞生。
1961年《南极条约》生效后,围绕如何制定南极矿产资源开发规则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尽管1988年在新西兰惠灵顿举行的第四届南极条约特别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 Resources Activities,简称CRAMRA),但该公约所建立的矿物资源制度事实上削弱了澳大利亚“南极领土”要求的有效性,澳大利亚对此感到不满,也对可能在澳大利亚所主张的南极领土范围的矿产开发活动所带来环境保护问题感到忧虑。澳大利亚有政府官员指出,正式批准该公约“意味着我们放弃对南极的经济权利要求,而换来的却是一无所有。”(21)“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Debates”, 3 May 1989, Senate Office Hansard, Dec.12 2018.
1989年5月22日,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宣布,澳大利亚反对在南极从事矿业活动并拒绝签署《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相反,澳方将致力于达成一个全面保护南极环境的公约。8月,鲍勃·霍克同前来访问的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一致认为,在南极进行的矿产活动与保护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不相符合,《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不应再被视为一项能够保护南极环境的安全制度。澳法两国政府将合作促成一项公约,用以覆盖南极环境保护各个方面及其所依赖和关联的生态系统。(22)Jorg G. Podehl and Donald R. Rothwell, “New Zealand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gulation of Antarctic Mineral Resource Activities (CRAMRA): An Unhappy Divorce?”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Vol. 22, No. 1,1992, p.32.在同年第十五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澳大利亚联合法国以工作文件的形式率先提出“综合保护南极环境以及其特有和相关的生态系统”的建议,呼吁各国拒绝签署《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23)CCAMLR, “Final Report of the Fifteenth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Paris, 1989, pp.226-229.
澳大利亚立场的转变扭转了南极条约体系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在南极主权问题暂时搁置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抓住了保护南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南极的影响等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重点,适时将主要议题从规范矿产资源活动引导到环境综合保护上。另一方面,由于《南极矿物资源活动管理公约》需要所有参与国的签署方能生效,澳大利亚明确的拒绝态度致使其事实上已经搁浅,这就促使其他国家也必须重新审视、评估和调整其南极政策。原先一直观望的意大利、丹麦、奥地利与比利时和持反对意见的新西兰、美国等国与澳大利亚在保护南极环境问题上统一了立场,在随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内新条约文本的拟定即告完成。
1991年10月4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第十一届第四次南极条约协商国特别会议通过了《马德里议定书》,将南极地区确定为专门用于和平和科学目的的自然保护区,并规定了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如议定书生效后50年内,禁止在南纬60°以南区域进行一切商业性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等。这展现出澳大利亚在保留“南极领土”主权要求与维系南极条约体系之间寻求利益平衡所做的努力尝试,澳大利亚在这一具有进步意义的和平利用南极的条约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3 南极条约秘书处设立中澳大利亚的审时度势
1961年《南极条约》生效,但在其后四十余年里,一直未能建立起一般国际条约通常具备的常设运作机构——秘书处,以承担行政管理、提供工作服务便利、支持与执行条约决议等职能,这一度使《南极条约》成为唯一没有永久总部、没有网页站点、没有记录储存的国际公约。
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国家担心秘书处的设立会导致南极问题的国际化并对主权要求国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24)陈力、屠景芳:“南极国际治理:从南极协商国会议迈向永久性国际组织?”《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3页。在《南极条约》谈判初始阶段,澳大利亚与智利、阿根廷三国就否决英国关于建立某种形式的常设组织以促进条约目标实现的建议,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永久性的行政机构,而是将《南极条约》设想为旨在缓解南极领土争端与消除大国军备竞赛以保证该地区和平稳定并促进科学领域国际合作的安全协议。(25)John Hanessian, “The Antarctic Treaty 1959”,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9, No.3, 1960, p.462.这导致《南极条约》只得创设出一种最低程度的机构制度,即采取按缔约国字母顺序轮流举办年度会议的方式为各方提供场所与论坛,以交换情报、共同协商有关南极的共同利益问题和促成涉及南极事务的措施、决议。(26)Davor Vidas, Implemen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ime for the Antarctic, London, Kluwer Academic, 2000, p.125.相应地,每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的东道国在会议期间承担南极条约体系的行政工作与费用,对收集和整理的会议记录进行管理并作为成果移交给下届会议承办方。
这样显而易见的弊端在于:一成员方在履行信息交换义务时必须将相关数据资料分别送交给各成员方而无法直接交由一个中央机构汇总和再传达,这让南极条约体系的工作效率显得较为低下。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南极条约缔约国数量的增加、与南极环境保护相关活动的增长以及在南极开展的其他各类活动的规模扩大等复杂因素,原有南极条约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 Approach)运作方式更是显得力不从心,国际社会对设立南极条约秘书处的需求愈发迫切。从1985年起,几乎每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都将设立秘书处列入讨论议题,然而进程迟缓,在最初的头六年里始终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对于是否设立南极条约体秘书处的问题,澳大利亚在应对南极条约体系外部挑战和推动内部机制改革的双重压力下,几经利弊权衡,加入到了赞成者阵营当中。随即不久,由其促成的1991年《马德里议定书》的缔结让所有南极条约协商国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提高南极条约协商机制处理事务的效率,还是加速信息流转和促进议定书实施的便利化,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中心化的秘书处势在必行。(27)CCAMLR, “The Final Report in the Fifteenth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 Bonn, 1991, pp.12-13.澳大利亚还设想将南极条约秘书处打造成为一条以间接方式保护南极环境的额外防线,为《马德里议定书》及其附件生效和履行提供足够的机构支持。为此,澳大利亚在秘书处选址和财政等细节问题上作出相应安排。澳大利亚在因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而交恶的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积极斡旋,敦促阿根廷逐步降低本国南极科研项目对军事力量的依赖并通过重组与改革南极局来替代支持,换取了英国收回对秘书处选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反对意见,结束了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关于秘书处设立地址长达十余年的争论。(28)CCAMLR, “The Final Report in the Twenty-fourth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Saint Petersburg, 2001, pp.32-34.秘书处的财政资助方式采取的也是澳大利亚提出的设计方案:即秘书处年度预算的50%由出席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的全体协商国平均分担;剩余50%的分配比例不是简单比照协商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是由协商国所选择的衡量参与南极活动能力的系数类别所决定。(29)Stephen Powell and Andrew Jackson, “Australian Influence in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 An End or A Means?” in: Lorne K. Kriwoken, Julia Jabour and Alan D. Hemmings eds., Looking South: Australia’s Antarctic Agenda, Sydney, Federation Press, 2007, p.43.在2003年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就建立南极条约秘书处各项问题完全达成共识前,澳大利亚还承担了临时行政秘书处的部分职能以帮助其顺利完成过渡;在秘书处成立初始阶段,主动提供了本国南极局多年来收集的有关南极条约体系各项工作记录的副本,帮助阿根廷建立稳固的工作基础。
四、澳大利亚应对南极条约体系的外部挑战
4.1 马来西亚抛出“南极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马来西亚向联合国大会提议并被列入议程讨论的所谓“南极问题” (Antarctic Question)是南极条约体系迄今为止所遭遇的最为严峻的挑战。(30)关于马来西亚与“南极问题”的详细内容,请参阅:B. A. Hamzah, “Malaysia and the Southern Ocean:Revisiting the Question of Antarctica”,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41, No.4, 2010, pp.186-195.1982年9月,一心想在“不结盟运动”与“七十七国集团”中充当领导角色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第三十七届联大会议抨击“新殖民主义”的演讲中首次向南极条约体系发难。他声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概念为未来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树立了典范,同样,南极也不应属于少数几个领土要求国,就像原殖民地不再属于其宗主国那样。南极这类无人居住的地区,都应交由联合国管理以便所有国家都能从资源开发中受益。《南极条约》作为殖民时代的产物,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Anachronistic)。(31)Mahathir bin Mohamad,“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at the 37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29th September 1982”, Foreign Affairs Malaysia,Vol.15, No.3, pp.173-184.
从1983年第三十八届联大会议将马来西亚提议的“南极问题”正式列入议程开始,在之后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担当发展中国家代表的马来西亚与南极条约协商国代表澳大利亚展开了多次交锋。马方的基本观点是:第一,考虑到南极科学研究委员会(SCAR)在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中仅承担咨询工作而无决策实权,南极条约体系是否具备保证南极环境受到充分保护和能否公平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令人怀疑;第二,南极条约体系决策程序因其将广大非缔约国和国际社会的意见排除,而日渐沦为有利于少数“特权国家”的闭门秘密机制,是“殖民主义秩序”最后的残留痕迹之一。(32)Marcus Haward, “Australia and the Antarctic Treaty”, Polar Record, Vol.46, No.1, 2009, p.13.马来西亚据此呼吁,应当在联合国框架内为南极建立起全新的国际治理机制,将南极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由全人类公平享有和利用。
4.2 澳大利亚的针锋相对
作为“南极领土”要求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国寄希望于通过《南极条约》这个“专属俱乐部”(Exclusive Club)为南极国际治理树立起一道高标准门槛,避免联合国不设限制地允许任何国家参与南极事务所带来的对其“南极主权”的冲击。马来西亚的发难令长期以来一直想努力将南极问题局限于南极条约体系内部的澳大利亚等国大为光火,广大南极条约协商国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33)1959年《南极条约》创始缔约国有12个,包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挪威、比利时、日本、阿根廷、智利和南非;其中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挪威、阿根廷和智利等7国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共占南极大陆总面积的83%,而澳大利亚领土要求占南极大陆总面积的近42%,约600万平方公里,是最大的“南极领土”主张国。1985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十三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温德姆就“南极问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公开声明,“澳方无法接受近来一些国家的指责,相反,我们相信《南极条约》能够为本国以及国际社会的重要利益服务。”(34)CCAMLR, “The Final Report in the Thirteenth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Brussel, 1985, p.123.澳大利亚同时对马来西亚的批评予以反驳,核心内容包括:首先,《南极条约》最重要的优势之一是通过第四条的“冻结条款”搁置领土要求国之间以及与非领土要求国之间的争议,确保了南极和平稳定的局面和国际合作的顺利开展,目前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可以替代它的解决途径。其次,《南极条约》对所有愿意加入的联合国成员国开放,只要在南极开展了诸如建立考察站或派遣科考队等实质性科学研究活动的国家均可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对南极事务的管理承担起主要责任。巴西、中国、印度、匈牙利、古巴等国相继加入《南极条约》,缔约国的政治制度、地理分布、社会与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与广泛性已经得到显著体现。再者,由某项特定活动的主要参与国家负责管理与决策是国际关系中所普遍遵循的一项合理与可行的原则。这项原则在其他一系列国际协定和国际组织的实践中也能找到,包括联合国体系。所以,在南极从事科研与合作的国家就其相关活动进行协商和决议是很自然的,也是与他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相匹配的。最后,澳大利亚与其他六国对南极提出的领土要求是长期持续的,比“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这一概念的提出和联合国的诞生早上许多年,更何况1959年缔结的《南极条约》已经对南极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有效管理,这表明南极的法律地位不同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外层空间或深海海底。(35)T. B. Millar, Australia, Britain and Antarctica: Papers of a Conference Held at the Australian Studies Centre, London: Australian Studies Centre,1986, pp.40-46.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等南极条约协商国还做了大量外交工作,包括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南极问题的疑虑表示关切和理解,增进非缔约国对南极条约体系运行机制的了解并采取邀请部分非缔约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等举措,令马来西亚一贯排斥南极条约体系的原有立场有所松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马来西亚对其南极政策陆续作出调整,逐渐认同南极条约体系确立的原则,与澳大利亚等南极条约协商国关系也趋向缓和。2005年,马来西亚代表向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委员会提交修正案,建议将“南极问题”排除在联大议程之外。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60/47决议,决定不再将南极问题作为联大议程之一,标志着联合国对“南极问题”讨论的终结。(36)郭培清、石伟华:“马来西亚南极政策的演变(1982年—2008年)”,《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6页。
五、南极条约体系:澳大利亚南极利益的现实保障
南极条约体系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国际社会治理南极的坚实法律框架,促进了各国科研合作与考察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南极局势的长期和平稳定。它不但促使不同国家通过搁置分歧实现合作,还为各缔约国的南极利益提供了现实保障,对澳大利亚亦是如此。
5.1 确保“领土”安全
《南极条约》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本条约有效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行为或活动,不得构成主张、支持或否定对南极的领土主权的要求的基础,也不得创立在南极的任何主权权利。在本条约有效期间,对在南极的领土主权不得提出新的要求或扩大现有的要求。”该项所谓“冻结条款”对澳大利亚的意义在于,其在加入《南极条约》之前已提出的领土主张获得了现状维持并且没有遭到减损与削弱。对南极保留提出主权要求权利的美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与南极领土要求国存在立场分歧的南极条约缔约国在条约有效期内必须承认和接受南极现状,不得对包括澳大利亚“南极领地”在内的全部南极区域采取任何旨在谋求主权的行动,这些国家在南极开展考察或探险乃至修建机场等原本在国际法上具有宣示和巩固南极主权的法律意义的活动也变得无关紧要。
同样对澳大利亚有利的是,为了传达“……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南极应永远专为和平目的而使用,不应成为国际纷争的场所和对象”的愿望,(37)《南极条约》序言。《南极条约》分别在第一条和第五条作出了“禁止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措施,例如建立军事基地,建筑要塞,进行军事演习以及任何类型武器的试验等等”与“禁止在南极进行任何核、爆炸和在该区域处置放射性尘埃”的郑重规定。由此确立起来的南极地区无核化与非军事化原则避免了南极沦为大国核试验场所和核废料堆放地乃至壁垒森严的军事斗争前沿,稳固了澳大利亚“后院”的地区安全而不必专门投入大量国防力量进行守卫。《2016年度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也作出了乐观判断:在未来数十年内,因澳大利亚南大洋及其“南极领地”的国家利益遭遇挑战而需要作出实质军事反应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38)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White Paper 2016, p.54.
5.2 落实海洋权益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其适用范围内的岛屿所属国享有的海洋区域权利(如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的认可,促成了澳大利亚所属位于南大洋中的亚南极岛屿延伸至南纬60°以南的外大陆架区域划界申请案的成功。依照《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四条b款规定,本公约任何规定以及在本公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任何法案或行动“不应被解释为任何缔约方放弃或削弱,或损害根据国际法在公约适用区域内行使沿海国管辖权的任何权力、主张或这种主张的依据。”而澳属麦夸里岛、赫德岛与麦克唐纳群岛散布在南纬53°至55°之间的该公约适用区域,不属于《南极条约》所规定的南纬60°以南的“南极条约区域”(Antarctic Treaty Area),澳大利亚对上述岛屿所具有的沿海国身份以及享有的管辖权都不存在任何争议。最终,澳大利亚提交申请的赫德岛与麦克唐纳群岛200海里外大陆架(近119万平方公里)中近95%的区域(约113万平方公里)以及麦夸里岛200海里外大陆架全部8万平方公里区域,获得了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承认。(39)吴宁铂:“澳大利亚南极外大陆架划界案评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7期,第12页。实现了澳大利亚“名义上”对前述岛屿外大陆架延伸至南纬60°以南的 “南极条约区域”部分享有主权的重大突破。(40)根据澳大利亚缔结的《马德里议定书》以及本国颁布的《南极条约(环境保护)法》与《南极禁止矿产活动法》规定以及外交声明,不得开采其位于南纬60°以南的外大陆架区域的矿产。
5.3 提升国际地位
南极最大的领土主张国和地理上近南极国家的双重身份,使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在南极事务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而治理领域涉及诸多国际社会所关注“公共问题”的南极条约体系无疑为其创造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例如,《南极条约》在“冻结”领土争议的同时,通过对科学研究与考察的鼓励使之成为各国在南极保持重要影响力的一项关键指标。澳大利亚凭借一个多世纪以来南极科考的丰富经验以及灵活、高效和可靠的科研保障能力,在南极气候变化、海平面升降、环境检测、冰芯钻探、海洋生物养护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吸引世界上150多个国家或国际研究机构与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引领南极国际治理方向提供了充足的科学依据。(41)“Australia’s Antarctic Program”, Australia Antarctic Division, Apr. 27 2016, http://www.antarctica.gov.au/about-us/antarctic-strategy-and-action-plan/australian-antarctic-strategy/antarctic-program.在环境保护日渐上升为最具现实意义的南极治理优先议题的过程中,澳大利亚亦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促成1964年《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出台;推动谈判和缔结旨在全面保护南极环境的《马德里议定书》;联合中国、印度、罗马尼亚等国设立了唯一没有美国涉足的东南极洲的拉斯曼丘陵特别管理区;就人类活动对南极的影响率先建立环境研究与评估项目等。(42)吴宁铂、陈力:“澳大利亚南极利益——现实挑战与政策应对”,《极地研究》,2016年第1期,第125页。
六、结 语
以1959年签署的《南极条约》为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多边国际协定与各类实质性决定所构成的南极条约体系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在以南极条约体系为核心的治理机制下,国家南极利益关切及实践行动从来都是不同国家南极战略与政策出台、变化的根本原因之一。(43)丁煌、云宇龙:“中国南极国家利益的生成及其维护路径研究”,《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9期,第71页。澳大利亚作为《南极条约》创始缔约国,在此期间所采取的务实的外交政策与政治立场以及对相关国际法规则的主动创设和运用,在成功地巩固南极地区非军事化地位、保护南极陆地与海洋环境、增进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完善体系决策框架与程序以及引导治理议题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基本实现了本国加入《南极条约》之前已提出的领土主张不会遭到减损削弱、从南极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中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保持并增强在南极事务中的领导作用等政策目标。考虑到南极条约体系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未来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澳大利亚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南极条约体系并努力解决其所存在和面临的缺陷与挑战,推动它朝着更加稳定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与澳大利亚在南极外交、科学、后勤、管理等领域有着长期合作传统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迈向极地强国建设的全新历史阶段。加入《南极条约》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南极国际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在逐渐提升,从被动跟随转变为积极参与相关规则的讨论,能够主动提出一些倡议和议题,从南极治理门外人、旁观者逐渐走进决策圈。(44)“中国走进南极治理决策圈”,新华网,2017年6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17-06/16/c_ 136361628.htm。2017年,第四十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自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以来首次以东道国身份举办该项会议,彰显出中国在南极事务中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南极正成为中国亟待开拓的国家战略新疆域和彰显新兴大国责任的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的共商、共建、共存、共荣等价值理念与南极治理服务于全人类利益的目标高度契合。(45)郑英琴:“南极的法律地位与治理挑战”,《国际研究与参考》,2018年第9期,第7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在国际法层面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与创新并得以阐释、贯彻与实施是推动南极治理规则构建的重要路径,也是中国提升国家话语权和担当大国责任的必然选择。相信作为老牌南极事务大国的澳大利亚在南极条约体系存在与发展的六十年里所积累的国家实践,能够为中国探索在南极治理的热点问题中落实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法方案,形成中国特色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