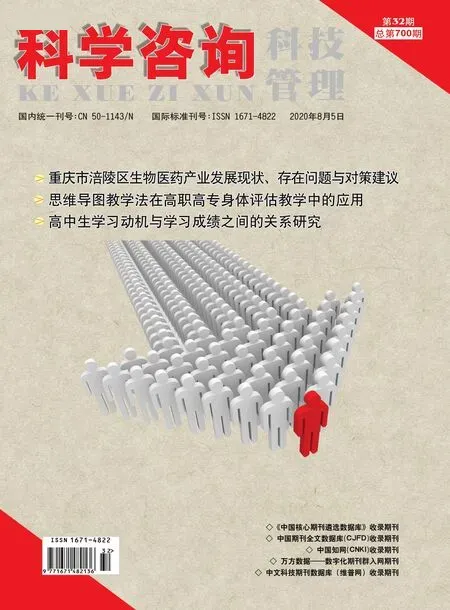孔颜之乐与费尔巴哈人本幸福观比较
——现代大众幸福何以实现
胡瑞琪 孟盼盼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一、孔颜之乐与费尔巴哈幸福观的差异
(一)缘起:幸福与道德何以安顿
在伦理思想的历史长河中,中西方思想家们对幸福与道德关系的探讨层出不穷。费尔巴哈是西方德福问题的代表人物;孔子则是儒家的万世之师和不祧之祖。他们对德福关系问题的思考,既已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问题进路,奠定了德福关系问题的两种基本致思路向。
1.费尔巴哈的“德性从属论”。费尔巴哈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即追求幸福,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人性不只创造了单方的排他的对幸福的追求,也创造了双方的相互的对幸福的追求。“道德的原则是幸福,但不是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的那种幸福,而是分布在各个人(包括我和你)身上的幸福,因而。幸福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或各个方面的。”[1]以追求本人幸福为道德的基础、以达到人人幸福为道德的价值目标,以爱为道德的核心、精髓和基本精神,构成了费尔巴哈幸福观思想的基本内容。“幸福是以德性为先决条件的,而且德性还是幸福的保障、工具和内容。”[2]
2.“孔颜之乐”中的“幸福从属观”。孔子在道德的框架下安顿幸福,强调对良好德性的培养与高尚德行的追求十分重要,如果行为有德,即得到了幸福,反之就无幸福可言。在此基础上,这种幸福观把理智与欲望对立起来,强调理性对幸福的作用,认为有德行在于人对道德的追求,要追求道德的生活,不仅要有道德的知识,而且要以理性来支配人的感性欲望。这就是孔子所提倡的 “居陋巷不改其乐”的苦行精神。
(二)幸福的主体向度:圣贤精英与普通大众
1.圣人之思。《论语·雍也》中有这样一段经典表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为什么可以做到居陋巷而怡然自得,究其原因,主要源自于颜回的圣贤人格。此外,在《中庸》中,孔子也提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3]。这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始终是我们普通大众的榜样和典范,是极少数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是普通大众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理想境界。
2.大众之乐。相比于孔颜之乐的圣贤气象,费尔巴哈幸福观则更加平民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本幸福所面向的主体是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等普通大众。人本幸福立足于人的动物性和自然性。与此同时,费尔巴哈借助宗教的力量宣扬其“爱的宗教”。他猛烈抨击宗教神学的幸福观,将人们从对宗教的盲目崇拜中拉回现实,转而开始关注人本身。他提出:“必须拿对人的爱当作唯一的真正的宗教,来代替对神的爱,必须拿人对自己的信仰及自己力量的信仰,来代替对神的信仰”。[4]
(三)幸福的呈现之态:理想境界与现实生活
1.安贫乐道。在儒家传统伦理观中,幸福之态呈现在两个方面,即“安贫”与“乐道”。所谓“安贫”,即能忍受穷苦困顿的生活。在普通大众看来,孔颜的贫寒生活似乎并无快乐可言,甚至可以说是不堪忍受。但颜回却能箪食瓢饮居陋巷,这既是圣贤之人的一种境界,也是“安贫”的呈现之态。所谓“乐道”,就是对于“以何为乐”“所乐何事”的回答。孔子自述粗茶淡饭、曲肱而枕,却能够“乐在其中”。这实际上是 “乐道”的表现。
2.安乐生活。费尔巴哈将幸福从高尚的道德境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在他看来,德行和身体一样,需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居。“幸福不是别的,只是某一生活健康的正常的状态,它是十分强健的或安乐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生物能够无阻碍地满足和实际上满足为它本身所特别具有的、并关系到它的本质和生存的特殊需要和追求。”[5]这样,人本幸福就被解读为健康的、正常的、强健的、安乐的生活状态。
二、孔颜之乐与费尔巴哈幸福观差异的当代启示
(一)有利于人们重新审视幸福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费尔巴哈的思考似乎更符合当代人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然而,现代人能否信服“功能论证”是值得怀疑的。如此一来,道德在“幸福论”中能否占据稳固的地位,就将成为问题。在这方面,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坚持,伴随着道德生活之自得之幸福(孔颜之乐)的阐明,无疑将会有助于在“幸福论”中建立道德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使道德活动在“幸福”生活的思考和实践中获得更多的实践动力。
(二)有利于维护民族关系和维护社会和谐
费尔巴哈人本幸福观面向全体大众,并借助宗教的力量宣传“爱的宗教”,主张无差别的爱。这种幸福观有利于维护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而在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只有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和谐与融洽,社会和谐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三)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借鉴
孔子与费尔巴哈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两大代表人物,其思想既存在着相同点,也存在着很多差异。面对中西方文化的这种差异,我们要做到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去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站在整个世界的角度上不断探索与寻求两种文化的桥梁与契合点,求同存异,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