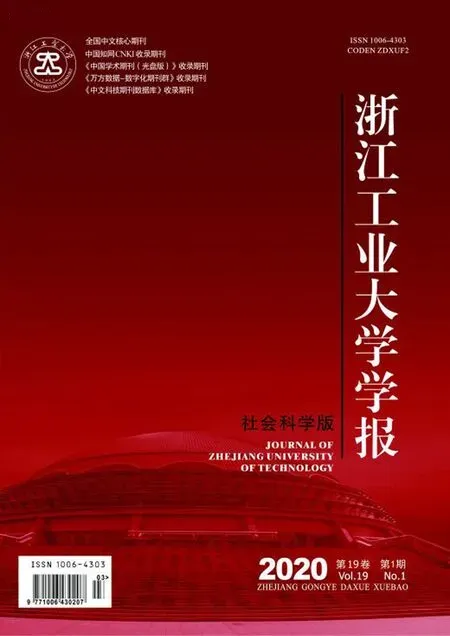“现实的”与“浪漫的”:当代文学的江南想象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有关江南的文化建构和地理地域建构,已经有很多的理论建树。同时,有关江南文学的文学史建构,主要集中在对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清理和归纳。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江南文学的状况的研究,大多都局限于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个别作家的江南文化特质和审美特质的归纳和探讨。笔者意在对当代江南文学进行宏观的观照,厘清当代江南文学的双面性——“现实的江南”和“浪漫的江南”,并试图从创作主体的站位和审美特质的差异两个方面来研究。
一、浪漫时空与陌生化凝视
有关江南的想象,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有关它的想象大多是浪漫的。当代文学中的江南想象,浪漫依然是主调。
田汉的话剧《关汉卿》讲述了戏剧家关汉卿受尽元朝统治者迫害之后,给了大团圆的结局。那就是,关汉卿与他的情人戏剧艺人朱帘秀,双双唱着《彩云飞》下江南。在田汉的想象中,江南是与元朝统治者的黑暗统治相对照的光明和自由、浪漫的所在。在田汉的叙述中,江南的内涵中,彩云飘飘,有自由,有出双入对的爱情,是没有异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和牢狱之灾的理想社会。田汉有关江南的想象,与安徽民歌《摘石榴》的想象是一致的,也与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中所想象的自由任情的江南是一脉相承的。与有关江南的回望式想象一致的是当代海外诗人的江南想象。余光中等人,少小即离开江南故乡,在时间上造成了其成为江南故乡母体之外的“他者”。所以,在他们的想象中,江南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爱情和父母亲人的故乡。在《春天,遂想起》中,余光中将有关江南的历史、传说、诗歌、江南的风物、江南的生活串联起来,通过不同时空的措置组合,将“我”和母亲,将“我”和表妹,置于同一场景中,勾勒了一幅春天里江南女子踏青春游图。而抒情主人公“我”的孤独和思亲,以及以梦自慰,又恰恰揭示了“我”作为故乡“他者”的悲哀的现实。诗人在文化记忆里,重绘了作为精神原乡的江南,体味回归的温馨也体味了原乡失落的忧愁。诗人通过“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引出了有关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历史记忆,又通过母亲在圆通寺的呼喊,道出了当代政治阻隔所造成的母子生不能聚首死不能尽孝的刻骨铭心的伤痛。思亲而不得,给美丽怡人的江南图景,糅进了伤感忧郁之色。有着同样的浪漫和忧愁的是郑愁予的诗作《错误》。在这首诗中,诗人展现了只有江南才有的风物——石板路、小楼,以及江南的水一样温柔多情的江南样的妻子。诗人把只有在古诗词中才有的游子思归和怨妇思游子的故事,放到当代历史背景下,进行了重述。在江南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故事。在故事中,有一个等待游子归来的古色古香、清朗透明的江南,也有一个等待游子归来的圆润、精致、倩丽、纯净、细腻的思妇;而另一面,那个归心似箭的江南游子正快马加鞭,回归故乡。思妇年复一年的翘首等待,游子的一生一世的团聚渴望。清脆嘹亮的“达达的马蹄声”中,是江南风格的,只有在江南的石板路上才能发出的,那声音也是穿越时空的,是将历史和现实蒙太奇般地叠映在了一起的浪漫图景。诗人运用戏剧逆转的手法,逼出了对于故乡的思念和对于青春时代的恋人的歉疚。特别是最后一句“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同样表达了游子与故乡的日夜思念又不能相聚的无奈和悲怆[1]。
传统的怨妇游子主题,讲述了既浪漫又悲怆的故事。这种浪漫主义,是感伤忧郁的罗曼司。在这样浪漫故事中,总有一个骑着白马的江南才子和一个美丽贞洁的江南美妇人。这种浪漫就如同司各特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一样,现实的爱情悲欢,是揉进了历史的场境的,所以,总是有着古典主义的情调。它的“怨而不怒”和“温柔敦厚”,是合乎中国传统诗学的江南精神的。海外游子对江南的想象,虽然饱含游子离乡之痛,但是,他们同样也在隔离的时空中构建了一个浪漫自由美好的江南形象。时空隔离,为构建有关江南的美好与自由想象提供了条件;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造就了有关江南的审美化形象。海外作家之所以有着江南情结[2],将江南作为归宿地和故乡来叙述,除了自然环境和这些作家出身于江南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其将江南视为血肉本体的文化传统,更是陌生化的美学语境中主体营构的结果。
当代大陆作家对于江南的浪漫维度的想象,其实也属于一种“他者凝视”的结果。很多诗人和作家在想象江南的时候,也是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来观看和叙述江南的。比如何冰凌的诗《车过苏州》就讲述了诗人作为旁观者的角度对江南(苏州)的观感—— “我看见苏州的小房子/亲爱的苏州小房子/像在云彩里点了淡墨/像评弹里的弦轴/竹枝词上的泪滴/像一群鸽子/和它们灰白的眼球/就有些心动/就想从壁画上走下来/加入它们”。诗人以他者的立场观看或联想江南,江南是历史文化中的江南,她选择了具有典型符号意味的江南景观——苏州(“江南景观的选择以佛寺、园林和名山等人文景观为主。这些景观集中于杭州、苏州、江宁和扬州等地,构成了一个有主有次、有轻有重的网络”[3]。)以及评弹、竹枝词、小房子、水墨画、鸽子来观照江南。何冰凌想象中的江南,是一个童话的世界,一个不沾染一丝现实尘埃的无忧无虑的纯粹的世界。她所呈现的是一个精致、灵动、温暖的超越现实的江南形象。何冰凌的江南想象,与海外诗人的又有所不同,由于诗人并没有乱离的体验,她的江南图景更多了几分甜丝丝的沉浸于童话中的幸福感受。
这种浪漫幸福想象,还出现在那些有着民俗考察倾向的当代有关江南风物和美食的散文中。谈正衡的散文集《清粥草头咂咂鱼》《花鸟物语》《梅酒香螺嘬嘬菜》和朱幸福的散文集《泥巴墙头辣味香》,都以一种周作人当年写作《故乡的野菜》一样的笔调,讲述了江南的花、鸟、野菜、水里的虾蟹,以及各种各样的吃食、戏曲、民俗。他们把江南的乐观和旷达寓于耳目,把江南的甜腻和幸福置于舌尖和味蕾上,去欣赏,去品味。他们笔下的那江南的形象,永远是水灵灵的滋润;那江南的味道,都是调适得最为适中的。他们塑造了一个四季花香,桃红柳绿,气候宜人,山清水秀,人民富足,生活惬意的鱼米之乡,一个落实到人间的真正的桃花源和杏花村。在他们的叙述中,驱逐了历史的严酷和暴风骤雨,当然没有人民的乱离,社会的动荡,山河的破碎;就是寒冬腊月万物萧条,江南的山水人物,也都滋润温婉。在他们笔下的江南,就是一个超越现实的梦幻般的江南,一个理想主义的江南。在他们的笔下,没有了《花间词》的“春花秋月何时了”的颓废和呻吟,江南永远是春花烂漫的春天。他们通过对于江南的丰盛的有特色的美食的叙述,将江南塑造成一个丰衣足食的人间天堂。在这样的叙述中,就是浮士德所痴心留住的那个浪漫的图景。创作主体对于世俗日常的忘我的沉迷和享受,表现得特别的鲜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也是一位江南想象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各种各样的江南美食的书写,虽然有着文化追溯的味道,但基本也是浪漫主义的。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虽然掺入了忧虑和感伤,但总体上还是令人陶醉的江南水乡情韵。小说中的芦苇荡,水鸟以及年俗等,都是典型的江南风格。他笔下的荸荠庵和尚们穿行于世俗和彼岸之间的生活,小英子和小和尚的情爱,活画出了一幅浓淡相宜的自由江南图景。温州籍作家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特别善于叙写温州的鱼虾、温州的河流、石桥、鱼丸等美食,以及温婉而钟情的女人。他将山水人文揉进了人物的骨子里,既传奇鬼魅,又清明爽朗。
当代作家在观照江南时的理想主义凝视,还表现在对于江南人物传奇故事的叙述。受到江南文化浸染的创作主体,一般都将江南置于与现实隔离的历史时空中,屏蔽启蒙主义,做浪漫的展现。江南出富商,江南出儒商。季宇的长篇小说《新安家族》回避了江南徽州商人程氏家族在商场的种种勾心斗角,从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塑造了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商人形象,展现了近现代江南商人在动荡历史中的坚忍不拔。卢文丽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讲述了“雪舫蒋腿”创始人蒋雪舫的曾孙女蒋小娥,在近现代动荡的历史波澜中的多舛的命运。小说中的外婆蒋小娥,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性形象,她美丽善良、聪慧坚韧、正直达观、贤惠隐忍。小说借外婆蒋小娥和“我”的经历,展现了以东阳、杭州、上海为轴心的江南文化,古老的村落和别具一格的江南建筑构制,历史永久代代相传的饮食文化、裁缝手艺、旗袍文化,以及江南的山水四季。但是,这部小说所着意的并不是追忆江南的梦幻,而是通过外婆的多舛的命运,展现在近现代动荡的社会历史中受尽了苦难的外婆,和备受折磨的江南的土地。季宇的小说《金斗街8号》则将背景拉到抗战时期的江南小城五湖城。小说在紧张的跟踪和反跟踪游戏中,彰显了地下党的革命智慧;采取戏中戏的手法,伴以盲人歌手看似悠闲的《马嵬驿》唱词,在危险气氛的渲染中叙述了革命的浪漫传奇。同样,小说《最后的电波》也在历史回忆中,讲述了皖南新四军通讯兵的传奇式的抗战历史。作家熟练地运用了悬疑小说的手段,表现了皖南新四军艰苦卓绝的突围战,以及作为“群众”的报务员李安本的奇功。小说在历史的危机点上,有力彰显了新四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革命历史传奇的讲述中,捎带融入了江南的自然风光和市井风情,是格非等江南作家的共同特点。这些江南英雄传奇,与红柯等人的北方传奇有着显著的不同,它细腻,柔韧,不粗糙,更少肌肉秀的匪气,透露出一股江南特色的优雅气质。其中所涉及到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也很少大大咧咧的豪放,就是一些山野女子,也多山野的灵秀气质。
历史场域中的江南浪漫书写,大多止于近现代革命史,很少深入到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最深处,但其同样呈现出柔媚、清灵与刚毅智慧并存的江南的精神形象。
二、现实处境与抵近观照
现实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对江南的文学想象中,现实主义观照依然不可或缺。当创作主体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对江南进行直面言说的时候,尤其是以启蒙主义眼光观照江南的时候,烟雨朦胧的乌托邦江南就会呈现出其残酷的另一面。
格非是一位有意在其小说创作中来呈现江南现实的作家。他早期的先锋小说《迷舟》《敌人》等作品,就表现了江南意蕴,在新历史主义的视野中,展现了江南历史的迷幻。新世纪以后,他连续以四部长篇小说,从江南原型意象——“桃花源”入手,讲述了政治理想在现实历史中实验的失败。系列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在近现代的历史长河中,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江南子弟实现梦想的过程,以及在梦想实现的过程中人民的苦难,继续承担着以启蒙主义的责任,执行文学话语刺破江南乌托邦的功能。在《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作家将中国传统诗性文化中的江南梦幻“杏花村”和“桃花源”重新命名为花家舍,讲述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江南大地实验乌托邦的过程。他一方面让主人公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三代艰苦卓绝地通过各种方式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并展现了他们眼中的桃源梦幻的和平、温馨和秩序井然,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实践者的观察,让现代性照射它,从现代化的价值去解构它,让所谓的桃源梦想变成了“被封闭在一个黑匣子里的恐惧和忧虑”[4]。这三部小说与其说是乌托邦的,不如说是反乌托邦的。作家在近现代历史中,让千古以来的乌托邦梦想,不但在实践中遭受曲折,而且也使其价值受到追问。格非以严峻的现实,刺破了“桃花源”这一飘荡千古的气泡,揭示了其在近现代革命和商业社会中的脆弱和农耕文明的本质。在历史的层面上,《江南三部曲》隐喻了江南社会在近现代社会的演变,展现了梦想在现实历史中的遭遇,将有关江南的梦想讲述为一个道德人心堕落的噩梦。在格非的笔下,所谓的田园牧歌情调,都不过糊弄人民的魔幻假象。格非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望春风》以江南村落——儒里赵村为讲述的发生地。在当代历史中,作家褪去了江南身上的五彩缤纷,呈现了其遍体鳞伤的肉身。这一看似出世的儒里赵村,始而在政治洪流中,战战兢兢,人心涣散,道德仁义丧失;继而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遭受城市商业文明的诱惑和折磨,直到最后被彻底拆迁,消失在现代化大潮的波澜壮阔里。人们或为生计而逃离故乡,或为金钱的诱惑而远走高飞。就是留守江南村落的人们,也并没有感受自己的村庄的美丽,反而是巨大的耻辱感:“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5]。更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故乡想象的死亡,“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甚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儒里赵村将被整体拆迁之后,我也没有感到怎样的吃惊。只有当你站在这片废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丽的故乡被终结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幻想是多么的矫情、谵妄!”[5]这部小说用启蒙的眼光,观照儒里赵村历史演变,悲悯它的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命运。格非讲述了作为“故乡”和“归宿地”的江南的失落。
启蒙主义视野中的“写实江南”[6],由鲁迅所延续下来的国民性批判意识必然要落实于具体的江南人物的精神痼疾之上。在格非的小说《江南三部曲》中,无论是普济村的村民还是梅城县的官员还是鹤浦,除了几个疯子在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外,所有的人都极其的务实、精明、善于算计或蝇营狗苟,就是那被称为世外桃源的花家舍,也一样地充满了尔虞我诈、窥视、出卖、控制、落井下石和血腥的杀戮。格非写出了人性层面的暗黑和无耻。在叶文玲的小说中,江南虽然有着粉墙黛瓦,红花修竹,但是,“实用、务实、促狭”的江南的男女既不可爱也不浪漫,甚至还很可憎。《无梦谷》中的老卒实用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挖空心思,“拔光牡丹、绣球、芍药。拆掉养金鱼、睡莲的水池,把厢房的美丽的后花园,彻底改造成既可养猪又能种菜的生息地”[7]。他们将聪明智慧,化作精明的算计和勾心斗角。《浪漫的黄昏》中的奶奶尽管已经风烛残年,但对于钱就如同鲁迅小说《故乡》中的杨二嫂一样的贪婪。
相较于格非、叶文玲等人的启蒙主义视野,李凤群、陈庆军等人的小说则更多地书写江南人民的生命困境。李凤群以自身的江南生命经验为出发点,系统地叙述了她所感受到的江南一带人民的生命症候。她的系列长篇小说《良霞》《大野》《大风》《大江边》大都以长江边或江心洲为叙述的地理背景。江心洲上的孤独的人生,就如同极易被汹涌的江水冲刷的江心洲一样,生活在江心洲上的人们在时代大潮下,进进出出,外在的世界难以适应,回到江心洲,又必然要承受那折磨人的不安全感。在长篇小说《大风》中,从外地飘零到江心洲的张氏家族,在历史狂飙吹落到江心沙洲上所享受的只能是荒诞和无奈。人民在历史的风雨中,所享受的不是春花秋月的浪漫,而是为狂风暴雨所舔舐的人生,苦难动荡和说不尽的生命蹉跎。长篇小说《大野》讲述了两个生长在大江边的70后女孩的故事。“在乡”的县城女子今宝勉强读完高中,回乡帮助母亲维持家庭,而两个弟弟很早就辍学,干起了偷盗营生。今宝在现实的刺激下,嫁给了城郊做电缆生意的老三。又让丈夫带着两个弟弟做生意,结果两个弟弟将姐夫老三骗得倾家荡产。今宝借着到外地参加朋友婚礼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在城”的在桃出生于大江边的普济圩农场。在父母离异的打击下,离家出走混社会。她跟随剧团走穴唱歌,歌厅卖唱被人包养,以及追星被歌星玩弄。她在城里经历了无数的屈辱之后,回乡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场男人。李凤群通过两个好姐妹的看上去相互对照的命运故事,讲述了当代江南人民的生存困境。
浙江作家余华的小说,虽然以当代政治话语的叙述见长,但仍然可以见到江南水乡的影响。他早年的小说《世事如烟》等先锋小说,将江南一带的巫术等民间信仰,带入了现实叙述,形成了小说既严酷又阴柔的叙述格调。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以打鱼人的生活为背景,表现了工业化给传统的江南人民的生活习惯带来的变化。这篇小说最初被评论界注意的是其文化寻根特质,将其解读为表达传统生活方式的失落和现代性焦虑。但是,现在看来,作家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工业化给山青水秀的江南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是当代生态文学的发端之作。余同友的小说《白雪乌鸦》通过一个母亲在受尽屈辱之后变成乌鸦的荒诞故事,控诉了社会的道德堕落和不公,以及他们的愤怒。陈庆军的长篇小说《天堂鸟》通过神秘的天堂鸟,展示了长江两岸水网地带人民在抗战前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这部小说的作者陈庆军先生显然对于水乡的历史文化,以及水的生活有着特别的了解,也有着特别的感受,对于水乡人民的生命状态有着深刻的体察。
传统的农耕文明的江南在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以后,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现代化的大都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的第三部《春尽江南》实际是在江南的城市里展开的。作家似乎放弃了对于农耕文明的花家舍的叙述,直接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展现了溆浦城的人欲横流道德堕落的现实图景。在溆浦,人们不择手段地赚钱,要死要活地消费。人们不仅消费物质财富,也消费女性的肉体,更消费道德理想。当年的花家舍,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边缘的“高级会所”,一个“销金窟”。残余的一丝诗意和出世梦想,只不过是供人们玩弄的“多余的东西”。与格非善于从启蒙主义政治出发书写江南小城人物的政治生活不同,小说家李为民笔下的江南小城,有着更为浓郁的都市气息。他将江南小城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精致和诗情,放到一边,着力书写都市里的商战。他的小说显然受到爱伦·坡的影响,扑朔迷离的利益纠葛中,暗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血缘纠葛。在他的云山雾罩的故事里,总有一个卧底的警察在。但他的故事绝不是侦探故事,而是利用对卧底警察的恐惧,为故事立一根看不见的线索,驱使叙述的推进。他的小说展现了现代都市的生活场景和人心世态。他的小说的结局,多少有着好莱坞电影的效果。李为民有着流畅的叙述语流,他对都市生活了解得多,懂得深透,他急不可耐地一股脑地要将这些都表现出来,他不得不把其中的有些情节流程掐断,剪掉,这就造成了情节的断裂,而在艺术上,这恰恰是一种绝妙的遮掩术。李为民的小说,表现了现代都市道德浇漓,都市生活的魔幻,以及现代主义的动荡不宁的、对于生存无法把握信任的心理状态。
三、虚拟的江南文学构造
当代文学在观照江南的时候,往往是难以归纳的,因为文学想象中的江南实际上是存在着分歧的。比如“现实的江南”就不符合江南的概念,而“浪漫的江南”似乎才是江南。可能这恰恰印证了伊格尔顿所说的,“根本就不存在文学的‘本质’这回事”[8]。尽管如此,我想我们对于江南的“共识”还是存在的。而之所以出现上述的分歧,其原因还在于,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江南是在历史的建构中被本质化和固化的,也是将江南作为“故乡”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审美化的想象;而本质化的符号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必然会发生内涵的错位,也导致主体的失落,其实也不完全是对于江南的失落,而是对于故乡的失落。在文学的实践中,有关江南文学的历史建构和审美建构,实际上是混淆了“‘本有’和‘应有’”[9]的主体愿望行为。
在上述的理论前提下,我认为,“现实的江南”和“浪漫的江南”,加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江南形象。而在文学的范畴之内,无论是现实的江南,还是浪漫的江南,其基本的调式都取决于江南的“水”的情调。在浪漫的江南中,江南的山水人文,江南的人物,都是浸透着江南的为水所滋润着的柔媚和婉约。但是,我们必须分别的是,现代时期的江南想象,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带着很浓重的脂粉味道,带着很浓重的花间词的风格的,但当代文学的江南书写,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基本上是脱离了脂粉味的,对于颓废也是有着免疫力的。就海外中国诗人而言,他们特别善于在文化符号上来构筑江南意象;而对于当代中国大陆的作家,虽也有时候也将其作为文化符号来引发怀古幽思,但大多都是以一种“生活者”的姿态来书写,由于身在其中,也很少有符号的感觉,他们只不过对生活进行书写而已。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家没有江南意识,因为他们的江南意识都浸透在了其字里行间了。江南意识已经成了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创作主体的集体无意识了。就如同长江的水流,有时候温柔如处子,但很多时候又凶暴如虎狼。但是,以水为基础意象的叙述,虽然有时候很残酷,但底子里的,还是浪漫温婉和柔媚。就如同现代时期一样,有关江南的想象,一直在当代作家的笔端潆洄缭绕。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浪漫的,江南文学都与贾平凹等人的黄土地书写,与莫言等人的山东书写,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不厚重,但它同样承载着历史的负累;它没有过于沉重的道德压力,但它的自由放浪之中,也绝不轻薄。古老的吴越文化和楚文化,在其叙述中,也会偶露峥嵘,其神秘主义审美与中原文化和黄土地文化虽然不同,但也同样存在。
在江南文学想象中的浪漫的书写,大多有着较为典型的农耕文明特征。而江南文学想象中的现实书写,则大多是现代性危机意识下的产物。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农耕文明的沉迷与现代性的危机,是互文的。启蒙主义在理想主义的江南书写中,往往是缺席的;而这种启蒙的精神分析在现实的江南书写中,几乎又是大行其道。以此,似乎可以说明,现代性的危机在江南书写中的普遍性。当代作家在想象江南的时候,其主体位置也很重要。那些在历史的时空中受到长久阻隔的主体,在他们回想江南的时候,往往对江南采取陌生化的处理方式,过滤掉其中的残酷的元素,而展现其浪漫的一面。而那些身在江南的主体,因为感同身受,江南的感受却常常呈现出其残酷的另一面。而如格非等人的江南想象,又与一般的写实主义不同,他是在寓言化文本构造中,刺破江南的梦幻,并无情地使之回到残酷的现实。但不管怎样,就是“现实的江南”也还是一种有关记忆的“梦幻”。这是由文学的本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