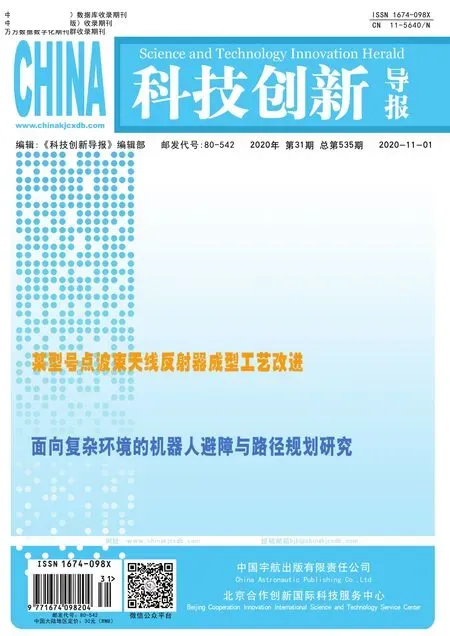水中1,4-二恶烷的去除研究进展①
刘喜 肖劲光 陈伟
(1.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410014;2.中电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 410014)
1 水环境中1,4-二恶烷的来源及污染现状
1,4-二恶烷,别名二氧六环、1,4-二氧己环,是一种稍有香味的无色液体。1,4-二恶烷通常用作氯化溶剂,特别是1,1,1-三氯乙烷的溶剂和稳定剂。虽然目前1,4-二恶烷在溶剂稳定方面的使用有所下降,但仍被用作生产纺织品、纸张、溴化阻燃剂、药品、油漆、抛光剂、涂料和增塑剂的重要溶剂。同时,它也是涉及环氧乙烷生产的副产品,并且残留在许多洗涤剂、洗发液和化妆品中。
1,4-二恶烷亲水性强,一旦释放到水环境中,就显示出高迁移率。其在土壤和有机质上的吸附能力低,可快速通过土壤和砾石层渗入地下水。因此,含1,4-二恶烷废物的使用、储存和处置不当,容易造成地下水和工业废水污染。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记录了在水体中检测到的1,4-二恶烷。1995—1998年,几乎所有在日本神奈川县采集的河流、近海和地下水的水样都检测出被1,4-二恶烷污染,其中一些地下水样品浓度高达94.8μg/L,受到严重污染。污染地下水样品中1,4-二恶烷和1,1,1-三氯乙烷的浓度相关性最高。过去被1,1,1-三氯乙烷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仍然是1,4-二恶烷的可能来源。
Ursula等[1]调查了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可能存在1,4-二恶烷的地下水地点,在这些选定的位点上均观察到1,4-二恶烷的存在,测得的最大浓度范围为0.15μg/L至152μg/L。最近的调查显示,德国许多河流受到1,4-二恶烷的高度污染,达到2.2μg/L的水平[2]。
在美国加州超过2000个地下水受到氯化溶剂和/或1,4-二恶烷影响的地点中,194个地点检测到1,4-二恶烷。在已鉴定1,4-二恶烷的部位,羽流中值最大浓度为365μg/L[3]。
2 去除目标和标准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1,4-二恶烷列为2B类药物,即对实验动物致癌性证据充分,但对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因此可能对人类具有致癌性。美国环保局也将其列为可能的人类致癌物,终生饮用含0.35μg/L 1,4-二恶烷的饮用水的癌症风险在百万分之一以上。虽然美国环保局迄今尚未制定1,4-二恶烷的饮用水标准,但几个州已经制定了指南或标准,如马萨诸塞州(0.3μg/L,饮用水准则),缅因州(4μg/L,饮用水最大暴露准则),新罕布什尔(3μg/L,环境地下水质量标准),科罗拉多(0.35μg/L,地下水标准),佛罗里达(3.2μg/L,地下水标准,130μg/L,地表水净化目标水平),北卡罗来纳州(3μg/L,地下水质量标准;0.35μg/L,地表水供应标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饮用水的指导值为50μg/L,韩国和日本均采用了这一标准[4]。
我国关于水体中1,4-二恶烷的环境风险和质量标准的研究尚属空白,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成果,尽快开展相关标准的研究和建设工作,为水体中1,4-二恶烷污染的防治提供技术指导。
3 1,4-二恶烷的去除
1,4-二恶烷在水体中广泛存在,影响了水环境,威胁着人类健康,因此对1,4-二恶烷去除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3.1 污水处理设施对1,4-二恶烷的去除
1,4-二恶烷独特的化学性质,如高水溶性、低亨利定律常数,以及与氯化溶剂和其他污染物的共存,增加了有效清除1,4-二恶烷的挑战。由于1,4-二恶烷性质稳定,在传统的生物处理技术下被认为是不可生物降解的。
在传统污水处理厂和天然地下水系统中,该化合物的生物降解潜力均较低。Stepien等[2]测定了4个生活污水处理厂废水中1,4-二恶烷的含量。四个水厂的进水1,4-二恶烷平均浓度在262±32ng/L到834±480ng/L之间,而出水平均浓度在267±35ng/L到62260±36000ng/L之间。在水处理过程中未观察到1,4-二恶烷的去除。
3.2 物理方法对1,4-二恶烷的去除
1,4-二恶烷的高溶解度和低亨利定律常数限制了物理修复。但在特定环境下,蒸馏、吹脱和吸附等物理处理可能是可行的技术。
国际大石油公司对2019年后的投资预算调增幅度较大。例如,埃克森美孚计划2019年后持续增加投资,到2025年达到300亿美元,回归到2015年的投资水平;其他大石油公司也在2018年预算基础上增加投资10亿~40亿美元不等。投资增长推动产量增长加速,预计未来5年国际大石油公司油气产量实现年均4%~7%的增长,这是2000年以来产量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蒸馏指通过沸点分离化学品。1,4-二恶烷沸点较高(101℃),且与水沸点接近。所以,采用蒸馏从水中分离1,4-二恶烷需对大量的1,4-二恶烷污染水进行热处理,能耗高且效果不理想。华盛顿Longview的TRS小组利用电阻加热将1,4-二恶烷污染的水从25℃加热到100℃,使地下水中的1,4-二恶烷挥发以去除1,4-二恶烷。处理后,两个污染点的1,4-二恶烷分别从140g/L和44g/L降至1.4g/L和低于检测水平[5]。
空气吹脱通常用于处理高挥发性和非水相液体,由于1,4-二恶烷是一种非挥发性亲水性化合物,因此空气吹脱处理1,4-二恶烷效果非常有限。2007年,Earth Tech公司采用空气吹脱方法(空气水比为183~291)处理了一系列不同浓度(7.6至11.1μg/L)的1,4-二恶烷污染水,出水浓度范围为7.0至10.0μg/L,其中最大可能的去除率仅约10%。
吸附是将水体中污染物集中在吸附剂的表面,从而降低水中污染物的浓度。活性炭为去除1,4-二恶烷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吸附剂。在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地下水中的溶剂处理项目中,发现进水地下水中二恶烷的浓度高达1500μg/L,用活性炭的吸附处理后,分析的出水样品中不存在该化合物。该结果可能归因于处理系统的进水浓度和流速非常低(0.5gpm)或在四氢呋喃(另一进水组分)存在的情况下1,4-二恶烷在碳表面被生物降解。研究发现各种有机材料来源的颗粒活性炭中,用核桃壳和山核桃壳制成的活性炭对1,4-二恶烷的去除效果最好(去除率可达50%),并且水蒸气活化的坚果壳碳产品比二氧化碳活化吸附效果更好。
已有文献报道了活性炭以外的其他一些吸附剂对1,4-二恶烷的吸附去除效果。陶氏化学公司合成的一种高分子吸附剂AmbersorbtmTM560具有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坚硬、球形和可再生的特点,去除1,4-二恶烷的效率很高[6]。实验室规模的处理试验表明,Hiatt Distributors Limited生产的活性三碱球团碳,在吸附质水比大于1:20时,对1,4-二恶烷的吸附作用较强,分配系数为264.7L/kg。以上研究表明,在合适的场地条件下(即流速和低浓度),使用合适的吸附剂时,吸附可能是可行的技术。
3.3 化学方法对1,4-二恶烷的去除
化学处理被认为是去除1,4-二恶烷的有效手段。1,4-二恶烷为环醚类化合物,性质稳定,氧化处理需要氧化电位大于2eV的氧化剂。目前,常见的水处理氧化剂中,只有芬顿试剂(H2O2+Fe2+)、紫外+过氧化物、臭氧+过氧化物和过硫酸钠具有氧化1,4-二恶烷的足够高的电势。
多篇文献报道了臭氧和过氧化物联合降解1,4-二恶烷。在实验室规模的研究证明了臭氧以及臭氧和过氧化氢的组合可有效降低1,4-二恶烷的浓度,还发现了亚铁、螯合铁和碱度作为添加剂与臭氧反应,同样可有效的处理1,4-二恶烷。目前,过氧化氢和臭氧基系统已应用于多个二恶烷污染地下水修复工程项目中。例如,某个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埃尔蒙特南部的地下水修复工程,安装建设了臭氧和过氧化物联合系统,作为去除二恶烷和降低受污染地下水中氯化溶剂浓度的预处理步骤。该系统可将二恶烷浓度从4.6μg/L降低到1μg/L以下。
紫外光激发H2O2产生的羟基自由基,将1,4-二恶烷快速降解为CO2。多篇文献报道了紫外和过氧化物联合降解1,4-二恶烷,考察了影响氧化过程的因素,例如pH值、碳酸氢盐、氯化物和硝酸盐[7]阻碍光催化,而超声搅拌和二氧化钛的存在显著提高了1,4-二恶烷的降解。在加利福尼亚麦克莱伦中使用过氧化氢和紫外光组成的AOP系统对二恶烷污染地下水进行了大规模修复。该系统于2003年10月重新启动后,每月处理约270万加仑的地下水,将二恶烷的浓度降低到6.1μg/L以下。
先进的电化学氧化可产生具有强氧化性的自由基,可有效用于原位和异位处理1,4-二恶烷。Park等[10]研究了新型金属-TiO2纳米粉末复合涂层钛网阳极对工业废水中1,4-二恶烷(10mg/L)的强化降解,其中Ru:Ti 摩尔比为0.6:0.4~0.9:0.1时,适当包覆的RuO2-TiO2复合钛网阳极对1,4-二恶烷电催化降解最有效。Jasmann等[11]研究了在黑暗条件下,用电化学催化活化了TiO2颗粒,1,4-二恶烷的降解率高达97%。
化学处理具有时间短、去除效率高的优点。例如,使用过氧化氢在2h内可去除96%的1,4-二恶烷;通过过氧化氢和亚铁离子的组合可在10h内去除超过99%的氢过氧化物;当使用peroxone活化过硫酸盐降解1,4-二恶烷和氯化溶剂的混合物时,测定半衰期为12.2h[12]。
然而,化学处理缺乏选择性(如可能在卤化物存在下导致形成有毒卤化副产物)和高成本(如电化学电池中的掺硼金刚石电极的高成本)仍然是未解决的障碍。Jasmann等人[13]利用化学法与其他方法耦合处理可克服化学法的缺点,达到快速高效处理水体中1,4-二恶烷的目的。如化学氧化法降解1,4-二恶烷的产物通常是乙醇酸、甲酸、乙二醛、乙酸和草酸等低分子量脂肪酸,它们可通过传统的生物处理进行生物转化[14],甚至微生物可以在中性pH条件下催化芬顿反应,并建议化学氧化法耦合生物处理方法应被视为可行的处理策略。光催化高级氧化工艺在浆膜反应器与膜过滤耦合,可完全降解1,4-二恶烷,因此也是有吸引力的选择[15]。其他各种单元操作的集成,如电化学处理与膜过滤或臭氧氧化集成,目前虽已有一些研究结果但需要进一步研究[16]。
3.4 生物方法对1,4-二恶烷的去除
生物修复是指利用生物活动富集或降解污染物从而达到处理水体的技术。生物处理1,4-二恶烷具有节能、低价的优点,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替代方法。生物修复可分为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
3.4.1 植物修复
植物修复主要是通过根系向上的质量转移和植物叶片的蒸腾作用,以及通过酶降解根区的化学物质来解决地下水中的挥发性有机物。研究表明,采用杨树杂交扦插,9d内可从核电站反应堆中去除平均54%的1,4-二恶烷;14C标记的1,4-二恶烷中碳的分布表明,从反应器中除去的1,4-二恶烷中大部分(77%)是挥发的,其余大部分存在于茎中。研究人员将杨树和生物强化与Amycolata sp CB1190结合使用,在45d内去除100 mg/L 1,4-二恶烷,直到其低于1 mg/L的仪器检测限值。以上研究成果表明,杂交杨树对1,4-二恶烷的吸收迅速,再加上根区的生物强化,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是一种可行的修复技术。另一项小型研究,1,4-二恶烷可以通过细胞色素P450通过膜向茎和叶氧化。因此,研究建议测试筛选更多能够修复有机污染物的候选植物,如桦木、香根草和侧柏[17-18],以进行1,4-二恶烷植物修复并揭示潜在的新生物降解酶和降解途径。
1,4-二恶烷植物修复的植物修复的局限性包括生长季节限制和植物可利用水的深度,现场应用文献仅限于2007年的一项研究。为解决地下水渗漏对地表水的潜在影响,在约8000平方英尺的区域内建立了植物修复系统。在垂直于地下水流向种植了12排共100多棵杨树,并在上述杨树之间再种植了100根杂交杨树扦插苗,以增加快速吸水能力。2007年夏季,由于渗漏取样点干燥,无法取样,这被解释为树木脱水(即吸水)能力的直接结果。
3.4.2 微生物修复
1,4-二恶烷通常被认为无法进行厌氧生物降解。但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富含铁还原菌的厌氧污泥可以降解1,4-二恶烷,零价铁在混合铁还原培养基中促进了这种缓慢的活性[17]。然而,铁还原菌在1,4-二恶烷厌氧生物降解过程中的直接作用和厌氧途径目前尚不明确。
1,4-二恶烷好氧生物降解最常见的微生物为广泛分布在环境中红球菌、分枝杆菌或假诺卡氏菌[18,19]。这些微生物主要通过代谢和共代谢两种途径降解1,4-二恶烷[20]。代谢途径指一些好氧细菌和真菌可以在1,4-二恶烷上代谢和生长,并将其作为碳和能量的唯一来源;共代谢途径指通过加入其他碳源,诱导微生物产生酶来降解1,4-二恶烷。已成功用于1,4-二恶烷共代谢的主要底物[21-22]包括气态烃(C1-C4烷烃)、环醚(如四氢呋喃)和醇(1,4-丁二醇)。
代谢和共代谢可有效生物降解的1,4-二恶烷的浓度有明显区别。1,4-二恶烷代谢细菌的生长通常是低效的,并且1,4-二恶烷的半饱和常数的浓度范围可高达160mg/L(假诺卡氏菌CB1190),也可低至17.5 mg/L(黄杆菌DT8)[23],均远超过污染水体中常见的1,4-二恶烷的浓度。因此,目前已知的大多数1,4-二氧烷代谢菌株不太可能在低环境浓度下对1,4-二恶烷的生物降解起到实质性作用。但在共代谢系统中,活性微生物可以降解低得多的1,4-二恶烷浓度[24]。现场研究表明,即使在存在潜在竞争性和有毒氯化污染物[25]的情况下,丙烷氧化微生物可以共代谢降解地下水中μg/L级别的1,4-二恶烷。总的来说,对于1,4-二恶烷出水要求达到μg/L水平的情况,微生物共代谢比微生物代谢处理的效率更高。
4 结语
国内外一些学者报道了水环境中1,4-二恶烷的来源及污染现状。尽管报道的数据非常有限,仍然表明了1,4-二恶烷已经在生态环境中广泛存在,并可能对人群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在各类处理方法中,蒸馏、吹脱和吸附等物理处理技术仅在特定环境下可行;化学氧化处理和生物修复技术被认为是去除1,4-二恶烷的有效手段,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我国针对水环境中1,4-二恶烷的相关管理政策和环境标准尚不完善,需及早开展1,4-二恶烷情况调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研究1,4-二恶烷污染防治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