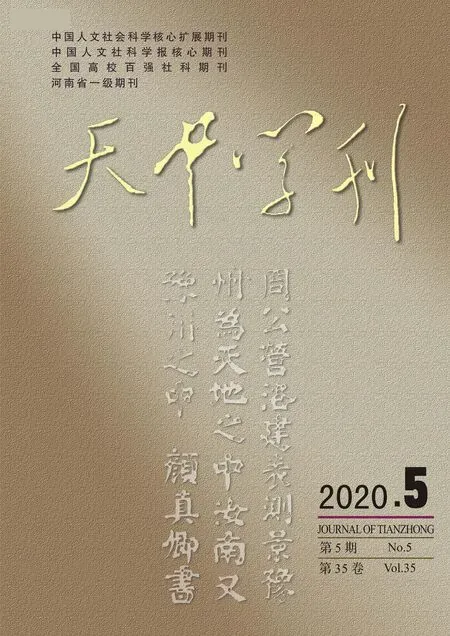杜甫的胡适存在
王元忠
杜甫的胡适存在
王元忠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立足于新文学建设的需要,胡适对杜甫进行了极富个人特点的理解和接受。胡适无论是在社会问题诗中对杜甫的推崇,还是在白话化诗和小诗中对杜甫的强调,其中极多误读和误解。但是胡适的身份和读解中的新思考,却使得他的意见在价值取向、观念和方法诸多层面启迪了现代杜诗的研究,具有了些许发生学的意义。
杜甫;胡适;个性化接受;发生学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胡适是对杜甫谈论较多的人,同时也是在新诗写作的实践中有意对杜甫写作的“好”进行过借鉴的人。此外,胡适是新文学重要的发起者,某种程度上讲,称得上新诗写作的祖师爷,他特殊的身份影响了其后很多年的杜甫研究。无论是顺向的接受还是逆向的反驳,不同言说所构成的话语景观,不仅显现了杜甫研究的新变化,而且也揭示了新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资源之间复杂的运作关系。缘此,梳理学者既有的研究成果,在文学和学术双重观照之下,还原胡适本人对杜甫的解读和认知,辨析他人对胡适的批评和研究,自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一、学术表现
胡适对杜甫的学术评价,主要见于他的两部文学史,一部是《国语文学史》,另一部是《白话文学史》。《国语文学史》原本是1921年至1922年他在北京大学给学生授课时的油印材料,1927年正式出版。在该书的第二编“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之中,胡适对杜甫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杜甫是唐朝的第一个大诗人,这是我们都可以承认的。但杜甫的好处,都在那些白话化了的诗里,这也是无可疑的。杜甫是一个平民的诗人,因为他最能描写平民的生活与痛苦。但平民的生活与痛苦也不是贵族文学写得出的,故杜甫的诗不能不用白话。[1]41
这段话包含了这样几个重要信息:一是给予杜甫极高的评价,说他是“唐朝第一个大诗人”;二是说杜甫创作的好处“都在那些白话化了的诗里”;三是认为杜甫是一个“平民的诗人”,最能描写平民的苦和痛。《白话文学史》是胡适在《国语文学史》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材料和发现,经过补充和修改,于1928年6月由新月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新的文学史。在这部新著中,胡适专列一章对杜甫进行重点描述。胡适不仅延续了过去的评价,从宏观上说杜甫是唐朝“这个时代的创始人与最伟大的代表”,是“我们的诗人”,而且进一步细化,从思想主题和表现形式多个方面对杜甫的诗歌写作进行了评述。
在诗歌内容上,胡适肯定了杜甫对时事特别关注的一面,认为杜甫的写作实际上开了后世“社会问题诗的先河”。并于此基础上,特别肯定了杜甫写作的现实主义特色,通过对杜甫写作中的现实关注、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因素的强调,从五四思想启蒙的目的出发,将杜甫和李白进行了比较,以为“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的诗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实写人生或讽刺时政的,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的话,李白便不能说,这才是李杜优劣的真正区别”,从而引发了现代杜诗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扬杜抑李”之说。
而在诗歌形式上,胡适不仅突出了杜甫的俳谐体、打油诗之类的写作,以为“杜甫最爱作打油诗遣闷消愁,他的诗题中有‘戏作俳谐遣闷’一类的题目。他作惯了这种嘲戏诗,他又是个最有谐趣的人,故他的主要诗(如《北征》)便常有嘲戏的风味,体裁上自然走上白话诗的大路。他晚年无事,更喜欢作俳谐诗,如上文所举的几首都可以说是打油诗的一类。后人崇拜老杜,不敢说这种诗是打油诗,都不知道这一点便是读杜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本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1]324,而且于杜甫各体诗的写作中,特别提及了他的“小诗”写作,认为“他晚年作了许多‘小诗’,叙述这种简单生活的一小片,一小段,一个小故事,一个小感想,或一个小印象……杜甫的‘小诗’常常用绝句体,并且用最自由的绝句体,不拘平仄,多用白话。这种‘小诗’是老杜晚年的一大成功,替后世诗家开了不少的法门;到了宋朝,很有些第一流诗人仿作这种‘小诗’,遂成中国诗的一种重要的风格”[1]327。
此外,胡适在其他文章之中还散在一些对杜甫的论述,如在《中华民族的人格·序》文中,他列出23人的人格代表名单,其中唐代共4人,分别是唐太宗、魏征、杜甫和陆贽,杜甫赫然在列,显见他对杜甫一贯的推崇。只是总体而言,这些散论基本上都是前两部文学史观点的重复或推衍,内中很少个人的新见。
胡适对于杜甫的言说,有其作为一个学者的认真、严肃的一面,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六经注我”或“托古改制”的“心不在焉”“指鹿为马”的不专业、不严肃的一面。从新文学建设的思想内容一面,他突出了杜甫创作中的“平民文学”“人道主义”的特质;而从新文学建设的话语和文体一面,他则夸大了杜甫创作的白话运用、谐趣追求和小诗写作,而对一贯被人们看重的杜甫律诗特别是七律诗的创作极为蔑视,言其不是“只成一些有韵的歌括,既不明白,又无诗意”,就是“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1]331。
据此评判,胡适的杜甫解读,其中虽然有契合杜甫本原的正悟,但也有不少误读、误解的成分。缘此,对于胡适的杜甫研究,一直以来持批评意见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在以“李杜优劣论”为话题评述曾毅的《中国文学史》时,提及《白话文学史》中胡适有关杜甫的研究,学者罗晨认为虽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在许多方面都独具手眼,在李杜优劣论上亦复如是”,但他具体的论述“可分两点来看:首先,以内容为标准难以判断艺术创作之优劣。中国文学史上所谓‘写实’之作,自古有之,若写实者皆优于其他题材的诗歌,则优于李白者何止千万,而这显然绝非事实。胡适《白话文学史》实有观念先行之弊。其次,从此段论述中可见,相较于从形式上立论,胡适显然更看重内容上的立论。然而在同一部《白话文学史》中,亦存有形式优先内容之论,如论杜诗,重绝句而轻律诗,甚至将律诗完全否定,即是一例。可见胡适论述之中有观念矛盾冲突之论,实为观念尚未成熟之表现”[2]。在具体评述胡适《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中有关杜甫的论述时,学者高玉侠不仅逐点分析,指出胡适许多的“强说”和“硬说”之弊,而且由此总体论断,“由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论杜诗未免太过激进从而走入了一个极端”[3]。
二、杜诗研究的贡献
胡适对杜甫的理解,因为动机不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更多是借杜甫这杯酒浇自己有关新文学建设之块垒,所以本质上便有了“六经注我”或“托古改制”的意味,其目的就是要借此为新文学张目,从中国文学传统内部,别寻一些能够促进新文学生长和发展的养料。然而,颇具吊诡意味的是,由于胡适在新文化建设(包括新文学和新学术)中倡导者的特殊身份,因此他原本并不专业也不专心的杜甫研究,却在有意无意之中改变了既有的杜甫研究模式,为后来的杜甫研究指示了一种新的范式。所以胡适之后许多人的现代杜诗研究,无论对其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便都有了一点由他引发且针对他的潜在对话的意思。在这种意义上,胡适的杜甫解读对于现代杜诗学而言,甚至有一点发生学的意义。
(一)杜诗研究新取向的确立
对于杜甫诗歌的研究,传统主流的取向,主要是以杜诗作为诗歌写作的最高标准,意图通过学习而最大限度靠近它。谈到诗歌学习的榜样,宋人严羽曾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4]明人李梦阳更进一步,说“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5]。话语中显见他们对杜甫无以复加的推崇之意。以实际的创作来佐证,自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师以来,元明两代,潜心学杜、尊杜的写诗者代不乏人,到了清朝一代,承江西诗派余绪,于一波一波的尊杜、学杜风潮之中,一批又一批的诗人更是以能模拟、接近杜甫为能事,形成了顽固的尊古拟古之风。从发展的机制内部看,这阻碍了汉语诗歌从创造的质地上更新和变故的可能。
有感于中国文学内部积重难返的僵硬和腐朽,特别是从新文化建设的启蒙目的出发,胡适意识到中国文学旧有语言的表达和人的现实生存经验的严重脱节,他在立足新文学建设这一根本任务之时,便从揭示现实问题、表现平民的痛苦以及白话运用方面,明晰了杜甫诗歌对新诗写作乃至整个新文学写作所能给予的帮助,从而确立了以有助于新诗发展为根本目的的新的杜诗研究态度和取向,对杜甫的非律诗的白话化写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二)杜诗研究新标准的建立
传统杜甫研究对于杜甫诗歌的价值评判,集中于两个具体的面向:一是在主题内容上突出诗人以“忠君”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表现。北宋大诗人苏轼在给朋友的信里就曾讲:“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6]南宋学人曾噩也以为:“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7]一是在艺术表现上沿袭中唐元稹“集大成”之论,认为杜甫诗歌创作的价值具体体现于其句法上的“以散文入诗”,字词选择上的擅长用典、“无一字无来处”,律诗特别是七律写作中的结构谨严、音韵整饬,风格上的抑扬顿挫和艺术效果上的“温柔敦厚”。这些评价不可谓不确当,然而代代相袭之中,在对杜甫诗歌价值的揭示之中也带来了相应的价值遮蔽,使得后继者愈来愈为传统的伟大所窒息,从而鲜有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见。
立足于新文学的建设,同时受西学新理论的冲击,胡适则在主题思想一面有意淡化了杜甫与君王、朝廷和整个封建官僚体系的关系,别立他和底层百姓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标准,认为“杜甫是一个平民的诗人,因为他最能描写平民的生活和痛苦”,将杜甫称之为“平民的诗人”和“我们的诗人”。而于艺术表现一面,胡适则反传统所持的习见,对人们极为推崇的杜甫七律如《秋兴》《诸将五首》等深表轻视,认为其不过“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相反,胡适从写实、白话化的程度和生命表现力等新的标准出发,突出了杜甫的社会问题诗、打油诗和小诗写作的作用和价值。胡适认为这样的诗,区别于精致、僵硬的贵族“雅化”写作,并因其通俗生动的特性,使得杜甫的许多诗歌有了“一种解放束缚的力量”,也使得杜甫本人“终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衰颓,风味不干瘪”[1]311。
(三)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引进
五四精英一代,大都有明显的西学背景。缘此,有意识地引用西方观念和方法,通过西方概念来“整理国故”,也便蔚然成了当时的一种风尚。胡适留学美国多年,于西方文学和学术多所修习,所以他的杜甫言说,也便常常显现出较为自觉的西方眼光、思维方式和概念话语运用特点。
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以进化论思想为依据,畅言“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1]282。他遵进化论思想之原理,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今日发展的应有形态。缘此,从不断进化的白话化文学史观出发,他不仅突出了杜甫诗歌创作中的白话成分,而且着意强调了这种白话的表现对于后来优秀诗人创作的积极影响。在《国语文学史》第二编之《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一节里,他放言直说,以为“杜甫的好处,都在那些白话化了的诗里,这也是无可疑的”[1]41。而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之第十五章“大历长庆年间的诗人”之中,胡适则认为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元结、孟郊、韩愈、元稹、白居易等,都深受杜甫白话化写作的影响,从而别开唐诗的辉煌,使得“从杜甫到白居易,这一百年(750―850年)是唐诗的极盛时代”[1]331。基于此,胡适创作的唐以下古代白话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基本成了杜甫白话化和现实化创作的影响史。
观念的变化必然导致方法的变革,以进化论文学史观反观中国古典学术的表现,胡适敏感地注意到了它们感性、模糊和碎片化的存在特征。为此,他有意识地引用了西方理性、清晰、系统的科学理论,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方法,先总体假定中国古代存在着一种白话文学,而后再以此为依据,观审和判断杜甫的诗歌创作,从中考察出哪些是白话诗,其优点何在,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样的西为中用或者今为古用不一定都合适,所以有时难免因为分析对象的不同以及人们对于这种不同的忽视,导致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牵强和附会。譬如胡适认为杜甫诗开“社会问题诗”之先,并认为杜甫这样的选择决定了他写作的现实反映力度和对平民的必然靠近。对于他这样的说法,学者高玉侠等不以为然,认为“所谓社会问题诗,只是后人在阅读杜甫的诗歌时用抽象的思维,从大量的诗歌作品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特征。因此,笔者认为纯粹的社会问题诗,只是存在于后人对杜甫诗歌的理解之中,而在诗人个人的实际创作中是不存在这样一种概念的。因为文学的对象是具体的行动中的人,所以作者常常会写他自身的生活境遇及所见所闻中周围人的生存境况与悲欢离合,因此诗人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只是用爱憎分明的强烈情感和泾渭分明的是非观念写出了对遭奴役、遭迫害、遭损害的弱小无辜者的深切同情,同时写出了人生中愿望无以实现的酸楚及那个时代中一切存在着的不公与创痛。尽管这在客观上反映出当时特定历史时代的大量社会问题,但是诗人个人并无这样的初衷。一言以蔽之,杜甫并不是为了社会问题而写了社会问题诗,因此胡适说这是杜甫的创体及写诗的技术未免是不科学的”[3]。问题极为分明,但是因为异质带来的新颖,胡适的尝试在事实上对现代杜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的各种对话,依然承续着“平民写作”“社会问题关注”和“白话化”等主要话题的表达,无论是顾彭年、冯至、萧涤非等人的顺向延伸,还是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逆向反驳,现代杜诗学由是在旷日持久的争辩之中,营造出许多别样的话语景观。
三、创作表现
胡适对杜甫的接受,不仅表现于他意欲进行新文学建设的理性认知,而且也具化于他的诗歌写作实践。这种实践,可以分为自觉和不自觉两个时期。
不自觉时期,主要指胡适还没有根据新文学建设的需求,对杜甫进行审视和吸收之时的表现。胡适开蒙很早,他早期的学习,因循的依然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模仿古人作诗作文。胡适三岁之时即在其父亲铁花公的指导下诵读古诗,及其少长,便于私塾老师的督促之下开始学作古诗。他初始写诗的时候,对于杜甫的诗歌,大都是最基本的引用或化用,如《口号》之“可怜家国计,都是稻粱谋”句,即是对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之“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句的化用;《赠别黄用溥先生》之“何时重聚首,相向泪阑干”句,即是对杜甫《月夜》之“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句的化用;《赠鲁楚玉》之“谁为患难交?翻手成雨云”句,即是对杜甫《贫交行》之“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句的化用。他的这种引化,相当于书法练习开始之时的临帖,虽然临者不同,所临之帖也各见临者性情特点,但总体而言,所临之帖作为先在的存在,还是内在规约着临帖者的实践,所以在其一招一式之中,显见原帖的笔画、结构痕迹。
随着从不自觉的模仿到有意识提取的过渡,一如临帖者临着临着,有了不看帖而创作的想法,胡适对杜甫的接受,也便从具体词语和句子的引化,逐渐发展成为对其写作精神和取向的实践应用。首先是白话口语的选择。他既然认为杜甫的好都在他的白话化了的诗作里,所以他自己写诗,为杜甫所启示(最起码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也便逐渐地弃文言而从白话。此外,因为对杜甫那些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热爱祖国的“社会问题诗”的高度认可,他在自己的诗作里也便不时地抨击黑暗政治,如《你莫忘记》《威权》等;表达自己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之情,如《读报有感》《双十节的鬼歌》等;书写自己对下层民众的体谅,如《人力车夫》;抒发对祖国繁荣强大的期盼,如《睡美人歌》。胡适极力汲取杜甫积极入世、乐观处世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并将之应运于自己的诗作,如《春日书怀和树永》之“高谈好辩吾何敢?回天填海心难灰”句的乐观,《朋友篇,寄怡荪,经农》之“时危群贤各有责,且复努力不须哀”句的积极,还有《乐观》《努力歌》《后努力歌》《平民学校校歌》等作品所表现出的努力向上的人生态度。
不过,胡适对杜甫的学习,更多侧重于形式的借鉴。以“打油诗”“小诗”为代表的那些“散文化”诗作,未能深层体现杜甫诗作的精神和审美观,所以他自己所得意的一些尝试之作,如《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恭送赤脚大仙》《戏和周启明打油诗》等,自以为风趣、幽默,但时过境迁,以旁观者眼光审视,则分明表现出他对杜甫写作理解的偏差,倍显因油滑过度而致的无聊。而他模仿杜甫所倾力打造的那些“小诗”,如《湖上》《鸽子》《小诗》《也是微云》等,虽然造境平和、书写自然,有一定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诗情和想象力都不充分,主体的内化不够,与他推崇的杜甫的绝句小诗,有着不小的距离。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是春天的诗人,他的诗是青年的歌唱,所以很难领悟离乱之际久经磨难的杜甫成人式的诗篇,因而远没有登堂入室,得老杜精髓。其实这不能全怪胡适,从个人来看,很多诗人对于杜甫的诗歌开始领悟乃至爱不释手几乎都在中年以后,从时代来看,往往经历过世事坎坷、家国变迁的一代才能更多地贴近杜甫。”[8]研究者孔令环所说的这段话,从接受者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时代所给予的生活经验两方面,较为客观地说明了胡适对于杜甫接受的局限性。
要之,杜甫的胡适存在,一方面是胡适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主动选择、积极接受的结果,其在新文学整体的“西学”或“学西”的背景上,显见了新文学开创者从传统,特别是主流知识分子写作传统之中别寻本土资源,为新诗的写作助阵也希冀发现新的经验的努力;另一方面,因为太过功利的现实目的,杜甫的胡适存在,也是古典的杜甫被现代的胡适误读、误解的结果。这样的“误”,有可以理解且明显的新颖之处,其在业已僵硬、模式化的古典杜诗学研究之外别开新路,引导了几个时代的现代杜诗学研究,但也存在太多问题,它的浅表和偏见,在对杜甫的现代价值进行建构之时,也遮蔽了更多的价值可能。所以,在对其中的枝枝蔓蔓和来龙去脉进行梳理之时,在“同情的理解”之外,我们也须得进行仔细的分辨。
[1] 胡适文集:第8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罗成.民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李杜优劣论”:以曾毅《中国文学史》中“李杜优劣论”为中心[J].杜甫研究学刊,2018(2):75–84.
[3] 高玉侠,周沐红.论胡适的杜甫诗歌批评[J].语文学刊,2012(3):89–90.
[4]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8.
[5] 何良俊.四友斋丛书:第2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苏轼文集:第4册[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517.
[7] 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4:788.
[8] 孔令环.杜甫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以胡适、闻一多、冯至为例[J].中州学刊,2007(5):212–216.
The Existence of HU Shi in DU Fu
WANG Yuanzhong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741001, China)
Based on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terature, HU Shi had a very personal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DU Fu. He not only praised DU Fu's poems defecting social problems, but also emphasized his colloquial and small poems. Many of his comments are full of misunderstandings. However, His identity and new thinking in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have inspired the present study of DU Fu's poetry in many aspects and has phylogenetic meaning.
DU Fu; HU Shi; personal acceptance; phylogenetics
I206.2
A
1006–5261(2020)05–0104–06
2019-12-08
王元忠(1964―),男,甘肃甘谷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