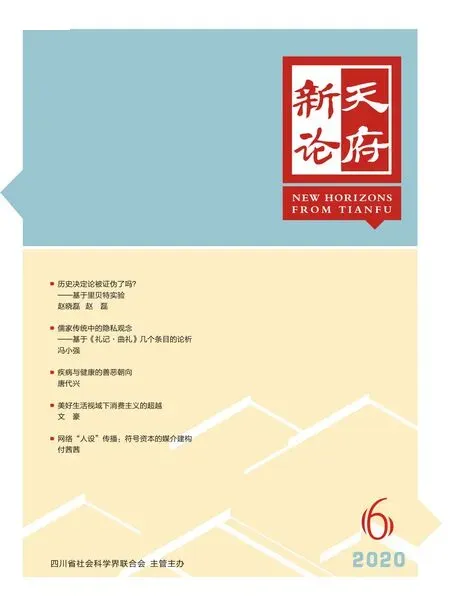美好生活视域下消费主义的超越
文 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中国社会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生存需要)已得到较好的满足。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导向,人民的需要已从相对单一的物质文化层面提升到了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内容的美好生活层面。然而,吊诡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丰富物质供给,以及人民在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得以满足之后所释放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也正好契合于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社会日渐兴起的消费主义,并为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消费主义观念支配下,无尽的物欲将代替正常而有限的需要,将人们囚锁于拜物教这一异化的牢笼,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向往相背离。因此,从消费主义的视角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后暗含了一个悖论性的事实:消费主义既与美好生活需要相伴生又相背离。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消费主义视角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行重新审视,在廓清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消费主义关系机理的基础上,探索消费主义的超越路径。这既是中国消费主义问题研究的新维度,也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需要着力思考的重大现实命题。
一、新时代的中国:美好生活需要与消费主义的时空同场
美好生活需要的产生与消费主义的兴起都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都以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从这一视角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它既昭示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产生,也意味着消费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基础日益夯实。美好生活需要与消费主义在新时代的中国这一时空场域的相遇难以避免。
(一)大众规模化消费:消费主义兴起的物质基础
何谓消费主义?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界说,但是基本都绕不开欲望驱动消费这一本质性特征。正如国内学者王宁所言:“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欲望的不断更新和无节制膨胀是消费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1)王宁:《“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欲望驱动的消费现象其实自古有之,如中国晋代王恺和石崇的斗富。关于消费主义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学者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B Veblen)和德国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2)1899年,美国学者凡勃仑在其《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炫耀性消费”,以此来说明有闲阶级通过浪费性的消费来显示身份并获得心理的满足。1901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从时尚消费的视角,指出时尚变化的根源在于上层阶级为了凸显身份,实现自我标榜的需要。他们的研究都共同指向了消费动机中商品的符号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挤占。。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凡勃仑和齐美尔所处的时代,有限的消费品和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的低收入水平,使得具有消费主义性质的消费实践还只停留于社会上层阶级这一少数群体。
消费主义真正成为一个社会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建立在大众规模化消费的基础上,以20世纪初美国福特主义的诞生为重要标志。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技术革命带来的强大生产力和海外殖民市场的饱和带来的产能过剩,使得大众规模化消费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资本增殖的逻辑结果。在福特主义的指导下,生产上的规模化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物质商品,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提升了大众的消费能力,大众规模化消费进而成为可能。“大众规模消费和高水平生活一旦被视为经济体制的合法目的,所有这一切就出于社会对变革的需要及其对文化变革的接受而产生了”。(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资本联合媒体,以广告和分期付款制为主要手段,共同构筑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突破了美国主张禁欲、节俭的新教伦理传统,成了维系大众规模化消费并实现资本增殖的重要文化力量。
因此,追求欲望满足的消费主义建立在大众规模化消费的基础上,它超越了实际需要的有限性,必须以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民众与之匹配的消费能力为支撑。于是,一个国家消费商品的丰裕程度和国民消费能力的高低将构成消费主义能否兴起的物质基础。
(二)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成:大众规模化消费的可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所以发生变化的现实背景作出了如下说明:“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既表明了人民产生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背景,也意味着大众规模化消费的社会基础已渐成熟。
首先,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状态,总体小康的实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临近,意味着从总体上而言,中国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已得到较好的满足,民众已具备较强的消费能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大众消费能力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同时也是判定小康社会实现水平的重要变量。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这两项数据已分别达到28228元和19853元,并且城镇居民的相关数据明显高于农村居民(4)《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20年5月21日访问。。
在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提升的同时,我国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在逐年降低。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已经跌破30%(5)《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2020年5月21日访问。。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已达到了富裕的标准。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表明中国人民满足生存需要的消费支出在个人消费支出总额中占比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同时也说明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在中国人民消费比重中不断扩大。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水平的提高,以及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中国大众已具备较强消费能力这一客观事实。
其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助力,也是社会消费品得以充足供给的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时期内,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造成整个中国社会物质消费品的紧缺,民众被迫处于一种低消费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产能过剩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制造业产值连续8年居世界第一位,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一些产品甚至出现大量过剩。”(6)林兆木:《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日报》2018年3月30日。中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除了国内生产力所提供的商品供给之外,在今天这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借助发达的国际商贸物流体系以及电子商务等便捷的购物渠道,全世界的商品都成了中国民众的消费对象。在中国当下的消费语境中可资消费的“物”已变得空前充裕。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已高达383466.54亿元,是十年前(2009年)的三倍(7)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0年5月21日访问。。在制造业生产力之外,近些年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长6.7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的拉动高达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8)《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2020年5月21日访问。。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在为民众提供更为充足的服务性消费供给的同时,也反向证明了居民消费力的不断增强、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
概而言之,从物质基础而言,美好生活需要与消费主义是一种伴生关系。中国消费主义发展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改革开放后,产生并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迎合了当时中国民众从长期被动的压抑性消费中寻求解放的心理需求以及“好面子”的文化传统,契合于当时中国新兴市场经济中的资本逻辑,进而伴随着中西之间的商贸交往与文化互动进入中国。随后,这种价值观在改革开放后“先富群体”的实践引导、大众传媒的宣传导向、透支性的现代金融手段(信用卡、淘宝花呗、京东白条等)等多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兴起于今日的中国,并成为部分国人(如沉迷于消费的“月光族” “剁手党”)所追求并践行的人生信条和生活方式。如今,中国消费主义的实践主体已从早期的“先富群体”,以及进行职位消费、非工资性收入和集团性个人消费的少数群体(9)郑红娥:《中国的消费主义及其超越》,《学术论坛》2005年第11期。,蔓延为“双十一”消费狂欢和“粉丝经济”中的普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群体。麦肯锡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显示: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1/3,平均每户消费奢侈品的家庭支出近8万元购买奢侈品,“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分别占到奢侈品买家总量的43%和28%,分别贡献了中国奢侈品总消费的56%和23%”(10)麦肯锡中国区服装、时尚与奢侈品咨询团队:《中国奢侈品报告2019》,2019年4月,https://www.mckinsey.com.cn/wp-content/uploads/2019/04/McKinsey-China-Luxury-Report—2019-Chinese.pdf,2020年5月21日访问。。
不过,当前由于我国发展的不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存在较大差距。消费主义的实践主体伴随着这种不平衡,还只停留在部分人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未来我国将在平衡和充分发展的方向上不断迈进,地区、城乡、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因此,从物质基础上看,消费主义的实践主体将随着国家的平衡和充分的发展而扩张到更广泛的社会人群。也正因如此,消费主义成了我们在新时代的中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二、消费主义与美好生活需要的背离
美好生活是人类自古以来共同的向往和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 “小康社会”为美好生活构筑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安排。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思想家们对“美好生活”进行了理念上的抽象和建构。他们从形而上的“终极存在”出发构建了纯粹理论式的生活理想,从苏格拉底“有价值的生活”到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莫不如是。马克思提出哲学家应该重在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进而实现了从传统抽象理念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向。马克思力图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理解人,以“自由人联合体”作为构建“美好生活”现实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者从“需要满足” “人的本质” “价值” “共同体” “综合”等不同的维度对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研究和概括。(11)时伟:《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关于“美好生活”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3期。回归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语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丰富而现实的,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的需要体系,是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达到一种美好状态所不可或缺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体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它不同于古希腊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上的抽象化的生活理想,而是沿着马克思的思想路径,在生活世界中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目标之下的一种生活状态。
从人的本质上看,人既与动物一样是生存于自然环境之中的生命存在物,同时又是拥有能动意识并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精神存在物,人的存在是客观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可逃离的三组基本关系。真正的美好生活离不开经济和文化建设所带来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满足与和谐,离不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对社会秩序的规范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三组关系的和谐状态是构筑人民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欲望的满足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获得了被社会认可的“正当性”。消费不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我买故我在”(芭芭拉·克鲁格言)成了消费主义的箴言。消费主义作为一种隐蔽的霸权统治力量,使人们沉溺于广告所建构的超现实的仿真世界,在商品符号意义所激发的“虚假需要”的控制之中,难以抽身。正因如此,人们在消费主义的生活实践当中,将消费能力和消费的对象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极大地破坏了人自身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三组关系应有的和谐状态,与真正的美好生活向往产生了严重的背离。
(一)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失和
精神需要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隔,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它主要指的是人获得尊严、地位、认同、赞许、信任、精神愉悦等心理情感上的满足。在实践中,文化消费和物质消费都是满足精神需要的重要途径。然而,在资本逻辑支配的消费主义中,文化也不断被商品化。工业化时代的规模化生产所带来的大众文化,失去了文化的“灵韵”,它以通俗、快捷、感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勾起人们消费的欲望,统摄着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大众失去了在精神世界中的深刻。近年来,国内大众文化的流行载体从篇幅较长的博客到140字以内的微博,再到声像感官刺激更强的短视频的转变,正是消费主义下文化消费景观的绝佳注脚。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就曾对此批判道:大众文化以流行为标准丧失了个性,人们在大众媒体的控制下,沉迷于浅层次的文化消费欲望之中。(12)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大众文化的消费狂欢消弭了人们批判性的思维向度,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在汽车中,在高保真收录机中,在错层式居室及厨房设施中发现了自己的灵魂”(1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9页。。
与此同时,在消费主义的文化结构中,资本联合媒体通过人和商品的双重编码,将人关于爱情、尊严、人生的意义等精神世界的需要编码成符号,与物产生了对应的关联。商品的符号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A物与A意义的固定关系,使得商品有了自我指涉的功能,“消费的逻辑被定义成了符号的操纵”(14)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第48页。。在消费主义的观念中,商品的符号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了消费的对象,精神需要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来完成。高端的商品代替了道德品质和工作成就成了人们赢得尊重、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近些年,一些女大学生通过摧毁尊严底线的“裸贷”方式,贷款购买高端化妆品,只因为她们必须借助于与周围的人相同的物来建立所谓的“平等”进而获得所谓的“尊严”。这生动地体现了在消费主义之下,人的精神物化的可怜窘境。
在精神物化的背后,对于普通收入群体而言,追求欲望满足带来的过度消费甚至透支性消费(如月光族),将大大降低人们在经济上的抗风险能力,一旦遇到疾病、失业等突发性的变故,立即就会陷入贫困的境地,连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都难以满足。更高要求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而消费主义有可能给人们带来物质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沦丧。
(二)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与对立
在消费主义的文化结构中,人与人的关系被物化,商品成了维系社会关系的媒介。关于人与人的物化关系,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的阐释中就进行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商品到货币“惊险的一跳”,商品获得了高于人的神圣性。在此基础上,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被物与物的商品交换关系所取代,人的社会关系由物来替换。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一书中提出“物化”(reification)的概念,进一步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物化,并将其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而必然的现象。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视角,从商品的符号化分析了消费主义中人与人的关系物化的本质。由于商品符号的差异化编码,不同的商品指代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进而使得消费拥有了划分社会阶层的权力和功能。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通过与他者的对比实现自我身份的认知——我是谁?我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或团体?于是,消费能力和消费内容成了阶层身份识别的“标准化权力”。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在现今资本主义消费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5)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第48页。
消费主义暗含了一种虚假的民主和自由:身份和地位不再被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所固定,只要通过消费获得对物的占有,就能实现身份地位转变。然而,高地位阶层身份的维系由一系列的商品符号(房、车、穿戴等)构成,并且商品符号的差异化编码会不断地转换,每年都有不同的时尚和新款。因此,高阶层身份需要持续性的高消费来维系,并通过刻意保持自身在消费上的差异性来实现身份的认同。阶层身份表面上由物来划分,本质上由个人的财富拥有量来确定。人与人之间在财富上是不平等的,这就注定了只要人们陷入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就必然呈现出等级的划分。在商品符号的等级秩序中,人们容易落入“比较式生存”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之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16)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林克、曹卫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1页。消费主义将使人们在互动中强烈地感受到符号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感,激发内心深处的羡慕甚至嫉恨和仇富,进而导致社会的不公、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三)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
资本联合媒体制造的“虚假的需要”,使人们不再直面自身所处的客观生活世界,而将广告营造的仿真和超现实景观当成自己向往的人生目标。它突破了真实需要的有限性,将大众带入了无法满足的欲望黑洞。这种欲望在消费实践上主要以炫耀性欲望和占有性欲望来呈现。炫耀性需要通过对商品差异化的符号价值的占有来完成。“假如我们承认需求从来都不是某一物品的需求而是差异的‘需求’(对社会意义的欲望),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永远都不会有圆满的满足,因而也不会有需要的确定性。”(17)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0页。占有性消费意味着人们将消费过程的享受和对物无止境的占有,作为人生乐趣的重要来源以及人生意义的集中体现。“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郑重地宣称,生活的意义存在于我们所拥有的商品之中。因此,消费就是生命的全部活力所在,为了保持生命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不停地消费”(18)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化社会学的基础》,田禾、黄平译,《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消费主义下的过度消费,表面上是大众非理性消费的结果,实质上是资本为追逐利润扩大生产进而实现资本增殖的逻辑结果。诚如美国著名学者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所言: “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19)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为此,西方工业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计划性淘汰”一词,如今我们却似乎身处其中。“计划性淘汰”从表面上看是企业通过产品的内置或外观设计,有意缩短产品寿命,或者加快产品的更新迭代,使消费者重复购买同类产品的周期缩短,本质上则是“培养消费者的一种欲望,让他们在尚且不必要的时候去购买更新一点、更好一点的产品”(20)芬巴尔·利夫西:《后全球化时代: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王吉美、房博博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48-150页。。不断扩大的生产借助消费主义产生的过度消费,形成了一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体系中,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承载力的下降,严重破坏着人与自然应有的和谐共生关系。
虽然中国目前还尚未完全进入消费社会,但是消费领域的浪费及其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触目惊心。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7中国快递领域绿色包装发展现状及趋势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达312.8亿件,共消耗约32亿条编织袋、68亿个塑料袋、37亿个包装箱以及3.3亿卷胶带。光是一年消耗的快递包装盒所需的瓦楞纸箱原纸就多达4600万吨,相当于消耗了7200万棵树。(2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快递包裹的“过度包装”,消费者并不喜欢》,2018年5月13日,http://www.cbcgdf.org/NewsShow/4854/5180.html,2020年5月21日访问。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市场项目主任金钟浩在《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2018》中指出,2015年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总量为1700万~1800万吨,相当于河北省同年粮食产量(3363.8万吨)的一半。(22)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2018》,2018年,https://www.docin.com/p-2100530955.html,2020年5月21日访问。食物的浪费不仅仅意味着食物浪费本身,更意味着资源的无效消耗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
三、美好生活与消费主义的超越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今天,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消费主义同时在场又相互背离。面对这一悖论性的问题,超越消费主义已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考量。学界就如何超越消费主义这一问题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和探讨。其中,占据主流的是批判性视角。这类研究通过对消费主义批判,提出了禁欲式的节俭性消费或适度消费作为超越路径。但这种超越的路径因为自身的局限,无法对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有效的回应,严重影响了消费主义批判的针对性和超越的有效性。正因如此,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成为另外一些学者批判的对象,并被视为对消费主义的“过敏症”。他们强调以价值中立的立场看待消费主义,将其视为市场经济的一个正常产物,进而为消费主义“正名”。(23)参见王宁:《从 “苦行者”社会到 “消费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吴金海:《对消费主义的“过敏症”:中国消费社会研究中的一个瓶颈》,《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吴金海:《面向社会责任消费:消费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及其反思》,《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而这些观点又对消费主义的危害性选择了忽视,从而滑落到另一个极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一种目标,成为判断和衡量消费主义的重要尺度。我们需要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对消费主义的超越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美好生活需要与消费主义边界的确定
消费主义边界的确定是探讨如何超越消费主义的前提。基于消费主义追求欲望满足的本质特征,一些学者将其界定在超越生活的正常(真实)需要而追求欲望满足这一范畴,进而通过倡导“适度”消费的理念来超越消费主义。然而,在消费实践中,只有人们最低的生存需要(温饱层次)是相对确定的。在美好生活需要的视域下,“对物质文化更高要求”意味着我们不能将物质消费仅仅停留于满足基本生存的层面,还需要有一定“质”和一定“量”的消费。那么,在基本生活需要得以满足的基础上,消费多少算适度?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消费能力和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一,在消费实践中也不可能一致。因此,我们难以在正常需要和欲望之间进行统一的明确划分。所谓的“适度”也成了一个“美好但不具实践性”的概念。为此,一些学者从符号消费的视角出发,将消费主义框定在对商品符号意义的追求而非使用价值的满足。(24)黄平:《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代序)》,见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但事实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是并存的,高档汽车不仅有高的符号价值,在汽车性能和舒适度的使用价值层面也高于普通汽车。在消费实践中,我们也无法从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的二分中划定消费主义的边界。
基于以上考量,国内学者郑红娥从个人、社会、生态三个层面对消费主义的边界进行了卓有意义的界定。其中,从个人层面看,只有当个人超出了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甚至压抑基本生存需要而去追求高档、奢侈性消费时,才能称得上是消费主义。(25)郑红娥:《社会转型与消费革命:中国城市消费观念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89-291页。在实践层面,消费主义落实在个人消费行为之上,个人在消费时无法预估自身的消费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因此,为使消费主义的超越更具针对性,笔者倾向于将消费主义框定在个人消费范畴。郑红娥从个人消费能力出发,对消费主义的实践进行了界别,保障了人们消费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规避了符号价值与使用价值、过度消费与适度消费之间的模糊性。然而,这一界定却忽视了消费主义在“量”上的问题。因为,如果仅仅从消费能力上作出限定,那么只要在自己的消费能力承受范围内,消费再多都是正当的。值得注意的是,沉溺于消费过程的快感而导致对商品量上的过度占有,进而产生的浪费是消费主义造成人与环境紧张的根源。综合以上考量,我们将消费主义的边界划定在以下范围: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超出个人消费能力追求奢侈性消费和为了享受消费过程的心理满足感而造成的浪费性消费。此外,为了明确正常需要与过度占有的边界,我们将浪费性消费框定在“购买但不使用”的范畴。
(二)美好生活需要与节俭型消费的扬弃
消费主义带来了炫耀性消费、攀比性消费、浪费性消费等消费乱象。为了规避这些乱象,结合我国长期以来黜奢崇俭的文化传统,一些学者试图回归这一传统,以禁欲式的节俭性消费文化来超越消费主义(26)郑红娥:《中国的消费主义及其超越》,《学术论坛》2005年第11期;石元波:《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现实困惑与超越》,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我国古代黜奢崇俭的传统,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俭性消费文化,都是建立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之上。在产能过剩的时代,节俭性消费忽视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经济的增长是维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保障。与此同时,节俭性消费也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高要求的物质文化”相冲突。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内投资过剩和国外市场萎缩的现实难题,经济发展已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维持在50%以上,其中2015年高达69%,2019年为57.8%(27)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20A&sj=2019,2020年5月21日访问。。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却并不高,2017年仅有38.7%,而世界平均水平在60%以上。(28)国家统计局:《2019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要积极建立“消费型社会”(29)莫少群:《消费型社会:历史逻辑与现实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义在经济发展上具有完全的正当性。首先,在人们的正常需求满足之后,我们没有理由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要求人们再浪费一些,这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其次,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过度性消费抑或浪费性消费,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承载力的下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消费主义也会侵蚀社会的公平性进而与共享理念相抵牾(30)田月荣,赵玲:《论共享理念与消费主义的矛盾及化解之道》,《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这与当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发展理念相违背。
为此,我们需要在否定消费主义和节俭性消费的基础上,倡导一种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观。这种高品质生活,需要培养人们更高的审美情趣,积极进取的个人发展观,以及健康而丰富的兴趣爱好。在此基础上,在物质文化消费领域,鼓励人们在消费能力范围内杜绝浪费性消费,追求更高品质的物质文化消费。同时引导人们从当前过于集中的物质消费领域抽离出来,扩大人们在继续教育、知识付费等领域的发展型消费,以及兴趣爱好领域的消费支出。这种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观,建立在人们对于人生意义和幸福观念的自主性认知的基础之上,消费只是满足自我对生活向往的手段,而非以消费来界定自己向往的生活。它不仅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匹配(31)近些年来,我国在经济领域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代替低端产品,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更好地推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可以有效地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同时也符合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体现。
(三)美好生活与商品符号的建构
商品的符号化是导致炫耀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的根源,符号是隐藏在物的背后对人进行控制的隐蔽力量,是造成消费主义与美好生活相背离的重要因素。突破商品符号的控制,是超越消费主义的关键。为此,一些研究者提出要通过商品去符号化,破解符号对人的控制,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去符号化”都不可能实现。
人在本质上是具有精神需要的社会性存在,符号是人与人交往互动的媒介,体现为主体间性。因此,符号在人类的生活世界中无所不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无论如何,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生活世界的核心结构自身依靠的是相应的再生产过程,反之,再生产过程也是因为有了交往行为的贡献才‘成为可能’。”(3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87页。消费不只是简单的生理满足过程,它还是一个社会化或者说文化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符号是不可或缺的媒介,商品的符号化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作为商品的物与符号意义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而是通过编码人为建构而成。这就意味着,在消费主义之中,商品的符号化存在着解构和重构的可能。
在美好生活的视域下,要突破消费主义符号系统构筑的文化结构,重构商品符号价值和文化意义,首先需要社会责任(社会伦理)的关照。消费行为表面上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行为,具有深刻的公共属性。正如,一个社会中部分人的过度消费造成的资源紧张和环境压力,使得其他人也必须共同承担。学术界对社会责任消费的理解从最初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关注,扩展到了“环境意识消费”和“社会意识消费”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暗合了美好生活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实追求,为消费的文化意义和商品符号价值的建构确定了两个基本的伦理框架。这种应然性的价值追寻是抵抗或消解消费主义背后资本逻辑下商品符号价值体系的伦理基础。近年来,一些消费群体对真皮制品的抵制和“光盘行动”的倡导,正是对高档皮具奢侈性和浪费性点菜“面子符号”的解构,同时也是绿色理念在商品符号意义建构中的有效实践。
其次,要充分保障人的个性。美好生活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导向,这意味着美好生活内含了对人个性发展的尊重。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日益多元。美国学者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审美已经覆盖到日常生活之中。(33)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 年,第95—105页。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在生活审美上的个性化扩张,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下的集体共律,在各类消费行为之中得以彰显,消费是彰显个性的重要手段,商品是个性化审美的重要载体。在现代消费社会中,资本联合媒体借助于商品符号意义的建构定义了个性和流行。人们看似自由的个性化表达,被隐秘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控制。然而,人们在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中,应该是先有个性化的自觉,再赋予物以意义来承载自己的个性,是“人定义物”,而非“物定义人”。人要从符号的异化中寻求解脱,必须保有强大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突破“单面人”的异化窠臼,在消费活动中确立自我的主体性意识。只有这样,人才能最终逃离商品符号的控制,在消费中占据主体性地位,将消费作为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将商品的符号作为个人表达人生态度、审美取向、价值追求的备选项,而非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