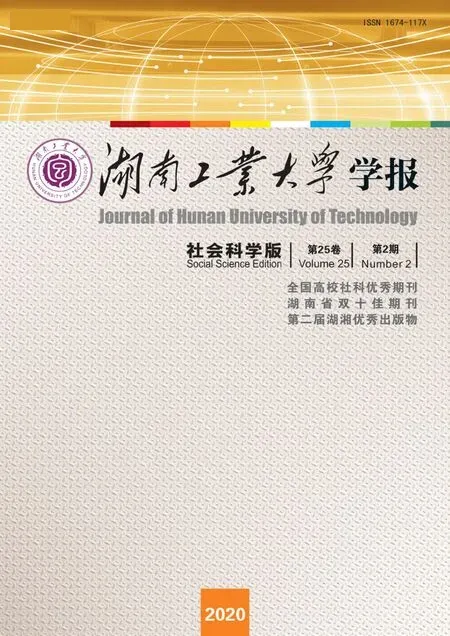从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立场转变及原因
刘 超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国际主义立场长期被看作中国共产党文艺思 想合理性的重要支点。近些年,随着国人学术视野的扩展,国际主义立场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民族主义立场也不再被否定。去掉先在的固化判断,重新回顾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可以发现其发生了非常微妙的转向,从国际主义曲折转向了民族主义。
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与呼应“五四”的传统,将西方文艺作品与创作思潮看作是新文学效法的榜样、改造国民人格的利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思想融合在一起,被引入国内,其合理性依托于西方思想整体的优越,具有明显的世界主义或者说国际主义倾向。陈独秀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该采用共产主义的主张:阶级斗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1]李大钊也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视角看俄国革命,认为“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2]。瞿秋白在谈苏联文艺的时候,说到:“国际一切第一流的文学至少也表同情于无产阶级。”[3]国际认同是无产阶级文学具有合理性的前提。
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态度非常暧昧。大体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思想近于五四主流的国际主义立场。当时,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保皇派推崇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以其规模和深度,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拱心石。”[4]高举反封建旗帜的共产党自然排斥民族主义。不过基于国共合作的事实,共产党人又理应接纳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想,于是他们作出了有条件、有保留的妥协,如邓中夏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在这变相殖民地的中国适用而且必要的”[5],恽代英也说过国民党“是讲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他的成功,总可以有利于一般农工阶级”[6]。不过在共产党人看来,阶级对立是更为基础的矛盾,中共中央的通告中一度要求共产党员宣传三民主义的时候要多举事实,以说明离开阶级斗争就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最终实现民族独立。
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压制共产党,但共产党在文化思想,特别在文艺思想的传播、文艺实践与论战上却出人意料地活跃,一定程度上对国民党形成了压制。此时共产党文艺思想彻底告别之前的暧昧与妥协,坚定地站在了国际主义一边。1927年,太阳社成立于上海,成员多是共产党员。相较于创造社,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更加密切。创造社的主力是从日本归国的爱国学生——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太阳社成员也有类似的留学背景,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夏衍、林伯修、殷夫、冯宪章等,多留学于苏联或日本。鲁迅、创造社、太阳社围绕“革命文学”的论争,背后既有日本福本主义的影子,也有苏联文艺论战的痕迹。太阳社排斥“同路人”鲁迅的态度,正是受苏联“岗位派”影响。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小说创作,也吸取了经由日本人藏原惟人转介的新写实主义思想。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到后附的《行动总纲领》,再到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讲话,均围绕着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展开。阶级论正是区别于普遍人性论的、左翼的国际主义立论基础。后续鲁迅与梁实秋论战,鲁迅不断强调的正是文学中普遍存在阶级性的观点,“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7]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左联被吸收为联盟支部,主导联盟的“拉普”派文学观成为左联的指导思想,其国际主义立场进一步被强化。
总之,1921到1930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与“五四”新文学运动逐渐分道扬镳,形成自己特色、站稳自身立场的时期。如果说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学思想还较为含混,那么在1927年太阳社成立、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与1930年左联成立这一系列的事件中,作为个体的文学批评家已凝结成了具有统一思想的群体,有组织地共同发声,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特征与国际主义立场也清晰展示在了世人面前。
二
提出挑战—立场转换—理论建构—文艺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由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四个步骤。1930—1934年,左联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论战,是提出挑战时期;1935—1936年,从“八一宣言”到左联解体,是立场转换时期;1938—1942年,则是最后的理论建构时期。在建构的同时,文艺实践也并行展开。
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党因左翼文学运动的挑战同样意识到要提出自己的文艺思想,树立文化旗帜。这样,后续就有了1928年的三民主义文学主张、1930年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1932年的通俗文艺运动、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核心纲领,民族主义作为重要的线索,或明或暗贯穿于国民党的文艺思想之中。1930年朱应鹏、范争波、陈抱一、傅彦长、叶秋原、潘公展、王道源、向培良等文人集会于上海,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组建了“前锋社”。在前锋社的引领下,民族主义文艺从理论到创作,一度声势非常浩大。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左联干将与前锋社的国民党文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民族主义问题变得不容回避,国际主义倾向的阶级论与民族主义的矛盾日渐突出。从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民族主义更是作为一个时代性的全民性的问题,被放在了共产党面前。
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至革命根据地瑞金。1934年,党中央跟随红军开始长征。一方面,位于上海的左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变得困难;另一方面,其受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思想影响。面对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左联人士的反应僵化又拧巴,甚至孤立了自己。例如1931年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于中国无产文学的决议案》要求左联“加紧反民族主义文学及对胡适派及其他各种文学上反动思想的斗争”[8]。于是在与国民党文人就民族主义问题论战的同时,左联又与胡秋原、苏汶等中立的文人展开了论争。作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在《阿狗文艺论》一文中反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嘲讽其用一种中心意识形态独裁文坛,实际是奴才奉命执笔。显然,左联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就政策的转向而言,从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多少有些突然。1935年,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精神,中共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而早在一年前,周扬发表的《“国防文学”》已经强调民族危机迫在眼前,呼吁创作“国防文学”作品。1936年春季,左联匆忙解散,引起了鲁迅的不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9]随后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文协”取代了左联,强调“文艺上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10]。共产党的文艺思想明确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基于联合抗战的立场,1938年3月于武汉国共两党又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还是透露出了共产党文艺思想转向的混乱仓促,以及内在指导思想的缺失。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主要建构者。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接替张闻天,确立了自己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他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以官方正式文件的方式,肯定了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1],也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系性、纲领性文件。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转向才有了核心的指导思想。此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是《新民主主义论》在文艺方面的深化。
在共产党建构民族理论的同时,在对抗战初期文学创作进行反思的背景下,1938年于延安发起了“民族形式”问题大讨论。这一讨论正是毛泽东民族理论向文学领域的延伸。其不仅影响广泛,在地域上走出延安,扩展到了重庆、香港、桂林等国民党控制区。在讨论中,共产党与国民党民族理论的差异也凸显出来。最为重要的是,民族形式讨论向上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通俗文艺运动”没有解决的“普及与提高”“现代化与民族化”等问题。在大讨论的基础上,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既是民族形式讨论的总结,也是讨论的深化。在《讲话》的影响下,产生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一批新式通俗小说,也产生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较为严肃的经典文学作品。
三
20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交织在一起,有自己的特色,旗帜却并不鲜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文艺问题、制定文艺思想。当国民党与保守文人转向民族主义的时候,共产党的文艺思想扎根在了国际主义的立场之上。1930至1942年,共产党的文艺立场由国际主义转变为了民族主义,具体则经历了1930—1936年的挑战期、1936—1938年的转变期、1938—1942年的理论建构与文学实践期。这种转变是在一种张力中发生的,有着复杂的多层次的原因。首先,完成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诉求是间接却根本的原因;其次,共产党走出“左倾”思想,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的积极尝试,则是转变的内在与直接动因;最后,回应国民党民族主义倾向文艺思想的挑战,这是转变的外在契机与原因。
完成现代性与建立民族国家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来的诉求,从政治运动到文学思潮转变,均受限且服务于这一大的时代主题。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最早奉行的是政治改良主义。国家尚存,现代化的优先级大于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剧,特别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果实在帝国主义的干预下被北洋军阀篡夺,至最终军阀割据,中国与欧美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民族自决独立这一主题就超越现代化,成为了时代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民族问题与现代性问题均会出现分离与脱节的情况,19世纪欧洲的希腊、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等国均是如此。离开了民族独立,现代性任务是很难完成的。正如余英时所言:“一切与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现代化运动,其最终的成就都是没有保障的。”[12]李泽厚所言救亡压倒启蒙,实质也是民族主义压倒了现代性。
从1919年五四青年“火烧赵家楼”到1929年“中东路事件”,再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人的爱国情绪与民族情结不断加强。其间,前锋社的国民党文人提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口号,不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是前锋社的理论纲领,其认为当前的中国文艺界是畸形和病态的,一是“有人在保持残余的封建思想”,一是“那自命左翼的所谓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因存在这两个极端,新文艺上甚少成就。想要突破僵局,必须找到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民族主义。“文艺底最高的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一句说: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13]文艺活动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尽管1931年前锋社即解散了,前锋社创办且风行一时的《前锋月刊》《前锋周报》《现代文学评论》纷纷停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国民党刊物《黄钟》却发行到抗战前期,作为前锋社重要盟友的《当代文艺》也是1944年才停刊。不过,前锋社解体之后的民族主义刊物,立场更加柔和,党派性质淡化。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可见民族主义已经深入人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左联迅速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控诉“被毁灭的中国民众,已经不止十万二十万。……甚至于小孩子妇女,都受到空前的残暴的凌辱和残酷的宰割”[14]。抗日本身就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可惜阶级论与保卫苏联的倾向,削弱了控诉的力度。同时,20世纪30年代很多左翼作家虽不明确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但内在的民族倾向与民族认同非常明显。如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小说,其中对特定地域及土地的眷恋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依恋于一片神圣的领土,即依恋被圣贤们、英雄们和哲人们神圣化,也被祖先的陵墓和纪念碑所神圣化的先辈领土。”[15]这正是民族认同形成的基础。郭沫若《堂棣之花》《屈原》等具有寻根倾向的作品,茅盾《子夜》《林家铺子》对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失败的感叹,也可一定程度上归为民族主义文学的范畴。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16]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面对的这种外在压力是逐渐加大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3年喜峰口战役、1935年“何梅协定”与“一二九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从1931年到1937年,战争的阴影与灭国的恐惧直接笼罩在华夏大地之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达到了高潮。在这种煌煌大势中,经历了长征浴火重生的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影响,迅速转向了救亡与抗日,文艺思想自然也无例外地融入民族主义的主流。
四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清算“左倾”错误之前,“左倾”思想一直主导着共产党的文艺思想。1934年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出现了1927年瞿秋白盲动主义、1930年李立三冒险主义、1931年王明的教条主义三次重大的“左倾”错误。内部纠正“左倾”错误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现实,这是其文艺思想由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内在原因。此时,“左倾”主义思想在多个方面一度成为转向的阻碍,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是将阶级论放到了民族主义的绝对对立面,彻底否定了两者融合的可能性。基于“反帝”与建立民族国家的共识,共产党与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在大革命中即合作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此时,在共产党的认知中,国民党沦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国共的政党对立,变成了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受境外帝国主义掌控的资产阶级的对立。但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是非常复杂的,更为重要且不能否定的是,作为受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代表着中华民族。因此,共产党基于阶级论反对国民党的同时,难免也连带否定了民众合理的民族主义诉求。
第二是制定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路线与口号。如1929年中东路事件之后提出的“保卫苏联”的政策与口号,严重影响了鲁迅、茅盾等人的文学批评立场与方向。1934年鲁迅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17]因党派政见而迁怒民族主义本就是对民族主义的狭隘化,基于党派路线而置国土沦陷而不顾,更是将自己放到了自己民族的对立面。实际上,在鲁迅这里,一方面要支持共产国际与左联的文艺思想,一方面也常常流露出对民族国家的焦虑,情感纠结且拧巴。1935年鲁迅推崇并亲自作序出版的萧军《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生死场》,即有抗日救亡与民族寻根内容,二者都完全可以是看作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国民党文人也就此大做文章,讽刺左联文人“受了苏俄的卢布的津贴,就甘心做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工具,鼓吹在中国不能运动的阶级斗争,和杀人放火的暴动,而来破坏中国三民主义的革命”[18]。
第三是关门主义的问题。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如日中天的时候,不仅左翼批评家,中立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也对其展开了批驳。1931年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正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文章。胡秋原的核心观点实际是维护文学艺术的自由与独立,认为将艺术堕落到政治的留声机,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当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均存在将文艺工具化的倾向。胡秋原虽否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却也同时触到了左翼文人的痛点。随后左联与胡秋原、苏汶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到创作实践,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关门主义的负面影响,还不在论战本身,而在固执己念,不去正视论战引出的一系列己方的问题。如苏汶强调:“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种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更重要的是,这政治目的要出于作者自身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出于指导大纲。”[19]实际切中了左翼文学的弊病,也提出了政治如何影响文学这一重要问题。1932年胡秋原的《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更是指出了左翼文人在接受与理解马克思主义时的误用问题。这些问题都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左翼作家与批评家如果认真对待、虚心接受批评,能够妥善又及时地弥补自身的诸多缺陷。可惜激进的斗争氛围,灭杀了此种可能性。
追溯“左倾”思想的成因,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其盲从共产国际的指导、迷信苏联经验,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特别是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融合在一起。自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在《共产主义之人间化》(1922年)、《现代民族问题讲案》(1926年)中系统介绍翻译列宁的民族理论后,中国共产党即基于僵化的国际主义立场解决民族问题。1930年,毛泽东谈到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正确问题,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20]可惜这种观点直到毛泽东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才成为主流。
总而言之,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有理论资源协调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二,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期,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的重要性;第三,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操。一方面在“左倾”思想的控制下,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不断受挫,一方面党内已有了对左倾的反对声音,这两方面的合力在恰当的时机下,最终克服了“左倾”思想,为文艺思想转向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
五
共产党文艺思想的转变是在民族主义的时代诉求中发生的,也是在与敌对的国民党文艺思想的对抗中发生的;特别是1930年开始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直接引发共产党文艺思想转变的重要外因。1929年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会议,其迫于左翼革命文学的压力,推出了三民主义文学主张。三民主义文学没有形成影响力,随后才有了1930年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实际上,国民党文艺思想给了共产党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表面上表现为出版限制、禁书、迫害左翼作家与批评家,内在则是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曹聚仁认为:“在所谓民族主义文艺之下,既无作家,也无文艺理论。比较有分量的几位作家,如胡适、梁实秋、黎烈文,都是自由主义文人,和国民党不相干。”[21]当前有学者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倡导者在理论基础、社会意义、题材内涵、艺术表现与文学批评诸方面多有探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不仅有主张,有队伍,有阵地,而且推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作品。”[22]从现有的资料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几个方面的事实的确不容回避。第一,这是一场吸引了大量作家与批评家的文艺运动。一方面正如曹聚仁所言,胡适、梁实秋、黎烈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民族主义的讨论;一方面左联文人叶灵凤、周毓英,因参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被左联除名。第二,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如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万国安的《国门之战》。第三,民族主义运动资源丰富,其间,有关方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申报》副刊等报纸期刊,还汇聚了几十种其它刊物共同造势,如《黄钟》《草野周刊》《长风》《文艺月刊》《民族文艺》《当代文艺》等等。第四,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与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形成了呼应,得到了全民族的支持与相应。《前锋月刊》的流行,民族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的流行,都能证明此点。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产生的声势与影响力,给左翼文艺思想提出了巨大挑战,于是瞿秋白、鲁迅、茅盾等左联干将,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反驳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党派色彩浓厚,一些国民党文人想借运动来铲除文坛异己、统一文化思想,这是事实;但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有着复杂的一面,因为参与运动的有国民党内的文化官员,也有较为纯粹的大学教授以及热血激情的青年学生。正是因为后两种人的加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才在主导运动的激进国民党官员离职之后继续发展下去;而左翼显然没有将他们进行区分,甚至连中立的胡秋原、苏汶也一并进行了批判。
更重要的是,左联的批判文章将符合民意的民族主义作品与国民党官方独裁的狭隘民族主义理论糅合在了一起。以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代表作家黄震遐为例。前锋社力捧,国民党官方背书,不等于黄震遐在创作上就唯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一是史实,一是现实,这两个方面在黄震遐的创作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黄震遐的修辞试图弥合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裂隙,然而那样的裂隙是很难有效弥合的,于是意识形态与现实的裂隙便成为其文本叙述本身的裂隙”[23]。囿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左联对黄震遐作品的批评没有切中肯綮。如茅盾的《〈黄人之血〉及其它》,认为黄震遐《黄人之血》写的西征就是进攻苏联,而且还暗示了“古代黄色人种联合起来西征俄罗斯,现在黄色人种为什么不联合呢?在进攻苏联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应该联盟,而且不妨像宋大西受蒙古军官的指挥似的去受日本人的指挥”[24]。对比小说文本,茅盾的批评其实很牵强的,其论多是基于主观猜测。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明确强调:“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也不是某一主义的极端倾向者,一切都跟着历史走,书里才敢说出大胆的话。”[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于国民党的文艺思想大陆学者关注的较少。一些学者严重低估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影响力以及其对左翼文学的压力。无视敌人的强大也会降低斗争的难度与胜利的可贵,就共产党文艺思想的民族主义转向而言,则缺少了必要的环节。大的时代语境要落到实处,形成一个公共的民族主义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内外因才能够结合。
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以及历史潮流是契合的。转向民族主义之后,围绕中国作风与民族形式,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艺术尝试,并通过这些尝试创造了新的作品,引领了新的社会文化,也极大地调动与团结了民众。虽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此时并不了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但却在一系列的艺术与文化实践中,在各种文艺论战中,敏感意识到了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而民族主义转向正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与关键步骤。转向之后的基于民族主义的新理论建构必然要面对各样的现实与理论挑战,毛泽东的“讲话”体系正是在民族主义转向背景下,对各种挑战的回应,其影响了此后中国几十年的文艺理论建构。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