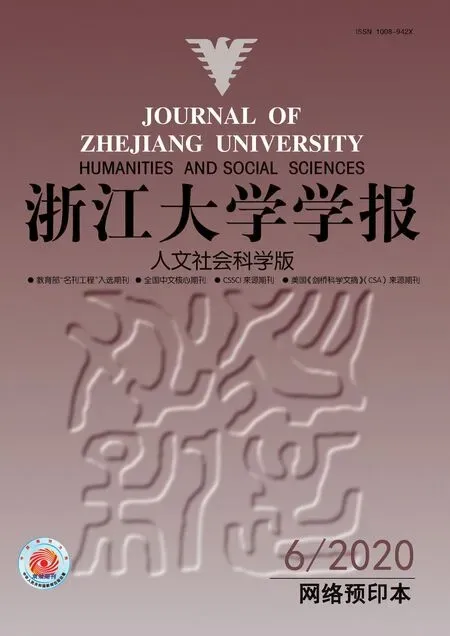1811年日朝外交中的交流机制与文化主导权争夺
王连旺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16世纪末爆发的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以及17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致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受到重大冲击,日本因而产生“华夷变态”的思想,朝鲜则以“小中华”自居。自1607年至1811年,李氏朝鲜共派遣12批通信使访问日本,开启了日朝两国间延绵两个世纪之久的对等外交关系。日朝之间虽然语言不通,但双方的知识分子阶层均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文笔谈遂成为双方交流的主要方式,并为后世留下约170种外交笔谈记录。其中部分笔谈文献于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历史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在这12批次的日朝通信使外交过程中,朝鲜使节与日本儒官、文士、僧人等围绕中国文化展开了长期的交流。葛兆光将这一时期的日朝交流称为“文化间的比赛”[1]32,朝鲜长期占据优势;张伯伟认为1764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酬笔谈活动,是东亚汉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朝鲜使节由此对日本有了全新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日本则对朝鲜诗文流露出贬抑之情[2]131。但至1811年,日本的整体文化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克服文化自卑感的思潮,并将此上升到了维护国体尊严的高度。所以,1811年朝鲜通信使访日,恰好为展示日朝间的文化主导权争夺提供了一个舞台。本文利用1811年产生的8种日朝外交笔谈资料,以及相关“行使录”文献,在复原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士文化交流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审视这个日朝“文化间的比赛”的拐点,并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日朝两国的政治意图及其历史影响。
一、 “易地聘礼”与1811年日朝外交史料
日本天明七年(1787)五月,江户幕府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1773—1841)继位之际,连年饥荒导致民怨沸腾,暴动频发。按照惯例,新将军袭位之后的两三年内,朝鲜应派遣通信使团前往祝贺。但在财政困难的形势下,德川幕府已无力承担巨额的接待费用。于是,日方先是不断向朝方提出“延期聘礼”,后来又提出在距离釜山较近的对马藩举行“聘礼”。但朝方认为,如此一来,不仅改变了在江户(东京)向幕府将军递交国书、交换国礼的旧例,还降低了接待规格,难以接受。双方僵持不下,反复交涉长达20余年,才促成日朝最后一次通信使外交。1811年三月到六月间,日朝双方外交人员在对马藩会晤,这便是有名的“易地聘礼”。朝鲜通信使团由正使吏曹参议金履乔、副使弘文馆典翰李勉求等336人组成,人数上比以往的近500人有较大幅度的缩减。使团于三月二十九日抵达对马岛,六月二十七日返程,在日访问近三个月。
1811年以前的朝鲜通信使团仅在对马岛短暂停留,然后经由马关进入濑户内海,途经鞆之浦、牛窗、兵库等港口抵达大阪,然后在大阪淀川河口换乘幕府及西国大名为其准备的“川御座船”,行进至淀(今京都府伏见区)改行陆路,近500人的使团,再加上对马藩约1 500人的向导、护卫人员,浩浩荡荡向江户行进。至江户后,入住位于浅草的东本愿寺,然后在大广间向幕府将军递交国书和礼品,得到幕府将军的返翰和别幅(回礼)后,启程返回朝鲜。
从对马岛至江户的数千里往返过程中,朝鲜通信使团中有人专门记录所见所闻,留下了众多的纪行类资料。而沿途的日本文士在通信使团经过其地时,会蜂拥而至,求书索画,笔谈唱酬,还有人将自己的诗文集或书画作品送给朝鲜使节,求序跋,邀品评,若能得到朝鲜使节的高度评价,便会在日本声名鹊起,一夕成名。
但1811年的“易地聘礼”却不同以往。由于改为在距离朝鲜较近的对马岛举行聘礼,朝鲜使节于三月二十九日抵达对马岛后,行程便基本完结,使节们也就无法像以往那样观察对马岛以东沿途的地理人文、社会风俗等情况,因此纪行类的记录也在对马岛戛然而止。如正使金履乔《辛未通信日录》[3]第八卷,110-177的记录时间起自李氏朝鲜纯祖九年(1809)八月,主要记录朝鲜组团出访的始末,抄录了各类文书档案,而到对马岛之后的记录则甚为简略;军官柳相弼《东槎录》虽然比《辛未通信日录》的记录详尽一些,但记事也失之于简:“(六月)二十一日,阴,早朝江户林太学头率弟子三四人,以私礼入谒,两使与诸文士移时笔谈;(六月)二十二日,朝阴,暮雨。”[4]第5册,317实际上,六月二十一日的笔谈者是日本派出的官方最高级别的文化交流团,参与的人有多少,交谈的内容是什么,《东槎录》都没有提及。六月二十二日,大学头林述斋派其弟子松崎慊堂再赴客馆笔谈,但《东槎录》只记录了当天的天气,对松崎来访一事只字未提。正使书记金善臣也著有一本日记,名为《清山岛游录》,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该书主要收录朝鲜使节与日本文士的诗文往来,没有收录笔谈内容。
“易地聘礼”同时也给日本提出了新的课题。以往幕府将军均在江户接见朝鲜使节,交换国书,举办飨宴,而让德川家齐远赴对马岛接见朝方使团是极不现实的。所以,日方任命小仓藩主小笠原忠固为正使、龙野藩主胁坂安董为副使,随员有大学头林述斋、松崎慊堂、古贺精里、草场佩川(“佩川”亦作“珮川”)、樋口淄川、冈本花亭等人。从成员所担负的职能看,正副使负责完成外交任务,代表幕府将军交换国书和别幅,并主持飨宴。而以林大学头为首的儒官、学者、文士则负责文化交流,这也是日朝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官方派遣的成员外,以酊庵的五山僧以及少数日本地方文士也与朝鲜使节有过笔谈交流,留下了8种55件笔谈文献。这些资料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日朝双方的交流实态,而且可以大大弥补朝方纪行类记录的不足,价值极高。这些笔谈文献具体如下:
(一) 对马藩以酊庵轮番僧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资料
以酊庵是协助对马大名宗义调从事对朝外交事务的五山僧景辙玄苏(1537—1611)在对马藩建立的寺院。享保十七年(1732),大殿毁于火灾后,又移至西山寺瑞泉院。宽永十二年(1635)的“柳川一件”之后,江户幕府从京都五山中选拔硕学之僧轮番驻扎,任命其为“朝鲜修文职”,专门从事起草对朝外交文书、监督日朝贸易等工作,此即以酊庵轮番制。1811年朝鲜通信使在对马岛最先接触到可以笔谈酬唱的,便是以酊庵的轮番僧,现存笔谈资料有以下3种计4件:《朝鲜人诗赋》《辛未和韩酬唱录》各1件,二者同书异名,均藏于日本蓬左文库;贴有朝鲜通信使相关诗笺的屏风1件,现藏香川县观音寺市兴昌寺;《辛未马岛唱和》1件,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鹗轩文库。
(二) 江户儒官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资料
自林罗山起,林家世代作为幕府官方最高文化代表参与对朝外交事务,并与朝鲜使节笔谈交流,本次亦不例外。大学头林述斋被幕府指派赴对马藩接待朝鲜使节,任务便是与朝鲜使节进行文化交流。林述斋率领的文化交流团于1811年闰二月二十八日出发,于五月二日抵达对马藩。林述斋一行由三组成员构成:第一组为林述斋及其弟子松崎慊堂,他们于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与朝鲜使节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笔谈与“笔战”;第二组为古贺精里及其门生草场佩川、樋口淄川等人于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草场一人)参与了与朝鲜使节的笔谈,内容多探讨学术文章,并有诗歌酬唱;第三组为画员冈本花亭等人,画员被禁止直接与朝鲜使节接触,所以冈本花亭与朝鲜使节的笔谈酬唱是通过古贺精里传达的。
江户儒官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资料有3种计49件:松崎慊堂《接鲜纪事·接鲜瘖语》,该本有松崎慊堂亲笔书写的草稿本、清稿本、精抄本及后世传抄本、活字印本,计有34件;古贺精里、草场佩川、樋口淄川《对礼余藻》,该本有古贺侗庵整理本、草场佩川校订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草场佩川自笔抄本等13种写本;冈本花亭、古贺精里《享余一脔》《精里笔谈》各1件,二者同书异名。
(三) 民间文士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资料
对马岛虽然远处日本边陲,但依然未能阻挡民间文士的交流热情。根据现存资料可知,远赴对马岛的有江户画家二代喜多川歌磨、京都篆刻家源方启、京都儒士三宅威、江户文人四十宫淳行和千叶平格等人。现存笔谈资料有2种:《鸡林情盟》1件,1812年刊本;《唱酬笔语并诗稿》1件,现藏佐贺大学图书馆小城锅岛文库。
除了上述笔谈文献外,由于江户儒官及日方正副使随员均需长途跋涉至对马岛接待朝鲜通信使,漫长的路程与沿途的见闻促成了日方纪行类文献的产生,出现了草场佩川《津岛日记》、樋口淄川《对游日记》、三宅橘园《薄游漫载》以及《小仓藩朝鲜通信使对马易地聘礼记录》等多种日记,对研究此次日朝外交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对这批笔谈文献,李元植《文化年度的笔谈唱和及其遗墨相关资料》[3]第八卷,100-101、高桥昌彦《朝鲜通信使唱和集目录稿》[5]211-291等目录中有所著录,可为整体了解这批资料提供基本指南。但李元植目录存在误收、漏收、重复著录、复本著录不全的情况;高桥昌彦目录则侧重著录刊本、抄本等书册形制的笔谈资料,但也存在复本著录不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 日朝外交中的文化交流机制
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日朝两国在通信使外交机制下,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与日本相比,李氏朝鲜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在礼仪、服饰、儒学、诗文、书法、医学等方面的文化优越感,使其在两国外交中获得了某种平衡,实现了与日本分庭抗礼的对等外交。而日本在与朝鲜长达两个世纪的通信使外交中,却始终面临文化自卑的问题。
江户中晚期,日本汉学研究水平大幅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中井竹山(1730—1804)在《草茅危言》中感慨:“朝鲜终不可以武力施加于我,遂欲以文事来凌驾于我,诚如新筑州之《五事略》所论。因乘我邦学暗之处,欺我无知,道中之卤簿建‘巡视’‘清道’‘令’之旗,无礼之极。”(1)原文为日语,引文系笔者翻译。参见中井竹山《草茅危言》卷二,大阪大学怀德堂藏1796年写本。中井竹山为大阪怀德堂第四代堂主,学识渊博,门生众多,是当时关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儒学家之一。中井竹山提到,朝鲜通信使高举“巡视”“清道”“令”等大旗招摇过市,有失礼制。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失礼”,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在文化交流方面。由于日本长期在文化方面处于劣势,所以每次朝鲜使节来访,日本官民争相求见,求和诗、讨书画、问序跋、邀品评,让朝鲜通信使疲于奔命,在获得文化优越感的同时,也产生了厌倦情绪。如第9批朝鲜通信使的制述官申维翰(1681—1752)《海游录》中便有这样的记载:“日本人求得我国诗文者,勿论贵贱贤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货之如珠玉,即舁人厮卒不知书者,得朝鲜楷书数字,皆以手攒顶而谢。所谓文士,或不远千里而来待于站馆,一宿之间或费纸数百幅,求诗而不得,则虽半行笔谈,珍感无已。”[4]第3册,365由此可见,朝鲜使节每次访日,都能掀起一股“文化旋风”,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极大的礼遇与尊重。另外,申维翰《海游录》中还记载了掌管幕府文化事业的林家大学头林信笃有过请求朝鲜三使(正使、副使、从事官)笔谈酬唱而被拒绝的情况,且林信笃的文笔被申维翰评价为“拙朴不成样”,还被朝方正使指责“国书未传、使事未了之前,闲漫吟咏,道理未安”[4]第3册,317。
而至江户晚期,日本的国学、汉学、艺术全面发展,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天保八年(1837),太山诚在前述《精里笔谈》的序文中称:“国家兴二百有余年矣。文明之化敷乎海内,英特有名之士起于四方,诸儒自立,各成一家。或诗以名家,或书以名家,或文章以名家,其所见,其所闻,异说纷挐。”(2)参见古贺精里、冈本花亭《精里笔谈》,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1817年太山诚写本,1a。太山诚对1811年日朝外交笔谈文献《精里笔谈》的阅读体会,反映出日本历经两个世纪所积蓄的文化力量足以与朝鲜一较高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1811年江户儒官赴对马岛与朝鲜使节会面,为日方提供了一个证明自我的舞台。以江户儒官林述斋为首的日方文化交流团对参与笔谈的人员进行了内部选拔,对日方正副使随员参与笔谈的资格进行了严格审查,在江户至对马岛的行进过程中加紧“备战”,至对马岛后日朝双方相互获取对方情报,对马藩也对民间人士能否参与与朝鲜使节的笔谈加以审查。这一系列的措施鲜明地呈现出日朝两国外交中的文化交流机制。
(一) 对江户儒官内部参与笔谈人员的选拔
与日本官民进行文化交流是朝鲜通信使访日的重要一环,但最后一批通信使为“易地聘礼”,地理空间的局限性大大限制了朝鲜使节与日本人士的接触机会。对马岛虽有儒士及以酊庵的五山学问僧,但还难以全面体现出日本的文化水准。由此,德川幕府派出大学头林述斋及儒学教授古贺精里作为文化代表,率团赴对马岛与朝鲜使节交流,以此展现出愿意积极与朝鲜进行文化交流的姿态。
大学头相当于我国的国子监祭酒,是一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古贺精里是“宽政三博士”之一,精于朱子学,长于诗文,赴对马岛时62岁,正是学问老成之时。此次赴对马岛,林述斋率领的弟子有松崎慊堂等数人,古贺精里率领的弟子有草场佩川、樋口淄川等八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林述斋对此次参与与朝鲜使节交流的人员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筛选,并非人人皆可与之笔谈酬唱。樋口淄川《对游日记》三月三日条记载:“先是每韩人来,其途所由,苟少有文词者以得其片言只字为荣,必就求唱和,彼厌倦敖惰,我苦请而得。或村学究、新近书生妄言不讳开争端者,间亦有之,实欠国体,为不鲜矣。以是,是行祭酒、博士之外,惟许两家门人两三人笔谈,自余一切禁绝。于是林公以挂川儒官松崎复名上,先生以泰与棣芳名上,故予辈途中每逢文士必唱和,欲以习拙速为它日接韩人之地云。”(3)参见樋口淄川《对游日记》,筑波大学图书馆藏写本,4a。樋口淄川更将文化交流中的“彼厌倦敖惰,我苦请而得”“妄言不讳开争端”的情况上升到了“实欠国体”的高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林述斋对参与笔谈交流的人员进行了严格限制。除林述斋本人及古贺精里外,只有松崎慊堂、泰(樋口淄川)、棣芳(草场佩川)三人入选。
松崎慊堂是林述斋的得意门生,与佐藤一斋齐名,被誉为文政、天保年间的大儒,门生中有安井息轩、盐谷宕阴,其学术支脉对日本近代汉学影响极为深远。他赴对马岛时41岁,正值壮年。草场佩川工诗赋,善书画,通汉语,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珮川诗钞》例言记载:“家君今年六十又三,赋诗率一万五千余首,为二百五十卷。”草场佩川赴对马岛时24岁,是难得一见的青年天才,所著《津岛日记》图文并茂,记事翔实,是研究辛未通信使的重要文献。樋口淄川精于诗文,善写行记,足迹纵贯日本南北,赴对马岛时26岁,其所著《对游日记》用汉文书写,记事尤详。
(二) 对日方正副使随员参与笔谈的资格审查
日方正副使的随行人员中也有儒士数人,他们也期盼能与朝鲜使节笔谈交流,可惜未能达成。如蓬左文库藏《朝鲜人诗赋》《辛未和韩酬唱录》均为日方副使的家臣猪饲正谷于1811年五月写于对州金石客馆的。金石客馆即副使在对马岛的驻所,猪饲正谷之所以誊抄以酊庵僧人与朝鲜使节的笔谈,或许是出于收集情报的任务,但也隐含着其有意与朝鲜使节笔谈交流的愿望。
《津岛日记》五月十二日条中,有草场佩川、樋口淄川否决日方正使随员石川彦岳等人参加与朝鲜使节笔谈申请的记载(4)参见草场佩川《津岛日记》上卷,佐贺大学图书馆藏写本,第30页。。石川彦岳(1745—1815)是小笠原藩的藩校思永馆的第一代学头,此次作为日方正使的随员来到对马岛。五月十二日,他带领次子宗吉、门生塚田武访问古贺精里,草场佩川与樋口淄川接待了他们并与之诗歌酬唱。据石川彦岳讲,其父石川文翰在明和元年(1764)第11批朝鲜通信使访日的前三年,便有与之笔谈“文战”之志,且刻苦准备。但朝鲜使节来日本之时,石川文翰染病咯血,未能成行,含恨而终。所以石川彦岳此次来对马岛,强烈希望能与朝鲜使节“笔战”一番,以实现其父的遗愿。正是因为他的申请充满“复仇”情绪,所以未被通过。还有小笠原藩的某位医师,写了七言律诗二百韵,托草场佩川、樋口淄川代为投赠朝鲜使节,二人读之只觉发困,故未帮忙传送。更有甚者,正使的随行人员中有人作了一首八百韵的长诗请草场佩川、樋口淄川代为投赠朝鲜使节,二人无暇审读,故此诗亦未能投赠。由此可见,日方正副使的随行人员中有多人想与朝鲜使节“笔战”,但这种“虚喝夸诞、炫多斗靡”的恶意竞争行为均未能通过审查。这也说明了日方对此次参与文化交流的人员控制之严格。
(三) 对马藩负责民间文士参与笔谈的资格审查
民间文士与朝鲜使节的交流也不是随意可为的。如上述三宅橘园是通过以酊庵观瑞和尚的周旋,才取得对马藩的同意。《薄游漫载》五月三日条记载:“诣以酊庵,致东福寺即宗院书,谒观瑞和上,嘱韩客唱和之事,即宗院玄道,余同乡旧故,久在东福,余在京十年未尝相值。今春涅槃会余游于彼,不期邂逅,已而余有行色,玄道为余致书于观瑞和上,恳嘱和上大为余周旋,请之藩府,是日雨甚且雷。”[6]卷之三,2a三宅橘园于五月二日抵达对马岛,三日即冒雨持书赴以酊庵拜谒观瑞和尚,请其与对马藩周旋,以取得与朝鲜使节笔谈唱和的资格。由此可见,日方对民间人士与朝鲜使节的接触是有所控制的。
(四) 沿路备战与情报互取
林述斋一行自1811年闰二月二十八日从江户出发,至五月二日抵达对马岛,历时两个月,在此期间拜谒沿途大儒,接待来访文士,探讨学问,酬唱诗歌,完成了一次日本儒学界的内部交流,而这也大有益于他们后来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交流,是交流前的“备战”。前文所引樋口淄川《对游日记》便道出“故予辈途中每逢文士必唱和,欲以习拙速为它日接韩人之地”。
佐贺大学图书馆藏本《津岛日记》的五、六月间,收录了古贺精里制作并名之为《后师录》的“例题集”(5)参见草场佩川《津岛日记》卷上,佐贺大学图书馆藏写本,第78-96页。,前有古贺精里题词:“韩人问答书,上板数十种,而我谈富岳则彼以金刚压之,我问其广袤则以二万里诧之,不殆于儿女迷藏之戏乎?邦儒多堕其窠臼,而白石为甚。余闲中举其语或能惑者,使草场、淄川二生驳之,非敢捃摭前辈,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欲鉴旧辙不复蹈耳。精里识。”(6)参见草场佩川《津岛日记》卷上,佐贺大学图书馆藏写本,第78页。从《后师录》的内容来看,古贺精里从日本已经刊行的日朝笔谈集中选出若干问题,命草场佩川、樋口淄川模拟回答,并一一反驳。这种练习还不止于此,古贺精里之子古贺侗庵所著《侗庵秘籍》中,收录了一篇《拟答朝鲜使节问》,日本学者梅泽秀夫指出,这很有可能是侗庵与父亲精里共同预想的问答内容,或者是侗庵自己想象将来有机会与朝鲜使节交流而预设的问题[7]15。但无论如何,都能说明古贺精里一行通过收集往年的日朝笔谈问答集中的问题来预设问答,模拟训练。
朝鲜通信使于三月二十九日已至对马岛,至林述斋一行抵达,已苦等一月有余。但林述斋一行抵达后并未马上造访客馆与朝鲜使节交流,而是一直等到聘礼结束后的六月二十一日才前往笔谈。实际上,这是林述斋与松崎慊堂商定的“先公后私”计划,如此一来,日方不但在交流中取得主动权,而且为获取朝鲜通信使的情报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对游日记》中便有很多关于探听朝鲜使节虚实、获取其诗文的记载(7)参见樋口淄川《对游日记》,筑波大学图书馆藏写本,22a,22b,23a,23a,24b,26b-27a,27b。:
五月三日,棣芳出问彦岳翁,借以酊庵僧与韩客唱和什来,先生命门人誊写。
五月八日,文乡从丰洲造韩馆夜对,儒官柴田左中持同僚沧浪与韩人唱和诗来示。
五月十二日,文乡、子容从丰洲造韩馆,逢韩人河清一、皮东冈,得东冈诗而归。
五月十四日,子常、公益从丰洲造韩馆。
五月十七日,天寿、文乡从丰洲造韩馆,逢医官金镇。
六月八日,子常、子容从丰洲至韩馆。
六月十三日,玉堂持韩两使答龙潭长老诗及对人所钻灼之龟来。
可知,林述斋、古贺精里的随员中,丰洲、天寿、文乡、子常、子容多次以民间文士的身份造访韩馆,打听虚实。此外,还借抄朝鲜使节与以酊庵僧人的笔谈酬唱,以了解朝鲜使节的诗文水平。《津岛日记》六月二十日条收录了当日林述斋与古贺精里的一组书信,并抄录了与朝鲜使节笔谈的《旧来之官法》(8)参见草场佩川《津岛日记》卷下,佐贺大学图书馆藏写本,25-30a。,可以看出,关于访问韩馆的时间,林述斋、古贺精里有过沟通与协调,并做好了会面前的最后一次准备。
对于林述斋等江户儒官迟迟不来交流,朝鲜使节颇为不满。据《对游日记》六月四日条记载:“铃木文左至,云昨日韩人李显相游清山寺,归途唐突从监官诉曰:‘吾等归期已迫,而未许笔谈,何也?是公等为政不善也。盖对人本不欲使官人与韩人应对,故托言于公事未毕而不许私觌也。’韩人亦知之,故有此事也。”(9)参见樋口淄川《对游日记》,筑波大学图书馆藏写本,26b。铃木文左是对马藩的文士,从韩人李显相与铃木文左的对话可知,朝方认为是对马藩从中作梗,导致江户儒官没有赴韩馆与朝鲜使节笔谈。此外,《唱酬笔语并诗稿》六月十四日千叶平格(号鸡山)与朝鲜使节有以下笔谈(10)参见四十宫淳行、千叶平格《唱酬笔语并诗稿》,佐贺大学图书馆1811年写本,9b-10a。:
韩客:何时齐会笔谈耶?
鸡山:未知在何日。
泊翁:古贺弥助?
鸡山:今在马岛。
泊翁:何处人?
鸡山:江户儒官。
泊翁:与林大学头文章如何?
鸡山:仆等何比之?非平常之人,公推可知耳。
据此笔谈可知,朝鲜使节不仅关心何时能与江户儒官笔谈交流,还探听了古贺精里、林述斋的文章学术。《鸡林情盟》载,六月二十日正使书记金善臣在与三宅橘园(别号威如斋)的笔谈中,更是抱怨日方正副使先于朝鲜使节离开对马岛,而且未能与江户文士笔谈[8]笔语,4b:
清山:江户两使何其忽忽发船也?
威如:七八月间,海洋多飓少晴,故先秋而发耳。
清山:江户文士闻多来此者,而竟失一面,可恨!
威如:彼亦皆怅怅耳!但缘合在天,不可奈何。
就在金善臣发出抱怨的第二天,即六月二十一日,林述斋、古贺精里先后率弟子造访韩馆,双方开始了最高级别的笔谈交流。六月二十二日松崎慊堂再访韩馆;六月二十三日古贺精里、草场佩川、樋口淄川访问韩馆;六月二十四日草场佩川三访韩馆;六月二十六日草场佩川在以酊庵与朝鲜使节笔谈告别。
三、 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及其影响
《对游日记》六月二十一日条记载:“祭酒林公与朝鲜使节笔谈于客馆,令松崎复执笔,朝鲜使节自尊,口授令书记执笔,故林公亦如此云。”(11)参见樋口淄川《对游日记》,筑波大学图书馆藏写本,28b。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林述斋并未挥笔,而是口授,由松崎慊堂代笔。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礼仪对等的考虑,因为朝方正副使也是“口授令书记执笔”。实际上,双方见面的前提不止于此,从松崎慊堂《接鲜纪事》[9]60-66中可知,林述斋与松崎慊堂事先已经做了周密的准备,希望借助这次“易地聘礼”的机会,变革接待朝鲜使节的礼仪,“善者尊焉,弊者革焉”,甚至还提出如果不及时更正,会“竞损国体”。
具体改革方案归纳如下:
(1)日方为大学头林述斋增设一名书记官。以往林氏访问朝鲜使节,对方正副使“专使制述、书记辈主之”,林述斋对此非常不满,所以任命松崎慊堂作为自己的书记官同往,自己口述,由松崎慊堂负责记录、书写,这样就能做到形式上的对等。
(2)先公后私。林述斋和松崎慊堂认为,假如在聘礼之前便私下会务,有可能透漏太多信息给朝鲜使节,使其“驾自便之说”,所以决定举行完正式的聘礼之后再进行私下的文化交流。
(3)简化礼仪。见面时省去烦琐的礼仪,“公堂见面,交揖即可”。
(4)以往都是日方主动访问韩馆,这次要求朝鲜使节先提出邀请,然后才去访问。
(5)级别对等。林述斋访问韩馆时,通信正副使需要出面接待。若仅有书记、制述等人接待,则只派古贺精里去。“且彼三品,与我三位”,即要求级别对等。
(6)服装对等。以往林氏着大纹官服访问时,朝鲜使节往往穿便服接待,这样服装就不对等了,所以这次林述斋一行也穿便服访问。
(7)诗歌酬唱的顺序。以往都是日方先投赠,然后朝鲜使节和诗。这次要求朝鲜使节先赠日方诗,日方作和诗。
揭诸前文,至江户晚期,随着日本汉学研究水平大幅提升,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在这种思潮之下,江户幕府于文化八年(1811)实现了唯一一次“易地聘礼”,负责接待任务的林述斋及其弟子在远赴对马岛之初,就制定了打破朝鲜文化优越感的接待方案,要求先公后私,并且在得到朝方邀请后才去会晤,更是提出级别对等、服装对等、简化礼仪等诸多要求。
松崎慊堂和朝鲜使节李太华笔谈时问道:“清诗不足取乎?”[9]92李太华以“以小事大,势也。以诗相和,末也。何必俯问”[9]92为借口,没有正面回应,接着写道“贵国亦应知我国冠裳”[9]92,想以此转移话题,并希望得到松崎慊堂对朝鲜“大明衣冠”的评价,而松崎慊堂却以“如其冠裳,横目者见之,所问不在此”[9]92为由,未予置评。笔谈中还反映出日朝两国对清朝考据学评价的不同,李太华提到:“我国学问自退陶(李滉——笔者注)以后,名硕辈出,皆以考亭(朱熹——笔者注)为主。元无异端之间其间矣。”[9]96对于将朱子学以外的学问视为异端的看法,松崎慊堂直接予以了否定,并提出“如近世阎百诗、朱竹垞、顾亭林一辈说,是也”[9]97,认为阎若璩、朱彝尊、顾炎武的学说是值得肯定的,这与江户后期日本儒学界崇尚考据的学风也是一致的。对此,李太华再次强调“此我国无主张者,特观其说而已也”[9]97。二人的讨论针锋相对,互不示弱。在评价朝鲜使节的诗歌时,松崎慊堂甚至说:“有人寄两书记舟中诗筒至,其诗拙陋,至不能成语。”[9]114并以此为由,没有将“两书记舟中诗”收录进其所编的《接鲜瘖语》。
总而言之,在松崎慊堂看来,这次接待朝鲜通信使时,“一手之所录出,当彼三五辈”[9]65,打破了朝鲜使臣的文化优越感,认为“比之从前,其为得体也”[9]63,所以“订定立言之法”[9]66,作为今后接待通信使的标准模式。可见,松崎慊堂在撰写《接鲜瘖语》时,不仅仅是为了纪事,还强调了此书的“立言”功能,希望此书能在之后的日朝外交活动中发挥指导性作用。从现存《接鲜瘖语》30余种抄本及印本的流布地域之广、流传时间之长可以看出,松崎慊堂的这种思想在日本得到了积极呼应,影响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对朝态度。而长期以文化优势在对日外交中取得对等地位的朝鲜,失去了最有利的筹码,日朝关系在文化失衡下出现一个历史拐点。1918年,日本政府为了表彰松崎慊堂在对朝外交中发挥的变革旧礼、弘扬国威的贡献,追赠其正五位勋位。可知,松崎慊堂的对朝外交思想得到了日本官方的积极响应,突显了《接鲜瘖语》在近代日朝关系中的重要影响力[9]46-48。
除林述斋、松崎慊堂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外,以酊庵的五山僧、京都文士三宅橘园、古贺精里及其门生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交流总体上是非常友好、融洽的,朝鲜使节对以上人士也是大加赞赏。但在平和的表面下,却隐含着日本文士在对朝交流中文化心态的变化,他们已由最初的仰视对方,变为平视,甚至俯视。古贺侗庵在为其父整理的《对礼余藻》中写有两篇跋文,其中一篇在附录之前,写于文化十年(1813),很好地反映了日本文士文化心态的转变。内容如下[7]531:
我日域巍然峙立于海东,对岸之国以十数,除西土之外,其稍知礼仪而可与交使币者独有朝鲜而已。是以庆元而还,许其入贡,接遇极优。即彼之典章文物、人才国俗,地形之广狭,兵力之疆弱,虽不能希望本邦之仿佛,而朝廷故以敌国相待,可以见朝廷含弘之美矣。文化壬申之春入贡,小仓侯往对马州受聘,家君实与焉。竣事而归,辑其答问之语、唱酬之什为一卷,题曰《对礼余藻》。
夫国初以来,接朝鲜使节者遗文俱存,历历可睹。源君美及徂徕门诸子,由此其选也。煜间尝繙而阅之,每恨其好胜之心炎于中而溢于外。或以我之强侮彼之弱,以我之大蔑彼之小,以我之丽藻曼辞凌暴彼之枯肠短才,是以公夷人不肯降心以从,动以不肖之语相加,纷呶弗已,宾主揖让之礼扫地,其辱国体、贻笑外夷何如也!家君有鉴于兹,及接韩使节,卑以自牧,不敢有凌加。试阅斯编,绝无虚喝夸诞之语,炫多斗靡之作,是以彼亦感悦欣慕,无敢枝梧朝廷之威,不待震耀而自威。二国之好,不假申盟而愈固。
夫人必地丑力敌不相屈下,然后始有好胜之心。如本邦之于朝鲜,大小悬绝,臣畜之而有余,而白石以下诸子以好胜之心待之,是以敌国自处也,是自小而自卑也。今也家君居之以谦,接之以礼,而彼自知大国之可畏,不敢有侵轶,则亦何苦而效从前好胜之为哉。
文化癸酉维暮之春,儿煜再拜敬书。
古贺侗庵跋文的主旨是批评新井白石以来产生的日本文士与朝鲜使节笔谈时“虚喝夸诞、炫多斗靡”的好胜之风,指出以往的日本文士之所以争强好胜,皆出于自卑心理。而明智的做法应该像其父古贺精里一样,谦和有礼,让朝鲜使节心生敬畏之心,这也是大国应有的心态。换言之,这是对日朝“文化间的比赛”的一种否定。跋文中多处称朝鲜使节访日为“入贡”,甚至讲出日本与朝鲜“大小悬绝,臣畜之而有余”的狂言。古贺侗庵所说的“大小悬绝”不仅限于疆域与国力,应该也含有极高的文化自信。这种“不待震耀而自威”的对朝文化交流策略,虽然不及林述斋、松崎慊堂大刀阔斧地变革礼制那样有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但影响也同样深远。
四、 结 语
本文以最后一次朝鲜通信使访日为例,利用以酊庵五山学问僧、江户儒官、民间文士等三类群体的笔谈文献以及相关资料,综合呈现了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士交流的实态。1811年朝鲜通信使访日虽然在日本边陲对马岛举行聘礼,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并未缺失。由大学头林述斋、儒官古贺精里以及他们的弟子组成的日方“文化交流团”,首先对参与此次笔谈的人员进行了内部选拔,对正副使的随行人员提出的与朝鲜使节笔谈的申请一一驳回,对马藩对民间人士能否参与笔谈也进行了审查。具体而言,林述斋通过严格控制笔谈参与人员的数量与质量,保证了日方参与人员的交流水平,遏止了动辄以二百韵乃至八百韵斗奇争胜的“虚喝夸诞、炫多斗靡”之风。除此之外,林述斋一行对此次与朝鲜使节的笔谈也做足了功课。通过与沿途日本文士诗歌酬唱以练习和诗,认真研究以往日方人员与朝鲜使节的笔谈案例及“旧来之官法”,从以酊庵五山学问僧那里抄录朝鲜使节的诗文以了解对方的诗文水平,又多次派出弟子以民间文士的身份去探听虚实,做到了知己知彼,从容应对。
江户后期,随着日本诸文化领域的全面繁荣,日本文士在与朝鲜使节交流时的心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便是林述斋、松崎慊堂变革旧礼,先公后私,要求级别、服饰、礼仪等方面都要对等,对诗歌酬唱顺序也提出了要求的真正原因所在。而笔谈中的多次交锋,从形式到内容,对当时的日方而言,无异于打了一场“文化翻身仗”;而古贺精里的博学与谦让,所谓“不待震耀而自威”,则更是这种文化自信的典型表征。自此,朝方长期以文化优势抵消日方军事优势的近世日朝对等外交体系逐渐失衡,日朝“文化间的比赛”的历史拐点由此出现,它无疑影响了此后日朝外交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