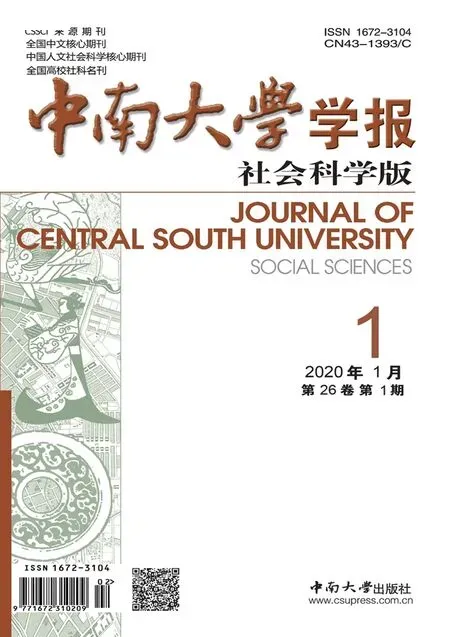论司法对法律漏洞的习惯救济
——以“可以适用习惯”为基础
谢晖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该规定明示了“可以适用习惯”的前提是“法律没有规定”。这似乎是个无须继续探究的话题。然而,何以被概念化、类型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法律及法治,居然还会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现象?“法律没有规定”时,为何要适用习惯,而不是政策、道德、纪律或其他社会规范?在“法律没有规定”时,法院和法官应按什么原理适用习惯?显然,这些问题并未在上述规定中当然解决,所以还需要在学理上探究其理由所在。
一、法律:人造理性与逻辑缝隙
(一)法治与逻辑自洽的法律追求
追求一种体系完备、逻辑严谨、包罗万象、无所遗漏的法律统治体系,不仅是近代“依法主治”观念形成以来才有的理念,即使在前现代时,人类就一直怀揣那种借助法律而经纬天下的梦想。这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法家学说中得以体现。兹以商鞅、管仲和韩非的论述为例: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①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②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先王知之矣。③
这些古人对法律治理的热切期盼,等到秦始皇“挥剑决浮云”,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之后,更是被推到制度实践中,形成所谓“以法为教”的治理框架和绵密严谨,甚至被形容为“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④的治理体系。此后“汉承秦制”“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1],中国千古之治乱循环,成于斯,也败于斯。
众所周知,在西方,笃信法治的亚里士多德强调“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2](167−168)。而在西塞罗和他的朋友看来,法律的统治就是符合天理人心的统治:
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就是法律。因此……智慧即法律,其含义是智慧要求人们正确地行为,禁止人们违法……法(jus)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3]
正是这种对法律和法治的理想定位,催生了罗马人蔚为大观、兼蓄并包、公私兼顾、肇启后世的罗马法,其深刻影响不仅及于欧美,而且惠泽远东、朗润天下。至于在宗教世界人们对法律的崇信,乃是和其内心信仰紧密勾连的话题。宗教世界,就是一个围绕经典及其规范的信仰和行动体系,因之,也是相关的法律体系。如在伊斯兰世界,“沙里亚法以要求穆斯林对真主启示和先知逊奈的信仰和保护并为之献身而获得对社会的支配权力,从而使伊斯兰获得社会性和历史性”[4]。这种情形,不止在伊斯兰世界,而且是所有宗教法作用的基本机制,甚至也因此而影响到世俗法。诚如伯尔曼所言: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为狂信;
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最文明的社会,也有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也信奉终极目的和关于神圣事物的共同观念;同样,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社会,也会有社会秩序的组织与程序,有分配权利、义务的既定方式和关于正义的共同观念……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与宗教共享某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人们的法律情感赖此得以培养和外化。否则,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同样,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也都具有法律的要素,没有这些,它就会退化为私人的狂信。[5]
至于在近现代社会,法治主义思潮的广泛影响不但使法律在诸规范系统以及人与法的关系上获得至上地位,而且曾一度使人们迷信法律的统治就是完美的统治,或者它至少是可以通往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正义、博爱和法治之境的“法律帝国”——其迷信之源,就来自法律逻辑无缝的假设。诚如有人所言:
事实上,上述论点(法律的完美统治,译者注)是基于这样一个确定无疑的假设,即法律是一个封闭的、完整的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的体系,它本身没有漏洞、自相矛盾和歧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基本上是逻辑上的一种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系统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的概念是一个逻辑概念。这种类型的逻辑概念在思维方式和认识论方面对法律从业者有着巨大的影响。⑤
可见,所谓“法律帝国”,无论是完全通过立法者的法律规范所缔造的,还是通过解释者的不断阐释所缔造的,都是排除了其他一切社会规范的纯粹法律的统治。其他规范要影响法律的统治,要么按照法律整全性的理念和自我完善的方法进行有效的阐释[6],要么按照法律体系的原则,只要涉及诸如习惯之类的规范,必须通过司法和法院的正当程序,将其结构在法律体系内——就如同拉兹所言那样:“除非习惯被法院立法化,否则习惯就根本不是法律……”[7]
(二)不可避免的法律漏洞
不无吊诡的是,即使人们如此崇尚法律的统治,且将法律描绘为一种理想的、近乎完美的、能够通向正义之路的体系,但法律作为人的理性,仍然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事体。法律面对社会事实的捉襟见肘、顾此失彼,几乎是必然的。
如前所述,在法律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秦朝,按理说当局已经制定了足以规范社会方方面面的法律,到了“赏善不遗匹夫、刑过不避大夫”,从而把所有人都结构在法律治理体系之地步。即便如此,法律还会因为漏洞而予以解释。其中“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就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当时在成文法之外,法律解释的隆重情形。对此,该竹简的整理 者写道:“当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有某种需要时,执法者可以不依规定,而以判例办案……”⑥它事实上表明秦朝这个严格奉行“国本位”的成文法时代,法律本身的漏洞所在。这在我国“家本位·判例法”时代、“国、家本位·混合法”时代⑦国家及其法律解释者对判例和家法族规的重视中,都可判断出事实上法律漏洞的存在。
古罗马的法学家尤里安在阐释法律时多次公开申明:“法律和元老院决议都不可能制定得囊括所有可能偶然出现的情况”;“……对于第一次被确定的法律,需要通过解释或者最优秀的皇帝的谕令而使之更加确切”;“人们不可能使法律和元老院决议详尽地囊括所有情况……”[8](57)这不正表明在古罗马“立法者”和法律解释者心目中,法律漏洞存在的必然性吗?
对上述情况,中西方法律史上的思想家似乎都心知肚明。孟轲就清楚地认识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9];亚里士多德也清晰地告诫人们:“法律确实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并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2](171);孔颖达更是明确指出面对法律漏洞时的棘手:“法之设文有限,民之犯罪无穷,为法立文不能网罗诸罪,民之所犯不必正与法同,自然有危疑之理……”[10]
可见,对法律作为人的智虑不可能完美无缺的体认,不仅在现代法学家笔下才可见到⑧,在一两千年前,它就是中西思想家论战的主要话题。这或许正是儒家⑨与法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分歧的缘由所在,也是在伊斯兰教法律史上,何以在《古兰经》这一根本经典,“也是早年麦地那穆斯林民族共同体(乌玛)的最高章程,成为立法、行教、建国的根本依据”[11]之外,还有《圣训》以及教法学家解释的缘由。只是这种情形,在现代学者的笔下,不但给出了诸如“空缺(开放)结构”⑩、“法律漏洞”这类概念化、逻辑化和系统化的解释,而且指出了救济它们的方法,即漏洞补充方法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适用习惯”的规定,正是立法者对法律不可能穷尽所有事实,从而必然存在漏洞,并进而通过司法的正当程序,借用习惯补充法律漏洞的一种救济性规定和举措。
(三)法律漏洞的类型
法律不可能完备无遗,从而必然存在漏洞。那么,法律漏洞都表现在什么地方?或者,对法律漏洞如何予以分类,如何使其类型化?笔者认为,从人们对法律要素的一般理解出发来剖析法律漏洞之类型,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众所周知,法律之要素,通常被描述为概念、规则和原则⑫,笔者赞同这种对法律要素的分类⑬。相应地,也认为法律漏洞可以分为概念漏洞、规则漏洞和原则漏洞⑭。
(1)概念漏洞。所谓概念漏洞,是指法律中对于法律所调整的、理应予以概括性阐述的对象,如具体的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行为等,未给出定义性、一般性的概括,从而出现概念空白,并对人们掌握、理解相关问题带来一定的麻烦。例如我国《民法总则》在“自然人”一节,虽提及自然人,但并非开宗明义讲自然人的概念,而是讲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与此同时,它尽管规定了自然人、权利能力、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等概念,但并没有给出概念化的解释。在此意义上,这些概念的含义在法律上处于空白、漏洞状态,因此,在日常理解中,需要借助学理解释,予以概念化说明;在司法中,如有需要,也要在个案中通过概念化解释,让当事人明白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
(2)规则漏洞。众所周知,法律规则用来具体规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要素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同时也是法律中最容易出现漏洞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事实和社会关系事无巨细、异彩纷呈、千变万化,而法律规则却必须大体概括、荟其精要、立基当下。这使得法律规则之漏洞,几乎无可避免。特别是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需要时,既定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可能全部满足。例如司法面对祭奠权、网名权、网络财产权、信息权、知情权、新型人格权……的保护要求,在现行法律上寻找根据时,可以发现几乎付诸阙如。因此,如何通过司法救济,在个案的裁判中补充法律漏洞,完善法律体系,就殊为必要。
(3)原则漏洞。法律原则规定一部法律的精神层面,贯穿于一部法律之始终。一般说来,一国之法律在原则层面出现漏洞的可能性较小,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形不存在。例如在我国法律中,曾一度囿于意识形态,对有关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保护私人财产原则等都未加规定。只是在最近20年来的立法中,才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物权法规定了上述原则。也就是说,在上述法律修改或制定之前,相关法律原则在法律上存在空白、漏洞的情形。再如,尽管我国最近颁布了令人瞩目的《民法总则》,但无论是该法,还是之前制定的《合同法》,都没有规定成文法国家所公认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又称“私权神圣原则”)。可见,这项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上仍是空白。面对这样的空白,司法应当有所作为。
二、何以适用习惯补充法律漏洞,而不是其他?
(一)何以不是其他规则补充法律漏洞?
《民法总则》第十条的规定,在立法上不仅坦承法律可能会存在“没有规定”的情形,即坦承法律会存在漏洞,而且明令法律一旦存在漏洞时,用以补救它的替代规范,即习惯。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交往规范,除法律、习惯之外,其他各类社会规范零零总总、花样繁多、不一而足,诸如国家(或政党)政策、公共道德、宗教教规、社区公约、社团纪律、企事业章程、乡规民约、家法族规等。对于公民的日常交往,它们各自发挥着在一定时空内构建秩序的作用,即便对于增进法律秩序的理解也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所以,“在格尔茨看来,法律是一种类同于其他事物的充满想象力的意义结构,这些事物包括等级、艺术、意识形态和仪式等”,“那么学习法律最好的方法,就是对于某些观念进行解释学的研究,这些观念构成了社会制度的基础和法律的文化表达,而不是对于法律的逻辑原则是如何适用于实践结构和思维结构进行假设性的考察”[12]。
当然,也必须承认,在不少时候,规范多元也是对法律秩序之妨害——这种情形,与习惯之于法律的关系完全类同。既然如此,为什么《民法总则》规定了“法律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习惯”,而不规定“法律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政策、教规、公约、纪律、章程、规约”等?对此,笔者不妨就政策的规范特征稍加展开⑮,并以此为基础,说明法律为什么不选择这些规范,而要规定在法律供给不足时,授权可以适用习惯的理由。
日常所谓政策,是指党的政策,但事实上,在我国,党的政策总会通过法定的或非法定的方式,演变为国家政策,因此,对两者的刻意区分,在实践中很难。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的主要规范参照是政策,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还经常出现究竟是政策高于法律,还是法律高于政策的讨论⑯。这导致政策曾经在我国《民法通则》(第六条)中,被赋予了民法渊源之地位:“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该遵守国家政策。”因之,在司法中、特别是在民事司法中仍存在着一些适用政策来裁判的个案[13]的情形。与此同时,尽管《民法总则》业已制定,且未规定政策之法源定位,但迄今为止,《民法通则》并未失效。这种情形,是导致在学理上,有些学者仍坚持主张把国家政策作为法律渊源的重要根据之一⑰。
然而,其一,选择政策裁判案件,乃是在国家法治不完善,且因为社会鼎革对习惯普遍抱有意识形态偏见下的产物,也是司法尚未获得专业化背景下的产物。其二,随着我国法律体系之日臻完善,同时也因为政策的过于灵活多变、规范性不足以及难以操作等,导致以政策裁判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接受性都存在问题,因此,以政策补充法律的时代背景已不太明显。其三,我国作为事实上党政一元的国家,执政党的重大政策是经由法律化而转为国家政策的,当我们论及“国家政策”这个概念时,它已经主要是被结构在法律内部的概念,而不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没规定时,必然意味着也无该种“国家政策”。所以,把国家政策作为法源规定的意义空间越来越小。
或许,人们会在此提及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共政策”作为法源的事实:“由于法官吝于承认他们的职权曾受任何公共政策的影响——因为他们的工作在说明‘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如何’——于是一位普通人可能会在(英国)习惯法的判例中,惊讶地发现,法院偶尔采用了‘公共政策’的观念,或是在(欧陆)民法(civil law)体系下法官的判决中,看到另一个几乎相同的用语:公序良俗(morals and public order)。”[14](262)但应强调的是,首先,英美法系所谓公共政策这个名号的获得,与习惯法的名称的获得一样,都是经由司法判决的结果;其次,即使存在经由司法裁判获得的公共政策,但其在法院那里,完全不同于适用习惯,而是有严格的约束和限制,甚至法院在相关活动中,还要考虑适用之声誉会否受到影响⑱。可见,在英美法系的司法中,公共政策补充漏洞的功能实际上非常有限。
(二)何以通过习惯规则补充法律漏洞?
论述至此,我们就可回过头来进一步观察立法者为何在众多的社会规范中,要选择习惯作为法源,用来补充法律漏洞的理由了。这些理由,大体上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积淀及古老。在谈及法律为什么有效时,人们辄喜引用托克维尔的如下名言:
英国法学家之所以尊重法律,并不是因为法律良好,而是因为法律古老;即使他们要对法律进行某些修改,使其适应社会的时势,他们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对祖先留下的东西进行修修补补,只发展祖先的思想,只完善祖先的业绩。不要期待他们会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宁愿被人指为荒谬绝伦,也不愿承担冒犯老祖宗遗训的大罪。⑲
托克维尔的这段名言,系建立在普通法对习惯的承续、认可和保护基础上的判断,故用来说明习惯的有效性或许更为恰当。早在罗马时期,法学家就强调:“那些有长期习惯确认了的并且被常年遵守的东西,同写成文字的法一样,被作为公民间的默认协议。”[8](63−64)其实,类似的情形,在我国也存在。“祖宗之法不可变”,乃是古已有之的遗训和传统,直到如今,在民间仍盛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法俗”。而在山东胶东一带,人们在论证一项举措合理性的时候,常常喜欢说:“老辈子就是这么做的!”这种掷地有声的论据,常使对话者哑口无言。而在涉及民间纠纷的处理时,年事已高、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人,是出面解决纠纷的最佳人选。对此,一位德国学者也注意到了:
习惯性的规范在中国流行的情形绝不比其他地区逊色,而且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更有权威,譬如对于父母和祖先的尊敬,以及对家庭中其他分子的扶助与蓄养……在法律争端方面,中国人……认为,法律上的正义是由人类本于宇宙间的和谐精神去调和各方利益的结果,而人类的智慧早已蕴藏了许多关于宇宙间和谐状态的暗示。这样的社会,无论在社会关系或经济关系方面,必定会把一种以根深蒂固的法律架构或社会规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在不妨碍那个基本架构的范围内,搀和高度的弹性与变化性。[14](231)
可见,习惯之所以能作为仅次于制定法的法律渊源,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传统性、积淀性、古老性以及由此出发已然构造社会秩序的有效性。
第二,信念及确信。古老的习惯给予人们的,不仅是传统和积淀,而且是经由习惯所带来的强烈信念和坚定确信。这种信念和确信可以一分为二。
其一是规范信念与确信。对此,波斯特玛、萨维尼等都有精彩的论述:
普通法是民族的统一因素,是它的根本法。它不仅确立了社会关系,分配了社会权力,而且还将包括国家基本的宪法性法律,进而界定政治关系,分配政治权力。普通法是远古的习惯,所以它界定的宪法和权力关系也被看作古老的习惯。于是,普通法的概念、信念、态度和前见将会深刻影响那个时代的政治语言,是不可避免的。[15]
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远古的时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个民族所特有的,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不仅如此,凡此现象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它们实际上乃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取向,而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特立独行的景貌,将其联结一体的,乃是排除了一切偶然与其任意其所由来的意图的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以及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认识。⑳
其二是效力信念与确信。规范是用来给人们分配权利义务的,但规范能否产生效力?这是人们是否尊重规范的关键所系。习惯的传统积淀、古老流传以及人们对它的信念和确信,不仅让人们知晓其作为分配权利义务之规范的存在事实,而且足以使人们确信按照习惯行为的基本预期,那就是经由习惯的裁判行为,可以像人们预先所知道的那样,带给人们预期的权利,加诸人们预期的义务。诚如有学者所言:
习惯法是一套最为适应民众需要的制度,也是最为契合民众传统观念和社会价值的,马拉维民法典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子……为了保证统治国家的人民能够接受新制定的民法典,民法典是以习惯法为基础制定的。[16]
因此对司法裁判而言,习惯的这些特点势必导致裁判的可接受,从而既降低司法的成本,也提高人们对司法的信赖,实现以习惯来补救法律的漏洞之立法宗旨。所以,在法律供给不足时,“可以适用习惯”的规定可谓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第三,权威及互补。在人类秩序发展史上,渐积渐成的习惯,既是最为古老的规范,同时,因为习惯的观念熏陶和行为模仿,也使它获得了至高无上的、铭刻于人们心底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既来自其古老,来自人们对它的内心确信,也来自因为习惯的权利义务分配和保障,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习惯去做时,所带来的方便和利得。所以,在埃利希看来,习惯法尽管可以是裁判规范,但它主要还是行为规范:
一如萨维尼和普赫塔所认为的那样,在习惯法中,产生于民族法意识中的东西直接转化为习俗,民族不仅意识到他们的法,而且还以他们的法来生活,他们依此而行为,依此而变迁,而且正是这种依法而行不仅是习惯法的表现形式,也是它的一种识别手段。也就是说,习惯法既是行为规则,也是裁判规范;更确切地说,它始终首先是行为规则,通过行为规则才变成裁判规范。[17]
埃利希的论述,事实上找到了作为权威的、日常的、能够给人们带来和民族法意识相勾连的生活规范——作为行为规则的习惯法和裁判规范之间的勾连关系,正是这种勾连关系,促成了习惯法基础上的法官法,进而实现对国家法漏洞的补充。这已经预示了习惯法通过可诉机制和裁判规范的工具,与国家法之间所形成的互补关系。对此问题,笔者将在下文展开。
第四,立法及可诉。既然法律总是有缺陷,总是会出现漏洞,那么,设法通过一定的规范化手段救济法律漏洞,就是立法应关注的问题。从法律运作的事实看,相关的救济手段,既有基于法律内部立场的救济,如法律解释、类推适用、效力识别等,也有基于法律外部视角的救济,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授权司法可以适用习惯,即把作为法律外部的规则——习惯,通过司法结构到法律可接纳的范围中,作为裁判案件的规范根据。这种情形,虽然在近代成文法历史上曾一度衰落,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民法典中未予特别重视,甚至还明显忽视(尽管两部法律都不否定习惯法作为行为规范的价值)。但自从《瑞士民法典》第1 条第2 款明令“无法从本法得出相应规定时,法院应依据习惯法裁判”以来,赋予司法适用习惯以救济法律漏洞,就是世界多国的立法例。例如在韩国:
殖民地时期习惯法建设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韩国的现代民法和现代司法。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后,虽然殖民地当局颁布日本的民事法律作为朝鲜的通用法律,但同时颁布命令朝鲜人之间的绝大多数法律的私人关系仍旧适用韩国的习惯。因为高丽人时期的朝鲜没有成文的私法,因此习惯法的改造就被委托给法官和法学学者,他们查明并用西方的法学概念解释朝鲜习惯法。殖民地时期的法庭坚持相信来源于过去流行行为的习惯法,并且他们经常把习惯与理性相结合加以改造,然后与西方法律历史的发展做类比。[18]
而在我国,近代以来的诸次重大民事立法活动中,辄赋予司法通过适用习惯以救济法律漏洞的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赋予司法通过适用习惯来救济法律漏洞的情形,不独是近代的产物,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我国古代法律特别是司法中所存在的礼法并重、春秋决狱、以例破律、引礼入法、情理法兼顾等事实,是司法运用包括习惯在内的社会规范救济法律漏洞的重要方式[19]。而在古罗马法上,法学家在解释法律时,也予明示:“在不采用成文法的情况下,必须遵守由习俗和习惯确定的那些规范”(尤里安);“在无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那些长久的习惯常常被当作法和法律来遵守”(乌尔比安);“那些由长期习惯确认了的并且被常年遵守的东西,同写成文字的法一样,被作为公民间的默认协议”(赫尔莫杰尼安);“……对于产生于法律的疑问,习惯或长期以同样方式确定的有效判决应当拥有法律效力”(卡里特斯拉特);“所有的法或者由合意设定,或者由必要性创立,或者由习惯确认”(莫德斯汀)[8](62−65)。由此可见司法适用习惯以救济法律漏洞传统之久远。
如果说在成文法国家,习惯是司法之重要的救济法律漏洞的规范的话,那么,在法判例国家,习惯每每是生成判例的根据;如果说,在一位德国自由法学者的笔下,“法律是理性化了的习俗”[20](137)的话,那么,这句话用之于判例法国家,也可谓恰如其分。
古今中外立法例上对于习惯作为法律渊源的肯定,事实上使得习惯获得了理性化和可诉性。基于这种理性及可诉性,两造才得以主张适用习惯处理纠纷,法官才能在法律供给不足时,据以适用习惯,来救济法律漏洞。
可见,法律之所以赋予司法可以适用习惯,以补充法律漏洞,恰恰在于习惯的如上特征。
三、司法适用习惯以救济法律漏洞的方式
法律出现漏洞后,司法救济的方式是多样的。法官既可以采行内部救济的方式,即在法律内部寻求和案件事实的特征最相类似的条款,通过类推来裁判案件,以补充法律漏洞。这就是所谓类推适用㉑。因为类推适用既要说明三段论运用中推论过程和推理结论的合理性(内部证成),也要提供用来推理的大前提之合理性(外部证成),所以,类比推理必然连带着类比论证[21]。除了类推适用之外,法律漏洞的其他救济方式还有法律发现和法律续造。在笔者看来,司法适用习惯以救济法律漏洞,乃是法官通过法律发现补充法律漏洞的活动㉒。那么,何种法律漏洞需要司法适用习惯以救济?司法适用习惯救济法律漏洞的机制是什么?在法律有明令时,司法可否适用习惯?就这些问题,下文将略加展开。
(一)司法适用习惯来补充法律漏洞之效力
如前文所述,以法律要素为参照,法律漏洞可一分为三,即概念漏洞、规则漏洞和原则漏洞。这三种漏洞,法官是不是皆可适用习惯以补充?回答是肯定的。对如上三种法律漏洞,司法经由习惯的补充,也会分别产生当然补充、连带补充与造法补充的三种效果。
(1)当然补充。所谓当然补充,是指在法律出现漏洞时,司法只要适用习惯,对法律规范而言,意味着其当然地起到补充作用。我们知道,法官适用习惯的场合,是面对所谓疑难案件时,即当下案件没有法律作为裁判根据。一般说来,当一例案件没有法律根据时,是说没有法律规则,而不是说没有法律原则。因此,司法适用习惯时所补充的漏洞,首先是对规则漏洞的补充。这也意味着法律只要出现规则漏洞,但有相关的习惯足以弥补法律的规则缺陷时,司法就可以通过适用它来补充。因此可以说,只要司法在法律漏洞条件下适用习惯裁判案件,就意味着习惯对法律规则漏洞的补充。所以,法官适用习惯裁判案件,对于法律之规则漏洞而言,产生当然补充之效力。如果司法适用习惯进行裁判,而对法律的规则漏洞不能产生补充效果,那么,习惯的适用在客观上就无效——这样的习惯,事实上无力裁判案件。可见,在存在法律规则漏洞之时,只要司法适用习惯以裁判案件,就意味着习惯对法律规范漏洞产生当然补充的效力。
(2)连带补充。所谓连带补充,是基于当然补充的效力所产生的连带效果。这与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的关系紧密相关。一般来说,一个法律概念,是镶嵌于法律规则当中的概念,法律概念本身不是法律规则的外在物,而往往是结构在法律规则之中的。作为名词的法律概念,和作为动词的行为指向一起,构成人们交往行为的规范。因此,尽管在分析的意义上,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是两码事,但在结构和功能视角,两者即使不能说是一而二的,但至少可以说是二而一的。可见,法律概念连带在法律规则之中,进而,法律规则之漏洞,也每每意味着法律概念之漏洞。这就表明,当法律出现规则漏洞时,司法适用习惯对法律规则漏洞产生的当然补充效力,也意味着其连带地补充了法律概念之漏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所适用之习惯中的概念经过适用,就自动转化为法律概念,也不意味着法官要对存在漏洞的法律概念,通过适用习惯的个案裁判给出定义化解释,只是说,当法官在法律规则有漏洞而适用习惯以补充它的时候,习惯对法律概念漏洞的补充,连带地涵盖其中了。
(3)造法补充。它是指当法律原则出现漏洞时法官运用习惯裁判案件所作的补充,一定是具有造法功能的补充。司法的造法功能,在英美法系国家是常例,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例外。因此,对司法造法格外关注,也格外谨慎。“法院应该使一个裁决针对某一类案件,对这类案件形成一个共同的法官规则。也就是说,法院对某一判决所适用的某一类案件创造出新的、关于该类案件的、普遍有效的法律规范。”[22](379)虽然这一说法也适用于法院适用习惯时对法律规则漏洞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未必产生普遍有效的法律规范。例如,当司法所适用的习惯囿于一个很小的时空范围时,它虽然对已经裁决的个案会产生补充法律规范不足的效力,但对发生在其他时空范围的类似案件,就未必适用,也未必能产生一般法律规范之效力。但是,对法律原则漏洞的习惯补充则不同。一个很小时空中的习惯,一定无以补充法律原则的漏洞。而能够对法律原则之漏洞进行补充的习惯,一定是在广大的时空范围内可被接受的习惯。这种适用习惯的判例一旦生成,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会起到法官造法的功能。因此,笔者把它称之为“造法补充”。
(二)习惯救济法律漏洞的基本手段
习惯作为自发生成的秩序规范和秩序体系,如何勾连国家的理性秩序体系?即它以什么方式救济作为理性秩序体系的法律之漏洞?对此,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向来有两样的做法和说法:一是习惯的理性化,一是“可诉性”。
理性化是作为经验事实的习惯升华为理性事实的法律,并用来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理性化的基本方式,通常是立法的认可和司法运用习惯的裁判。但是在成文法国家,因为立法对习惯的认可这一理性化机制,表明习惯已然被纳入制定法体系中,因此,不是这里讨论的对象——因为它不存在法律漏洞问题。所以,这里所谓经验习惯的理性化过程,就是把习惯交由法院和法官进行识别、处理和运用,并用来补充法律漏洞的活动。
对于习惯经由司法适用的理性化,人们有并不相同的看法。或强调“法官所造的法律与社会标准及习惯之间存有一种自动认同作用”;或强调“法官所造的法律容易根据它本身的思维发展成某种自主的天地,譬如它创造了许多文雅、巧妙、专门以及拟制的职业性法律意见,却摒弃一位普通人可能用来判断他日常交易中是非问题的简易方法。而且随着岁月流转,这些专门技术很可能会不断增加,使法律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距离愈来愈远”[14](234−235)。但无论看法多么不同,这些看法的共同点,是对司法理性的基本认同。
经由这一进路,人们常对习惯和习惯法予以分解:习惯不同于习惯法。对这一点,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学者,还是大陆法系的学者,大都予以坚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奥斯丁说:习惯法的“基础是这样的:法院参考了预先存在的习惯,然后进行司法立法……当习惯成为法院判决的理由的时候……这种习惯,的确就是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规则”[23]。而哈特强调:
除非是获得法律的承认,否则这样的习惯并不具有法律地位……只有在以下的条件下习惯才会成为法律:特定法体系‘确认’(recognize)某个类别的习惯为法律,而这个习惯是这个类别的其中之一;
……在决定某个习惯是否符合法律确认时,法院所适用的检验标准包含着像‘合理性’之类的流动性观念……㉓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很多,像萨维尼、韦伯、凯尔森、拉德勃鲁赫、魏德士[24−26]等都有论及。例如韦伯就认为:“习惯不同于习惯法……根据一般的术语学,作为习惯法的规范,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类似的强制性实施机制,尽管这种强制效力是来自于同意,而不是制定;习惯则不以任何强制性机制为特征。”㉔魏德士强调:“通说认为,习惯法以法律共同体中的长期实践(‘习惯’)为前提,此外,这种习惯必须以法律共同体的普遍的法律确信……为基础。”[22](106)
上述对习惯和习惯法两分之论说,仍是强调司法理性化的方式,对司法适用习惯以补充法律漏洞、弥合习惯与法律理性之间关系的方法意义。所以,如果说“法律是理性化了的习俗”的话,那么,我们宁可将这句话修改为“习惯法是理性化了的习俗”,因为“真正的标准存在于社会习俗转变为法律习俗,即转变为法律这样一种理性化的过程之中”㉕。
至于“可诉性”,按照康特诺维茨的看法,是用来区分法律与社会习俗的标准。他指出:
笔者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寻找到了区分于社会习俗的法律标准,即他所称的规则的‘可诉性’——它能被法官所适用的性质。‘法官’被理解为这样一个权威者,他通过有意识地适用一般性的程序与裁判规则,或至少通过依照这些规则进行(事实上的……)案件审理与裁判,来对发生冲突或有疑问的个案进行裁判……‘可诉性’……运用于这样的规则,它们被认为‘适合被司法组织适用于某个特定程序’。[20](157−158)
“法的可诉性是指法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27]这是笔者曾经给法的可诉性下的定义。今天看来,这一定义突出了纠纷主体,而没有突出纠纷裁判者——法院,是其明显不足。如果在上述界定基础上,再加上“并由判断主体(法院)运用于案件裁判”的字眼,也许界定会更为完整。当然,这是针对法或法律而言的。在司法中运用习惯,以补充法律漏洞时的“可诉性”,乃是指习俗的可诉性,或者是把习俗结构在法律理性体系中的可诉性。只有这样的习俗,才有可能获得习惯法的名号,并通过司法在个案中的适用,来救济法律漏洞。这样一来,“可诉性”既是判断习惯可否被司法适用的重要标准,也是司法适用习惯,以救济法律漏洞的具体技术。
(三)法律有明令时,司法可否适用习惯?
法官可否以习惯修改法律?或者法律有明令时,司法可否适用习惯?这在判例法国家的实践中并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㉖,但在成文法国家,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带来对法律公理的挑战,会影响成文法的权威——因为在成文法国家,法官曾长期被认为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㉗。相应地,成文法被人们赋予了神圣的、不可逾越的地位㉘。
尽管如此,过度美化成文法的理性还是被历史实践所证伪。作为人的理性,法律不但会出现漏洞,而且即使没有漏洞的法律,也会存在种种病灶,如意义模糊、意义冲突等。甚至有些明令的法律还可能会违背人类公理(例如纳粹的法律)。那么,法院和法官在面对这样的法律时,究竟应该怎么办?是对法律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是根据包括社会习惯在内的其他社会规范以及法官的内心确定安排案件的审理活动?对此,在凯尔森看来,因为法律不可能存在间隙,即便法律之间存在问题,法官也只能在“上级规范”中寻找解决的方案。但问题是当上级规范本身出现问题时又该怎么办?我们知道,他虽然推出了一个理想的且难以实证的“基础规范”[25](124−182),但这一概念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坚守自由法学理念的康特诺维茨则强调,在制定法不可能提供更好的裁判方案时,法官可根据其内心的自由确信和良知,来确定裁判方案。他写道:
法官……必须也应当看到,首先,制定法可能并没有为他提供一个确凿无疑的答案;其次,依照他的自由确信与良知,判决时存在的国家权力机关很可能不会像制定法所要求的那样作出决定。在两种情形中,他都应当这样来判决案件,依照其确信,他所作的判决将与现在的国家权力机关遇到这个个案时所会作的决定一样。假如他不能形成这样一种确信,他就应当依照自由法来进行判决……可以肯定,在民事诉讼中,应当听任诉讼双方通过共同申请,来免除法官遵守任何国家法律规范的义务。㉙
尽管康特诺维茨并未明示法律有明文但不能为法官提供确凿答案时可以适用习惯,但从中我们可以推知,他对法官在其确信和良知作用下适用习惯的内心默许。问题是,习惯何以在法律有明文且无漏洞时,还可以适用?在笔者看来,其基本原因是习惯对法律非法的校正功能。法律之非法,既指法律之价值非法,如臭名昭著的纳粹法;也指法律之技术非法——特别是法律的规定与它所欲调整和保护的社会关系格格不入、南辕北辙的情形(对此,在绝大多数学者的笔下依然被纳入“法律漏洞”之范畴,但在笔者看来,它属于法律意义冲突的范畴。法律之病症,除了“意义空缺”,即“法律漏洞”外,还有“意义模糊”和“意义冲突”[28](29,157),三者应严格区分,不可对其模糊理解并模糊处理)。在法律价值非法时,只要社会中有替代法律既定价值的、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习惯,那么,司法就能够运用习惯或习惯法校正法律之价值非法㉚。在法律技术非法(笔者称之为法律调整不能[28](241−242))时,尽管法官可以采取其他的技术手段校正其非法,但如果实践中有现成的可以校正法律调整不能的习惯时,法官何乐而不用呢?
注释:
① 参见《商君书·画策》;《商君书·君臣》。载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8 页、第485-486 页。
② 参见《管子·明法解》;《管子·任法》。载黎翔凤撰,《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13、906 页。
③ 参见[战国]韩非:《韩非子·饰邪》。载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359、366-367 页。
④ [汉]宽桓:《盐铁论·刑德》。载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65 页。当然,这是对秦法的一种否定性评价。但从中我们可以推知秦始皇君臣想通过建立完备无遗的法律而一劳永逸地统一天下、治理人间的浪漫“法治”理想。
⑤ JAN M.BROEKMAN.Beyong legal gaps,law and philocophy,Vol.4,No.2,Legal Reasoning & Legal Interpretation (Aug.1985):p.217.
⑥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 页。关于“法律答问”解释技巧的研究,参见陈锐等:《素朴的技巧:<法律答问>中的法律解释方法》,载《政法论丛》2011年第6 期。
⑦ 相关划分,参见武树臣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499 页。
⑧ 在当代法学家笔下,法学的发展、司法的创造,每每是在法律存在漏洞、法官面临“疑难案件”的情形下。因此,对法律漏洞的体认,原因之探讨,在中外学者中可谓论者云集。笔者的论述,参见谢晖:《沟通理性与法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99 页。
⑨ 在有些学者看来,儒家虽不主张甚至反对法家以刑为统的“法治”,但并不反对甚至还认真对待另一种“法治”,即以“伦理法”为基础的法治。关于儒家的“伦理法”特质,参见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333页。
⑩ 最典型地把法律漏洞事实予以概念化、逻辑化论证的是哈特,他把这种事实命名为“法律的开放(空缺)结构”或法律的“不确定性”:“无论我们到底选择判决先例或立法来传达行为标准,不管它们在大量的日常个案上,运用得如何顺利,在碰到其适用会成为问题的方面来看,这些方式仍会显出不确定性;它们有着所谓的开放性结构(open texture)。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开放文本,特别是在立法这种传播形式中,视为人类语言的普遍特征;为了使用包含一般化分类语汇的传播形式来传达事实情况,边界地带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 页)。
——来自广西金秀的田野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