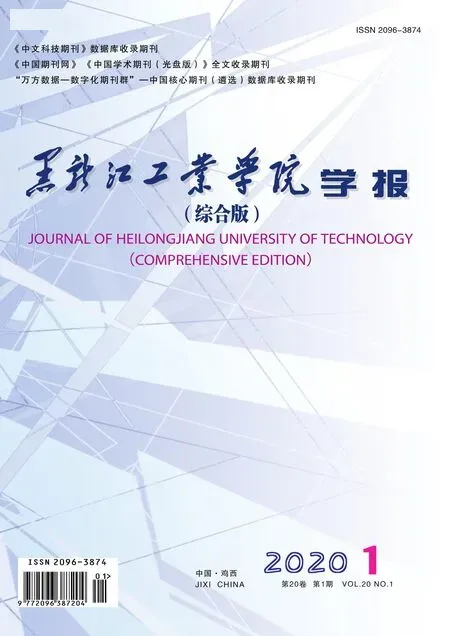“气”与“境”偕
——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意蕴
廖愿平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新时期文学家汪曾祺认为,“有一些散文化的小说所写的常常只是一种意境”。[1]他的小说数量不多,但都别具情志,自成一格。汪曾祺追求小说散淡的诗情美,不止于描绘真率自然的民风民情,而是努力营造出一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意境。这种不着重写人物,写故事,而着重写印象,写感觉,呈现出作者的主体意识很强的诗化意境,与他推崇的“文气”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汪曾祺从小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古文教育,在对韩愈、桐城派等传统文气论继承与创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汪曾祺的写作是对传统话语认同与回归,弥补了中国传统文论在现代处境的断裂状况。
汪曾祺以气为本的创作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之“气”,指作家的精神、气质,要求作家要以气运笔;二是指文中之“气”,重神气,重气氛,认为语言的内在节奏即“文气”,提出了“气氛即人物”、以“节奏”代结构等一系列创作思想。“文气”这一范畴,对汪曾祺小说中意境的审美生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虚则无意境的产生,而虚是不离“气”。“气”在心与物、情与景、形与意关系中,发挥了类似中介性质的重要作用。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情”与“景”的统一,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形成了“气”与“境”相偕而生的独特审美特征,以他的创作实绩引领了新时期创作的新方向。
一、情与景:气氛之美
情景交融是意境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情”与“景”的关系,汪曾祺从不直接表现出自己的情感倾向性,而是完全对象化、主体化于环境中,透过人物主体形成一种气氛传达给读者,从而实现物我相融、意与境浑的结果。即在汪曾祺的审美创作中,主观感受之情与客观现象之景的沟通与交流并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制造一种难以言传的气氛,达到妙合无垠的境界。
汪曾祺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创作思想,对小说中景与人的关系,主张“要贴到人物来写”,极为强调人物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但在实际创作中,汪曾祺对人物和情节几乎没有太多描绘。比如《大淖记事》,全文仅一万二千余字,开头就用了三节篇幅全写风土人情,直至第四节才出现主要人物。看似是闲来之笔,实则是一气呵成,少一分则太少,多一分则太长。开头对大淖水性地域的描绘,水不止是故事的叙述背景,“水”的意象还浸染了人物与情节。水孕育了自然和人,人物的性格也具有水之特性,明澈如水,真率而自然。十一子和巧云的故事,也只有置于大淖这种独特地域民情文化中,才会被理解与发生。汪曾祺小说中写景即是写人,景中处处离不开人物的色彩,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意境。
这种诗化的审美风格,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成,而“气”是贯穿于汪曾祺创作的根本性线索。他曾明确提出“气氛即人物”[2],即写景及人,重气氛,重意蕴。这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诗人气质,可以从其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中探寻文中之“气”。汪曾祺有意识地打破小说与散文、诗之间的界限,有的只是人物素描,透过气氛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因而他的小说中没有鲜明的典型人物,也不具有完整而复杂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像戏剧一样必须去组织尖锐深刻的矛盾冲突,有的只是根据一定的构思意图去掠取生活中某些片段和场面。因为他对于小说的书写,就是写回忆,写印象,写自己的感觉。他把笔触延伸到久远了的过去,其小说中的地名、人物和情节大部分实有其事,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如《受戒》中英子的形象,是写对于初恋的一种朦朦胧胧的印象;《大淖记事》中的“大淖”是汪曾祺的家乡,巧云和十一子的故事也有其原型。这种回忆式的写作基调,所涉及的都是一些平平淡淡的事,但写得很精致。故事情节淡化的同时,呈现给读者的反而是一种景与人合一的气氛。只有体会到这种文中之“气”,才能感受到作品中的意境。
意境美的形成,离不开作家真感情的流露。汪曾祺很善于观察生活,很有耐心地进行一点点摄取和抒写、开掘,无论是景或人物,每一个细节都写得很细致。文学就是要反映真切、真实的生活,汪曾祺在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挚爱中,刻画了更真实更深刻的客观生活。他曾多次称自己是“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3],对作品中的人物充满了温爱和同情。他的作品中大都是一些小人物,但是都充满了人情味,如《岁寒三友》《陈小手》等诸多作品,流露出对下层人民生活艰苦的同情;《大淖记事》《钓鱼的一生》等作品,表现出对义气之举的赞赏;《鸡鸭名家》《天鹅之死》等充满了对世道人心的关注。他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可见,人道主义的情怀始终贯彻于汪曾祺的创作。
但他对于自己的态度和感情,却很少直抒胸臆,而是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调去叙事。他往往将感情融入描写与叙述中,从不脱离人物去单独表达,从而使得作品更隽永,意境深邃。比如在《黄油烙饼》那个社会形势复杂的时代,许多下层老百姓都因饥荒而死,而干部却用黄油烙饼,大人们是敢怒不敢言。父子之间的对话是纯真而又不失趣味的,但最后每个人眼里都流着泪,人物之泪正是作者心中之泪。透过他们一家人的命运,隐藏着作者对历史的严峻思考,但他并没有直接控诉,而是通过一个孩童的视角,隐含在人物对生活的真实所感、所见中,把故事写得很美。即使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也从不把自己的态度和感情直接倾诉,而是流露于字里行间,通过人物去实现。因此,汪曾祺对于环境或景物的描写,都是次属于人物,因人物而设定,即设置一种气氛的存在,让人物自己去感受。只有人物在其气氛中的感受是真的,读者才能真切感触到人物所生存的世界。这种贯注于人物身上的真感情,使人物神气十足,让小说的叙述也更含蓄,更富有美感,同时也更动人。
二、传神入虚境:流动之美
汪曾祺有意识地去写身边平常的人和事,力图展现生活的自然本真状态。而若是一味写平淡的生活,则为作品形成艺术意境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相反的是,他写平易之事,却能平中见奇,充满诗意,体现出别有一番滋味的意境美。其因在于,汪曾祺是一位语言的大师。他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极致,“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1]总之,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把语言看作是一门艺术,在语言的“实”里,创造了一个“虚”的审美空间。
那如何进行审美创造呢?汪曾祺认为气居于形神之间,要用语言文字去捕捉人物的神气,传神比写形象更为重要。小说直接去刻画人物的形貌,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是要化静为动,化描写于叙述。如《受戒》里写英子娘女三个一起去赶集,有一大段直接用精美的语言描写她们的眼睛与头发如何漂亮,虽细致但其形象不够真切。而末尾来一句“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就把人物长得好看这一特征给点出来了,使人信服。又如《大淖记事》叙述巧云的美,也是通过写别人看到她的反应,以及对她的欣赏和倾慕,间接把人物写“活”了。用美的效果来写美,远比单纯描写外貌怎样美更生动。同时,汪曾祺也很注意表现人物动态美。比如《大淖记事》刻画巧云的形象:“忽然回头,睁的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像听到远处有人叫她似的。”[4]读者感受到的是人物的一种动态美,一种流动的气韵。这种美感,更能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在动态中形成静物的意象。这种写法虽有技巧,但不露痕迹,自然妥帖。作者的写法是虚的,但读者的感受是实的。
同时,将有形之“象”引向虚无之境,也离不开语言文字的运用。清代桐城派刘大櫆认为神气是虚的,必须通过音节字句来体现。汪曾祺极为推崇,也很重视炼字析句。汪曾祺对于语言用字的锤炼,一是从民间文化与古典文化中汲取经验,以俗为雅,化古典为现代;二是对普通词汇的推敲和雕琢,偶尔来个奇字奇句的运用,淡中见奇。他对“竟”“而”“呜呼”“矣”等虚词的巧妙运用,以及在小说中的用典,表现出他对民间口语及古诗词的熟习。汪曾祺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也极为入微,如描写过夜的马在咀嚼草料时不仅是“安静”地,而且是“严肃”地。“严肃”一词是很常见的字眼,但极少有人将其置于此种情境下,这种运用既新颖又生动。只有作家在生活中进行深入地观察,才能有自己独到的体会,给读者留下真实的印象。汪曾祺的字词看似平淡,其实极耐人寻味。恰当的言辞对文中的气势形成很有作用,语言准确了才能传神,才能有境界。
汪曾祺不止讲究于用字,还极为重视语言的流动性。用字的精确与凝炼,是语言气韵生动的前提,而内在的流通正是语言之神气所在。汪曾祺把语言比作流动的水,像写字一样要讲究行气。他认为,“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1]因此他极为重视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的联系,要文气贯通,讲求语言的音节之美。他认为韩愈的文气说所提到的“言之短长”和“声之高下”,就是语言的内在节奏,是文气充盈于文本不同形式的表现。汪曾祺小说中的句子可长可短,也可交互运用,也有对仗与平仄,在无声中自然形成一种抑扬抗坠的节奏美。他在《羊舍一夕》中写道:“有很多鸡,都一色是白的;有很多鸭,也一色是白的。风一吹,白毛儿忒勒勒飘翻起来,真好看。有很多很多猪,都是短嘴头子,大腮帮子,巴克夏,约克夏。”[1]在行文声律的高低错落中,平常的语言显得更富有节奏和表现力,形成了一种连贯之气。
汪曾祺诗化语言风格的形成,就在于他极为重视文中之“气”。“气”之审美使语言文字不再是单纯枯槁的堆砌,而是活的,将文章的各部分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一种贯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同时也是作者精神的体现,包含作者的气质与感情,是作家凝神聚思之“气”,显现出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这种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又富有创造力的语言,使作品更加虚灵生动和淡远超越,与其它各要素融为一个整体,使作品在平中见奇的氤氲气氛中进入意境。
三、韵外之致:蕴气之美
唐代司空图提出了“韵味说”,他在《与李生论诗书》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5]他认为意境的韵味不仅有韵内之韵,而且还有韵外之韵,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揭示了意境中所蕴含咀嚼不尽的美的审美特征。汪曾祺作品内容具体、真切而生动,又包含了深厚的意蕴,含不尽之意,正是进入了这种意味无穷的艺术世界。
汪曾祺小说追求的含蓄之美,与中国的传统画论是一脉相承的。受其父影响,汪曾祺非常喜欢画,同时也把绘画中的一些艺术原则自然而然运用于写作中。他在创作之前,也像画画一样,“先有一团情志,一种意向……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凛气禀神构思好才写,否则会思绪纷杂,文气不贯。[2]定气的目的是要慢慢地写,尽量少写。他把中国画中“计白当黑”的审美原则引进写作,认为小说的艺术也要“留白”。“留白”是指不能直接将人物与故事说尽,要让读者去思索与想象,形成一种言尽而意无穷的意境之美。
汪曾祺小说中的空白,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讲究一种深藏的意义。他很重视语言的暗示性。他认为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于语言的言外之意,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1]《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与十一子夜晚在沙洲幽会,汪曾祺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大自然的浪漫场景只字不提,只写了一句:月亮真好啊!但读者能从弥漫的氤氲气氛中感受到这对小儿女的美好爱情。又如《职业》中那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本是一句简单的民间俗语,但极为容易就引发了读者对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小孩深切的同情。通过小孩的叫卖声,表现出了人物的生活气貌以及背后的艰辛,语浅而意深。
汪曾祺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含藏的空白还体现在结构的随便性上,但这也是苦心经营的随便。[2]与其说结构,汪曾祺重视的是文章的整体节奏。他小说中这种自然无形的结构,就是文中之“气”所形成的内在节奏。因而他主张小说的散也是精心琢磨过的,特别是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在《徙》的开篇,只有一句:很多歌消失了。据作者回忆,这是他反复斟酌,删稿重写而成。这一句十分简练的开头,基本上就定下了文章的基调,引发读者想象,使下文带有怀旧之气。又如《受戒》结尾只提到了英子和明海把船划进芦花荡,写了一段充满诗意的景物描写就戛然而止了。“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4]作者描绘了一幅清丽的图景,寓意深远,语短意长,使读者对这段爱情的结局进行无数的猜想。对于故事情节,作者也有意隐匿。如在《故里三陈·陈四》的开头,只交代了陈四是一个瓦匠,接着用大篇幅的笔墨去描写迎神赛会,把民俗风情写得很细致,而主要人物、情节等构成要素被淡化。但在散漫的叙述之中,有着内在的凝聚之气,使文章的内在的节奏和有机联系很强。因此,在虚实交错的空白之处,自然而然地就带入了某种不确定的、难以言传的气蕴,使读者的想象空间增大,扩大加深了作品的内涵。还有诸如《陈小手》《复仇》《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有通过有意的留白,使读者去想象,指向作品背后的逸气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