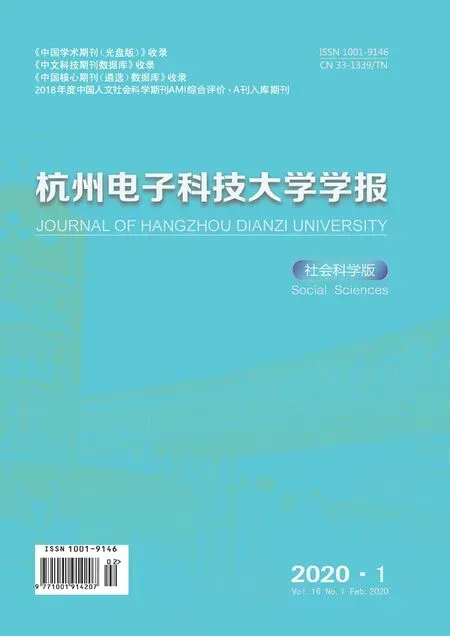王维诗歌中的多重自我
——兼论王维部分诗作的再理解
刘万川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1]477这是王维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当然,诗句带有戏说成分,但综观王维诗作,诗人确实存在着一种有意识的自我形象塑造和呈现,并且,不同时段、不同环境中王维的诗歌中的自我形象都不相同。
一、自我形象的时段性
王维诗作中的自我形象存在时间上的阶段性特征。随着仕途的起伏,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作者入仕之前基本没有对个人身份的表达,自太乐丞被贬官之后,直至任右拾遗期间,开始屡次提及自己的身份。如开元九年,自太乐丞“坐累济州司仓参军”[2],《被出济州》中提到自己的身份——“微官易得罪”[1]37,慨叹“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宿郑州》说自己是“孤客亲童仆”“穷边徇微禄”[1]39。《和使君五郎西楼望远思归》是在济州之后的作品。“能赋属上才,思归同下秩”[1]50,对自己司仓参军的低级官吏身份深以为然。也正是这种在意,他在写给张九龄的干谒诗歌中才更为谦卑和恭敬。“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上张令公》)[1]102之句,说自己宁可列居人群之末,也要跟从张九龄。《献始兴公》中“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1]112之句,干脆直接谦称“贱子”。
王维这一时期的作品,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往往显露自己的宦游和孤独者形象。如“已恨亲皆远,谁怜友复稀?”(《送崔兴宗》)[1]101“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山中寄诸弟妹》)[1]112等。还有《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一诗,与内弟的离别中更加强调自己的背井离乡。还有《观别者》中“余亦辞家久,看之泪满巾”[1]68一句,说明个人的漂泊,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所说,“只写别者之情,观字只末二句一点自足。”[3]
任右拾遗之后,是王维一生中较为平淡的一段时期。期间创作的应制酬唱类诗歌,对个人普通官员身份的自我认识都中规中矩,既没有骄傲,也无牢骚不满。如《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中的“侍从有邹枚”[1]126,是自认文学侍臣;《和尹谏议史馆山池》中“君恩深汉帝,且莫上空虚”[1]128,是对帝王的颂扬。天宝元年,王维官居左补阙,朋友丘为落第,自己难以施助,所以说“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送丘为落第归江东》)[1]210与苑咸酬唱的《重酬苑郎中》有 “仙郎有意怜同舍”[1]258句,苑咸已经是郎官知制诰[4],自己身份稍低,却是不卑不亢的态度。
这一时期王维有较多赠诗,体现出的人生追求颇为矛盾。如《送崔三往密州觐省》是河西时所作,“鲁连功未报,且莫蹈沧州”154[1],希望崔三继续功业,不要归隐。《送赵都督赴代周得青字》称“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1]189也是唐代常见的功业追求。但他又常常流露出归隐之意。在长安为监察御史时作《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首》,第二首中“归欤绌微官,惆怅心自咎”[1]162,其他还有《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给事首春》中“素是独往客,脱冠情弥敦”[1]119,《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中“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1]222,《送张五归山》中“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1]274。与佛教中人的交往也表现出归隐愿望。如《资圣寺送甘二》:“浮生信如寄,薄宦夫何有。”[1]166不但提到人生如寄的感慨,而且直接提出为官的厌倦。还有《投道一师兰若宿》,其时道一在终南山太白峰,“岂为暂留宿,服事将穷年”[1]196称自己将在这里安居。形成对比的是,王维在担任拾遗之前有《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虽然诗中也有“隐者”“东山客”“采薇”等词语,但并无归隐意愿。
这一时期也有部分自处的诗作,应该更接近作者本心。如《终南别业》是隐居与终南所作,“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1]191,诗意随缘任性,却颇为孤单;《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中“吾生将白首,岁晏思沧洲。高足在旦暮,肯为南亩俦”[1]300,对亲戚抒写内心。
天宝后,王维诗中作者的隐者形象越发明晰,尤其在辋川隐居的诗歌中较集中体现。如:
《积雨辋川庄作》:“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1]444
《归辋川作》:“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1]448
《山居即事》:“鹤巢松树偏,人访蓽门稀。”[1]450
《山居秋暝》:“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1]451
《早秋山中作》:“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1]468
为安史叛军伪官后,王维内心恐惧羞愧,《谢除太子中允表》曾写道:“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伏愿陛下中兴,逆贼殄灭,臣即出家修道,极其精勤,庶裨万一。”[1]1003此时诗作中再无官员职责言说,都是说自己年岁衰老。她乾元元年有《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自怜黄发暮,一倍惜年华。”[1]492乾元二年有《送韦大夫东京留守》:“壮心与身退,老病随年侵。”[1]506《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寒更传晓箭,清镜揽衰颜。”[1]529
不同时段,个人形象不同,可谓归心日重,俗念日轻。
二、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自我
上文中,王维对诗歌中自我形象的呈现和认知,在趋势上恰好印证在王维仕途上的高低起伏。但无法解释王维的同一时期,为何出现矛盾的思想感情表达,比如崇佛与入世、归隐与为官的矛盾,赠诗中劝人出世与劝人归隐的矛盾。这种矛盾与其内心纠结有关,也与诗歌写作所具备的社会性有关,后者是下文讨论的重点。
古代诗歌的言志说与缘情说是着眼于创作内因,而表达与交际则是创作的外在动力,故有“兴观群怨”之说,这也是诗歌的基本功能。在不同的创作场合,内外因素发挥的作用不同。诗歌作为抒情工具,到底是一种自我表达,作为交际工具时,奉和应制,友人酬唱,抑或是寄赠送别,其写作目的所限定,诗歌在疏解个人情绪的同时还要标榜主张,注意诗作所产生的观众反应。所以,诗歌的写作场合,是与人唱和赠答还是自言自语,诗人对自我形象的呈现自然受到这种“场”的影响。个人都具备社会身份并牵扯社会关系,诗人既是朝中大臣也是家中丈夫,对方既是同僚也是朋友,这种身份促使他在创作时必须照应自己的社会属性。同时,每个人也都是单独的个体,他们久在樊笼,又常常在无人时吐露心声。所以,不同的写作环境,王维诗歌中就有不同形象。
在自我独处时极其在意个人的年龄与身体,而非功业理想。如《叹白发》:“我年一何长,鬓发日已白。俯仰天地间,能为几时客?怅惆故山云,徘徊空日夕。何事与时人,东城复南陌。”[1]390这种感触和个人情绪以及所呈现出的老病形象,在公共创作唱和场合都没有出现过。
与家人的创作多表现出长兄身份。王维诗文未提及父母,或是因其早逝。据《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河东王氏》,王维有弟:缙、繟、纮、紞。王维与兄弟姊妹的诗歌中所呈现出的自我感情多是对弟妹的怜爱:《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即是对家中兄弟的思念,《山中寄诸弟妹》是自己的孤单与相思;还有《别弟妹二首》其一:“两妹日成长,双鬟将及人。已能持宝瑟,自解掩罗巾。念昔别时小,未知疏与亲。今来始离恨,拭泪方殷勤。”[1]1213语句中充满慈爱。另外《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一诗,是对个人经历的总结感慨:“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无出人智。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清冬见远山,积雪凝苍翠。皓然出东林,发我遗世意。惠连素清赏,夙语尘外事。欲缓携手期,流年一何驶。”[1]349其中对自己的仕途评价颇为低调。
王维以官员身份写作时,诗歌倾向就因人而异。大部分送别同僚的诗作,只是着眼于客套送别、祝福前程,个人隐没其中。面对高级官吏,则诗作整体表现为谦卑。如《献始兴公》中“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1]112,《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中“司鉴方无阙,陈诗且未工”[1]216。对方如果是隐士或被迫归隐,便畅谈归隐之乐。如《送张五归山》:“东山有茅屋,幸为扫荆扉。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1]274《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羡君栖隐处,遥望白云端。”[1]280对志同道合者便谈理想,如《济上四贤咏·崔录事》中“已闻能狎鸟,余亦共乘桴。”[1]43《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中“明时久不达,弃置与君同。……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1]222对方若是方外之人,则多写个人对生命和佛法的见解。如《资圣寺送甘二》:“浮生信如寄,薄宦夫何有。”[1]166不但提到人生如寄的感慨,而且直接提出为官的厌倦。还有《投道一师兰若宿》:“岂为暂留宿,服事将穷年”[1]196,《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1]228,所表现出的对自己生命追求的转向。《酬黎居士淅川作》:“侬家真个去,公定随侬否?着处是莲花,无心变杨柳。松龛藏药里,石唇安茶臼。气味当共知,那能不携手!”[1]232这种应急走笔之作,更不能以此推断作者真实理想。
与此相关,诗歌不但在抒情的直白与隐晦上照应了人物的远近亲疏,在写作手法、措辞炼句上也随之变化。典型体现就是应制宴游和谈禅说佛两类作品风格的截然不同。
王维自开元九年擢进士第,解褐太乐丞,虽其后多有贬官与归隐,但司仓参军、右拾遗、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左补阙、库部员外郎、库部郎中、文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以及最终的尚书右丞,均属于官员身份。王维的应制类诗作,结构上具备传统宫廷诗歌特征:即主体部分歌颂盛德,诗歌结尾放低身段,呈现出谦卑的臣子形象。例如《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明君梦帝先,宝命上齐天。秦后徒闻乐,周王耻卜年。玉京移大像,金篆会群仙。承露调天供,临空敞御筵。斗回迎寿酒,山近起炉烟。”[1]212诸句都是颂圣,到尾句“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呈现自身一心奉道的自我。再看其干谒类作品,如《上张令公》前半部分称许张九龄的功德,其后“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1]102连用汉人故事说明自己的遭际,然后请求张九龄的引荐。再如《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写给李林甫,也是先称许李其后以自谦结尾,“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1]216,不无谄媚之意,但却是干谒类作品常态,亦不可理解为王维对李林甫的真实态度。此类作品旨在颂圣干谒,作品要求典雅端正,诗歌中整体铺排,诗人自我隐没,凸显奉承之意。
佛禅类作品用语常取佛典,表意空无。《与苏卢二员外期游方丈寺而苏不至因有是作》:“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回看双凤阙,相去一牛鸣。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手巾花氎净,香帔稻畦成。闻道邀同舍,相期宿化城。安知不来往,翻以得无生。”[1]340《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龙钟一老翁,徐步谒禅宫。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莫怪销炎热,能生大地风。”[1]362就都使用了较多的佛教用语,既见王维佛教造诣之深,又见诗人出世之想。
三、“创作场”与王维部分诗歌的再理解
不同的创作环境,诗人不同的自我认知,造成了诗歌中多种自我形象,甚至是自我的隐没。反过来,对诗作的理解必须结合当时的“创作场”。这里要说明的是王维的《辋川集》与《偶然作》两组诗,传统解释存在部分偏颇。
这两首诗都是同咏作品。同咏必然有相同的因由,所以指向明确。如王维有《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一诗:“绿树重阴盖四邻,青苔日厚自无尘。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1]289卢象同咏《同王维过崔处士林亭》:“映竹时闻转辘轳,当窗只见网蜘蛛。主人非病常高卧,环堵蒙笼一老儒。”[5]1221王缙同咏《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身名不问十年余,老大谁能更读书。林中独酌邻家酒,门外时闻长者车。”[5]1311裴迪同咏《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乔柯门里自成阴,散发窗中曾不簪。逍遥且喜从吾事,荣宠从来非我心。”[5]1315都有清凉林荫,都有隐居的主人,也都有主人与外在尘世的隔绝。又如王维《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和裴迪同咏之作,二者着眼于寺庙的幽静,并使用大量的佛教用语。
同时,同咏诗作必然面对其他作者和观众,诗歌便具备了社会性和表演性,语句中的感情需要理解中加以消解。如《别辋川别业》,若只看王维诗作:“依迟动车马,惆怅出松萝。忍别青山去?其如绿水何!”[1]466对辋川难舍难分,情深义重。但王缙也有同咏之作:“山月晓仍在,林风凉不绝。殷勤如有情,惆怅令人别!”[5]1311诗歌中对辋川别业也同样感情深重。王缙史料记载不多,但他也未曾有王维坎坷复杂的经历,是否在辋川有过长期居住也未可知,所以单纯分析诗歌文本,结论却有些令人生疑。同理,王维还有《崔九弟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城隅一分手,几日还相见?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1]292裴迪有同咏:“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5]1315王维诗作偏重于对崔九弟及时归隐的欣赏,而裴迪则着眼于希望其长期留于山中,隐在桃源,说明同咏之作可以有不一致的趋向。
王维同咏类诗歌多与友人同游所作,如《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就是与裴迪同游同咏。《辋川集》也是如此。《辋川集序》说:“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1]413考察王维与裴迪各自的诗歌,可以发现两组绝句实际创作于同时,是一组有意识的组诗写作,且二人有意识相互呼应。比如《孟城坳》,王维诗句“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1]413与裴迪“古城非畴昔,今人自来往”[5]1312-1315都在说明今昔对比;又如王维《斤竹岭》有“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1]416裴迪同咏有“明流纡且直,绿第密复深。一迳通山路,行歌望旧岑。”[5]1313对景物描写的视角,显现出二人属于同游之作。既然辋川绝句是在具备观众的情况下的创作,且有友人同时写作,其中“场”的影响和表演性不容忽视,而不能只就文本自身作单独分析。
如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1]425或有学者解释为以辛夷花的自开自落表现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但考虑到裴迪同咏诗作:“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5]1315虽然两诗很难区分创作的先后,但却可以相互印证。裴迪诗称辛夷花的颜色与芙蓉近似,王维诗作直言“木末芙蓉花”;王维诗作称花开又落,裴迪诗云“绿堤春草合”,均为暮春花落草密时节。两者从相同和不同的角度写景色之美与环境之幽,王维重在无人环境中的花开花落,裴迪重在《招隐士》典故中隐居情绪的传达。
再如《鹿柴》,王维诗作:“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1]417裴迪诗作:“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松林事,但有麏麚迹。”[5]1313二诗描写时间一致:一为返景复照,一为日夕;环境一致:一为空山深林,一为寒山松林;人物一致:一为空山人语,一为独往客。所相异者,裴迪尾句既写人兽罕至,又用《楚辞·招隐士》:“白鹿麕麚兮或腾或倚”[6]句。或谓王维常纯写自然而裴迪喜好用典,那再看吟咏归隐的《漆园》。庄子曾为漆园吏,王维诗作为“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1]426首句用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7],尾句用《世说新语·黜免》中殷仲文“槐树婆娑,无复生意”[8]语,相比裴迪同咏之作:“好闲早成性,果此谐宿诺。今日漆园游,还同庄叟乐。”[5]1315倒是更为随意的表达了。
王维与裴迪本就有较多唱和,如《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以古人为赠,《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中有句“君问终南山,心知百云外”[1]430,《赠裴十迪》称“风景日夕佳,与君赋新诗”,“请君理还策,敢告将农时”[1]430,还有《酌酒与裴迪》中的“酌酒与君君自宽”[1]435等等。上文所述的《辋川集》中几首名作的共同特征都是王维与裴迪的唱和。如果以唱和诗理解,王维《辋川集》就并非单纯抒情,而是带有游戏和标榜性质。站在写作“场”的角度,常见的对此类诗歌的解读,尤其是从佛理方面对王维诗歌的解读恐有过度阐释之嫌。
与此类似的还有王维《偶然作》和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1)《偶然作》原六首,陈铁民先生认为实为五首,且非同时所作,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均见《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七,相关事迹又见陈铁民《储光羲生平事迹考辨》,《文史》第十二辑。,也是同咏组诗。《偶然作》并无小题目,但从所咏事物依然可分析线索和主题。王维诗作:“楚国有狂夫,茫然无心想。散发不冠带,行歌南陌上。孔丘与之言,仁义莫能奖。未尝肯问天,何事须击壤?复笑采薇人,胡为乃长往?”[1]69储光羲诗作中有“狂歌问夫子,夫子莫能陈”[5]1385;“孔丘贵仁义,老氏好无为”[5]1384。王维诗作有“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黄金买歌笑,用钱不复数。许史相经过,高门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邹鲁。读书三十年,腰下无尺组。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1]76储光羲有“妾本邯郸女,生长在丛台”[5]1385;“逶迤歌舞座,婉娈芙蓉闺”[5]1385;“朴儒亦何为,辛苦读旧史。”[5]1385从题目上看,王作在前,储作在后。同理,对《偶然作》的分析亦不能纯粹从王维自咏来阐释。
还有颇具争议的一首诗:
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1]477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尝自制诗曰:‘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馀习,偶被时人知。’诚哉是言也。”[9]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记载类似。但细读张彦远语意,其重点乃在辋川图与绘画技能,“自制”非言题画,而是在“尝”。《唐人万首绝句》取中四句为绝句,题曰《题辋川图》,或是错解王维诗意[10]。王维此诗与《偶然作》中“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孙登长啸台,松竹有遗处。相去讵几许,故人在中路。爱染日已薄,禅寂日已固。忽乎吾将行,宁俟岁云暮。”[1]73都带有对外宣讲特征,旨在说明个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这与同组另五首诗歌存在的“创作场”的影响是一致的,因此王维《偶然作》的唱和性质,是理解其抒情内涵时不可或缺的因素。
四、结语
王维诗歌中的不同自我形象有自身随着年龄、仕历而来的自然变化,也有不同创作环境带来的不同标榜性形象。诗歌创作在自我言情与面对读者时既然不同,诗作中也自然有不同的诗人自我出现,这是“以意逆志”时不应忽视的因素,切不可只单纯停留于文本,进行想当然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