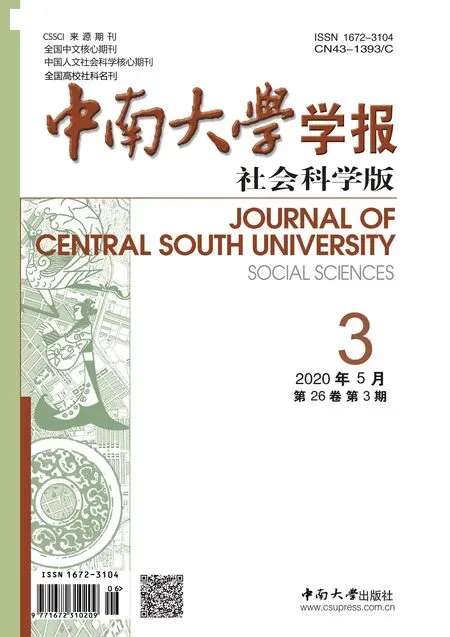中国现代“女性自由”主题话剧中的多重话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自晚清“废缠足、兴女学”女权运动开始,到“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关于“自由”的思想观念经由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译介对中国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两股浪潮的合流中,“女性自由”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话题。然而,“女性自由”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复杂与艰难却未因讨论的热烈而变得明晰或简单。相反,种种不同话语对“女性自由”的遮蔽、置换、曲解、利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围困“女性自由”的话语之网。这种情形在叙事者隐没而以人物台词为主要内容的话剧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本文将通过对中国现代“女性自由”主题话剧中的多重话语的辨析,探讨“女性自由”话语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现代女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困境,呈现宏大叙事遮蔽的隐微历史图景,探究话剧艺术所可能实现的反思与突围。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语境中,“女性自由”是一个不易界定的复杂概念,它并不只是对“自由”所涉的主体加以限定,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和外延。“女性自由”,简单地说就是指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被干涉与阻碍,其外延主要包括婚恋自由、社交自由、受教育的自由和获得职业的自由等——这也是多数“女性自由”主题话剧集中表现的内容。我们很难在以赛亚·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区别“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框架中对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的“女性自由”做进一步区分,因为面对当时极其狭窄的女性自由空间,即使为了在最低限度上免于受到外部干涉(即实现“消极自由”),也必须通过充分发挥个体自由意志的行动来主动争取(即实践“积极自由”)。因此,诸多社论和作品中所呼吁的女性“自决”“自主”也是“女性自由”的重要内涵。此外,还应意识到,以男性启蒙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女性自由”倡导者们最初大多是出于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忧虑而关注女性问题,他们更多是在“个体/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中而非“男性/女性”的框架之来中理解“女性自由”问题,他们对“女性自由”的呼吁所指向的是民族国家利益和新的社会政治图景,而这一命题本身所具有的性别内涵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对于其中隐含的问题,许多剧作予以了揭示和反思。
根据以上对“女性自由”的界定和理解,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自中国话剧诞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女性自由”为主题的四十余部剧作①,通过分析其中典型作品的话语来理解剧作所折射的“女性自由”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话剧艺术对于争取“女性自由”的话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一、社会舆论的围困与话语的突围
在众多“女性自由”主题剧作中,不同身份、立场的人物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现实诉求出发,发出了彼此交汇或交锋的多重话语。其中不少台词虽然出自某个虚构的剧中人物之口,实际上却是当时某种舆论声音的回响。诚如巴赫金所说:“任何一个被说熟了、被争论过了的对象,一方面是得到了阐明,另一方面又被杂语的社会意见和他人议论所遮蔽。”[1](56)当不同身份、立场的人们共同谈论“女性自由”时,这一话题本身也在纷杂的社会意见中变得复杂、模糊。在观念冲突、利益冲突以及强大历史惯性的作用下,社会舆论中出现了对于“女性自由”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和压制。这是“女性自由”在话语层面所遭遇的第一重困境,也在话剧作品中留下了显见的痕迹。
中国近现代“女性自由”观念的产生是以对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思想资源的译介与整合为基础的,它所形成的是一套全新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然而,对于没有接触过西方近现代启蒙思想体系的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往往是在既有的认知系统中理解“自由”“平等”等新概念,因此容易产生望文生义式的误解。欧阳予倩《泼妇》(1925)一剧的开篇,陈以礼老先生便感慨道:“现在这些人说的话,我真不懂,作的事越发不懂!”[2](37)陈以礼夫妇对儿媳素心的讨论,即体现出两套话语体系的隔阂:
陈以礼风头总是要出的,爱情总是要讲的,自由总是要学的。
吴氏要说自由呢,像我们少奶奶哪些儿不自由?麻雀也让她打,大世界新世界也让她去逛;她自己不打不逛怪谁呢?不过她是疯疯癫癫的学时髦罢了。[2](38)
吴氏所谓的“自由”是作为笼中玩偶的“自由”,素心所追求的自由却是要打破笼子、改变玩偶的地位。她的这种追求始终不能被长辈所理解,因为在长辈的话语系统或思维系统中,只存在顺从丈夫的“贤妻”和不服从丈夫的“泼妇”,而不存在将妻子视为独立个体的观念,更无“自由”“平等”的观念。因此,素心从人人平等的观念出发,与“小妾”王姑娘以礼相见,便被赞为“贤惠”;她同样是从人人平等的观念出发,要求解放并带走王姑娘,便被斥为“泼妇”。素心言行一致,却顷刻之间得到两种相反的判定。而陈慎之从学生时代起就宣扬平等、解放、“永不讨小”,婚后却买人、纳妾,反被视为平常。人们无法在传统的伦理系统、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中理解“自由”“平等”等来自另一套价值体系的观念,然而这些产生于传统价值判断体系的舆论话语,仍以道德、责任等名义对女性施压,使追求自由的女性承受着沉重的心灵负荷。
在徐益棠发表于1920年的五幕剧《赘婿》中,女主角朱华玉被要求服从父亲的遗愿赘婿。华玉虽然理智上知道不应以自己的终身幸福来换得“孝女”的名声,但最终还是痛苦而无奈地选择了服从。她感慨道:“做女儿的真不自由!……我顾了我自己的幸福,那社会要骂我,父母要恨我;我迎合了社会、父母,我自己的良心要责备我。”[3]女性,尤其是走出深闺,走向社会公共空间所谓的“新女性”,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社会的注视甚至是监视之中,稍有与旧例常规不同之处,掌握着话语权力的匿名复数群体就会通过舆论手段对她施加压力。这种话语规训往往会进一步内化为自我审查和自我约束,牵制着女性对自由的追求。
如果说上述剧作表现的是不堪负荷的“自由”之重,那么还有一些剧作则反映了同样不能承受的“自由”之轻。在鸳鸯蝴蝶派作家金啸梅的一幕两场剧《五点钟的婚约》(1922)中,一女子与男子订婚之后又打着“自由”的名号很快取消了婚约。男子感叹说:“唉,自由恋爱,做了五个钟点的未婚夫妻,可叹!”[4]顾一樵的四幕剧《孤鸿》(1923)讲述的也是“自由恋爱”的伤痛,被抛弃的未婚妻自我宽解,“爱情不是勉强的,自由恋爱本来很自由的”[4];失去女友的男子则强烈不满,“什么自由恋爱?女子禁不住一顿大菜一 场舞的诱惑就变了心”[5];婢女则直白地戳破“自由恋爱”的伪饰,“要不是少爷看小姐标致,小姐看少爷阔绰,哪里会有什么爱情不爱情的!”[5]
五四以来,社会大众对“女性自由”的关注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婚恋自由”上,而“自由恋爱”的思想在青年男女中传播之后,的确产生了一些以“自由恋爱”为托词的现象[6](84−85)。上述剧作反映了这类社会现象,也传达出社会舆论对于“自由恋爱”问题的一种意见和看法,与此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大众对“新女性”的误解和偏见。事实上,任何一种话语模式都是“对现实的简化,目的是要通过强调某些重要信息而舍弃一些细节,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现实”[7](62)。而在简化取舍的过程中,不同的话语面对相同的现实“素材”,则传达出不同的价值倾向与现实诉求。上述两部剧作对社会现实的简化取舍,只强调了“自由恋爱”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却缺少深刻的追问和多维的观照。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剧作则试图通过塑造追求自由的正面女性形象来从这种舆论话语中突围。署名为E.C的五幕剧《女界之光》(1926)即通过展现女校学生朴素、进取、自律、关心社会的正面形象,驳斥了第一幕剧中社会上对于女校学生的偏见。不过,剧作完全避开了社会舆论中评判“新女性”时最尖锐、最集中的问题——婚恋问题。虽然这是出于某种策略性的考虑,但也自我窄化了“女性自由”话语,加之人物塑造的扁平与情节安排的松弛,剧作的反驳略显无力。
相比之下,面对社会舆论的种种围困,真正实现话语突围的是另一类剧作,这类剧作不仅针对社会舆论的内容进行了反驳,而且直指这种话语运作的方式。只有在这一层面上对种种围困进行拆解,才能从那些对女性行为进行命名和道德评判的整套话语系统中解脱出来。欧阳予倩的剧作即是如此。
在欧阳予倩的独幕剧《回家以后》(1922)中,自芳发现留学归来的治平巧言掩饰他与玛利的私情,遂嘲讽道:“中国的学堂里为什么不设言语一科?美国的学堂是很注重这一科的。”[2](8)事实上,欧阳予倩剧作的长处就在于对“言语”的敏感,而剧中的女性角色往往正是因为拆穿了话语的圈套,才敢于用新的话语支持自己的行动,有理有据地做出舆论所不赞同的选择。
在五幕剧《潘金莲》(1927)中,潘金莲面对武松称她为“淫妇”的指责,昂然对曰:“本来,一个男人要折磨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帮忙,乖乖儿让男人折磨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折磨而不死的,就是淫妇。”[2](77)《泼妇》一剧,更是层层击破了封建家庭用以维持“体面”、规约女性的话语。这套话语的运作方式就是通过含有价值判断的“命名”,将人的思想和行为限定在某种秩序之中,既以“贤妻”等“美名”诱惑人服从秩序,又以“淫妇”“泼妇”等“恶名”恐吓、禁止所谓“出格”的行为。“名”与“实”错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话语在实践层面实现对人的规训。叶绍钧曾经指出这类话语中存在的“诱惑主义”,即“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的人格”[8](126)。在《泼妇》中反复出现的关于“贤惠”的话语就是这样一种圈套,“贤惠”的“美名”之下是一整套夫权中心主义的“为妻行为准则”。剧中的姑母在将陈慎之纳妾之事告诉其妻于素心之前,屡次强调“你是个贤惠人”[2](48),实质上就是向她提出了按照“贤妻”的方式顺从丈夫、接纳妾室的行为要求。陈以礼夫妇甚至还要她对外宣称是她主动为丈夫讨的妾,表面上是为了彰显她的“贤名”,其实不过是为了掩饰陈慎之的丑行。一般情况下,妻子们对于这种“贤名”只有追求的义务,却没有拒绝的权利。而素心却清醒地拒绝了这一套说辞,“我没有这样贤惠;我,也不会作这样……”[2](48)。当“贤惠”之“美名”的诱惑失效之后,陈以礼又以“争风吃醋”的“恶名”来评判素心为争取自由和平等而要求丈夫退还“妾室”的行为。素心的反驳简洁有力,“我主意已定,不是加我些龌龊罪名,就吓得住的”[2](51)。认清语言陷阱之后,“美名”和“污名”都不能够诱惑或恐吓素心了,素心随后的出走于是具有了冲破现实阻碍与冲破话语罗网的双重意义。虽然女性自由的真正实现需要一系列社会物质层面的保障——素心能够出走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但是从话语层面对围困女性自由的种种舆论进行拆解,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欧阳予倩以他对女性的真正同情和对话语的敏感,使其剧作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都达到较高水平,也为“女性自由”在话语层面的突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二、男性“同盟者”的话语策略及其内在矛盾
如前文所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为“女性自由”呼吁的主要是男性启蒙者。但他们所谈论的“女性自由”与其说是一个具有“性别针对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和历史的针对性”[9](41)的命题。无论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还是在“五四”时期,男性启蒙者提出的“女性自由”“女性解放”等口号更多是以社会变革为诉求,并以此与“被启蒙”的女性建立同盟关系。其主要针对的不是男性的性别压迫,而是“封建”意识形态乃至当政者的政治统治,最终是为了实现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新的社会秩序的宏大目标。“女性自由”因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正如有论者指出,“女性”是“新文化斗士手中的一张牌”[10](387)。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男性“新青年”和“新女性”在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时,往往容易忽略“同盟”内部性别之间存在的冲突和问题。这些冲突隐没在公众的高谈阔论之中,但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却显露无疑。不少话剧作品所关注的正是婚恋、家庭场景,并由此勾画出被宏大历史叙事忽略的微观图景,揭示“同盟者”话语中的隐蔽真相。通过分析话剧作品中男性“同盟者”的话语,可以发现其中交织着欲望和权力的话语策略,以及话语自身的矛盾与混乱。如果说社会舆论话语对女性自由的反对、误解和质疑造成了一种外在的困境,那么男性“同盟者”话语内在的矛盾与混乱则为女性自由的真正实现增添了更为内在也更加难以辨识或挣脱的罗网。
无论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还是在虚构的话剧场景中,都存在着所谓男性“同盟者”以启蒙话语包裹、伪饰欲望的情形。最初呼吁北京大学开放女禁的徐彦之曾坦言提议的动因,不过是由于和友人对坐谈天总觉得寡味,“继而悟道,这是没有女性的缘故”[11]。这种为女性自由平等的受教育权大声疾呼的背后,实则是“红袖添香伴读书”的传统观念,并未真正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主体,而“只是为了扩大和维护男性的既得利益”[6](57)。石评梅的剧作《这是谁的罪?》第一幕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美国留学生王甫仁接到家信后准备回国,邀同学陈冰华女士同归,并做了一段求婚的表白。他从社会改造谈起,认为改造社会首在改造家庭,改造家庭即要求婚姻自由结合,继而提出冰华应当选择与他自由结合成新式家庭,以改良社会、国家。王甫仁用一个宏大的社会改造命题将他的私人欲求包裹起来,这套话语策略使他的求婚似乎具有了超越男女之情的社会意义,仿佛冰华只要赞同社会改造之必要就首先应当与他自由结婚。表面看来,两人的婚姻关系似乎是改良社会的“盟友”关系,而剧情的发展随即击碎了这套脆弱的说辞:王甫仁回国后很快就妥协,接受了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改造社会的志向未及实现,自己就先被大环境改造了;冰华自我毁灭式的复仇更与社会改造的初衷毫不相干,而是出于狂热的情爱。
如果说这种借由“女性自由”启蒙话语建立的“同盟”关系在最初就隐含着伪饰与矛盾成分的话,那么这种矛盾在男性“新青年”与“新女性”走入婚姻家庭之后则更加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关系结构的变化:面对作为共同敌人的传统势力、封建家庭结构时,男性“新青年”是“新女性”的“盟友”,可以与她们一道争取“自由”;然而当女性在“同盟关系”内部要求“自由”时,利益关系的变化使男性“同盟者”的态度和立场就变得矛盾而暧昧了。另一方面是由于当他们将对于“自由”的象征性追求落实到复杂的现代日常生活之中时,也不得不面对尚无充分的物质性、制度性条件保障的自由如何实现的客观现实。而现实的坚硬与复杂则毫不留情地戳破话语的表象,显露出其中的虚伪、脆弱和矛盾。
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1919年,潘韧秋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独幕剧《妇女解放者的家庭》,虽然该剧剧情比较简单,但别具洞察力地关注到社会公共空间之外的家庭内景,揭示了在报刊上支持女性自由的公共发言人于私人生活中表里不一的另一套话语。男主角“某甲”在扮演“妇女解放者”角色的同时,在家庭中却不肯放弃封建纲常赋予“丈夫”的权力和利益,搬出“女出从夫”的“古话”,阻止妻子接触新思想,要求她绝对服从自己。他将对外和对内的两套话语隔绝开来,以在社会和家庭两处都获得最大化的个人利益。然而在赵先生突然来访的戏剧性场景中,从旁躲避的妻子听见赵先生对某甲报刊文章的盛赞,于是径直向访客揭示某甲的言行不一,赵先生惊讶地拂袖而去,妻子亦提出离婚,某甲的“两个世界”在打破隔绝之后随即崩塌。
张鸣琦独幕剧《残疾》(1926)中的男主角则通过更为复杂而虚伪的话语策略,借一次偶然事故大做文章,撕破他“支持”妻子自由参加社会活动的假面目,让妻子重新成为“家庭的奴隶”。这次偶然事故就是,在妻子暂时离家参与“自由协进会”的活动时,独自在家的孩子从床上摔了下来。先回到家的丈夫发现孩子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痛心之余似乎终于找到了阻止妻子继续参加社会活动的理由,要求妻子“为了泉儿的关系,要停止一切社会活动,安心地在家里看护着他!”[12]面对妻子的申辩,他搬出“女人的自由是在家里,社会上没有女人的地位”[12]的论调,偷换“自由”概念,甚至直接要求妻子做出牺牲,“我也爱自由!然而现在的我,为了你们父母,已把自由整个地弃掉……不到社会上奔劳……我早已牺牲了自己,你还不能牺牲?!”[12]妻子无法摆脱对于孩子残疾的负罪感,也就无法反驳丈夫以此为据的要求。她最终选择退出“自由协进会”,重新成为家庭主妇,既是屈从于丈夫的强词夺理,也是因曾经支持她的丈夫如今的态度而为女性自由的理想感到绝望。剧作最后讽刺性展现丈夫享受着重新将仆人、孩子都交由妻子负责的安闲,而孩子的残疾——作为他责备妻子最有力的理由——直到最后才被他“忽而又想起”。
建立联系,建构身份,皆是话语的重要功能。剧中丈夫的主要话语策略就在于通过话语重新建构了事件之间的联系,将孩子的意外与妻子的社会活动表述为因果关系,使妻子的社会活动与其家庭责任之间形成矛盾,再借助作为“权力装置”的家庭关系结构,强化妻子的家庭角色而否认其作为社会成员独立个体的身份。家庭关系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家庭中的人由于“为家小所累”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对于每位成员而言皆是如此。然而它之所以对女性的束缚更大,在于女性的行为被置于家庭系统中加以解释的频度远高于男性[13](161)。比如剧作中妻子参与社会事务,就会被丈夫判定为“把为妻为母的责任忘了”,反之,男性参与社会活动却很少会被认为是不顾“为夫为父的责任”。而通过让妻子对孩子、仆人直接负责,她作为母亲和主妇的身份则进一步被强化,脱离旧家庭的妻子再次深陷于新家庭的关系网结之中。剧作展现的场景,在新文化运动热潮过后的现实生活中有着普遍性②。而男性“同盟者”利用话语策略重构的家庭性别权力关系,也悖离了他们此前作为“同盟者”的立场。
如果说独幕剧《妇女解放者的家庭》表现了男性“同盟者”的虚伪,《残疾》表现了进入婚姻之后“同盟”关系的崩溃,那么陈白尘的五幕悲喜剧《结婚进行曲》(1942)则是在三年的时间跨度中呈现了一对青年男女婚前婚后更为复杂的情状。《结婚进行曲》不仅表现了男性“同盟者”在婚姻关系中立场的变化,而且别具洞察力地表现了男性“同盟者”不能自圆其说的多重话语的内在矛盾与混乱,实质上也揭示了“新青年”变成“丈夫”之后不能贯彻自己新思想主张的根本原因。
女主角黄瑛是个天真任性又充满幻想的女学生,男主角刘天野是她的同学,刘天野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女性在婚恋和职业上的自由,但是也受到了一些流俗观念与习气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刘天野在不同情况下说出的话语自相矛盾,实际上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而黄瑛机敏的反驳则让他漏洞百出:
刘天野 哎,你们女人呀……
黄 瑛 什么女人,女人!
刘天野 都是气量狭窄!
黄 瑛 噢,你们男人度量大?
刘天野 自然呐。
黄 瑛 那为什么排斥我们妇女?
刘天野 我排斥你?
黄 瑛 你们男人连一个职业都不给我!
刘天野 得了,别不满足了,你的薪水比我还多五块钱哩!
黄 瑛 瞧!这就是歧视妇女!我就不能比你多拿五块钱?
…………
刘天野 可不是?人家优待你们没结婚的小姐,才多给了五块钱。
黄 瑛 胡说!
刘天野 怎么是胡说呢?我们局里就是这样:年轻漂亮的小姐用上两三个,装饰一下门面;这就叫做“花瓶”!
黄 瑛(生气)你这是侮辱我们妇女!我揍你!
刘天野 唉,你别生气呀。这不是我侮辱妇女!(忿激地演讲起来)我们这个社会,男女就是不平等嘛!一个妇女,不论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地位上、家庭关系上,在一切地方都是和男子不平等的,为什么在一切方面不能和男子平等?这首先是由于妇女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妇女的经济地位为什么不能独立?……
黄 瑛 是呀,为什么呢?
刘天野(笑起来)嘿,我又卖狗皮膏药了!——把去年在抗战宣传队动员妇女抗战的那一套又背出来了!
黄 瑛 唉,小刘,你倒说一说,妇女的经济地位为什么不能独立呢?
刘天野 得了,得了,我再宣传下去呀,不但是你们妇女,连我的经济地位——我的饭碗都要打破了!现在连谈抗战都过时啦![14]
刘天野激愤的演讲在触及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实质性问题时戛然而止。他不认为自己有“侮辱妇女”的主观意图,但他的话语却显露出他其实接受了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性认识。社会中不同的话语模式对个体话语系统的渗透固然在所难免,然而一个人要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话语,就必须对他人的话语进行辨别、反思和取舍[1](126−128)。刘天野显然没有做到,因而面对黄瑛的追问,他就无法自圆其说。
这段对话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隐蔽的社会现实:许多提倡“男女平等”“女性自由”的男性“同盟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言论的意义,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有限度的、有目的的“鼓吹”或“标榜”。一旦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他们就会转而采用另一套话语来应对。这种话语的矛盾与混乱,也显示出一个人所具有的多重身份之间的内在冲突。具体到刘天野身上,就是他作为丈夫、作为男性职员以及作为抗战宣传队员三重身份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标准的不一致。可悲的是,许多随潮流而动的青年甚至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虚伪、脆弱与矛盾。因此刘天野婚前所保证的“绝对独立,互不妨碍”“绝对自由,互不干涉”“绝对平等,互不侵犯”[14](130),也只能像他背熟的宣传词一样,很难有实际意义。在第五幕展现婚后生活的场景中,当家务缠身的黄瑛终于得到一个小学教员的就业机会时,当年和她在同一条战线上帮她争取职业机会的刘天野却换了面目,他禁止黄瑛离开家庭,要她继续承担家务。黄瑛终于失去了这一难得的就业机会,最后的呼喊几近梦呓,“我有行动的自由,我有独立的人格!我有……”[14](223)
黄瑛等“新女性”的困境在于:她们具有追求“自由”的意识,却并不能从现实的社会制度中获得实现自由(首先是经济独立)的机会。社会公共生活留给女性的自由空间已然很狭窄,而当年的男性“同盟者”又将对她们自由空间的侵犯和剥夺延伸到了家庭生活内部,使得她们的突围变得困难重重。上述几部话剧生动具体地表现了男性“同盟者”意图隐秘的话语策略和矛盾杂糅的话语体系。这不仅显示了女性自由所面临的另一重困境,而且深刻地揭示了启蒙话语的盲点——启蒙话语所询唤的主体与他或她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个人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如何完成对接与整合,同一个体的多重话语如何实现自洽,这是启蒙观念向实践转化的关键,也是本文所论的“女性自由”话语实践始终面临的难关。
三、女性主体话语空间的遮蔽与重建
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在讲述她为何由写小说转向创作剧本时写道:
怎样去写那些不写作的人?……这个疑问近二十年来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出现在我面前。直到不久前,我才开始有了答案。问题在于,要让他们……说话。但是怎样使他们说话?怎样才不致以我的声音压过他们的声音?我找到了某种后来使我受益匪浅的方式,那便是戏剧,它帮助我让人物开口。[15](224)
作者不以自己的身份说话,而让人物直接开口,是戏剧体裁显著的形式特点。一般而言,相对于诗歌、散文、小说而言,话剧的创作要求创作者更趋近“无我”状态,以创造一个能够容纳“他人”的话剧空间,让人物直接走上台前。理论上说,话剧可以为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提供一个发出声音的空间,然而,当我们试图在这些以女性为主角的剧作中寻找女性的声音时,却屡屡发现女性的缺席。
1920年,在《新妇女》所刊的凌均逸与陆秋心合编的《醒了么?》、严棣的《新旧家庭》《自决》《心影》等最早的几部探讨女性自由问题的剧作中,肩负宣扬女性自由与解放之责的“新女性”呈现出较为类型化的面貌。她们很少参与到事件之中,而是作为旁观者、评判者和宣传者对剧中其他角色——也是对观众——直接宣讲。她们的台词往往与剧情关系松散,几乎是当时报刊社论的直接摘录。台词虽由剧中女性角色说出,传达的却是剧作家的观点和一般启蒙者的观点,女性的声音实质上仍是缺席的。
剧作者借人物发声,还存在一种更为隐蔽的情况。在汪静之的独幕剧《新时代的男女》(1927)中,已有妻室的青年教师疑古与同事玉娟相爱后,便要求与没有知识的妻子“离婚”。疑古的父亲责备疑古没有理由这样“出妻”,玉娟则出面反驳他,说这是“离婚”不是“出妻”——无视丈夫与旧式妻子之间实质存在的不平等地位而为“出妻”改换名目,打出“平等”的旗号使之获得虚假的合理性,这只能使弱势一方更加无法申辩。剧中辩白的话虽是出自玉娟,却让人感到这分明是有着类似经历的剧作者一厢情愿地借玉娟之口为疑古辩白③。汪静之此剧充满自我辩白的意味而缺乏反省,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主动提出离婚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状态④。在这部剧中,不仅被抛弃的“旧”妻子完全缺席,“新”女性玉娟的台词也不过是剧作者意愿的投射,与“旧”妻子同样处于失语地位,属于女性的话语空间,在这部剧作中仍然是被遮蔽了。
事实上,与“玉娟”有着相似处境的“新女性”,很少会像汪静之塑造的“玉娟”这样绝境无情。她们的内心往往充满矛盾和负罪感,殷梦萍《爱的创伤》、石评梅《这是谁的罪?》等剧作反映了“新女性”内心的波澜。例如在殷梦萍《爱的创伤》中,女主角对她深爱却已有家室的男老师说:“我爱你,这是我的自由,但你绝对不可以爱我!因为这自由于你是早已丧失的了!”“……若你与现在的妻子离婚,这就是我的罪愆。”[16]——她对于“自由”的辩证认识,对于未出场的“她者”的想象,使这部短剧具有了真实动人的力量,也发出了一种来自女性主体的声音。
那么,“女性自由”的主体究竟是谁?它是全部女性,还是特指一部分?“女性自由”话语总是与被称为“新女性”的主体密切相连,那么谁才是“新女性”?是否从一开始就有一部分“旧女性”被排除在“自由”的大门之外?事实上,对女性进行“新”“旧”判别的话语体系,实质上造成了对弱者更为沉重的压制。如果说“新女性”在话剧中的话语空间时常因为被代言而受到遮蔽,那么“旧女性”的话语空间则更是被挤压得几近于无。
在这种情况下,袁昌英的《人之道》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部剧作实现了埃莱娜·苏西所说的“让不写作的人说话”,为失去话语权的人重建话语空间的戏剧创作理想。《人之道》中欧阳的“旧妻子”王妈在欧阳和素莲组成的新式家庭中出场,是一个关键性的戏剧时刻。由此,“新女性”与“旧女性”同时在场,两种话语彼此撞击,使人们得以重审“女性自由”“婚恋自由”等新式话语及其所指引的行动之中存在的问题。剧中,王妈的“自述”打破了这类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女性”在历史中的失语状态,在现代中国常见的离婚故事从王妈的角度重新被讲述了一次:他们夫妻虽然是由父母之命订的亲,婚后感情却很好。在丈夫读书期间,“他一来家,若是天气好,我们就到屋后的岭上或是茶园里或是菜圃里去散步闲游。有果子的时候就争着摘果子吃,有花就采花玩。天下雨的时候,他就坐在家里读书,我就陪着坐在旁边绣花”[17](112)。这段朴素而诗意的台词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完全不同于素莲等“新女性”对于丈夫那位无知无趣“乡下前妻”的想象。然而“这个贫穷的女人用这个家庭能够凑起来的所有资源来支持欧阳在海外求取‘现代知识’的学业,结果最后才明白这个‘现代’里面没有她的位置”[18](200)。
王妈的讲述激烈地冲击着女主人素莲和来客梅英的内心,并引发了她们之间关于新旧伦理的论争。素莲既同情王妈,又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合理化,她试图以“爱情神圣”“礼教罪恶”等说辞辩白,却在梅英针针见血的反驳中愈见其辩词的虚伪脆弱。她希望自己不至于成为制造悲剧的同谋,梅英却指出这种情形对于被抛弃的“旧妻子”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且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只是她们大多“苦无从诉”。
虽然梅英几乎是剧作者袁昌英的代言人,但并没有因此盖过王妈和素莲的声音。王妈的讲述不但与素莲的辩白平等地出现在剧作中,而且直接冲击着后者的合理性根基,形成了有着内在紧张关系的多重女性话语。而只有让不同立场的女性角色发声,才有可能重现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现实,创造出能够容纳不同女性主体话语的戏剧空间,进而揭示“女性自由”话语自身的盲点,进行更深刻的反思与重建。
如福柯所说,“话语承载和生产着权力”[19](75),掌握更多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强势话语往往会压制或遮蔽同时期的弱势话语;然而话语又是流动和变化着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改造旧话语,创造新话语,争夺话语边界,扩展话语边界”[7](31)。因此,借由话语进行突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再现一种话语就是再现一种现实的面向,在多重话语的冲突与融合之中,才有可能完成话语的重建。在这一意义上,以“女性自由”为主题的中国现代话剧通过对来自不同主体的多重话语的再现,呈现被忽略的现实与被遮蔽的声音,进而导向对话语围困的突围、对言说策略的拆解与对其内在矛盾的反思。如果说在多重话语的围困、交锋、补充之中,重建一种逻辑更为自洽也更具实践性的“女性自由”话语仍是这些剧作尚未完成的任务,那么至少在这些剧作之中已经蕴含了更新的可能。
注释:
① 此四十余部剧作依照两项标准筛选统计而来。首先,“女性自由”应是剧作探讨的主要问题,剧作情节、核心冲突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其次,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交织于“女性自由”问题上的多重话语,因此要求所选剧作的人物台词中明确出现“自由”二字(或前文所说作“自决”“自主”等字眼),且其指涉主体为女性。所以有些虽涉及女性婚恋、教育等问题,但并未点明“自由”一词的剧作,则不在此统计范围之内,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剧作即多属此类。在具体的统计过程中,笔者首先以收录近6 000部剧目的2012年版《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修订版)为基础,根据其中的剧情提要进行初筛,然后通过对所选剧本的进一步查证阅读确定了四十余部符合要求的剧作。1915年12月《留美学生季报》所刊《波兰女之自由梦》是第一部以“女性自由”为主题的中国现代话剧;1919年胡适的《终身大事》引发了持续性的创作热潮;1920年代是“女性自由”主题话剧创作最密集的时段,《新妇女》《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镌》等报刊刊载的这类剧作计有三十余部,但其中一定数目的作品流于标语口号化;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类作品数量骤减,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话剧艺术自身摆脱早期口号化宣传模式走向成熟的趋势有关,袁昌英的《人之道》、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等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亦产生于这一时期。
② 这里录一则萧军日记中的类似事件作为参照:1943年3月21日晚,他与妻子王德芬去看京戏,回来后发现儿子鸣儿从床上跌下来,“这使我的心遭到一个几乎从没有过的冲击!一直到我把他抱进怀中,他才哭了。我要爆炸,我要给芬这个只顾自己享乐的自私的女人一顿残酷的打击!但我全没做。……‘假设鸣儿他跌死了,或残废了,我将要受一生的良心的鞭打!……’我这是说给自己,也是说给她,如果不是为了她,我是不会去看这晚会的”。参见《萧军全集》第十九卷,华夏出版社,第63页。
③ 汪静之本人也曾有过与男主角“疑古”相似的经历。他在杭州追求女师学生符竹因(后成为汪的妻子)时,家中已有一位未婚妻,汪静之曾为此写下一首《我都不愿牺牲啊》表达自己的两难,既不能放弃爱情,又不愿忤逆父母,并把此诗寄给父母,当月收到父亲电报告之“已退婚”。参见《汪静之文集·蕙的风》第70—71页,《汪静之文集·没有被忘却的欣慰》第7页、第172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关于这一时期的“自由离婚”现象,尤其是知识青年将这一个人选择与民族大义、进步公理“焊接”以自证其合理性的现象,可参见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的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中第三章《“自由离婚”:吊诡的现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