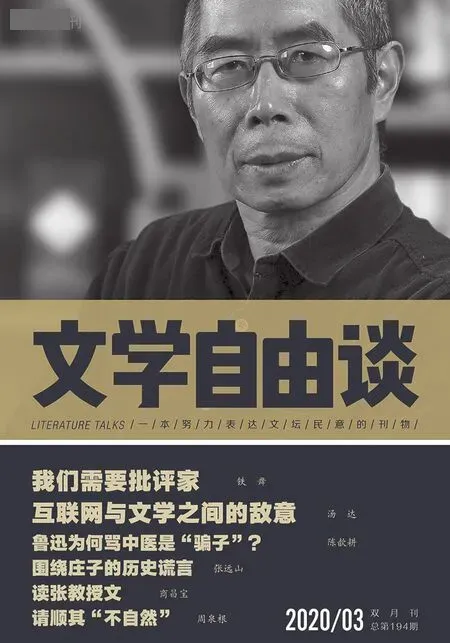我在文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 皓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久。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顿,盖因在逐渐深入接触了文学之后,文学所呈现出的不为人知或谓之并不美好的一面,让我很是纠结。想放弃,终究还有些不舍。写作的人不一定都是“作家”。“作家”的名号是一顶桂冠,需要一个人付出一生的努力,而不是简介里“当代著名作家”那几个字。能够清醒地认知自我,并不容易。
想起去年年末的一件事。当时我正挤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裤兜里的手机响了。铃声很是执着,我按了接听键,低声应答:喂,你好!话筒里传来亲切的家乡口音,很是热络,问我是否能听出来是谁?我略一思忖:嗯,你是董德华?德华兄!
董德华是我老家普兰店的一位文友,虽来往不多,但并不陌生。他说自己要出一本文学作品集,请我写个序。我说了几句推辞的话,大意是希望他找个更有文学身份和成就的人来写,才会为作品集锦上添花。他马上将了我一军:“×老师说你现在求不动,难道我也不行?”我是个面子很薄的人,这句话一下子突破了我的“防线”,只好应承下来,让他把书稿寄给我。
摁掉电话,在那辆颠簸的公交车上,我不由回忆起与董德华交往的点点滴滴。
1990年春,我在沈阳空军当兵。家乡普兰店当时还叫新金县,县里成立文联并召开第一届文代会。那时我当兵刚一年,根本没有探亲假,拿着文联姜凤清老师发来的邀请函,这才请了假。记得文代会去了很多人,虽形形色色,但人们对文学还很是热衷,都一脸的虔诚。尽管之前许多人并不认识,但一提各自的名字,便一见如故。由此我认识了很多家乡的文人;董德华也在其中,且印象颇深。隐约记得董德华穿着一身稍嫌皱巴的蓝西装,扎着一条红领带,戴着一副茶色眼镜。对他有印象,还因为他是我母校文学社的顾问,而这个文学社的前身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创办的。
直到我退伍回乡,我们的交往才真正开始。那时新金县已经改名普兰店市。能写点东西的所谓文人就那么些人,没事都爱往文联溜达,你去我也去,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和董德华的交集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董德华的真实身份是个“土导游”。普兰店市星台镇境内有一个巍霸山城风景区,景区内有个清泉寺,也叫吴姑城庙。山城传说是薛礼征东的遗迹,说是风景区,其实主要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道观。作为义务讲解员,董德华在那一干就是多年。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挖掘出大量的史迹资料,写成典故传说,作为风景区的导游词,使得这个土得掉渣的风景区有了文化附着。道观香火日盛,得到文化旅游部门的重视和扶持。
在乡间劳作、义务讲解之余,董德华手边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他如饥似渴地读,读完了就写,写完了就向文联的老师请教。我一次次在文联与董德华相遇,他也热情地邀请大家到吴姑城参观游览。经不住一再真诚地相邀,索性就去了。在吴姑城,我看到一个浑身绽放着活力的董德华。他用胶辽方言打底的蹩脚普通话,口若悬河地给我们讲解,有时候唾沫星子乱飞,我们就禁不住笑。他不为所动,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吴姑城,他显得那么接地气,简直与那片山水融为一体;他显得那么自信,是历史和文学给了他底气;他显得那么有仪式感,依然是那套稍嫌皱巴的蓝西装,红领带,即使山间尘土飞扬,他也板板正正地打着手势,把辽远的眼神埋在茶色眼镜后面。在这吴姑城,我觉得董德华更像是一个传说,他在那里可谓“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离开普兰店是在1999年底,董德华什么时候离开的那片土地,不得而知。这二十年间,我与他疏于来往,但偶尔也能在大连一些与文学相关的场合见上一面,寒暄几句,便匆匆别过。我不知道他为何选择离开钟爱的导游事业,就像自己不知道当初为何义无反顾地踏上开往大连的火车。说是为了文学理想,其实无非都是为了生计,为了能有一个更为宽阔、宽容的空间,离世俗远一些,离文学近一些。
我没有与董德华进行过推心置腹的交流,我的揣摩到底能不能抚摸到他真实的心跳?他的书稿在我办公室的书架上放了一段时间,春节来了。紧接着“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有了看书思考的时间,有了安静写作的机会。写了十几首长短不一的诗歌,读完《浮生六记》《伪满洲国》,终于静下心来,开始看董德华的书稿。在阅读的同时,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又来了,一个终生爱好文学的人和文学本身之间,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董德华的书稿是用《学生处工作计划》的废旧打印纸的背面打印的。厚厚一沓的书稿,有描写家乡风土人情的篇章,有人生感悟、揭示生命哲理的短文,还有大量的游记以及对读书的认识见解等,共分六辑。文字的水准高低不等,人生感悟里面个人独到的见解不多,游记和家乡风情世故的文字摘抄资料较多,我隐隐有些许的担忧……
看简介,得知董德华先后在几所民办学校从事宣传之类的工作,想必是遂了自己从事文字工作的初心。工作之余,国内国外不少名胜古迹也都去过。他很勤奋,每走一处都留下一些游记,间或夹杂一点个人的感悟,倒是与其当初的导游身份挺贴切。对于游记,我多少是有些排斥的,尤其是那种大量摘抄景点说明、导游词、典故的流水账似的游记文章,在编辑工作中是慎而又慎。我能够理解董德华写游记时的心情:见到梦寐以求的景区景点,难免激情澎湃。但是,在写作这些游记之前,他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就匆忙落笔了。有时候,我们的脚步或许停不下来,但心可以静下来,等一等那些哲学的思考。唯有思考,才能填补语言的苍白。在旅途中,我们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是我们在看景,还是景在看我们?我们到底是一个旁观者,还是景物的一部分?文学是不是就如这诱人的风景,一次次吸引着我们趋之若鹜?山顶无限风光,而山路崎岖,有的人轻易就抵达峰顶,有的人一辈子都在路上。
董德华,我,以及我生命中的诸多文友,后者居多——后者,便是这些一辈子对文学孜孜以求的人,文学没能给他们带来多少荣耀和财富,反倒一次次左右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文学是个象牙塔,我们这些底层的文学爱好者,到底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对于文学而言,它就像个冷艳的、不近人情的美女,我们单相思一样地爱着它,为它痴狂,夜不能寐。而这一切,文学根本不知道,文学不会因为你的痴情而格外开恩和垂青于你。文学从来没有强求谁去爱它,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一厢情愿。
换个角度看,在我们沾染了文学的短暂一生中,文学又是个什么角色呢?当年少时,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找到的一切文学书籍,我们为小说营造的巨大生命空间而陶醉,我们为诗歌散发出的浪漫气息而彻夜难眠。我们还没有情窦初开,却没头没脑地与文学早恋起来,像丢了魂儿似的,对文学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作家、诗人,成了太多人或明或暗的理想。至于文学到底长什么样子,无人知晓。没有一个真正的引路人,能带领我们度过那座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我们空想着,自大着,发表了一首小诗,就忘乎所以;投稿中了一篇小说,就感觉摸到了文学的命门。好像有了文学,我们打着补丁的衣服就有了光环,走路都带着风,贫困已不足虑,吃糠咽菜也幸福,就取得了一生一世的功名,一劳永逸。
然而,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像镜中花、水中月。当发热的脑袋终于恢复到平常的温度,火热的心冷却下来,我们发现,文学就是虚幻的代名词。文学与名利相伴相生,表面光鲜,背后却生满了密密麻麻的虱子。文学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没有恰如其分的审美标准。它的秤杆子,始终掌握在一部分人的手里。特别是自媒体时代,泥沙俱下,文学的标准变得更加可有可无。文学有时候是自慰器,有时候是咬人的狗。有的人还没有摸到皮毛,就自认为看清了文学的全部,小丑一般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全无廉耻之心。更有一些好为人师者推波助澜,搞得文坛乌烟瘴气。这样看来,文学无非是皇帝的新装。
当文学为你揭去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你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不为所动,不埋怨,不气馁,依旧从容淡定。没有一个人是为文学而生的,文学给予每个人的光芒都是平均的,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有的人著作等身,但他绝不是作家。有的人一辈子没留下只言片语,他却读懂了文学,真正知道文学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在董德华这个书稿里,《清泉寺揽胜》《清泉寺石龟的传说》等篇什,都是他的印记,饱含着一种衷情;而《家乡的野梨花》《杜鹃花开》则选取了辽南乡间最常见最朴素的花朵,把一腔热血寄托其间:
无论你在哪里碰到它,都会像遇见乡亲似的,露出一脸的憨厚,在对你笑。(《家乡的野梨花》)
乍暖还寒时,杜鹃花开,它无意以重色夺艳,又不以冷色袭人,只以不温不火的姿色排列在尚且冷冻的枝头,迎接着暗涌的春潮。(《杜鹃花开》)
这样的语言,尽管有些刻意的华丽,但它是董德华自己的语言,是他独特的认识和感受。或许,与名家的笔墨相比,它轻佻了些,单薄了些,笨拙了些,但它散发的,难道不是地地道道泥土的芬芳么?
像董德华们一样,我依然爱着文学,像西装革履的董德华那样,带着仪式感,带着敬畏、悲悯和感恩。我珍惜我们的文学友谊,我们拉着手、并着肩走在上山的路上。累了,就坐下来看看路边的风景:树木、花草、沙砾和石头。你等着我,我等着你,谁也别落下。因为我们坚信,文学是有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