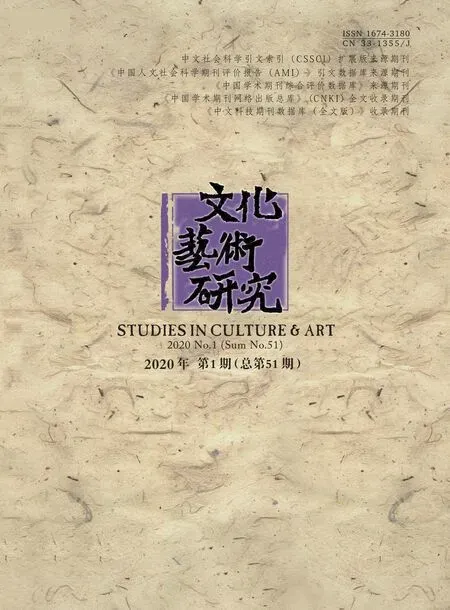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路径*
——电视剧《小欢喜》的创新性研究
石 蓓
(浙江传媒学院 电视艺术学院,杭州 310018;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杭州 310028)
2015年广电总局的“限古令”对所有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古装剧的播放集数进行了限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单独强调了将现实主义题材作为国家提倡的创作方向。2019年广电总局对武侠、玄幻、历史、神话、穿越、传记、宫斗等所有古装题材网剧和电视剧设置了新的播放限制。据《中国电视剧风向标报告2019》统计,2019年上半年,卫视晚黄金档共播出电视剧328部,现实题材占65%,其中当代剧占50%,近代剧占比不足1/3,古装剧仅占5%,当代现实主义题材剧成为卫视首轮剧的首选。①转引自小熊《尹鸿解读2019电视剧产业特点与走向》[EB/OL].(2019-11-13)[2019-12-22].https://new.qq.com/omn/20191113/20191113A0QIDX00.2019年热播的《带着爸爸去留学》《少年派》和《小欢喜》更是引爆了当代教育话题,教育题材成为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蓝海。据统计,2020年已有16部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备案,其中不乏柠萌影业教育四部曲的后两部——《小舍得》《小痛爱》以及正午阳光的《以子之名》和观达影视的《起跑线》等。[1]
教育题材并非电视剧新类型,近年来教育题材剧扎堆涌现,一方面得益于国家政策导向为现实主义题材剧提供了有利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创作者似乎找到了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创作新的切入点,新的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法,使教育题材电视剧焕发新鲜的面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2019年播出的《小欢喜》开播一周即成为两大卫视收视冠军,CSM52平均收视率过1,网播量破30亿次,豆瓣评分高达8.4分,成为该年度豆瓣评分最高的国产电视剧,也是21世纪以来第一部高收视率、高话题度和高口碑的教育题材电视剧,打造了当代国产教育题材电视剧的现实主义范本。
一、教育题材电视剧的现实主义回归之路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提倡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学者认为, “影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或表现生活,但它并非照镜子似的反映,而是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创作要有一种‘对人生现实深切关注和对现实人生理性审视’(秦兆阳语)的现实主义精神”②转引自范玉刚《现实主义电影与社会主流价值传播》,《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2期。。然而,一方面,现实题材本身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容易触碰敏感话题;另一方面,观众易于将现实题材的作品与日常生活相对照,质疑其真实性,导致作品的真实度和可信度难以把握。再者,现实题材作品难以打造系列作品。基于此,长期以来国产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难成主流,也难以获得观众的认可。教育引发的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热点,是全民关注和参与的话题。教育题材电视剧必须走现实主义路线才能引发观众共鸣,它无法脱离社会现实,但又往往因涉及敏感话题、真实度与可信度难以把握等原因而偏离现实主义。
20世纪80年代《寻找回来的世界》《师魂》《绿荫》等电视剧关注师生冲突,以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思考人生、走向正确的道路展开叙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教育体制的弊端,并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案,获得了较高的口碑,奠定了教育题材电视剧的现实主义道路。20世纪90年代,《十六岁的花季》《十七岁不哭》《花季雨季》等教育题材电视剧将叙事主体转向青少年学生,走上了青春校园路线。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受港台、日韩青春偶像剧的影响,《十八岁的天空》《青春派》等校园剧主要书写校园爱情,完全脱离现实主义教育题材。
21世纪以来,一方面,随着政策对青春校园类型的调整,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必然回归现实主义道路;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和教育制度的不断调整,当代的教育问题已与以往不同,必须寻找新的现实主义路线。这一时期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并不少,但由于观众对剧情真实性的质疑以及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关照等问题,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的现实主义路线并未确立。直到2015年电视剧《虎妈猫爸》以一种极端、全新的叙事视角引发了大众对这类题材电视剧的热议。虽然剧中教育观念和行为较为极端,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阶级面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并折射出大时代都市家庭生活的新样貌和新矛盾,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和话题。继该剧之后,《小别离》《少年派》《陪读妈妈》《带着爸爸去留学》等教育题材剧涌现,引起大众热议。这些剧集人物相似、情节相似,形成了当代教育题材剧的叙事模式:第一,找准教育的关键阶段为叙事切入点,例如幼升小、初升高、高考、留学;第二,以教育为切入口,实则书写亲子关系;第三,几组家庭平行叙事,涵盖都市中产、新富阶层以及平民家庭;第四,父母的形象普遍设定为“虎妈猫爸”;第五,植入中年危机、二胎、婚外恋、离婚、离家出走、抑郁、早恋、辞职、卖房、租房、陪读等情节。诚然,现实题材并不等同于现实主义,雷同化的情节和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关怀终将导致伪现实主义的现象。
电视剧《小欢喜》尽管也存在上述套路,但剧作正视了当代教育的敏感话题,真实再现了当今社会学校和都市中产家庭的教育观和亲子关系,真实的人设和生活场景设定,贯穿始终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怀和真善美的价值导向,引起了各年龄段、各阶层观众的共鸣,找到了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路径。
二、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
(一) 当代社会教育观、亲子观的真实反映
中国的应试文化形成已久,20世纪50年代高考制度实施以来,“一考定终身”“唯分数论”“竞争式快乐”等文化心理深深根植于普通大众。然而,随着30年的高考制度改革探索,受过良好教育的“70后”“80后”新式父母群体的树立,以及在较为优越的物质条件下接受过多元教育的“00后”子女的成长,学校教师、父母、子女的教育观均已明显变化。一方面,他们默认高考是人生的关键时刻,接受应试教育;另一方面,他们愿意尝试和寻找更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家庭教育超越学校教育,成为影响子女成长与学习的重要因素。城市中产阶层更加主动也更容易接受新的亲子观和教育观,《小欢喜》真实地反映了这种观念变化。
该剧采用小视角展开,还原生活的真实。剧中主要人物为三组家庭的六位父母和四个子女。尽管人物身份有新富阶层、官员阶层和白领阶层,但并没有突出强调人物的身份特征。在面对孩子高考时,他们有共同的心理,代表了普通大众中相对自由民主的家庭、离异家庭和空降父母的问题。以高考为名,实则将剧情聚焦在三组普通家庭的琐碎生活和亲子关系的处理中,具体讲述三组家庭在孩子高三这一年的事情和人物的内心变化,将大题材转化成琐碎的小事件。通过夫妻的情感沟通、父母与子女的情感沟通细致呈现三组家庭真实的心理历程。小事件、小人物、小情爱的设定使所有观众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感受到发生在周遭的事件和情感,真实感油然而生。
(二) 正视敏感话题和生活的痛楚
教育有诸多敏感话题,《小欢喜》正视早恋、性教育、自杀、抑郁等敏感话题,用理性的思考和行动亲身示范,将问题的解决最终导向教育观和正确亲子观的树立。童文洁和宋倩误以为乔英子和方一凡早恋,进而担心他们会因缺乏性知识而犯错。方圆和童文洁纠结于如何向儿子讲述性知识,当他们艰难地张开口时,方一凡坦然、直白、清晰地讲述了在学校接受的性知识,方圆和童文洁既讶异又惊喜。方圆、童文洁、宋倩、乔卫东约定时间正式、严肃地“审问”乔英子和方一凡是否早恋,最终弄清两人之间只是纯洁的友情,两人的深情拥抱来源于学校的心理疏导课的拥抱疗法。丁一在父母的强权教育下考上了父母眼里理想的大学,却违背了自己的专业理想,最终长期抑郁无法入眠导致跳楼自杀……剧情没有过度的悲伤渲染和压抑,父母们在沉痛惋惜中理性反思。英子长期在母亲的控制下内心压抑,当母亲一次又一次反对自己参加南京大学组织的夏令营,反对自己报考南京大学天文学专业后,长期失眠导致重度抑郁离家出走。当宋倩和乔卫东找到英子时,英子在大桥上嘶吼出内心的真实感受,宋倩虽然心如刀割,但积极反思自身的问题,努力改变对英子的态度和行为,坦然带她接受心理治疗,乔卫东回归家庭,最终英子得以治愈。
该剧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生命痛楚,小切口折射出了大时代的大悲欢,但始终以冷静的思考引导观众面对生命的阴暗面,同时传达给观众这样一种观念:父母勇于面对生活的痛楚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的理念。方圆中年失业,几经波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过内心斗争决定做一名滴滴司机;童文洁在公司遭遇小人陷害、色狼老板威胁,选择辞职;方圆的父母抱着赚大钱的幻想被骗巨资;季胜利由于儿子的跑车事件官场失意;刘静患乳腺癌。这些事件都是人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典型事件,无一不折射出当今大众的集体诉求和内心焦虑。然而,剧情并没有渲染悲伤。方圆和童文洁认为儿子已经成人,有权利和义务知晓家庭现状、面对家庭困难,将家庭经济危机坦诚告知方一凡,并对其进行思想疏导;方一凡在父母积极面对困难的影响下开朗、乐观。刘静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后,为了不影响儿子高考,冷静地独自面对病痛;当季胜利无意中发现其病情,两人在短暂的悲伤过后积极应对生命的考验,并将实情告诉季杨杨,季杨杨从一开始无法接受现实而离家出走,到意识到父母的不易和勇敢,学会了勇敢面对人生的痛楚,从而努力学习,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份责任感。
(三) 精心的语言设计强化真实感
影视作品的真实度是通过多方面和细节共同体现的,该剧看似啰唆的语言设计功不可没。
《小欢喜》中大量的人物对白和旁白均采用了后期配音,却丝毫没有假的感觉,这主要得益于:第一,剧中所有主要演员的对白和旁白均为演员本人在录音棚完成,保证了人物形象与声音的一致;第二,剧中主演都是老戏骨,语言功底扎实,声音辨识度非常高,使得人物语言形象生动、饱满;第三,录音和后期制作比较精细,使不同场景的人声与环境较为一致,提示了真实度。
该剧有大量的对白与旁白,大有“抢戏”的嫌疑。方圆的话语更被网友总结为“方圆经典台词20句”,或收入“《小欢喜》经典对白100句”之中,观众对方圆大量的言语丝毫没有“厌烦”“啰唆”的感觉,反而乐于倾听。这是为什么?第一,中国家庭普遍比较含蓄,父母双方、父母与子女间大都缺乏交流,很多时候“说不出口”“懒得说”,心事常常闷在心底不敢说不想说。该剧主要通过方圆的话将观众平常说不出口、懒得说和不敢说的话诚恳、真切地说出来,观众感觉自己也得到了宣泄。第二,该剧充满文学性、饱含人生哲学却又十足口语化的对白,着实让观众学到了沟通的技巧,令观众折服。方圆劝导童文洁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比喻更是成为经典。第三,该剧多处采用口语化、内心独白式的旁白/解说,拉近了电视剧与观众的距离,并起到了介绍人物关系、加速剧情发展的作用,话里所传达的观念得到了观众的认同。
三、现实主义精神关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2]《小欢喜》在真实呈现当代应试文化和亲子矛盾的同时,深刻反思了教育观和亲子观,尝试给出问题的答案。
(一) 应试文化的真实呈现与反思
一部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即使无法提供教育改革的出路,至少也应该在引起观众共鸣的同时让他们进行反思,亦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的观念,引导大众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教育方式转化。《虎妈猫爸》采用较为极端的方式将当代中产家庭子女教育的紧张和焦虑放大,首次将幼儿园升小学的问题推到了应试文化的层面,让人窒息。剧中尝试提出对“毕胜男”式教育理念的反思,仅仅点到为止。《小别离》中从“84.5分和85分之间差着一个操场的人”“中考不考这个”的极端唯分数论应试理念转向送孩子出国的另一种极端,出国成为解决当代家庭教育的唯一出路。《少年派》中过多地插入青春校园故事、父母中年危机、二胎等情节,虽然也试图通过“猫爸”林大为反思教育的出路,但显得势单力薄,并未提出清晰的解决思路。《陪读妈妈》和《带着爸爸去留学》则完全避开了国内的教育问题。
《小欢喜》将集体无意识的应试文化真实地呈现出来,诸如,童文洁常说的“考不上大学,这一辈子你就完了”,“高考是人生最关键的一场战役,打赢了,终生受益;打输了,终生遗憾”,宋倩说的“必须考上北大清华”,备战高考期间夜里灯火通明的学生房间,带着孩子奔波于各种补习班的家长,学校反复强调的一本线、本科率……观众默认剧中对待高考的集体无意识,与剧中人物的心理达到共情。同时,学校、教师和父母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例如,学校取消留级制度,多次组织心理健康活动,组织家长和学生参与“畅言会”;老师发表“现在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言论;童文洁最终认可方一凡的音乐天赋,支持其报考艺术院校;宋倩支持乔英子报考南京大学,追求天文梦想;季胜利和刘倩支持儿子选择酷爱的汽车专业,留学深造。
(二) 亲子矛盾的真实呈现与反思
《小欢喜》将应试文化带来的问题更多指向亲子矛盾,亲子之间教育理念的矛盾缘于父母对子女持有过高的期望,或者是空降父母、离异家庭等家庭状况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教育的焦虑大多来自中产阶级自身。化解的关键在于父母自身教育理念的改变。营造和谐的亲子关系、尝试多元化教育、帮助子女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人生发展路径才是家庭教育的关键。
该剧将父母和子女的行为与态度同时展示给观众,使观众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发现自身的问题,从而对自身的亲子关系进行反思。例如,学校组织的畅言会上,方一凡说出“爸、妈,我想告诉你们,我真的喜欢唱歌跳舞,我也真的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妈,你以后别对我这么凶了,我不是个坏孩子,我只是个学习不好的孩子……”,随后给父母唱了一首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这一幕感动了董文洁,也触动了无数父母观众的内心。我们不得不反思:究竟应该怎样面对成长中的少年?在分数与兴趣爱好之间究竟如何选择?英子在大桥上的嘶吼、季杨杨信里对父亲的控诉,都启发观众反思自身的亲子关系。与此同时,该剧为亲子矛盾的解决给出了正向引导:正因为方圆这一亲切、智慧、通达的父亲角色始终深度参与家庭生活,童文洁最终转变了教育观念和亲子观念,方一凡形成了开朗、乐观的性格,保有自己的理想;乔卫东回归家庭使宋倩得到温暖,母女矛盾得以快速缓和,英子的病彻底治愈;季胜利暂时放下工作,回归家庭,尝试儿子酷爱的赛车训练,暗中通过网络打开儿子的心扉,父子关系终于良性发展。
四、真善美的价值导向和轻喜剧风格
尹鸿、梁君健在分析2018年国产电影现实主义主流化时指出:“真正主流的现实主义,也许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现实、揭露现实、抱怨现实、不满现实——尽管这些也可能是电影的功能之一,而是应该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去表现人们如何推动现实的改变。主流的现实主义,看到的不仅是现实,而且是通过改变而不断走向更加美好的现实。”[3]西方电影理论强调“美”与“真”的统一,中国电影强调“美”与“善”的统一。[4]电视剧与电影的美学理论是相通的,《小欢喜》则通过轻喜剧的风格做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小欢喜》中没有“坏人”。剧中所有老师都一心为了学生考出好成绩、真心爱护学生;所有家长都一心为了孩子辛苦付出;所有孩子都有追求自由和梦想的内心,即使“学渣”方一凡、季杨杨,也只是学习成绩不好,并非坏孩子,他们都能够体谅和理解父母的爱。所有的教育矛盾、亲子矛盾都一一化解,最终三组家庭都获得了小小的欢喜。这种善的设置表面看并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然而,该剧并非是非对错的伦理/道德剧,而是教科书式的亲身示范。当你面临生活的痛时,应该如何反思和调整心态与观念,从而抚平焦虑与不安,体验到生活中的“小欢喜”,感受到生活的美?轻喜剧的风格使教科书式的剧情演示并不枯燥、严肃,而是令观众在轻松、温暖的氛围中慢慢体会、反思,切身感受生活的美好。
结 语
《小欢喜》以高考为切入点,为当代教育题材电视剧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新路径,不仅再现了生活本来的面貌,更观照了人的内心。观众对该剧真实度的高度认可为相同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范本。诚然,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应止步于现实生活的再现,而应该是超越现实,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层面启迪人心。《小欢喜》已将国产现实主义教育题材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优秀的同类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