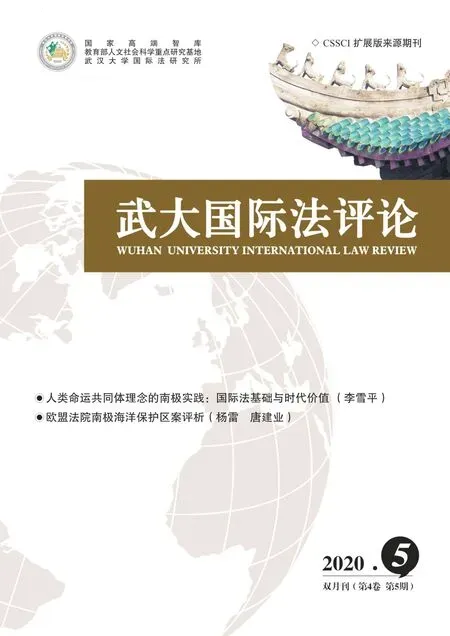欧盟法院南极海洋保护区案评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属性之争
杨 雷 唐建业
公海保护区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焦点议题之一,①See Danielle Smith & Julia Jabour, MPAs in ABNJ: Lessons from Two High Seas Regimes, 75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417-425 (2018); Olive Heffernan, How to Save the High Seas, 557 Nature 153-155 (2018);参见刘明周、蓝翊嘉:《现实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7期,第79-87页。也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BBNJ)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称“BBNJ 协定”)谈判的关键内容,②See Elizabeth M. De Santo,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of 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ABMTs) for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BBNJ), 97 Marine Policy 34-43 (2018); 参见罗猛:《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的国际立法趋势与中国因应》,《法学杂志》2018年第11期,第82-91页。而南极海洋保护区则是全球公海保护区实践的先行者。2018 年11 月20 日,欧盟法院(以下称“法院”)就欧盟委员会(以下称“委员会”)诉欧盟理事会(以下称“理事会”)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两个案件(以下称“南极海洋保护区案”),在合并审理及听取总顾问(Advocate General)的意见后,作出了最终判决。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尽管该案表面上是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之间关于权能划分的争端,但法院对南极海洋保护区政策属性的判定及其对南极条约体系相关法律制度的解读,将通过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集体外交行动,对南极条约体系以及包括BBNJ 协定谈判在内的全球海洋治理产生深远影响。②参见陈力:《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2期,第163页。为此,本文尝试从南极条约体系与国际海洋法的角度,对南极海洋保护区案进行评析,并结合海洋保护区相关国际实践,探讨和预测该案判决可能的影响。
一、案件背景及进程
(一)案件背景
2011 年,第30 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CCAMLR)会议通过了澳大利亚提交的《关于建立CCAMLR 海洋保护区一般性框架》(以下称《一般性框架》),即养护措施CM91-04,激发了一些国家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积极性,也引发了捕鱼国关于海洋保护区可能影响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担忧。③参见杨雷、韩紫轩、陈丹红等:《〈关于建立CCAMLR 海洋保护区总体框架〉有关问题分析》,《极地研究》2014年第4期,第525-534页。
作为CCAMLR成员,欧盟支持《一般性框架》,并积极推动了随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设进程。2012 年,欧盟向第31 届CCAMLR 会议提交了“关于在南极冰架崩塌或退缩所暴露海域设立保护区”的提案,④See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Proposal for Spatial Protection of Marine Habitats and Communities Following Ice Shelf Retreat or Collapse in Subarea 88.3,Subarea 48.1 and Subarea 48.5, CCAMLR-XXXI/30, 8 September 2012.与澳大利亚共同提交了“关于建立东南极保护区体系”的提案;⑤See Delegations of Australia, France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roposal for a Conservation Measure Establishing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East Antarctica Planning Domain, CCAMLR-XXXI/36, 8 September 2012.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牵头开展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的规划和准备工作等。①See SC-CAMLR, 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 Meeting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22-26 October 2012, para.5.28.随着2009 年12 月1 日《里斯本条约》的生效和2013 年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的出台,2014 年6 月,理事会更新并通过了《关于欧盟在CCAMLR所采取的立场的决定》(以下称《多年度立场(2014—2019)》,其中包括8项原则和6 个方针;同时规定每年的具体政策立场须由委员会经简易程序报理事会批准。②See Council Decision on the Position to be Adopted,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CCAMLR)(Council Document 10840/14), Brussels, 11 June 2014.《多年度立场(2014—2019)》根据2013 年《共同渔业政策》等,明确将CCAMLR 定位为负责养护和管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并把海洋保护区列为将渔业活动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的管理措施。
(二)案件进程
1.C-626/15号案件
2015 年8 月31 日,委员会根据《多年度立场(2014—2019)》确定的简易程序,以非正式文件的形式,向理事会渔业工作组(Council Working Party on Fisheries)提交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即《关于在威德尔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未来提案的设想》(以下称《设想文件》);委员会认为《设想文件》属于“共同渔业政策”③本文在此使用不加书名号的“共同渔业政策”,泛指欧盟历来的共同渔业政策,而《共同渔业政策》则是指具体的某个政策,如2002 年《共同渔业政策》和2013 年《共同渔业政策》。范畴,建议仅以“欧盟”名义提交给CCAMLR。2015年9月3日,理事会渔业工作组经审议批准了《设想文件》的内容,但认为该文件属于环境政策范畴,而非共同渔业政策范畴,因此应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提交。鉴于此分歧,双方同意将该文件提交给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2015 年9 月11 日,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主席宣布批准该文件的内容,但决定该文件应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提交。
2015 年11 月23 日,委员会在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关于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提交《设想文件》的决定。④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28-33;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s.24-28.2016 年4—5 月间,德国、西班牙、荷兰、法国、芬兰、希腊、葡萄牙、瑞典和英国9 个国家(以下称“9个欧盟成员国”)参与此案,①截至2020 年2 月,这9 个欧盟成员国中,德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荷兰5 个国家是CCAMLR 成员,目前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也是CCAMLR 成员;芬兰和希腊则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加入国;葡萄牙不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加入国,更不是CCAMLR成员。希腊和葡萄牙仅是《南极条约》的加入国;其他国家都是南极条约协商国。支持理事会。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43.
2.C-659/16号案件
2016 年8 月30 日,委员会再次按照简易程序,向理事会渔业工作组提交了关于其2016年参加CCAMLR政策立场的非正式文件,并于9月6日补充提交了3个具体关于设立或支持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议草案,涉及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罗斯海海洋保护区、东南极海洋保护区以及在冰架崩塌海域设立特别科学研究区等。为在CCAMLR 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交文件,委员会在将上述涉及海洋保护区的文件提交给理事会渔业工作组的同时,也以“欧盟”名义提交给了CCAMLR秘书处。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34-35.
2016 年9 月15 日和22 日,理事会渔业工作组审议后坚持认为,上述关于海洋保护区的文件属于环境政策范畴,并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这些文件应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提交给CCAMLR;第二,这些文件不适用《多年度立场(2014—2019)》规定的简易程序,应先交由欧盟成员国常驻代表委员会处理,再交理事会决定。2016 年10 月10 日,理事会第3487 次会议决定,关于海洋保护区的文件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提交,作为欧盟参加第35 届CCAMLR 会议的立场。2016 年12 月20 日,委员会在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理事会作出的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向第35 届CCAMLR 提交相关文件的决定。④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s.40, 42.
2017 年2 月10 日,法院院长决定,停止关于第C-626/15 号案件的审理,直至第C-659/16 号案件书面审理程序结束;将两个案件合并审理,包括口头辩论程序和最终判决。⑤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45,49.2017 年4 月25 日,法院院长同意上述9 个欧盟成员国和卢森堡参与本案,支持理事会。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48.2018 年3 月13 日,法院就两个案件举行了联合听证;委员会、理事会及有关成员国参加了联合听证。2018 年5 月31 日,总顾问提交了关于两个案件的法律意见。2018 年11 月20 日,法院(大法庭)作出正式判决。
二、案件核心争议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政策属性
(一)争端双方诉讼请求与案件争议点
在两个案件中,委员会向法院提出了两类诉讼请求:(1)撤销理事会于2015年和2016 年作出的关于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向CCAMLR 提交文件的决定;(2)命令理事会支付费用。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41,46.其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是:(1)理事会的两个决定违反了《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 款d 项下欧盟享有的在《共同渔业政策》框架下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专属权能,这是最主要的法律依据;(2)上述理事会的决定违反了《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2 款下欧盟享有的订立相关国际协定的专属权能。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68.理事会及支持它的欧盟成员国认为,法院应以委员会的请求不成立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责成委员会支付费用。④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42-43, 47-48.
从表面上看,南极海洋保护区案是关于欧盟对外关系以及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权能归属的争议,即欧盟应单独以“欧盟”名义还是以“欧盟及其成员国”名义,向CCAMLR 提交关于海洋保护区类文件。如果以“欧盟”名义,则意味着欧盟对此类事项享有专属权能,适用《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 款;如果以“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名义,则意味着欧盟及其成员国对此类事项共享权能,适用《欧盟运行条约》第4条第2款。
而实质上,案件争议点在于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CCAMLR 养护措施的法律性质及其适用范围。总顾问在法律意见中指出,在理论上,南极海洋保护区政策属性的界定可能涉及《欧盟运行条约》第三部分的环境政策(第191、192 条)与科研政策(第179~190条)以及农业与渔业政策(第38~44条)。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80.总顾问认为,科学研究政策在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措施中处于从属地位,在南极海洋保护区中开展的科学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终极目的,因此2015 年和2016 年理事会决定向CCAMLR 提交的海洋保护区相关文件中所包含的科学研究的内容仅是从属性质,不适用《欧盟运行条约》关于科研政策的条款。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s.84-87.因此,争议核心点在于,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措施是属于渔业政策范畴还是属于环境政策的范畴。本文仅分析此核心争议点。
(二)总顾问的意见
总顾问认为,尽管历史上共同渔业政策是制定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措施的法律依据,但它不应是唯一的依据。从《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 款d 项的措辞看,欧盟至少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海洋生物资源权能:一是依据共同渔业政策;另一是依据欧盟其他政策。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73.为确定法律依据,不仅需要考察欧盟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决定的目的和内容(aim and content),还应考虑此决定的背景(context)。④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76.
总顾问提出,根据欧盟法律框架,南极海洋保护区既涉及共同渔业政策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也涉及环境和科研政策的领域。一方面,海洋保护区是为了养护与研究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这是环境政策和科研政策的目的;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即可持续捕捞,这是共同渔业政策的目的。⑤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79.鉴于案件涉及两个以上可能的法律依据,总顾问采取了重心分析法(a center of gravity approach),分析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或成分,以确定其主要法律依据。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81.
如前所述,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共同渔业政策与环境政策之争。根据法院判例,一个行为不能因为考虑了环境保护要求而当然地被认为属于环境政策领域,而应顾及《欧盟运行条约》第11 条关于所有政策领域都应整合或融入环境保护的要求,特别是那些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88.根据法院关于区分共同商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判例,总顾问提出了本案区分共同渔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标准。一个行为如要被认定为真正的渔业政策措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行为明确和渔业活动相关,其目的必须是促进或管制渔业活动;二是该行为必须对渔业活动产生直接的和立即的效果(direct and immediate effects)。相应地,一个行为如要被认定为环境政策措施,它必须以环境保护为其核心目的或成分。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s.89-91.
在确定标准后,总顾问分别从目的、内容和背景三方面对2015年和2016年欧盟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决定进行重心分析。就目的而言,总顾问认为,所有这些海洋保护区的目的是为了养护、研究和保护南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减缓气候变化对南极的影响;拟保护物种不限于商业捕捞的海洋生物资源,还包括鸟类(如企鹅)和海洋哺乳动物(如海豹和鲸鱼)。就内容而言,尽管这些海洋保护区特别地关注渔船活动,但保护区要么禁止渔船活动,要么仅在特别严格的条件下才允许渔船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更重要的是,保护区不仅限制渔业活动,还管制污染倾倒与排放,促进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因此,海洋保护区不是真正的(genuine)渔业政策措施。就背景而言,南极海洋保护区不全属于渔业政策范畴,而是包含了一般环境保护的考量。例如,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5 条第2 款和《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该公约的缔约国,特别是CCAMLR成员,有义务保护南极环境免受各种人类干扰的影响。总顾问进而认为,因为影响南极环境的活动不限于渔业,也包括钻探或未来的风力发电等活动,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s.93-95.综合目的、内容和背景三方面考虑,南极海洋保护区本质上属于环境政策范畴,而不属于共同渔业政策范畴。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96.
(三)法院的判决
法院首先解读和确定《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 款d 项关于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权能范围,然后分析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背景、目的及内容,以决定其是否属于第3条第1款d项规定的权能。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81.对于第3条第1款d项的解读,法院认为根据措辞的“通常意义”(the ordinary meaning),只有那些根据共同渔业政策而采取,且无法与共同渔业政策分割的养护海洋生物资源措施才属于此项专属权能;而根据《欧盟运行条约》第4 条第2 款d 项,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渔业方面存在共享权能。④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82-85.实质上,法院支持了总顾问提出的关于两种类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权能的划分,以及关于共同渔业政策和共同环境政策之间划分的标准。此外,法院还援引1970 年《共同渔业政策》,认为欧盟关于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专属权能仅限于“养护渔业资源”(conserv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⑤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86.
在此基础上,法院分析南极海洋保护区是否属于《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款d 项规定的权能。与总顾问一样,法院从背景、内容和目的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在背景方面,法院认为尽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9 条赋予了CCAMLR 养护商业捕捞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责任,但是其他条款拓展了该公约的适用范围,如第1 条不限于渔业相关的生物资源(fishery-related resources),而是扩大到所有构成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生物有机体(living organisms),包括海鸟;第5 条第2 款要求《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缔约国同意遵守南极条约协商国通过的关于保护南极环境的措施,这更是超越了渔业管理的范畴。最后,法院认为CCAMLR养护措施CM91-04的目的也不是管制渔业活动或养护渔业资源,而是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适应气候变化等。因此,法院判定CCAMLR 的职责不仅是采取一些属于环境保护的措施,实现环境保护才是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和组成部分。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88-94.
在内容方面,法院同意总顾问的意见,认为2015 年和2016 年理事会决定向CCAMLR 提交的关于海洋保护区的文件,其主要内容是限制或禁止捕捞活动;仅允许极有限的捕捞机会,更证明这些海洋保护区是基于环境保护的考量。欧盟提交的海洋保护区文件中所包含的禁止污染物的倾倒和排放、科学研究等内容,也验证了南极海洋保护区不是关注渔船活动本身。因此法院认为,尽管这些内容部分地规制了渔船活动,但环境保护构成了其内容的主要组成部分。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95-97.
在目的方面,法院认为欧盟提交的海洋保护区文件的目的是关于养护、研究和保护南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生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这些海洋保护区所保护的物种对象,不限于商业捕捞的鱼类种群,还包括其他海洋生物资源,如海鸟与海洋哺乳动物等。因此,这些海洋保护区文件旨在实现如前所述《欧盟运行条约》第191条第1款规定的欧盟环境政策目的。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98-99.
基于上述分析与推理,法院最终判定:渔业仅是2015年和2016年理事会决定向CCAMLR提交的关于海洋保护区文件的附带目的(incidental purpose),实现环境保护是主要目的和主要组成部分。④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100.尽管2013 年《共同渔业政策》规定了生态系统方法,要求减轻捕捞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但相对于上述关于海洋保护区文件的目的,其目的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生态系统方法不能用以证明这些南极海洋保护区可纳入渔业政策范围。⑤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102.
三、对案件核心争议点的法律分析
总顾问和法院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政策属性问题都采取了分步走的方法,即先解释“海洋生物资源”,再确定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政策属性。在对案件核心争议点进行法律分析之前,应明确法院判决所指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概念,及其所处的国际法律框架,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南极海洋保护区应有的属性和要素,并对判决内容和影响作出正确评析。①需要说明的是,在南极条约体系中,有两类海洋保护区:一是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ATCM)根据《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称《环保议定书》)设立的南极特别保护区和南极特别管理区,它们可包含海洋区域;二是CCAMLR 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设立的海洋保护区,即CCAMLR 海洋保护区。二者在法律依据、目标和管辖活动等方面存在本质不同。从本案相关事实和所涉法律文件来看,法院判决中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系指CCAMLR海洋保护区。
(一)关于“海洋生物资源”的解释
在解释“海洋生物资源”时,总顾问确立的关于区分共同渔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标准显然对法院产生了影响。法院采取的“只有那些根据共同渔业政策而采取,且无法与共同渔业政策分割的养护海洋生物资源措施才属于此项专属权能”标准,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83.应该是参考了总顾问提出的两个条件。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90.但是,法院进一步援引1970 年《共同渔业政策》,将《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 款d 项所指的“海洋生物资源”狭义地解释为“海洋渔业资源”。法院的这种狭义解释值得商榷。
第一,《欧盟运行条约》中涉及共同渔业政策规定的解释,援引欧盟共同渔业政策没有问题,但是为解释2009 年12 月1 日生效的《欧盟运行条约》的某个条款而援引已经失效的1970 年《共同渔业政策》则难以理解。根据《欧盟运行条约》修定的2013 年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第48 条明确废止了原2002 年《共同渔业政策》。因此,法院在解释《欧盟运行条约》第3条第1款d项时,应当援引2013年《共同渔业政策》,而非早已失效的1970年《共同渔业政策》。如前所述,2013年《共同渔业政策》适用范围不限于“海洋渔业资源”,可采取的措施也包括了建立保护区,以养护水生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因此,如果法院援引2013 年《共同渔业政策》来解释《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 款d 项的“海洋生物资源”,则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第二,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 条第3 款,在解释条约时应考虑嗣后实践。国际法院在1949 年曾经指出:“作为一个实体的国际组织,其权利与义务依赖于其宪法性文件中所述的宗旨、明文或隐含规定的职责以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职责。”①Reparation for Injuries Suffer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49, p.180.2014 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2 条第4 款,以确定专属经济区给渔船加油行为和捕鱼活动之间的关联时,大量援引了2000 年以后通过的多边国际协定中关于“捕鱼活动”和“捕鱼相关活动”的定义,以及相关国家嗣后实践。②See the M/V“Virginia G”Case (Panama/Guinea-Bissau), Judgment, ITLOS Reports 2014, p.4, paras.216-218.因此,法院在解释《欧盟运行条约》第3 条第1 款d 项所指的“海洋生物资源”时,应考虑欧盟据此而参加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国际协定关于“海洋生物资源”的定义以及相关管理职责。截至2020 年2 月,欧盟以其享有的关于生物资源养护的专属权能参加的区域渔业条约及其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有12 个。③这12 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分别是:北大西洋鲑鱼养护组织、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地中海一般渔业委员会、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南印度洋渔业协定、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南方蓝鳍金枪鱼委员会、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和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除此之外,欧盟还在申请加入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需要注意的是,CCAMLR一直否认其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例如,2017 年修订的《关于西北大西洋渔业合作公约》定义了“渔业资源”(fishery resources)、“生物资源”(living resources)和“海洋生物多样性”(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等术语,④该公约第1 条将“渔业资源”定义为公约区域内的鱼类、软体动物和甲壳类,除定居种和高度洄游、降海洄游和溯河洄游等种群;“生物资源”是指海洋生态系统中所有生物组成部分;“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指海洋生物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综合体的变化。同时规定本公约的目的为“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鱼类资源”和“保护渔业资源所处的海洋生态系统”。⑤参见《关于西北大西洋渔业合作公约》第2条。
第三,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定义和实践看,该公约第1 条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定义为“南极幅合带以南水域的鱼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和包括鸟类在内的所有其他生物种类”。CCAMLR 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生态系统定义其管辖范围的区域组织,最早开创性地引入生态系统方法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CCAMLR 的生态系统方法强调捕捞活动不应对与捕捞目标物种相关的物种造成不可逆的不利影响。例如,在直接管理磷虾捕捞过程中,CCAMLR 还监测磷虾捕捞对磷虾捕食者(如鲸鱼、海豹、企鹅等)的影响。通过生态系统方法,CCAMLR 控制磷虾等捕捞活动,以维护整个南极生态系统的“健康”。⑥See CCAMLR, CCAMLR’s Management of the Antarctic 6 (CCAMLR 2001).
第四,1984 年12 月7 日欧盟①严格意义上,是“欧洲经济共同体”(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代表“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执行1982 年12 月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称《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鉴于本文不专门研究欧盟法,除非特别说明,一般都统称“欧盟”。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声明,欧盟拥有对“海洋渔业资源”(sea fishing resources)的养护与管理事项专属权能。②See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Competen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7 December 1984,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TREATY&mtdsg_no=XXI-6&c hapter=21&Temp=mtdsg3&clang=_en#EndDec, visited on 8 April 2019.1996 年6月27 日欧盟在签署《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权能分配作了详细声明。欧盟指出,欧盟对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管理事项享有专属权能,具体表现为:对内制定规则然后由成员国执行,对外和第三方或有管辖权的组织开展合作,这种专属权能适用于欧盟成员国的渔业管辖海域和公海。基于此专属权能,欧盟享有国际法下船旗国对悬挂欧盟成员国旗帜船舶的管制权,但欧盟成员国负责对船长及其他职务船员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4 条及其国内法进行行政、技术和社会方面的管理。关于共享权能,欧盟声明指出,它包括下列与渔业相关的事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科学研究、港口国措施以及那些针对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非成员国或《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的非缔约国的措施等。③See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Competen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with Regard to Matters Gover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ish Stocks Agreement, 27 June 1996,paras.5-8,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XXI-7&chapter=21&clang=_en#EndDec, visited on 8 April 2019.
综合欧盟的两个声明、新旧欧盟渔业共同政策以及欧盟参加的区域渔业条约等,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渔业资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渔业资源,是针对开发利用而言的,侧重于可商业利用的生物物种,即有鳍鱼类、软体动物和甲壳类;生物资源,是针对养护而言的,侧重于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可商业利用的生物物种和其他生物物种。第二,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特别是欧盟2013 年《共同渔业政策》后,应以一种发展的理念去解释欧盟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专属权能,即从“海洋渔业资源”到“海洋生物资源”,以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渔业活动及其对海洋环境影响的认知、《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第5 条规定的一般原则以及2013 年《共同渔业政策》。第三,欧盟关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专属权能,不是无限的,应仅表现在规则层次,即对内制定统一规则和对外签订合作协定;具体落实过程中,仍需要欧盟及其成员国相互协调,即权能共享,如科学研究、港口国措施、船舶及其职务船员的管理等。第四,法院审理本案时应充分考虑《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定义以及CCAMLR 的实践。法院援引1970 年《共同渔业政策》的定义,既不符合欧盟自身实践,不切合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语境,也忽视了CCAMLR对推动全球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发展的贡献。
(二)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政策属性
如前所述,总顾问和法院认定南极海洋保护区属于环境政策范畴,是基于三个理由:第一,《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序言第1 段承认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第二,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5 条第2 款和《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南极环境;第三,南极海洋保护区限制甚至禁止渔业活动,其目的不是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而是保护南极海洋生物多样性。所以,南极海洋保护区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缔约国履行南极环境保护义务的一种措施。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88-94;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s.93-95.这种解释,脱离了南极条约体系发展历史及嗣后实践,混淆了《南极条约》《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两个不同国际条约、ATCM 与CCAMLR 两种不同机制,忽视了南极条约体系以人类活动为管理对象并根据人类活动类型分配环境保护责任的基本逻辑。为准确认定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政策属性,本文先分析ATCM和CCAMLR的环境保护责任,然后从南极条约体系的角度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最后具体剖析总顾问和法院判决存在的问题。
1.ATCM框架下的环境保护与保护区
资源(包括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首先涉及资源归属问题,进而触及南极领土主权问题,《南极条约》谈判期间,各方刻意回避了这个资源问题;此外,环境保护问题在20 世纪50 年代也尚未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的初衷不是保护环境或生物,而是防止开发可能带来经济上的不利影响。②See Lorraine M. Elliot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rotecting the Antarctic 41 (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结合《南极条约》第6条,《南极条约》第9条第1款f项规定的“南极洲的生物资源”(living resources in Antarctica)应是指那些位于南纬60 度以南陆地、冰架和沿海的生物资源,不包括公海生物资源。①See Josyane Couratier, The Regim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a’s Living Resources, in Francisco Orrego Vicuña (ed.), Antarctic Resources Policy: Scientific, Legal and Politics Issue 1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M. W. Holdgate, Regulated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Resources, in Gillian D. Triggs (ed.), The Antarctic Treaty Regime: Law,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1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964 年《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是ATCM 根据《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第f 项通过的措施,②See Lorraine M. Elliot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rotecting the Antarctic 64 (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它仅适用于本地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不包括鲸类,不适用于公海的哺乳动物和鱼类等生物资源。③See S. K. N. Blay, New Trend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tarctic Environment:The 1991 Madrid Protocol, 86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0 (1992).1972年《南极海豹养护公约》是第一次突破《南极条约》第6条的限制,以独立条约的形式养护南极公海海洋生物资源。④See Christopher C. Joyner, Governing the Frozen Commons: The Antarctic Regim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20-122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8).
1991 年《环保议定书》吸纳整合了包括《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在内的相关措施,为南极环境保护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制度。为实现南极环境保护的目的,《环保议定书》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全面禁止了除科学研究外的任何与矿产资源相关的活动;二是针对《南极条约》第7 条第5 款下的所有活动制定了详细的管理规则。这些管理规则不适用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管制的捕捞及有关管理活动。⑤参见《环保议定书》最后文件,第7-8段;《环保议定书》第4条第2款。
《环保议定书》第2条将南极洲(Antarctica)指定为“自然保护区”,仅用于和平与科学的目的。根据《南极条约》第7 条第5 款在南极开展的所有活动,包括科学考察、旅游等,都应遵守《环保议定书》第3 条规定的环境原则,保护南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以及南极内在价值等,减少这些活动对南极环境造成的不利或重大不良影响,或有害改变,或重大危险等。《环保议定书》附件5“区域保护”部分规定,可通过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来保护以下南极环境目的,包括典型地貌、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生物重要栖息地;科学研究兴趣区;突出的地质、地形学等方面的特征;突出的美学和荒野价值;历史遗迹等。⑥参见《环保议定书》附件5,第3条。当然,南极特别保护区可以包括海洋区域。
综上所述,ATCM下的环境保护,只针对《南极条约》第7条第5款规定的人类活动,包括科学考察、旅游及一切其他政府性与非政府性的活动,但不包括《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下的人类活动。其环境保护的目标,是广泛意义上的南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以及南极内在价值。为保护特定的南极环境价值,可根据《环保议定书》附件5 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包含陆地与海洋,但海洋部分要经过CCAMLR事先批准。
2.CCAMLR框架下的环境保护与海洋保护区
1980 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是在南极有鳍鱼类资源被过度开发、南极磷虾资源将被大量利用,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介入等历史背景下快速出台和生效的,①See Fernando Zegers, The Canberra Convention: Objectives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Its Negotiation, in Francisco Orrego Vicuña (ed.), Antarctic Resources Policy: Scientific,Legal and Political Issues 149-1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突破了《南极条约》的适用范围,管辖海域范围拓展至南极幅合带,最北界限达南纬45度,与《南极条约》第6条规定的公海捕鱼自由和生物资源养护相对应。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目的是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其中“养护”一词包含合理利用。对于海洋生物资源,该公约将其定义为包括鱼类、鸟类等在内的所有生物种类。结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2 条第3 款和第6 条的规定,这种定义体现了该公约在养护原则方面的重要创新,即生态系统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定义理论上包括鸟类、海豹、鲸鱼等,但是这不意味着该公约可以管制直接利用这些物种的所有人类活动。相反,海豹和鲸类仍由《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和《南极海豹养护公约》规制,鸟类可以由《养护南极信天翁和巨海燕协定》规制。②《养护南极信天翁和巨海燕协定》是在《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框架下谈判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它于2001 年6 月19 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开放签署,2004年2 月1 日生效,秘书处设在霍巴特(Hobart)。该协定的秘书处与南极海洋生物养护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2015 年是双方最新一次更新谅解备忘录;同时,该协定秘书处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会议。See CCAMLR, Report of the Thirty-Six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Hobart, 16-27 October 2017, para.10.5.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其管理的人类活动是“捕捞及其相关活动”。考虑到南极磷虾是海豹、鲸类、鸟类等生物的食物,以及捕捞活动可能兼捕这些生物,因此CCAMLR 需要规制捕捞及其相关活动,以避免对海豹、鲸类、鸟类等生物的影响。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由于渔船可能在生产过程排放各种污染或将外来物种引入南极,特别是国际海事组织于1990 年将南纬60 度以南海域指定为《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附件1 和附件5 下的“特别区”,实施更严格的排放规定,CCAMLR 需要对这些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管理。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9 条,CCAMLR 分别通过了关于环境污染问题、兼捕问题、脆弱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等一系列的养护措施,如CM26-01、CM25-02 与25-03、CM22-06、22-07与22-09等。
2011年CCAMLR通过了《一般性框架》,即养护措施CM91-04,为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养护措施层次的基础。根据养护措施CM91-04 正文第2段,南极海洋保护区旨在实现6 类目标,包括保护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进程、建立科学研究参照区、保护易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区域、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功能区、保护对适用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区域等。《一般性框架》是CCAMLR 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9 条通过的众多养护措施之一,旨在落实“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目标和原则,所以南极海洋保护区的6 类目标不是独立存在的。即使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2 条第3 款c 项,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包含了“防止在近二三十年内南极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或减少这种变化的风险”的考量,其最终目的也是通过对“捕捞及其相关活动”的合理管理,实现“可持续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
综上所述,CCAMLR 负有一定环境保护的职责,但是这些环境保护职责仅针对“捕捞及其相关活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包括污染、兼捕哺乳生物与鸟类、海洋生态系统养护等。而南极海洋保护区是CCAMLR 采取的众多养护措施之一,旨在养护南极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防止“捕捞及其相关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变化,实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养护与合理利用。
3.ATCM和CCAMLR在环境保护与保护区方面的相互联系与区别
《南极条约》及其《环保议定书》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的(养护)措施、决议、决定等共同构成了南极条约规则体系,ATCM 与CCAMLR 以及其他机构则构成南极条约机制体系,分别管理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
考虑到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ATCM 和CCAMLR 相互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序言第6 段和第5 条第1 款先承认了ATCM 在保护南极环境方面负主要责任,包括《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序言第7段和第5条第2款则详细列出了ATCM通过的措施,如根据《南极条约》第9条第1 款f 项通过的《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以及其他可能通过的措施。承认ATCM 在环境保护方面负主要责任,一方面强调了《南极条约》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之间的联系,即构成南极条约体系;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及依此项通过的《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差异性。
正是这种差异性以及CCAMLR 的独立性,决定了ATCM 通过的环境保护措施不能直接适用于CCAMLR。《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5 条第2 款规定,CCAMLR 成员开展“捕捞及有关活动”时应“适当”(as and when appropriate)遵守ATCM 有关环境保护措施。事实上,CCAMLR 根据其管理活动的特点,制定一些养护措施,适当地转化了包括《环保议定书》在内的ATCM 环境保护规定,如养护措施CM26-01(捕捞过程中的一般性环境保护)、CM25-02(减少公约区域内延绳钓捕捞或延绳钓捕捞研究中海鸟的偶然捕捞死亡率)和25-03(减少公约区域内拖网中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的偶然捕捞死亡率)等。但是,CCAMLR 并非必须转化所有ATCM 环境保护规定。相反,《环保议定书》第4 条第2 款明确规定不损害各国依《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不适用于捕捞及其相关活动。
在保护区方面,尽管《环保议定书》附件5 规定,ATCM 可设立南极特别保护区和南极特别管理区,包括海洋区域,但是2005年ATCM第9号决定要求,凡是管理计划可能影响捕捞海洋生物资源或未来阻止或限制CCAMLR 相关活动的,应事先征得CCAMLR 的同意。也就是说,ATCM 下的保护区不能影响或损害CCAMLR 下的“捕捞及其相关活动”。CCAMLR 养护措施CM91-02(保护南极特别管理和保护区域的价值)附件A 也仅列明了那些经CCAMLR 同意的包含海域的10 个南极特别保护区和3 个南极特别管理区。一个值得注意的反例是第173号南极特别保护区。尽管它的海域面积占总保护区面积的98%,但美国认为该保护区的管理计划中不涉及捕捞活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科学委员会接受了美国的解释,①See SC-CAMLR, 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 Meeting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Hobart, 22-26 October 2012, para.5.63.所以第173号南极特别保护区没有列在养护措施CM91-02附件A中。
另一方面,鉴于CCAMLR仅负责“捕捞及其相关活动”产生的海洋环境问题,那些与此无关的南极环境保护则不属于CCAMLR 管辖范围,不能由CCAMLR 根据《一般性框架》设立海洋保护区。例如,2012 年乌克兰根据其2005—2011 年的科学调查提出在其沃纳德斯基(Akademik Vernadsky)科考站附近海域建立海洋保护区,以保护其底栖生物多样性,促进科学研究。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科学委员会认可乌克兰所提议海域的科学研究价值,认为值得保护,但是CCAMLR质疑了乌克兰以科研价值为由而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动机,认为应在ATCM框架下建立南极特别保护区或南极特别管理区,而不是CCAMLR海洋保护区。②See SC-CAMLR, 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 Meeting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Hobart, 22-26 October 2012, paras.5.39-5.4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ATCM 和CCAMLR 在南极环境保护与保护区方面存在清晰的职责划分。ATCM 根据《南极条约》及其《环保议定书》制定环境保护措施,CCAMLR 结合渔业管理的需要,视情况将ATCM 的环境保护措施(或相关部分)转化为其自身的养护措施,并“适当”遵守,但不是完全遵守,更不是直接适用。ATCM 设立的保护区,不应影响CCAMLR 下的捕捞及其活动;如果有影响的,应事先征求CCAMLR 的明示同意,再由CCAMLR 制定养护措施进行转化,适用于渔船。CCAMLR 的海洋保护区是以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不能用以实现ATCM的环境保护目的。
4.总顾问和法院判决关于南极条约体系解释的错误
总顾问尽管承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主要是规制捕捞活动,以实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是将《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5 条第2 款连起来解释,认为CCAMLR 有义务保护南极环境免受人类活动干扰,包括捕捞活动之外的其他人类活动和可能的钻探采矿活动。①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Opinion of Advocate General of 31 May 2018, para.95.法院的判决采纳了总顾问关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5 条第2 款的解释,同时,进一步认为《一般性框架》规定的南极海洋保护区关注的是海洋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与结构、适用气候变化等,超出了渔业范畴。为此,法院参考了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提案和CCAMLR 罗斯海海洋保护区,②2016 年10 月,CCAMLR 通过的关于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养护措施(CM91-05)主要禁止、限制和管理商业性质的渔业活动以及研究性质的渔业活动(research fishing)。法院判决未考虑这个实践。认为CCAMLR 的海洋保护区除管理渔业活动外,还保护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南极海洋保护区中渔业内容仅是小部分,更多的内容是保护环境。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 v.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tarctic MPAs), Joined Cases C-626/15 and C-659/16, Judgment of 20 November 2018, paras.93-100.因此,总顾问和法院错误地解释了《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法院还错误地解释了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目的。
在《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5 条第2款关系方面,总顾问和法院的解释有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错误地认为《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依据,且《南极条约》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之间存在层级关系;二是错误地认为所有ATCM通过的环境保护措施都应适用于CCAMLR管理的“捕捞及其相关活动”。
首先,如前所述,《南极条约》第9 条第1 款f 项是ATCM 制定《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的法律依据,但不是《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法律依据。《南极条约》第9条第1款f项所指的“南极洲生物资源”是指南纬60度以南陆地、冰架和沿海的生物资源,不包括公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所指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是指公海生物资源,旨在解决《南极条约》第6 条所指公海捕鱼自由问题,其地理范围超过南纬60 度至南极幅合度,而且海豹、鲸鱼和海鸟由其他条约规制。《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序言和第5 条特别将《南极条约》第9 条第1款f 项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环境保护义务之一和《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列出来,更明确了它们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之间的区别。因此尽管《南极条约》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共同构成南极条约规则体系,但是它们相互独立,不存在层级关系。①《南极条约》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缔约方数量,以及ATCM 和CCAMLR 成员数量,都反映了两个条约和两个机制之间的差异。截至2020 年2 月,捷克和厄瓜多尔是ATCM 成员国,但没有加入CCAMLR。纳米比亚是CCAMLR 成员,但没有加入《南极条约》。除此之外,仍有13个国家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没有加入《环保议定书》。
其次,ATCM 通过的环境保护措施并不当然适用于CCAMLR 管理的“捕捞及其相关活动”。这有两个反例:一是《环保议定书》最后文件明确规定,《环保议定书》第8 条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不适用于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而在南极条约范围内开展的任何活动;②See Final Act of the Eleventh Antarctic Treaty Special Consultative Meeting, Madrid, October 1991, para.8.二是南极特别保护区和南极特别管理区必须经CCAMLR 转化后,方可适用于渔船,那些没有经过CCAMLR 同意的南极特别保护区和南极特别管理区不会得到渔船的遵守。在2012 年的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南极与南大洋联盟提请大会注意有磷虾渔船进入第1 号南极特别管理区开展捕捞的问题,要求立即修订第1 号南极特别管理区的管理计划,并制定临时禁渔措施。③See ATCM, Final Report of the Thirty-Fifth Antarctic Treaty Consultative Meeting, Hobart, 11-20 June 2012, paras.162-168.后经CCAMLR 同意,第1 号南极特别管理区禁止捕捞活动,且由CCAMLR 将第1 号南极特别管理区列入了其养护措施CM91-02 附件中。④See CCAMLR, Report of the Thirty-First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Hobart,23 October-1 November 2012, paras.5.64-5.69.养护措施CM91-02 第1 段明确规定,仅要求渔船遵守列入其附件中的那些经CCAMLR 同意的10 个南极特别保护区和3 个南极特别管理区,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经CCAMLR 同意的南极特别保护区或南极特别管理区,如第173 号南极特别保护区,理论上渔船不必知晓和遵守。
最后,在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目的的解释方面,法院错误地将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目的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目的分割开(如果不是对立起来的话)。《一般性框架》序言第2 段明确提出,其目的是为实施《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9 条第2 款f 项与g 项。也就是说,南极海洋保护区是CCAMLR 为履行其职责和实现养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工具,而且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一般性框架》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目的的解释和落实,应考虑《一般性框架》序言第2 段,《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9 条第1 款、第9 条第2 款f 项与g 项。另一方面,虽然南极海洋保护区有很多目标涉及海洋生态系统,但根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2 条第3 款c项的规定,消除或降低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也是为了实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养护与合理利用。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是生物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前提条件,而法院忽视了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养护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犯了一个目前海洋治理中常见的错误,混淆了管理海洋生态系统和应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特定人类活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①See United Nations, Ecosystem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Ocean-related Activities: Training Manual 17-19 (UN 2010).联合国大会一再强调,“海洋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应以管理人类活动为重点,目的是维护并在必要情况下恢复生态系统的健康,以维持环境商品和环境服务,提供粮食保障等社会和经济惠益等”。②UN, GA Resolution 61/222, 20 December 2006, para.119.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不应是唯一和最终的目的。
综上,南极海洋环境保护是由全球性条约(如《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和南极条约体系共同规制。在南极条约体系下,尽管《南极条约》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存在一定联系,但是它们相互独立,分别规制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有环境保护义务。南极海洋保护区是CCAMLR为落实养护与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目的和原则而采取的一种养护措施,它仅能管制(不论是禁止或者是限制)“捕捞及其相关活动”,不能适用于《南极条约》框架下的开展一般性海洋科学研究的船舶,更不能用以实现《环保议定书》的目的。尽管《一般性框架》规定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目标多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养护,但是这些目标应服务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目的和原则。因此,在南极条约体系下,南极海洋保护区是CCAMLR 为实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一种工具,应属于渔业或者生物资源养护政策范畴,而不属于环境政策范畴。
四、案件判决可能产生的地区影响与全球影响
欧盟法院南极海洋保护区案表面上看是关于《欧盟运行条约》相关条款的解释问题,涉及的是一体化组织内部权能归属的争端,法院对本案的判决似乎仅是解决这种内部权能归属争端。但是,理事会的决策过程及其最终决定,总顾问和法院关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相关条款的解释及对南极海洋保护区政策属性的认定,以及所有参与案件的欧盟成员国对理事会决定和法院判决的支持,基本反映出当时欧盟28 个成员国(包括英国)在南极海洋保护区的目的和属性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这种新的共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以共同渔业政策和《多年度立场(2014—2019)》为代表的欧盟现行内部法律和政策,也和欧盟在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下的实践相悖,①在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欧盟代表其成员国行使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事项的专属权能,通过设立海洋保护区,管制渔业活动,以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在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欧盟及其有关成员国共同行使环境保护事项的共享权能,通过设立海洋保护区,养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但不能管制渔业活动。See Stefán Ásmundsson & Emily Corcora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NEAFC and OSPAR:From the First Contact to a Formal Collective Arrangement, UNEP Regional Seas Reports and Studies No.196 (UNEP 2015).同时,也超出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框架和职责范围,将南极条约体系不同机制混为一谈。
2019 年3 月8 日,委员会在《多年度立场(2014—2019)》尚未到期的情况下,向理事会提出关于制定2019—2023 年多年度立场和撤销《多年度立场(2014—2019)》的提案。2019 年5 月14 日,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多年度立场(2019—2023)》的决定。②See Council Decision (EU) 2019/867 of 14 May 2019 on the Position to be Taken on Behalf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Commiss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CCAMLR), and Repealing the Decision of 24 June 2014 on the Position to be Adopted, on Behalf of the Union, in the CCAMLR, L140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72-77 (2019).《多年度立场(2019—2023)》要求与2016 年11 月10 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和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国际海洋治理:我们海洋未来的议程》以及2017 年3 月14 日理事会相关结论一致,积极支持在南极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和成员国共同提交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对比《多年度立场(2014—2019)》、总顾问意见、法院判决和《多年度立场(2019—2023)》可以看出,法院的判决在很大程度上受欧盟内部政策和情势影响,未来将直接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参与南极和全球海洋事务的政策立场,并对南极条约体系和全球海洋治理规则塑造产生深远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程度亦取决于其他国家对判决所涉问题的反应。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和那些与欧盟持有类似观点的国家,可能会在南极地区或全球层面沿着判决指出的路径,推动国际规则的演变;另一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其他国家,可能就此判决提出异议或反对。这两种立场在南极地区或全球层面的博弈,将最终决定南极地区或全球海洋治理的发展趋势。
在CCAMLR 层面,如果未来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按现有提案的内容获得CCAMLR 的通过,则可能进一步增强法院判决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影响。如前所述,2014—2016 年间德国向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科学委员会提交的科学背景文件第1 部分“背景及国际协定”,明确援引国际环境文件以及《南极条约》及其《环保议定书》作为其提案的政策法律依据,德国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科学委员会表示,关于保护目标和相应保护程度的问题是CCAMLR 需要讨论的问题,①See SC-CAMLR, Report of the Thirty-Fifth Meeting of the Scientific Committee,Hobart, 17-21 October 2016, paras.5.23-5.25.但是德国却没有将包含该部分政策和法律内容的文件提交CCAMLR 讨论。因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科学委员会近3 年来主要对上述科学背景文件的科学部分进行讨论,而未能审议第1 部分“背景及国际协定”及相关政策和法律内容;同样,因为提案国没有将科学背景文件提交给CCAMLR 审议,CCAMLR 也没有机会对此问题进行讨论。随着法院判决的出台,如果CCAMLR成员在审议相关议题时认可了关于建立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的政策法律依据,以及威德尔海海洋保护区的环境政策属性,则可能进一步促进CCAMLR 从南极资源管理组织向环境保护组织转变,加强环保主义在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影响力。那样的话,CCAMLR 将可能重演国际捕鲸委员会全面禁止利用的结局。②See Joji Morishita, Multiple Analysis of the Whaling Issue: Understanding the Dispute by a Matrix, 30 Marine Policy 802-808 (2006).
在南极条约体系层面,对本案判决可能影响的评估,既需要考察欧盟及其成员国或持类似观点国家在CCAMLR 和ATCM 中的影响力,还需要考察案件所涉及的提案一旦在CCAMLR 通过可能产生的示范效应。截至2020 年2 月,CCAMLR 共有26 个成员,其中9 个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和英国;ATCM 共有29 个协商国,其中11 个是欧盟成员国和英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南极条约体系规则塑造,在政治、法律和科学等多个层面都具有很大优势。判决作出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将以此为契机在南极条约体系内推行海洋保护区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政策范畴的观点,促进CCAMLR 向南极环境保护组织转变,导致ATCM 和CCAMLR 之间职能的进一步交叠,如2018 年比利时、法国、德国等7 个国家向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协调南极条约体系下海洋保护倡议的文件就是如此。①See Belgium, Chile, France, Germany, The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Harmonisation of Marine Protection Initiatives across the Antarctic Treaty System(ATS), WP012, ATCM XLI, 28 March 2018.
在全球海洋治理层面,2016 年欧盟《国际海洋治理:我们海洋未来的议程》明确提出,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进程远落后于2020 年达到10%的目标,为此,欧盟将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及其效用;如果海洋保护区能达到30%,则将在2015—2050 年间产生9200 亿美元的收益。②See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International Ocean Governance: An Agenda for the Future of Our Oceans, JOIN(2016) 49, Brussels, 10 November 2016.事实上,在2006 年BBNJ 特设工作组第1 次会议上,欧盟就建议未来的新协定应规定,除其他外,建立海洋保护区、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禁止破坏性渔业活动等。③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ary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20 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 3-4 (2006).在2011年BBNJ特设工作组第4 次会议上,也就是海洋保护区被纳入“一揽子方案”的关键会议,欧盟呼吁履行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实施计划》设定的目标,弥补2008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9 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具有生态和生物重要性的海洋区域”与已有海洋保护区之间的差距,呼吁将海洋保护区纳入“一揽子方案”等,推进全球范围内设立海洋保护区的进程。欧盟此意见得到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和平等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支持。④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ary of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25 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 4 (2011).对于BBNJ 协定和现有国际协定或机制,如《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关系,尽管联合国大会决议明确指出,未来BBNJ 协定“不损害”(not undermine)现有协定或机制,⑤See UN, GA Resolution 69/292, 19 June 2015, para.3.但是各方关于“不损害”的解释存在明显分歧。⑥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ary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25 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 12 (2017).在海洋保护区方面,欧盟认为,更严格的保护措施不是对现有协定的“损害”;同样地,欧盟此观点得到了公海联盟等非政府组织的支持。⑦Se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mmary of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n Marine Bio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25 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 6 (2017).
综上,法院判决不仅可能促进CCAMLR 从南极资源管理组织向环境保护组织转化,导致CCAMLR 与ATCM 的职能趋同,还会间接影响未来BBNJ 协定和现有条约相互关系的处理,削弱现有海洋国际治理机制的职责。
五、结语
法院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案的判决,片面或狭义解释了“海洋生物资源”,混淆了ATCM 在保护南极环境方面和CCAMLR 在养护南极生物资源方面的职责,以及二者对不同人类活动管理的分工。法院关于南极海洋保护区属于环境政策范畴的结论,不仅从国际法角度看法律逻辑值得商榷,而且与欧盟当时有效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以及其在东北大西洋的实践不一致。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全球共识,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在具体法律框架下明确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不同管理机制的特点和分工差异。目前,海洋保护区因其面积直观且易测算等,被有组织地推崇为海洋治理的首要选择,存在脱离人类活动和具体现实需要、缺乏必要的量化分析和评估机制、片面追求保护区设立及其面积等趋向。现有相关区域组织的条约及实践清晰地显示,尽管养护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已经成为很多国际组织的共同管理目标,但是海洋保护区的政策属性、功能设计仍取决于保护区管理机构的法定职责,及其所管理的人类活动。
海洋保护区作为一种管理工具,没有好坏之分,但其运用和实施的方式、范围和程度可能重塑海洋保护与利用的根本规则,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成本与收益分摊效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设,不仅是影响海洋渔业本身的经济问题,也必然涉及新海洋规则的形成和战略利益的重新分配。①参见唐建业:《怎样看待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中国海洋报》2015 年10 月29 日,第3版。
鉴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南极条约体系以及全球海洋治理中的影响力,考虑到欧盟已有的政策主张与实践,可以预料,法院对本案的判决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地区影响和全球影响,而南极条约体系及BBNJ 协定谈判将是这种影响最直接体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