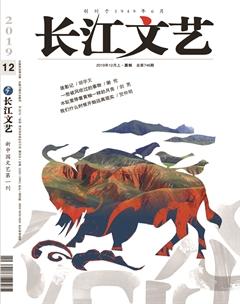漳河桥
喻长亮

早上,我要到镇上去开会。
离开会的时间还早,我站在窗前点了一支烟。
梅姐已经来了,双手握着长长的铁剪,嚓嚓地修剪花坛。偶尔,柔声对围在身边看热闹的孩子们说,小心露水打湿了衣裳啊!她穿着一件宽松的外衫,里边衬着一件桃尖领口的薄毛衣。随着身体的摇晃,丰满的胸部有节奏地颤动。她蹲下去时,桃尖领口低垂,雪白的乳沟若隐若现。
她住在镇边的一个小塆子里,姓梅,老师们都叫她梅姐。我也这么叫。她的儿子周小山在这儿读学前班,明年就上小学一年级了。她每天这个时候准时来校园做卫生,顺便接送孩子上下学,很方便。中午,手上的活儿做完了,孩子们也差不多放學了。她在校门口的门房里歇一会,喝口水,等儿子出来,母子俩一起回家。
从学校到镇上差不多十分钟的路程。抽完烟,时间快到了,我提着公文包出来。有老师到校了,拿着一串钥匙逐个打开教室的门。操场上有一群孩子在叽叽喳喳玩跳绳的游戏,见教室门开了,呼地一下散了,背着书包向教室跑去。我经过她身边时,轻咳一下,她本能地捂了一下胸口,赶紧站直身体,脸上泛起红晕。梅姐早!我说。她理了一下额上的头发,露出洁白的细牙,笑了,说,校长早!校长出去啊?我回答说,是的,去镇上开会。她说,校长真忙。我说,不忙不忙,便若无其事地出校门,径直往镇上走去。
路上经过漳河,河床上裸露着成片的鹅卵石,只有一条细流在缓缓地流动。河上有一座桥,叫漳河桥,用预制板搭成。这桥不牢实,每年都叫洪水掀掉,随后又搁上几块预制板,重新搭起。据说当年这里没桥,只是简单地摆几根木料供人们垫脚过河。后来有人在河里打上木桩,做了一座木板桥。为了阻击日本人进攻,当地抗日队伍拆掉木板桥,在河那边的山坡上据高凭险,杀死不少侵略者。战争结束后,小桥又恢复原来的模样。桥下有一口深潭,由大水冲积而成。潭水清澈,能见到水里的游鱼。夏天,孩子们经常在这里游泳戏水,大一些的孩子扎进水里,在石缝里摸鱼。常见他们提着一串黄鱼、鲫鱼什么的摇摇摆摆地回家去。
我踏着水泥板桥过河,参加镇政府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工作。会后,我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梅姐那儿。这是一栋单门独户的瓦房,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子,平常很少有人到这儿来。我去的时候,梅姐已经回来了。不用说,她提前做完手上的活,没等儿子放学,一个人先回来了。她把屋子收拾妥当,只等我到来。早上我说到镇上开会,实际是告诉她,我要去她那儿。她男人在外面打工,我去她那儿很方便。所以,“到镇上开会”,成了我们幽会的暗语。梅姐心领神会,从不爽约。有时去干别的事情,我也会找机会跟她说,到镇上去开会,然后去她那儿打个时间差。这件事我们做得很隐秘。表面上我们客客气气,实际上就是那种关系。
一年前梅姐托人介绍,找到我说,她儿子周小山在这儿上学前班,她每天都接送儿子上学,想顺便在学校找点事做,补贴一下家用。她身材凹凸有致,皮肤白腻光洁,让人想起温润的美玉。我打量着她,一口答应了。她高兴极了,激动得脸颊绯红,一再道谢。
她负责校园的绿化工作。她做人很谨慎,很少与人打交道,也不大与人说话,总是尽心地做分内的事,让我很放心。
她做完手上的活,就去门房那边等儿子放学,母子俩手牵着手一道回家。那是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左额发际处有一块指头大小的红色胎记,常见他在校园里跑来跑去。妈妈修剪花坛或浇水什么的,他也跑过去帮忙。梅姐停下来,亲亲他的小脸,让他跟孩子们一起玩去。
梅姐关上门,回身紧紧抱住我,说,怎么才来?我放下公文包,说,刚散会就来了。孩子呢?不用去接?
她熟练地解开我的扣子,声音颤抖,说,不用,跟着大孩子回来就行了!
我们很快进入状态。梅嫂的身体柔软而富有弹性,一点也不像个做体力活的女人。她看上去文文静静的,在床上却十分火辣。这正是我迷恋她的地方。她不停地扭动身体,撩得我火烧火燎,急吼吼地动作。她啊啊地叫着,含混地说,你要吃人啊,要吃人啊!
恰在这时,屋外哐地一声闷响,连床都震动了。我浑身一抖,跟突然出现一个人在跟前似的,惊出一身冷汗。我一下子趴下,她抓着,咬着,喘着气说,是狗,狗闹的。你来啊,快来啊。
我惊魂未定,手机又响了,只听副校长在里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出事了,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了!
我顾不得什么,穿上衣服,夺门而去。
屋檐下,一白一灰两条狗缠在一起,见了人,扭动身体往一边躲去,嘴里发出惊恐的叫声。我突然感到下边一阵剧痛,趔趄着蹲了下去。
不远处的河滩上全是人,水潭边、桥上全站满了人,他们不时地指指点点、叫嚷着。有人跳进水里,用长篙在深水处探捞。几个附近的农民背来渔网,用力向水中撒去。
老师们都来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口大腰盆,坐进盆里,徒手划到河中间,用竹篙在水里打探。
看到我来了,几乎所有的人扭过头来,将目光对准我。校长来了,校长来了!有人小声说。
校长一定要救救孩子!
校长有办法的!
他们像看到救星一样,远远地让出一条路。
怎么回事?我表情严肃,与在梅姐那儿判若两人。
一个孩子掉进去了。有人指指水潭。
是周小山。
周小山?我打了一个冷颤,梅姐的儿子?
我丢下公文包,脱掉皮鞋、西服,也加入到打捞的队伍中。
看,校长也来捞了。
这是一条毒蛇!
应该把它挂在树上,让它死无葬身之地。
不,应该把它烧了。
埋了,还是埋了好。
一个胆大的孩子将蛇挑起,用力往空中一抛,吓得孩子们尖叫起来,四散逃开。死蛇落地,他们又围拢上来。如此反复,乐此不疲,一个个兴奋得脸上红扑扑的。
这时,身后的河里咚地响了一下,他们不约而同地循声望去,只见河面上泛起一层层波浪。
谁?有人惊叫。
谁掉进去了?
他们呼地站起来。
谁?快看看是谁。孩子们惊恐地瞪大眼睛,像一群受惊的小鸟,回过头来你看我,我看你。
说不定是谁扔石头呢?有人怯生生地说。
周小山,周小山不见了。有人叫出来。
周小山掉进去了。
他们大叫,瞪着河面惊慌失措地喊:救命啊!周小山没命了!
梅姐得到消息,跌跌撞撞地跑到河边,双手深深地抓进河泥里,没命地哭嚎。两位婆婆将她抱起来,往坡上扶。她不,倔强地扑到水边,要下水捞孩子,浑身湿透了。
警察请来两名潜水员,潜入水下搜寻。但是没有结果。他们告诉岸上的人们,潭里的地形并不复杂,好多地方甚至很平整,潜下去便一览无余,根本没有小山的身影。为了避免疏漏,他们先后三次下水,一次比一次查找得认真仔细。他们肯定地告诉岸上的人们,周小山根本不在水里。
一河人只差把河水抽干了,也没有找到周小山的影子。梅姐满脸泪水,拄着木棍沿着河边一路寻找。按理说,河水没大流动,有的地方露出河滩,只有细流经过,小山即使掉进水里,也不会漂到别的地方。但是她仍然找到下游很远的地方。
警方怀疑小山叫人拐走了。至于落水,只是孩子们的错觉,或者是恶作剧罢了,理由是河里没有小山。那年头,经常有孩子叫人拐走。这么推断不无道理。有人说曾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在学校附近停了很久,这无疑增加了“拐走”的可能性。
事后,我去了梅姐家。她双眼红肿,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掩面而泣,说,我不该回的,我跟他一起回来就没事了。
我不该回的,不该的!她的眼神空洞无光,直直地看着远处,反复地说着这句话。
她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我握着她的手轻声说,没事的,警察说了,小山不在河里,他还活着!
她没有听到我的话一样,挣脱我的手,依然重复着那句话:我不该回的!她太伤心了,我知道这时说什么也没有用,只得黯然离开。
第二天一早,梅姐又出现在校园里。
她跟往常一样开始干活。清扫院子,修剪花坛,给花草浇水。一切看上去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没有任何异样。昨天的事情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放学铃声敲响了,她早早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从眼前走出去。我这才明白,她在等周小山一起回家。直到孩子们都走光了,她还站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望着空荡荡的校园,她眼里全是焦虑,不安地搓着手,喃喃地说,小山,小山呢?
一连好多天,她都如此。我发现了这些变化,对此深感不安。
早上,我来到她身边,故意说,梅姐早!她站直身子,还是客客气气的,说,校长早!校长出门啊?我有意说,是的,到镇上开会。她点点头,平静地说,哦,开会,校长真忙。
我跟过去一样,在那个时间点来到她的家门前。只见门上一把锁,她没有回来。我匆匆往学校赶,远远的见到她在河边走来走去。她在学校里没有等到孩子出来,又到河边寻找来了。
她在桥下的水潭边转来转去,像没见到我一样。一个下午过去,仍没有离开的意思。我走近她,说,梅姐,天快黑了,该回去了。她茫然地望着我,摇头说,不,我找小山呢!
日复一日,深潭边让她走出一条小路。那儿本来光秃秃的,现在却让她走出一条路来。
她瘦了下去,脸色蜡黄,双眼不再顾盼有神,头发如同受了霜的枯草,没有光泽。
我又试过几回,说到镇上去开会,希望唤醒她的某些记忆,让她明白孩子并没有掉进河里。结果她忘了我们之间的默契。这件事把她击垮了。
一次,我说,梅姐,小山在写作业,写完就回的。你先回吧。
哦。我先回?
是的。他一会儿就回家了,你放心。
她终于吁了一口气,说,校长让我放心,我就放心。她如释重负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我稍感宽慰,庆幸自己好不容易将她“劝”回去。
我仍不放心,远远地跟在她后面。她穿过漳河桥,直接进了塆子,掏出钥匙开门,然后在门口的石条上坐下来,痴痴地望着学校的方向。
我走近她,说,梅姐,怎么坐在这儿呢?石头上凉,坐不得。
她还是那样木然,说,我等小山。
要不,到屋里去等。
不,校长说了,他一会儿就回了。一会儿工夫,她就似乎不大认得我了。
要不,你进去做饭。饭做好了,小山就回了。
她摇摇头,固執地说,不,我要等他回来。我哪儿也不去。
小山要吃饭的。我替你在这儿看着,好不好?
小山要吃饭?
是啊,他饿坏了,孩子饿得快。你做慢一点都不行。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喃喃地说,小山饿了,小山要吃饭。她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尘土,转身进去了。
我在门外抽了一支烟,便闻到饭菜的香气。唉,她做的饭我吃过,真是好吃极了。
她出来了,说,小山,小山呢?
我灭了烟头,说,还没回呢。
还没回?饭都做好了。
要不,你先吃,我给他带一份到学校去。这孩子,怕是作业多,赶都赶不完。
没过多久,我调到山里边的云岭小学上班,校长的职务自然不再担任。组织上这么安排,我无话可说,反倒心里好受一些。换句话说,让我去坐牢也不过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丢了,我这个校长难逃其咎。
我经常梦见一个厉鬼举着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怪叫着追杀我。一会儿,又变成周开元追杀我,吓得我大汗淋漓,整夜不敢合眼,瞪着眼睛直到天亮。是的,我患上了失眠症。
不久,因为生源减少的原故,所有的小学都合并到漳河镇初中,镇中心小学和云岭小学也不例外。一时间,漳河镇中心小学变得冷冷清清,操场上再也看不到孩子们跑来跑去的身影,听不到上课的铃声。
梅姐一如既往地将校园的绿化做得井井有条,花坛修剪得清清爽爽。她还是那样一丝不苟,丝毫不受学校合并的影响。到了放学时间,她还是站到校门口,等待儿子周小山从里边出来。她的表情专注,似乎正看着一群群孩子从她面前经过,而周小山很快就会从里出来,蹦蹦跳跳地来到她身边。
我开始寻找周开元。
我猜测,周开元不露面,肯定跟我与梅姐的那段隐情有关。而周小山神秘失踪,一定又跟周开元有联系。他一定发现了我们的秘密,悄悄带走了周小山。这么想着,我汗透背心,无地自容。
不管怎么说,找到周开元,就有可能找到周小山。如果周小山回到梅姐身边,她的病一定不治自愈。
我以旅游的名义,跑遍所有周开元可能去的地方。东北、山东、河南、厦门、湖南、武汉,表面上看是在游山玩水,其实是在找人。只要听说他在哪儿做工,我都会赶过去,到处打听他的行踪。我甚至弄了一张他的照片,放大了带在手上,逢人就问:见过这个人吗?
自从那次在梅姐家受到惊吓,我再也做不了那事。老婆气急败坏地问我,不当那个校长,你就成软骨头了?后来她买了一张去南方的车票,再也没有回来。这真是报应啊。
我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精神恍惚,浑身乏力,经常一连几个昼夜不合眼。一位老同学见了我,担忧地说,这样下去你会得忧郁症的,那就麻烦了。他给了我很多预防忧郁症的建议,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离漳河镇二百多里,有一个叫走马岭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集镇,街两边是各种小店,卖水果的,做早点的,做小炒的,理发的,都窝一起。窄窄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十分拥挤。据说这里过去是一片洼地,除了一些菜农,没有多少人口。后来人们都往这里挤,人就多起来。走马岭那时只是路口一个卖早点的地方,不几年工夫,就发展成一个小集镇。到这里赶集的,大都是长住在这里的外地人。他们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大声地跟菜贩讨价还价。一些拉客的麻木突突地挤进来,在人群里招揽生意。
街头有一家超市,叫老郭超市。老板也是外地人,叫郭如海。
郭如海曾在一家电缆厂当搬运工。
这种活路不光要下死力气,还很危险。电缆材料卷成半人高的线筒,线筒码得跟山一样,一不小心就会倒塌下来,轻则砸伤人,重则出人命。很多人都不干这种活,宁可少拿点钱也要躲得远远的。郭如海不怕,只要多赚钱,他什么苦活累活都肯干。这些年他跑过很多地方,当过泥瓦匠,做过模工,干过清洁工,甚至给人做过饭,什么能赚钱他就干什么,哪儿有事就往哪儿跑。他个子不高,皮肤晒得很黑,身体偏瘦,还有些驼背,走路时喜欢低着头,仿佛从没抬过头似的。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相信,那么笨重的线筒,在这个瘦弱的男人的手上,竟然给自如地搬来搬去。干完活,他就回宿舍睡觉。偶尔出来转转,又不声不响地回到住处,再也不见人影。有一回,他无意中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买彩票。那样子跟开会一样,不停地讨论,今天出这个数字,明天出那个,各说各的理由,不时争论几句,气氛很热烈。他一时兴起,花两块钱买了一注。此后,便经常光顾那儿。他不多买,一次只买一注。第二天再去。这一买就是一年多。一次,他竟然中了五万元奖金。他跟做梦似的,差点晕过去。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他在工地上累死累活这些年,也没存这么多钱啊。
他一时手足无措,本能的反应是将这笔钱送回去,交到媳妇手里,才能放下心来。他跟厂里请了假,不声不响地坐上回老家的公汽。
不久,他来到走马岭,在这个陌生的集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
除了守店做生意,他极少与人接触,也不大说话。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待人和气,却又沉默寡言的男人。现在,他的小店变成走马岭最大的超市。超市里请了好几个营业员,帮忙打理生意。
他除了经常到超市里转转,就待在家里研究彩票。买彩票成了他唯一的爱好。他在客厅挂上一张大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数字,数字之间连着弯弯扭扭的线条,都是他一笔一笔画上去的。他戴着老花镜,凑在大图上圈圈点点,然后在小本子上记下一组数字。他每天还是只买一注,两元钱。奇怪的是,自从那次中奖以后,他一回都没再中过,连五元的小奖也没中。不过,他不以为意,仍乐此不疲。
小店开张不久,他的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一个小子来。小家伙叫郭一枫,来了就在走马岭上小学一年级。
逢年过节,这里的外地人都要回老家跟亲人团聚。每到这时,走马岭变得格外冷清。唯独这对父子,自打来到走马岭,就没见他们回去过。
郭一枫后来在武汉上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记者。一天早上,郭如海到外面早点店里去买了一杯豆浆,回来时被一辆麻木撞倒了。他是脑袋先着地的,除了一点擦伤外,看不出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他昏迷不醒,怎么喊都喊不过来,手里提着的豆浆撒了一地,方便袋也碾得破碎不堪。他很快被送进醫院抢救。
儿子郭一枫闻讯赶了回来,握着父亲的手哭喊道:爸,爸,你醒醒!
郭如海睁开眼睛,气若游丝地说:回家。
郭一枫凑近了,问道,什么?您说什么,爸?
回家,我要回家!
郭一枫泪如泉涌,这么多年身居异乡,从不轻言回家的父亲要回家了,这是要叶落归根啊。
此后,郭如海再度陷入昏迷,跟植物人无异。
在外面这么多年,郭一枫的脑子里早已没有老家的印象。奇怪的是,当车子开来时,郭如海竟然奇迹般地清醒过来,他甚至挣扎着坐起来,手指前方,让车子跟着他手指的方向前行。车子经过一座高大的水泥桥,驶进一个小塆子。车子停下来,他再度陷入昏迷,从此没有醒过来。
郭一枫看到一片空旷平整的稻场,场子的一角静卧着一只石磙。一幢低矮破旧的瓦房,木格窗,木板门,窄窄的门廊。他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这是他的家呀!他回家了。屋檐下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目光呆痴的女人,茫然无措地看着贸然出现的他们。他定定地看了她好久,终于认出来了,那正是二十多年不见的老母亲啊。他紧紧抱住母亲,说妈,你怎么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