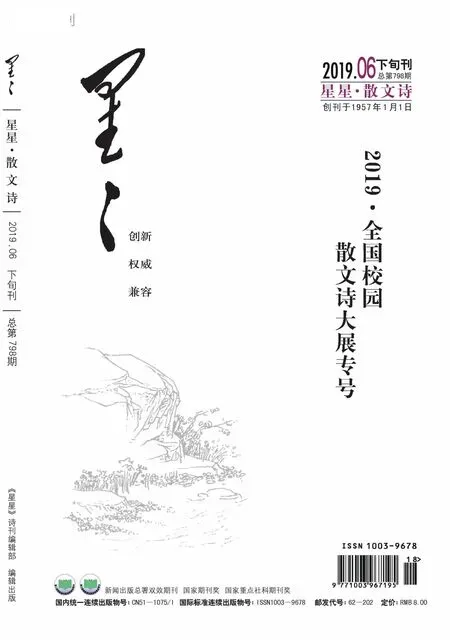风也有使命,只是一直很忙(外一章)
2019-12-30 11:06杨云天上海
星星·散文诗 2019年18期
杨云天(上海)
风也有使命,只是一直很忙——漂泊、徘徊、眺望、还乡。
卷起地上深埋的落叶,收掇大树遗忘的伟大志向。参天愿望,已被虫豸啃噬得只剩骨骸。
吹动岸边第一棵未发芽的春柳,是唤醒压抑多时的萌动。萌动!除用以形容冬天外,在柳世界只算是料峭春风的另一名词。
吹开教室有窗格的后门,制止血淋淋的窥探,让夏日课间那珍贵的风,谋划一场逃亡。
吹散梯田上簇拥的麦穗,是提醒被米酒灌醉的老汉,注意牵挂只在腊月间归家的子女,在凛冽寒风中能以“新酿”为由与父母沉醉一宿。
这都仅是些苍白的开始或结束,使命却终是个残酷的介词。
据说,风是一个诗人,善于开头与结尾,却总不能善始善终。他一直很忙,总会把使命用作动词。
那么我们都将是一阵风,从教室走廊到麦地田埂,从春天的游园到秋天的赏景,妄图拿单薄如蝉翼的动词填满这深渊般的长长介词。
但也因此,我们很忙,忘记漂泊、徘徊、眺望、还乡,最终都变成了一阵风,没有留下一点印记。
浮 尘
慵懒的仲夏午后,阳光像某种野兽,在黑夜里寻找猎物。
破窗而入!角落里窥视的浮尘慌忙逃散。
对于人类来说,逃跑方向最好是左和右。
它们却向上,起起伏伏地飘着,那是最易于被捕获的位置。
“大概在很努力地上升。”窗边的人如是说。
像我。以及那被阳光普照如同恩赐的生活。
一直等待,只能够等待!被俘获抑或落下。
静静地,直到我们都成了泥土。
猜你喜欢
气象学报(2022年2期)2022-04-29
学苑创造·A版(2021年8期)2021-08-09
湛江文学(2020年2期)2020-11-18
青年文学家(2020年16期)2020-07-13
东坡赤壁诗词(2020年3期)2020-07-04
东坡赤壁诗词(2019年5期)2019-11-14
人大建设(2018年7期)2018-09-19
当代教育(2018年4期)2018-01-23
阅读与作文(初中版)(2017年8期)2017-08-04
电影故事(2016年5期)2016-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