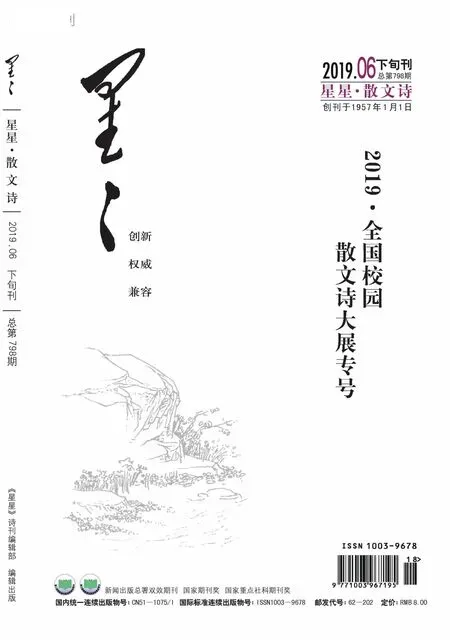剪辑旧时光
赵兴高(甘肃)
1
那年回乡,看见八十多岁的爷爷,佝偻着身子,背着一捆芨芨草,缓缓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
原本一米八的身板,躬到了一米五左右。人啊,有时不得不向命运低头。
爷爷一生背负得太多,宽厚的脊背,背过六个儿子、三个女儿、二十三个孙子,背过饥饿、埋怨、委屈。现在老了,老得只能背动一小捆草了,亦然没闲着。
听到我呼唤的声音,爷爷吃力地转过身来,仰起脸瞅着我。从缓缓舒展开来的笑容里,我感受到了爷爷对亲人相见时喜悦的仰视。我知道,那也是爷爷对幸福的仰视,对自豪的仰视。而我,岂敢让爷爷仰视。
我躬下身子,卸下爷爷身上的草扛在自己肩上,搀扶着爷爷缓缓前行。爷爷气喘得说不出话,一路上,只听见手上木杖落地的咚咚声。
如果说,俯身,是爷爷向故土深深的谢意,那么以手杖叩地,该是爷爷向故土的求助了。
到了我家门口,爷爷歇了会才缓过劲:“草你背回去,我先去你叔家,待会再过来。”
一条小土路上,爷爷躬着身子,拄着木杖,踽踽独行。走到小路尽头时,吃力地转过身来,吃力地挥了挥手中的木杖。爷爷,他知道在小路的另一头,茕茕孑立着肩扛一小捆芨芨草的孙子,在目送着他哩。
2
对奶奶的回忆,更多地来自母亲的叙述。母亲说,奶奶39岁就当婆婆了。
我就一直想着,39岁的婆婆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不下田干活?不入厨做饭?只是坐在堂屋里发号施令:大媳妇挑水、二媳妇烧火、三媳妇和面……
母亲笑着说,你还挺会想的。
母亲没肯定,也没否定,只是补充说,你奶奶有时琢磨不定哩,开朗起来说说笑笑,安静下来一言不发。
那时家口大,来往的亲戚多。亲戚之间往来要事,就是给人家做一碗像样的饭。做什么,做多少,全凭奶奶拿捏。奶奶让做一碗汤面,端上桌又骂开了:“这些媳妇们啊,让做干拌面,结果给做了碗汤面条。哎,亲戚们,凑合着吃点,下次来我亲自做。”
每次听到奶奶的训叨,母亲和婶婶们就不爽,这不都是你安排的吗?
我告诉母亲,你们可能误会奶奶了。在那个半饥半饱的岁月,以这样的方式待人接物,既给了亲戚面子,又长了自己精神,是何等的智慧啊!
母亲说,有时你奶奶一个人坐着,哪也不去,什么话也不说,让人心里发慌哩。有一次该吃饭了,谁去叫她都不动,不知道怎么了。后来又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该说说,该笑笑。
我突然觉出奶奶当初的无奈来。说实话,谁要是坐在一个大家族婆婆的位置上,那她注定是这个家族里最孤独的人。她能看到这个家族里所有的秘密,却又不能说破,就如同俯身向下的星星,只是更多的被人仰视,而自己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闪光、发亮。
听我这么讲,母亲点着头说,其实你奶奶凡事心中都有个谱系哩,在她离世前,婆媳说过很多知心的话。我不知道奶奶对母亲说了什么,但我知道,那些话,让母亲一直都感受着奶奶的好和不易。
3
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外公挑开门帘进屋,叫母亲取一只碗来。
外公个头不高,留两撇八字胡,戴一顶瓜皮帽。
因和我们邻村,外公来我家时,顺便拣了几把收割时撒落在田里的黄豆,母亲便炒了来,俩人一边嚼着豆子,一边说着话。
那些年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还小,按工分所分口粮根本不够吃,所以父亲长年在外搞副业,以图多挣点工分。母亲带着五个孩子艰难度日,和村上磕磕绊绊,受气的地方就多,甚至更多的不愉快,都来自亲人之间。外公便不时来我家,开导着母亲。
外公和母亲一粒粒嚼着黄豆,像是嚼着一件件不愉快的事。我想外公一定是想告诉母亲,生活其实就像嚼豆子一样,有时在咬碎豆子时,也会咬到舌头,甚至会咬出血来。
外公是读过书、外面闯过的人,说话中听。记得一次外公劝母亲,别太计较吧,相邻的井水往一块儿流哩,相邻的炊烟往一块儿拧哩。过好日子,不要在人前逞强,要在人后争强哩。
外公的一句人后争强,令母亲憋着一口气,像男人一样赶着毛驴车,上九条岭拉煤块;带着未成年的我们,整夜整夜从河坝里拉沙子,铺到碱地上改良土壤;有时彻夜坐在羊油灯下,一针一线缝补着艰难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