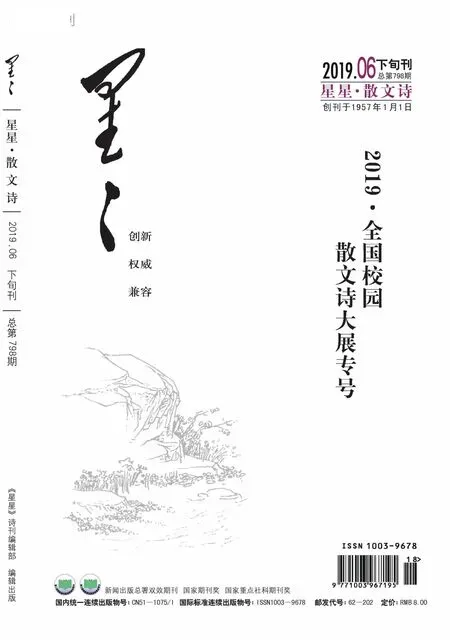明媚的忧伤(组章)
转 角(黑龙江)
妙笔生花的人
人藏在人中。
臻于我12个月的细致观察,当你路过了我的内心,另一个你已悄然上岸,而中间缺失的部分猛地消失。
太离奇了,中间部分是一个在黑夜里滑冰的光影,冰面泛着道道白光。
是你还是我?是另一个你还是另一个我?相互兼容地支撑着彼此,共同躺倒在松花江江面上,共享冬日,冰夜,和闪烁不定的对寒冷的无奈与愤懑。
横陈于此,身心清醒,我们各自安好。一件棘手的事情不再棘手了,我放下了你,你成为我新的粮仓,最微小的一粒,等待另一个你在我的欢笑中无怨地离开。
那个在画布上修饰人形面孔的人,逃走了。
一场喧闹成为我的道具,而你呢,在清绝寒冷的北方坐实命运的惶惶不可终日,被地狱之手遥遥召唤。
金属的爆裂声突然抵达!
令人猝不及防的还有我和你的另一个你我,整个世界都在紧张,恐惧,人形悬空在一堵墙上,再妙笔生花的人,也无法描述,不可描述。
冰面,陷入溃败之势。
火 鹤
佛焰,有毒。
靠在老藤上,可腐蚀爱与死。黎明沉默成白色,记忆之门将死于我的芬芳。在新年即将到来的最后一刻,黑夜躁动不明。
那曾使我恐惧的没有路灯的街道,每路过一次,就眩晕一次,如同火鹤在尘世隽永而凋零地不肯离开。
啊,或白,或红,清脆响亮的迫近留住了我蓬乱杂草一样的思绪。
所有虬枝都被温度或者湿度浸染成了不安的颜色,天空不再幽深,我文明的沙漠似乎凝固在海市蜃楼里了,驮我行止的大轮子飘忽不定,我已跑得太远,太远……
十二个美妇在跨年夜诉说着孤独,我知道我和死神不止隔着一小段空白。
十二信使成为我生命里最关键的说明。然而我妥协的办法已在泼墨似的一年中最后的夜晚栩栩如生,像石碑一样稳稳落座于一座浮岛上。
沙丘与繁花开始巡礼,这令我无比珍视的炽烈相见在还未见时又突然宣告结束。
一成不变的不信任纯真得可笑,神智在医生的注视里偃旗息鼓,我被自己或者另一个自己构陷——
沮丧,消沉,生得毫无意义。
一种毒性隐隐发作,一轮红日缓慢西沉。
黎明前一切尚无动静
人的意识形态有一种腐朽的棺椁的味道。
多年前,我还消陷于往返普陀山的轮渡上,无法摆脱一种神秘的指引,一份苦乐悲喜交相排斥的暧昧之中。
这种祭祀以冷漠的态度被海上观音所见,却并不为大多众生认可。直到此时,我依然认为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就是说,它第一次成为永不暗淡的信念激励我,并告诫我不要在抑郁里放弃蝼蚁之身。
鞭子在黎明到来之前不时地尖叫,如今,我以蓝色为鳍,以一尾鱼的形式省略了越冬之物。活生生的,不是玄幻,不是虚拟,静静匍匐在北方。
夜,安然醒在重复的命运里了。
向南之路濒临倒闭,而我却躺在油腻的中年为一份不得已的布局欢呼雀跃,或高或低地点数黄玫瑰的摆放位置。
不知道的可能还有我的生,是死的又一次预演。
不难想象,晨曦扑打在我的空身时,梦的苦味是否温柔地促使我又多活了若干年,以慰我莅临尘世瘦小,荒凉的一段时光。
我拿什么留住你呢?
在熹微到来之前,我的孤绝,我幽默的豁达的丰饶而美的黎明。
然而,一切都还尚无动静!
明媚的忧伤
一切的存在都在奇异地生发。
太阳,空气,水,事物,人伦,尘埃……而可怖的躁郁落拓难消。一个悖逆激惹,一个沉闷悲伤,松散复杂的内部包裹着两个互相争斗的人。
维系破败力量的唯一方式是胁迫。我是神奇壮美,我对自己严加管束;我是危险沟壑,我要给亲人带来力量和美。
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一个一有理由就逃跑的怪物,是上天的恩赐,孤绝独一。
比如黄昏,《圣经》《古兰经》《金刚经》等等一切怪诞的荒谬的精神枷锁,日落前,都不复存在了。
比如你我,畸形地相遇,总是不很老练地惴惴不安。
在白雪到来之前,我隐去我明媚的忧伤,带你认识黎明,在新的喧嚣和爱情里像王者一样接受颂赞和跪拜。
在你面前,我放下孤独一人,以圣徒的身姿眺望,对死的畏惧。
鬼魅偶有加身,似狂野的真实的存在。
我的可预见性以梦的形式享受微妙的欢乐。恐惧却如入无人之境,晨起光芒万丈,夜色降临,我又重新换了一副面孔。
生命之血时刻在海天交织处潜伏,颤抖着双手,特指绿色为故乡。
到哪里去呢?
只一个我,像神一样被四处放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