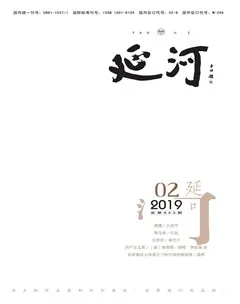隋唐诗二题
月夜春江
1
开皇八年(588年)的腊月,隋王朝派出了皇帝的次子杨广,统率数十万军队,由北而南,发起了大规模的渡长江之战。第二年的早春很快来临,战事就已宣告结束。只是不知道,彼时春日的长江,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这场灭国之战逼降了南朝末帝陈叔宝,继而招降了三吴之地和岭南。至此,杨氏王朝一统天下,结束了汉末以来多政权分立将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
转眼,整整十五年过去了。
那是仁寿四年,杨广继承父亲的皇位数月之后,陈叔宝去世。根据正史《陈书》的记载,帝国的新主人给了这位陈后主一个谥号:炀。
谥号,是古代对帝王将相之类人物一生功业的“盖棺论定”,人死了以后才有——所以,《康熙王朝》里斯琴高娃嚷嚷着的“我孝庄”,就是一桩笑话。
那么,“炀”是什么意思?
据《谥法》的解释:“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看上去很复杂是不是?其实不必劳神,总之不是什么好的字眼。它是那场渡江战役的胜利者,给他的手下败将,打的一个大大的“差评”。
瞧!胜利者多么志得意满。你死了也不放过你,要让你遗臭万年。
又将近十五年过去。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日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杨广的亲信宇文化及、司马德戡等人发动了一场兵变,并在翌日缢死了他们雄才大略的皇帝。
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是:皇帝确实雄才大略,但也确实能折腾;并且,早在这场兵变之前,天下已经被折腾得差不多了。他的表哥太原留守李渊已经攻入长安,扶植了他的孙子杨侑做傀儡皇帝,事实废黜了我们可怜的主人公。
对于李渊来说,表弟居然以这种方式从历史舞台谢幕,这倒算个意外。他滴了几滴鳄鱼眼泪,没几个月就接管了杨家天下的摊子,自己做了皇帝。大概是总归有点过意不去,他领导的新朝廷也给杨广搞了个谥号。
这个谥号,大家都知道。作为知名人物,杨广被后世称为“隋炀帝”,就是拜这位腹黑的表哥所赐。
历史总是那么富有戏剧性。
2
假如人在死后有知觉、灵魂有去处的话,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陈叔宝和杨广在某处相遇。生前的对手,两位谥号都是“炀”的皇帝,是相顾无言呢,还是愉快地“尬聊”一下旧日时光?很难说是谁坑谁了……
有这种促狭设想的人不止我一个。早在一千年前,我的诗人偶像、喜欢拿历史人物开涮的李商隐就谈到过这个方案。有《隋宫》一首为证: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只看末两句即知,有文化地揶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杨广啊杨广,当年你灭陈国时,讥笑陈叔宝耽于逸乐、疏于治理而致亡国,如今大隋在你手上及身而亡,你们九泉之下相遇,是否应该羞愧当初对人家陈叔宝的嘲弄呢?
陈朝末帝虽然不是个治国能手,但文艺才能确实高,曾据乐府旧曲《玉树后庭花》填上新词,有“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之句,艳丽非常。《隋遗录》卷上曾记载,杨广在扬州曾梦见和陈叔宝相遇宴饮,席间曾请陈的宠妃张丽华表演据《玉树后庭花》演绎的舞蹈。这是杨广第一次“问后庭花”。
李商隐的“岂宜重问”四个字,力道很大,有点得理不饶人:各自的国都亡在你们手上了,两个人的谥号也都是“炀”了,谁也没比谁更高贵,杨广你觉得你再饱含优越地跑去跟人陈叔宝打听人家的宠妃和艺术作品,合适吗?!
其实要我说,也没什么不合适的。大家艺术修养都很高,作为同好,就文艺问题交流交流,抛开政治,也是很和谐的场面。何况,据《旧唐书》,陈叔宝除了《玉树后庭花》,还写过一点别的,而且是首创,比如《春江花月夜》。不过陈叔宝版本的这首诗已经失传了,我们只知道他很可能是第一个创制此题的人。
有史可载写此题的第二个人,就是杨广——这也不失为一种致敬了。我消灭了你,但在有些领域,我向你学习。杨广大表哥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也写过不少诗,但他的诗里总有一股流连不去的杨广的味道。李世民在政治上总拿他的这位表叔作反面例子,但在文艺方面,我感觉,他还是学习了一下。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其一)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其一)
我曾在自己的公号“九枝灯”上,连载过一部分读《全唐诗》的笔记——《全唐诗》一翻开,就是李世民的一堆诗作,不得不面对——就专门讨论了李世民诗歌创作的影响源里,很可能包括杨广这样的作者。
杨广的这两首《春江花月夜》,或许还影响了初唐的另一首同题诗,它出自如今名气更大、近世以来被捧上了天的张若虚之手。清末的王闿运说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对之赞不绝口,还有出处不详的“孤篇盖全唐”之类说法等等。就最后一个说法而言,是不是这么厉害不知道,总之觉得很虚了。
3
杨广的这两首《春江花月夜》,写的内容全在题目里,五个字,一个字一个场景,齐活了。内容简洁,清新脱俗,意思理解起来也不难。因为写月夜春江的情境,所以先是“暮江”,接着月光映入江面而波光粼粼,然后才有“潮水带星来”的迷人景象。第二首的头两句,不止有色彩,还有气味和声音——带有露水的春夜里花气熏人,而春江水里摇曳着月光,仿佛荡漾有声。
第二首的末两句,用了两个古老而美丽的典故,表示在充溢着春意、江景、花气和月色的夜晚,作者期待有这样美丽的邂逅:刘向《列仙传》记载的郑交甫在汉水遇上两位女神,以及在湘江上守候舜帝的两位妃子娥皇和女英。
我看到过一个所谓“四大亡国之君”的说法: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怎么选出来的、是不是定论且不论,这四个人凑一起还真是有趣,因为他们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面文学艺术综合修养最高的四个人。
曹氏父子和萧衍父子也是文艺方面有数的人物,只不过他们的帝王生涯看上去没那么惨,以至于文艺才华也就没被衬托得那么醒目……另外,杨广的诗作也不全是《春江花月夜》这种尚存六朝气息的艳丽之作,还有西巡时候作的《饮马长城窟行》之类作品。这首诗被认为“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这或许是他在文艺气质上和曹操的一种联系?
就算杨广之作大部分时候不脱六朝诗余味,却也充盈着一股清新流美的新鲜气息,不同于宫体诗的基础格调。后人说他的诗“风骨凝然”,认为在艺术上能够“从华得素……清标自出……一洗颓风”,实在是不算过誉。
论起政治能力的话,隋炀帝杨广应该是四个亡国之君里面最强的,他的问题不在于治国无能,而在于步子迈得太大,玩得太浪,以至于“玩脱”了。他应该是个性丰富的人,确实也极具诗人气质。不过这种诗人气质比较疯狂,具有破坏性,一旦施之于治国,结果有点不堪设想。大家都知道,“元首”希特勒当年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斯大林也是俄罗斯当时的知名文艺青年……
4
我少年时代生活在乡下,除了一些常见的武侠小说和古典名著外,找不到太多可读的书。那时,父亲花过一笔巨款,在镇上唯一的私营书店,给我买了套我吵嚷着要了很久的“三言二拍”。他大概不知道,书里经常出现的香艳描写和以方框替代、欲说还休的段落,给当时的我带来了多大的震撼。
初读《隋唐演义》也是在十四岁前,我不知忧患的少年时光里。那时父亲尚在人世。当时并不觉得它的精彩程度能超过《警世恒言》或《初刻拍案惊奇》。在2013年的漫长假期,倒追过几集由严宽和姜武主演的同名电视剧。留下的最深印象的角色,却不是两位主角,而是由富大龙演绎的杨广。
富大龙版的杨广,或许比较符合我理解的隋炀帝的形象:有才华,腹黑,自负。他的表情夸张,不可一世而又贱兮兮的。从第二集对宇文化及得意地自我吹嘘“偶得妙句,与我品评一番”开始,到被逼吊死前再次念了这首诗其中的两句为止,整部剧里,大概有六七处杨广念诗的段落。
除了《胡笳十八拍》为前人所作、《我梦江南好》疑出自《南北朝演义》的杜撰和伪托外,其余五首,通常被认为确实出自作为历史真实人物(而不是小说里的演义人物)的杨广所作。这五首中,就有《春江花月夜》两首。另外三首分别是《野望》《早渡淮诗》和《幸江都作》。
在前人典籍中有时候视为缺题的《野望》,还被认为影响和催生了秦观的一阕名作《满庭芳》: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这是《隋唐演义》剧集中,杨广最初念的诗,以及死之前最后念的诗。剧中的杨广把自缢的白色腰带挂上房梁打成一个结,套上了自己的脖子,然后张口念起了自己的得意之作:“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临死不忘感慨性的炫耀。
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对他的评价很准确:
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是的——对美好事物的鉴赏,强烈的个性,炫耀性的想象力,野心勃勃的计划。并且,最重要的是……他整个人的一生,就是一出颇具张力的戏剧。
言辞之花
李白于沉香亭畔作《清平调》三首,以彼时盛放的木芍药比杨玉环,所谓“名花倾国两相欢”者是也。李濬《松窗杂录》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故而唐人所谓的木芍药即牡丹。
杨玉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确实当得起“名花倾国”之誉,这也与始于唐代对牡丹的追捧不无关系。洪迈《容斋随笔》内专有“唐重牡丹”一条,言人对此花的偏爱,白居易、元稹、许浑及徐凝等人皆将之付与篇什。
李商隐亦然。并且,以清人陆昆曾《李义山诗解》里的说法,这一首咏牡丹之作,可谓牡丹诗的翘楚,此类题材“唐人不下数十百篇,无出义山右者”。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招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
这是一首由不同典故堆砌而成的诗,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主题:牡丹。由于典故背后的色彩艳丽,内涵丰富,以至于我们必须原谅它的复杂与不同寻常。正如真实世界的牡丹,拨开层层堆叠的花瓣,我们方得以探入“意义”的花心。
诗的首句有原注——《典略》云:“夫子见南子在锦帏之中。”
卫夫人即春秋时卫国国君灵公的夫人南子,据说容貌绝美。孔子周游列国时到访卫国,接受召见,与南子隔着锦帐见面。《论语·雍也》里记载,孔门弟子子路对这场会见非常不满,认为老师不该见此风流艳丽之人。
对于这出“子见南子”的情节,后世颇多演绎。林语堂(1895~1976)据此编写过一出独幕剧,由曲阜二师的学生在1929年6月将之搬上了舞台,有保守人士将之视为“渎圣”之举,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2010年的电影《孔子》亦将此敷衍成了拥有具体对白和场景的情节,气氛颇暧昧,俨然是至圣先师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桃色事件。此处去除了这个典故里的文化附着,且只想象——
倘若当初南子掀开那面隔在两人之间的锦帐,出现在孔子眼里的,将是一张怎样绝美的脸庞呢?此句写乍见牡丹花瓣,艳丽如锦帐初卷后南子的容颜。
据《说苑》的记载,楚国的鄂君子皙泛舟河中,划桨的越人唱起歌来,表示对鄂君的爱戴或者是爱慕,鄂君为歌所动,扬起长袖举绣被覆之。我们大抵可以想象,即使身为男性,舟子的风采亦必定不同寻常,以至于有人认为,这首《越人歌》可能是最早的“同志”之歌。李商隐将牡丹花的绿叶比作鄂君绣被,而花盘则是俊秀的越人,花苞初盛而绿叶簇拥。
此是写牡丹花株的叶。“初卷”对“犹堆”,赋予静态的花色与叶况以动态和时间感。被堆叠起的叶子所簇拥的花枝风采卓绝。
颔联风起。两句互文。花枝摇曳,如身着由郁金草染色的裙的舞女,舞姿绰约,长裙飘荡,佩饰翻飞。垂手、招腰皆舞名,亦形容舞女舞蹈时的状态。
颈联的描写更深入一步,侧重于牡丹的色与香。出句用西晋时期富豪石崇的典故。石家常以蜡烛作薪柴烧,不必剪烛芯即可尽情燃烧出大片烛火,此以写牡丹花色之繁盛欲燃。对句用汉末尚书令荀彧“荀令衣香”典故,谓荀彧之所以衣香不绝,是依赖于香炉熏烘,而牡丹花香则更胜一筹,不待熏香,自然浓郁。
故而清人屈复《玉溪生诗意》注李商隐诗到此处,曰:“六皆比:一花,二叶,三盛,四态,五色,六香。”比,比喻是也,以同类相近者相关联。至于末句,屈复的解释更为简洁明快:“言花叶之妙丽可并神女也。”纪晓岚论诗眼光极高,常对李商隐诗发牢骚,对该作却赞不绝口,在《玉溪生诗说》里论此处用事借典之妙,所谓“八句八事,却一气鼓荡,不见用事之迹,绝大神力”。
但众口难调,也不是谁都愿意叫好。比如朱彝尊就说,这种诗体现的是咏物诗里最下乘的做法。
李商隐诗集中,写牡丹的诗不止于此首。他另有五言律《牡丹》一首,《僧院牡丹》一首,《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两首。和这一首写盛放时的牡丹的作品不同,《回中牡丹为雨所败》是典型的伤春尽、惜落花之作。他似乎更倾向于沉浸在这种伤春情绪里,而不是此处的明艳与丰盛。用他在《朱槿花》里的句子来形容,这或许是一种消极的激情,而消极的激情里有更决绝和彻底的力量:
君问伤春句,千辞不可删。
至于这首七言律《牡丹》的末句,我想借助一点题外话来谈。
牡丹的自然花期多在四、五月间,正是如今这般的春暮夏初时节。转眼花事将阑,牡丹姗姗来迟,却艳冠群芳。宋人高承《事物纪原》里记载了一则武则天与牡丹的传闻,虽颇为不经,却为此花平添了几分神奇色彩。常人皆道开到荼蘼花事方毕,对于诗人冯至(1905~1993)来说,在1929年“暮春的花园”里,牡丹与芍药的凋零,可能才意味着春天真正的终结:
从杏花开到了芍药,/从桃花落到了牡丹:/它们享着阳光的照耀,/受着风雨的摧残。//那时我却悄悄地在房里/望着窗外的天气,/暗自为它们担尽了悲欢://如今它们的繁荣都已消逝,/我们可能攀着残了的花枝/谈一谈我那寂寞的春天?
诗人在芳物将近的晚春极易觉出寂寞。但本年里的冯至所拥有的寂寞,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的寂寞。对于活了近九十年的作者来说,此时连人生的晚春怕都还没有到。等迈入暮年,回顾往昔,他在《自谴》诗里说“早年感慨恕中晚,壮岁流离爱少陵”,倒提示了我们《暮春的花园》里的伤春情绪,似乎多少契合于“刻意伤春复伤别”的杜牧。这也难怪,他会在随后留学德国的生涯里将杜牧的诗翻成德语并将之寄给友人。
作为诗人与小说家,冯至的朋友废名则更偏爱李商隐。冯至也好,废名、林庚、朱英诞及何其芳这些被称为“北平现代派”的人也好,或者冯至的弟子辈卞之琳也好,他们的新诗创作及诗学观念,皆颇得晚唐诗人之助。至于李商隐的这首《牡丹》诗,废名甚至不忘在自己的小说《桥》里大谈特谈。
他为此设计了程小林带琴子、细竹她们去八丈亭看牡丹的情节:
姑娘动了花兴了。细竹也同意。小林导引她们去。昨夜下了几阵雨,好几栏的牡丹开得甚是鲜明。院子那一头又有两棵芭蕉。地方不大,关着这大的叶与花朵,倒也不形其小,只是现得天高而地厚了。她们弯腰下去看花,小林向天上望,青空中飞旋着一只鹞鹰。
接下来,废名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就李商隐《牡丹》诗中的尾联,发了一通议论,或者说评鉴。在我眼中,这两段话是废名文字里最具神采的笔墨:
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
……
我尝想,记忆这东西不可思议,什么都在那里,而可以不现颜色,——我是说不出现。过去的什么都不能说没有关系。我曾经为一个瞎子所感,所以,我的灿烂的花开之中,实有那盲人的一见。
李商隐原诗的尾联,用“江郎才尽”典故(《南史·江淹传》:“(淹)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谓我亦有江淹先前那样的才华,愿于梦中得郭璞的五色笔,书写牡丹花叶的如斯之美,递送给巫山神女朝云,以遥寄情思——因为唯有巫山神女,才有如此集大成的雅艳容颜。
但以李商隐惯常的风格来看,“咏物”只是《牡丹》表面的主题,而末句泄露的是他的真正目的——藉艳丽富贵的色与香写牡丹花,进而藉写花以寓人。牡丹开得富丽堂皇,诗中典故亦是富贵人家故事,然则其间姬妾舞姬或为诗人之意中人耶?如此诠释,不免穿凿,而竟乎可以理解,或许是因为他以诗篇编织的幻境过于迷人罢了。其《燕台》诗曰:“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此《牡丹》诗或亦以寄托相思为念,是他以汉语的经纬编织出的言辞之花。
废名的理解则是更为明显的误读。然而这是一个异常美丽的误读。
我们亦不妨再三误读一下。
李商隐的心思,在写这首诗之前就“布置”好了,只待一丛牡丹触发起他动笔的兴致。诗的完成,就是一刹那所见的“朝云”,历经运思的暗夜,而呈现为这鲜妍动人的一幕。在这言辞的灿烂花开之中,我们的理解或许不着边际,然则亦不妨将之视为“盲人的一见”罢。那大概也有几分意思。
责任编辑:马小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