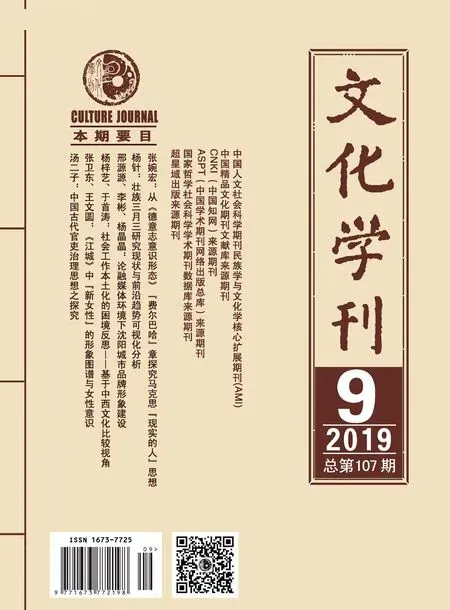试论苏轼的“空静”观
武茜佳 张金芳
一、苏轼“空静”观探源
(一)道家
“虚静”一词最早出现在周厉王时代的《大克鼎》铭文中,即“冲上厥心,虚静于猷”,这里指的是“宗教仪式中一种用以摆脱现实欲念,便于敬天崇祖的谦冲、和穆、虔敬、静寂的心态”[1]。先秦时期,道家从哲学层面出发,将“虚静”作为“道”存在的一种形态,进而开启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虚静”说。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2],庄子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3],均是将“虚静”看作万物之根本,是得“道”的最高境界。
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艺术空前繁荣,“虚静”说在陆机、刘勰等人的倡导下逐渐进入审美领域。《文赋》开篇,陆机便指出“虚静”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伫中区以玄览”[4],即强调创作前要以虚静之心体察万物。《神思》篇中,刘勰直接提出了文学构思的“虚静”理论:“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5]这里的“虚”仍指的是祛除内心杂念后的心境;这里的“静”,仍是不为外物所扰,使自身进入高度自由的创作状态。
(二)佛禅思想
僧肇,东晋著名僧人,尤擅般若空宗。他在《不真空论》中提出“万物之自虚”,他认为万物的本质就是“自虚”,即万物没有自己的独立本性,因此,一切皆空。这种“空”也即具化的“静”,在动静观上,僧肇强调“即动而求静”。
在禅宗看来,“空”才可容纳万物。六祖慧能认为: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人心虚空,则不再局限于自身的喜怒哀乐,才能遍照四方。在这里,禅家更侧重的是对于“空”的自我观照。
二、苏轼“空静”观的体现
(一)以静观动
在《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苏轼指出古代圣人都具备处静观动的优点,以静观动便是在凝神静气的状态下将所要观察的对象尽收眼底。他举“操舟者”与“奕棋者”两例,对此进行说明,他认为操舟者之所以不了解水道之曲折,弈棋者之所以不能预知自己的胜败,是由于“操舟者身寄于动……弈者有意于争”[6],即他们身处其境而心有杂念,而水道之外、棋局之外的旁观者之所以能够纵观水道、预知胜败,正是因为他们身处事外而能保持一颗纯净之心,不被外物所困扰。故静能观动,并能纵观全局而掌握要点。
在《送参寥师》一诗中,苏轼进一步将以静观动的观点运用于文学创作中:“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7]。想要写出好诗,便要做到空与静,虚静所以能懂得万物之变化,空明所以能接纳万事之境界。在这里,苏轼不仅强调了以静观动的重要性,还指出了在文学创作的思维中“空”的重要性。如果说静观是洞察万物,掌握事物规律的方法,那么“空”便是实现“静观”这一方法的必要条件。“空”便是摒除一切有碍于艺术创作的杂念,唯有实现“空”,创作主体才能凝神聚力,实现静观。由此可知,苏轼在这里强调在广识博学的基础上对万物保持静观的态度。
(二)寓意于物
正因为静了群动,空纳万物,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我们就必须寻求“空静”,以保持一颗无功利的审美之心。在《宝绘堂记》中,苏轼提出了“寓意于物”的原则:“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8]苏轼在这里提出了两种对待外物的态度,即寓意于物和留意于物。超功利的审美境界是“寓意于物”,即以无功利之心去看待事物;而带着功利色彩,过分地执着于物的占有之心,就是“留意于物”。显然,“留意于物”是没有摆脱利害关系、没有消除欲念的审美判断,因而不能产生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而“寓意于物”即以纯洁虚静之心去审视万物,这样产生的作品才具有普遍的审美价值。
总的看来,苏轼的“寓意于物”强调的是一种审美的无功利性,而要达到这种无功利性,同样离不开对摒除一切杂念的“空静”心态的探寻。
(三)不能不为
苏轼虽然提倡“寓意于物”,但他并没有流于空谈。他还提倡“有为而作”。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苏轼评论颜太初的诗时指出:“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要以伐病。”[9]这里的“有为”即是指,作家应该关注现实生活。将生活中的现象反映到作品中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对社会要起到“疗饥”“伐病”的效果,绝不是单纯地倾泄个人的私愤,而这种“有为而作”并非是勉强刻意地作文,而是受外物感发,“有触于中”的“不能不为之为工”,而要做到“有触于中”,就必须集中精神去反观自我的内心,只有外界的实与内心的真相结合,才能写出真正的作品。
“不能不为之”是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提出的观点。作者借山川之云,草木之华,说明了写文章“不能不为”的畅快之情。“能为之”之文即“有意”之文,而“不能不为之”之文即“无意”之文,作者在这里赞赏后者,即是对写作时心灵自由抒发的状态的赞赏,而要表达出自身的真情实感,使心灵达到自由抒发的状态,就需排除杂念,保持一颗虚空与宁静之心。这同样是苏轼“空静”观的体现。
三、苏轼“空静”观的意义
“虚静”说经过先秦老庄、魏晋陆机、刘勰等人的努力而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理论范畴。苏轼在融合了道家摒除一切杂念的“虚静”之心与佛禅“空纳万物”思想的基础上对“虚静”说加以继承、改造,为“虚静”说注入新意,形成了独特的“空静”观。后世的李开先、汤显祖、况周颐等都从其“虚静”思想中得到一定启发,对“虚静”这一美学范畴进行了补充与创新,使得这一范畴得以延续、完善,为中国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