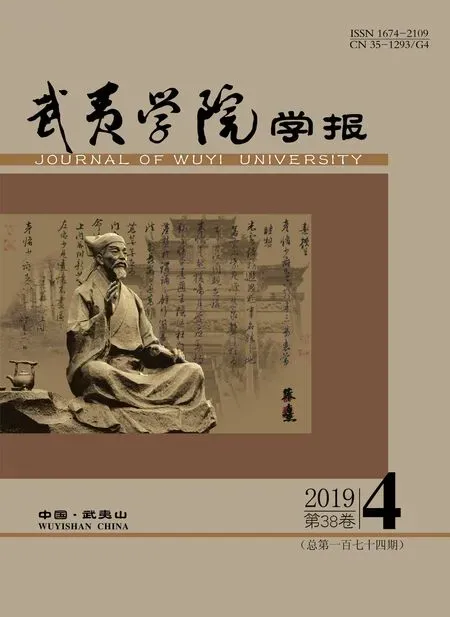从《雅言》看连横的文学观及其当代价值
杨雨晨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一、《雅言》及其成书目的
连横是台湾省著名的爱国诗人与史学家,一生著述甚多,《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诗乘》等都是体大思精之作,为后来者研究台湾文化铺设道路,对于台湾文化的保存功不可没。海峡两岸研究连横及其著述的文章为数繁夥,但对其笔记体著作《雅言》的观察仍嫌不足。《雅言》撰于1933年前后,当时连横以专栏形式连载于台南的报刊《三六九小报》上,后经人排印成书。《雅言》全书共包含303篇笔记,内容丰富驳杂,多则六百余字,少则三十余字。篇幅大多短小精悍,语言浅易,遣词造句丝毫没有诘屈聱牙之感。部分篇目以类相缀,如对于诗歌、戏剧等的论述;但亦颇有一部分乃属随心而谈,范围极为广阔,涉及到俚谚、民俗、博物学、地名学等各个方面。
根据学者孙风华的观察,目前两岸关于连横的语文学研究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五篇[1],其中以《雅言》为主要探讨对象的有汪毅夫的《雅言与台湾文化》及台湾赖丽娟的《<雅言>之台湾俚谚探析》。前者细致总结了《雅言》中出现的台湾方言、文学样式与民俗事象,后者则对《雅言》收录的台湾俚谚进行了汇总、分类及释义。此外,台湾学者邱德修著有《台湾雅言注译》,对《雅言》书中的各个篇目进行了分析与翻译。
在《雅言》连载的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逐渐深入且日渐残酷,在台湾本土强力镇压革命斗争运动。文学感受到社会变革的呼唤,亦风云交汇,在形式与内容上都进行着突破。通过《雅言》,连横不仅试图向外界描绘台湾方方面面的景貌,也试图传递自己对于文学、历史、民俗等方面的见解。这些见解或有偏颇及失误之处,但其间流露出的对台湾乡土及祖国的情感,已构成对日本殖民者的强烈反击。
《雅言》一书,在内容上既多样,作者之创作目的也就具有多重性。纵观全书,在创作目的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三层:
一是整理台湾乡土语言,是连横撰写《雅言》的表层目的。《雅言》开篇第1条中即指明“此书苟成,传之世上,不特可以保存台湾语,于乡土文学亦不无少补也。”[2]在进行乡土语言的讨论时,连横说明了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并把目光主要放在台湾的俚谚、俗语以及一些外来语在台湾本土的演变上。书中还屡屡提及他所编纂的《台湾语典》,《台湾语典》之自序云:“余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减,民族精神因之萎靡”[3],可见作者将乡土语言看得极为重要,这两本书在书写目的上也就具有了部分的一致性。
二是提倡台湾乡土文学,是《雅言》成书的深层目的。“夫欲提唱乡土文学,必先整理乡土语言”[2],发扬台湾乡土文学是作者关注乡土语言、整理乡土语言的目的之一。在《雅言》一书中,对于台湾文学的讨论占据了较重的篇幅,主要涉及诗歌、民谣、楹联等方面。而关于乡土文学如何发扬,作者则认为“夫欲提倡乡土文学,必须发挥乡土之美善,而后可以日进。”[2]同时他鼓励文学革命,鼓励民众多读书以发扬文学,认为“夫革命者在内容而不在外观,则精神而不在形式也。”[2]连横之所以如此大力提倡文学,是因为他将文学家的指导看作台湾复兴的一条重要途径。
三是深扎在《雅言》写作过程中的根本目的,则是保存台湾文化。《雅言》一书内容涵括多方,多角度地记录了台湾的文化状况。作者在书中多次袒露自己对于台湾的热爱之情与对郑成功的尊崇之情,表现了对清朝统治者及日本侵略者的厌恶和鄙视。书中对于台湾风土人情的展示非常充足,种种制度、习俗、器物皆是文化的一种载体,通过这类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就达成了作者保存台湾文化的目的。在着力记载的同时,作者也对文化保存一事持有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应当保存文化的精华,剔除文化糟粕,并呼吁今之台湾人应当兼包并蓄,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学习外来文化,以更好地发展台湾文化。
二、从《雅言》看连横的文学观
《雅言》中的多处探讨是漫谈式的,难以确定单一主旨。总体来看,涉及文学的部分约有六十余条,其中又有近半数是以民间俗语、俚谚作为主要内容。通过六十余条的文学讨论,我们可以管窥连横的文学观。大体上,这些篇目可分为两个方向——对于童话、儿歌、俚谚等通俗文学的讨论,以及对于诗歌、诗钟等严肃文学的讨论。
关于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界限的探究说法众多,分类方法也众口不一。在通常的认知里,通俗文学(亦即大众文学)与严肃文学(亦即纯文学、精英文学)为相对的两方,即前者追求故事性、娱乐性,满足人们潜意识的诉求,后者则追求在文学意义上思想内容、创作手法及语言表达的极致化。也有三分法,如杨春时在《文学概论》中所述,文学可分为体现审美超越作用的纯文学、体现现实作用的严肃文学及体现消遣娱乐作用的通俗文学。[4]这几个概念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本身就都具有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历史的前进也可能发生相互转换,我们只能从历史横切面上进行大致的区分。借用蔡翔的说法,纯文学是一个“移动的能指”,“一个叙事范畴”[5],同样通俗文学也可以如此描述,那么在这里讨论的就只是在横切面下两个集合之中划分较为明晰的对象,体现在《雅言》中,就是俚谚、儿歌、童话等作为通俗文学的部分,而诗歌、诗钟等则属严肃文学的部分。
(一)论通俗文学
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虽然在创作量上为数不少,也有诸多文人投身于小说、戏曲、笑话等文学样式的创作行列之中,但总体来看,通俗文学一直不为士大夫阶层重视,也不能登大雅之堂,在正史中很难见到它们的影子。直至近代文学观念变革后,小说从“小道”走向“载道”,戏剧也被重新发现价值,通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儿歌、童话、民讴等文学样式由于体裁本身便积弱,价值追求较少与意识及超意识相吻合,加之长久的历史传统影响,依旧位于文学评论的边缘,无法成为显学。上世纪30年代的台湾文化界,新文学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守着旧体的文儒仍坚守旧体诗园,文坛新将主要把注意力倾注于耕耘小说及新体诗,其余文学样式则无暇顾及。
在《雅言》中,体现出了连横的俗文学观。对于通俗文学,连横并不是将之作为一个整体,从本体论、创作论、接受论等方面来讨论,而是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对拆分出的诸多文体进行了评析。书中涉及到的有俚谚、番歌、褒歌、民讴、童话、儿歌、谜语、童谣和弹词,种类可谓多样。
书中涉及俚谚文学价值的篇目有逾三十条,连横基本采取先列举、再释义、或再加以评点的方式书写。据赖丽娟观察,《雅言》收录台湾俚谚内容包括禁忌、俗传、讽诫、气象、人生观、道德、赌博、风俗、不平之鸣、歧义殊见、不晓事理及歇后语式的俚谚等类别,从内容上见其涵类多方,可知连横的儒家人生哲学、时代感慨、胸襟识见及对当时社会现况的批判。[6]在第32条中,连横认为,俚言俗谚,闻之似鄙,而每函真理。古人谈论,每援用之。[2]在此后篇目里,连横除了借俚谚说理之外,还从几个方面来直述俚谚的价值。
首先,通过俚谚可以观察社会道德变迁,“他日有研究台湾道德之变化者,当就里谚而求之。”[2]其次,通过俚谚可以考察民德与民智,“苟以俗谚而考之,可以觇民德之厚薄而民智之浅深也。”[2]再之,人们可以从俚谚看台湾风光物色,“悉采里言,复叶音韵,诚可谓本地之风光而艺苑之藻绘也。他日如刊单本,布之海内,亦可为台湾之特色。”[2]此外,亦可由俚谚反思既成的科学命题,如“‘优胜劣败’之说,倡自达尔文;然世上之万事万物,优者未必胜、劣者未必败。何以知之?台人之言曰:‘一枝草,一点露;隐龟兮双点露’。”[2]俚谚的广传非一日之功,是在世代更迭中被证实其合理性,继而流传下来。据研究,现代的谚语研究始于20世纪上半叶,由于谚语的丰富性,目前所止的研究仍远远不够。[7]连横在彼时能够通过报纸申明俚谚的重要性,做扩大俚谚传播、宣扬俚谚价值的工作,着实具有先导意义。
番歌、褒歌、民讴及童谣都属于民谣类,连横以纵的视野,观察当时在台湾流行的民谣,将其与古已有之的文学类型作对照。番歌的初祖可追溯至《吴越春秋》所载的《断竹歌》[2];褒歌“为采茶男女唱和之辞,语多褒刺;曼声宛转,比兴言情,犹有“溱洧”之风焉”[2];民讴“为一种风谣,所以刺时政之得失;《小雅》《巷伯》之诗,已启其端。”[2]童谣则“造句天然,不假修饰;而每函时事,诚不可解。《国语》之‘檿弧箕箙,几亡周国’、《左传》之‘龙尾属辰,虢公其奔’,尤其彰明较著者。”[2]
连横认为“童话虽小道,而启发儿童智识,其效较宏。”[2]这一观点还带有“文以载道”的实用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子。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童话的教育性之外,连横还注意到了童话的娱乐性:“我台文学家当多作童话,采取自然科学及台湾故事而编之如 《伊索寓言》,为儿童谈笑之助;且可以涵爱护乡土之心,亦蒙养之基也。”[2]于儿童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初始时期,“儿童本位”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能够认识到童话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多重意义实属不易。在当时,童话、传说及寓言等尚未出现清晰的分流,故连横在第56条中所具之例还显杂混。如今,台湾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已较为蓬勃,优秀的原创童话也不断涌现,追溯起来,连横颇具开山之功。
《雅言》第80条所述,台南有一盲女,沿街卖唱弹词。又有人采拾台湾故事,编为歌辞。“今之文学家,如能将此盲词而扩充之,引导思潮、宣通民意,以普及大众;其于社会之教育,岂偶然哉!”[2]在这里,连横再次认识到通俗文学所具有的积极影响。通俗文学除满足群众消遣娱乐的需求外,也可以用浅显的方式传达正面的精神价值,起到人生教科书的作用。连横对通俗文学的主张,诚是“无论小说、戏剧或儿童文学,只要是台湾人写台湾事,必能发挥社会教育之功能,涵养爱护乡土之意志,宣通民意,鼓动思潮。”[8]
但连横并非对所有通俗文学一概而论,第84条就体现出他的文学价值观。针对当时台北流行的粗野歌谣,他深感悲哀,并疾呼“夫欲提倡乡土文学,必须发挥乡土之美善,而后可以日进。”[2]而若想将筛除通俗文学中的糟粕,就不得不从创作者入手进行改善,这种改善的作用远不止于净化文学风气,甚至于关乎到民族的发展前景,“台湾民族之衰落虽至如此,而前途一线之光明,尚有望于今日文学家之指导也。”[2]这说明连横深刻认识到了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
(二)论严肃文学
在注目通俗文学的同时,连横又深知严肃文学、尤指诗学的价值。他也在《雅言》中用一定篇幅论述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连横所处的时代,台湾文坛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动,也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的体式被呼吁革除,新的体式尚在建设之中。1924年的新旧文学论争中,连横站在旧文学的阵营,对新文学进行了批判,“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9]虽然这种保守的观点无法阻挡文学向前发展的潮流,但连横之言未尝无合理之处,新文学革命发展之初对旧文学的全盘否定是革命所难免产生的“牺牲”,但在后续发展中文学需要获得常态时,辩证的眼光就必然被提到对抗之前,文学传统的财富也必然得到继承。
《雅言》第85条中,连横对台湾诗学的整体发展做了一个大略的回顾,列举出在台湾诗歌发展史上值得注目的诗人及其作品,如“台人士之能诗者,若黄佺之《草庐诗草》、陈辉之《旭初诗集》、章甫之《半嵩集》、林占梅之《琴馀草》、陈肇兴之《陶村诗稿》、郑用锡之《北郭园集》,或存或不存、或传或不传,非其诗有巧拙,而后人之贤、不肖也。”[2]连横所编纂的《台湾诗乘》就是一部台湾诗学的发展史,通过他的自述——“二十年来,余既刊行《台湾通史》以保文献,又撰《台湾诗乘》以存文学;余之效忠桑梓亦已勤矣,而犹不敢自怠。一息尚存,此志不泯。余将再竭其绵力,网罗放失,缀辑成书,以扬台湾之文化”[2],可以发见连横竭力保存台湾旧体诗的目的仍是发扬台湾文化。
在诗歌的创作论上,连横首先认为,台湾诗人应当以台湾为创作对象,鼓励他们学习孙湘南、范九池等诗人,以台湾风光入诗。并感叹“今之作者何不著意于此,而乃作此毫无关系之题目!台湾诗人虽多,而真能为台湾作诗者,有几人哉!”[2]当时台湾各地盛行击钵吟,这也是连横的抨击对象。击钵吟常用于消遣作乐,现实意义不强,而连横通过提倡为台湾而写,就是希望能够少些空有其表的吟唱,多些真情实感的颂扬。除台湾风光外,连横还赞同描写底层人民的实际生活。他举李华的《草地人》为例,认为此诗可称是草地人的真实写照,并感叹“今之佃农,其景象又何如也”[2],表现了他对穷苦佃农的关怀。此外,在使用诗歌语言时,连横认为作诗应当使用台湾方言。他举唐人、宋人以当时方言入诗为例,认为台湾方言中的“骑秋”“禅雨”“海吼”等词汇皆是隽语,台湾诗人“当有取而用之者。”[2]
除诗歌外,连横在《雅言》中还记录了十四种诗钟的体例。第93条中,他总起“诗钟虽小道,而造句炼字、运典构思,非读书十年者不能知其三昧”[2],对诗钟的起源略作说明,详细列举了他所收集到的十四种诗钟:一曰“嵌字”,二曰“魁斗”,三曰“蝉联”,四曰“鹭拳”,五曰“八叉”,六曰“分咏”,七曰“笼纱”,八曰“晦明”,九曰“合咏”,十曰“鼎足”,十一曰“碎锦”,十二曰“流水”,十三曰“双钩”,十四曰“睡蛛”。[2]诗钟虽与击钵吟同为一种文字游戏,但在遣词及构思上乃精心为之,不同于后者的随手拈来,应当得到重视与传承。连横在《雅言》中表露出的鲜明的褒贬态度,证明相较文学的形式,他更看重文学的内容。而他对诗歌及诗钟创作的观点,也“显示台湾宿儒想以诗歌表达社会变动、对时势的关怀、以及知识分子面临政治压迫的心声。”[10]
(三)连横之文学观的当代价值
文学发展到今天,宽松的环境与民众的高接受度使各类文学体裁都竞相盛放,但连横在《雅言》中阐述的文学观依然对今日文学的成长有着借鉴作用。诚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变迁,小说已经成为一种主流体裁,无论在娱乐、审美还是现实层面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相照之下,其他通俗文学体裁得到的重视依然略显欠缺。连横用较大的篇幅论述通俗文学,不仅开其时代之先,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并举,也提醒着如今的文字工作者,重视对通俗文学的发掘与整理。通俗文学不仅历史悠远,蕴含深厚的社会道德内涵,也是来自民间、广受喜爱的文学样式。鼓励传承与发展通俗文学,与当今我们对于“人民的文艺”的提倡是方向一致的。
在《雅言》全篇临近收尾处,连横感叹道:
文学革命,闻之已久,至今尚无影响。夫革命者在内容不在外观,则精神而不在形式也。台湾今日文学之衰落,识者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则不好读书之敝也。夫不好读书,则不知世界之大势、不稔社会之进化、不明人生之真义;浑浑噩噩,了无生趣,而文学且熄矣。旧者将死、新者未生,吾辈当此青黄不接之时,尤当竭力灌输,栽培爱护,以孕璀璨之花。台湾今日之环境,万事万物皆不如人;而此纵横无尽之文学,乃亦不能挺秀争奇为世人所赏识,宁不可耻![2]
对文学革命的认知、对读书之用的肯定,直至今日,这番慨叹依旧具有警世的价值。作为一个旧文化的“守护者”,连横没有随时代的浪潮站到新文学的一岸,对于旧体诗也非一概而论地支持,而是赞其精华,否定类似击钵吟等罔顾家国安危,一味风花雪月的文体。“五四”过后,旧体诗的地位骤然降低,但百年过后,旧体诗的独特性被再度确认,而今从事旧体诗创作者不在少数。这说明连横对于旧体诗的保护及推广是正确的,他对于旧体诗的见解亦是历久弥新的,方言入诗、为民作诗等观点直至今日仍可引以为鉴。
跨过新旧文学之争后,台湾文学论争的焦点转移到了“乡土文学”的议题上。有的作家反对乡土文学,认为注目于脚下的乡土是目光狭隘的表现;有的作家虽倡导乡土文学,却实则没能发掘乡土文学真正的内涵,反而使其僵化。连横举起乡土文学的旗帜,并批判冠以“乡土”却内容空洞的伪作,在形式上认同使用台湾方言,内容上则扩展视野,认为谈乡土文学者应当“就其地之山川人物、礼俗、民谣编成乡土志,以保存一方之文化”,“舍此不为,仅谈文学,是犹南辕而北辙也”[2]。今日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创作愈发需要保持自身特色。一方面,作为文化大国,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合唱中,我们应当发扬自身独特性,在形式上注意方言使用,内容上注目本土;另一方面,“乡土文学”不等于文学的“地方主义”,不能作徒有虚表的唱和,写连横所谓的“伪作”,应由真切的热爱而深入本土,继而由个性彰显共性。
三、结语
连横在《雅言》中多次表露他维护、发扬台湾文化的决心,“余,台湾人也;既知其难,而不敢以为难。”[2]在种种论争的浪潮之下,他秉持此决心,编纂、创作出一部部煌煌巨著,在文坛留下不朽的光辉。连横作为台湾日据时代学界的先行者,终其一生关注着祖国的政局发展,为保存和发扬台湾文化鞠躬尽瘁,正是其诗句“执戈齐敌忾,报国有书生。一死身何惜,三年血尚赤。”[11]的真实写照。《雅言》一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无论是连横的个人精神还是台湾的人情风物,都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值得挖掘。汪毅夫曾评价,“对大陆的文化认同与对异族的文化反抗,对台湾文化的历史负责,也对台湾文化的未来负责,这是连横在《雅言》一书中充分表现出来的一个爱国学者的良知。”[12]这也可以作为对连横一生宏富著作的总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