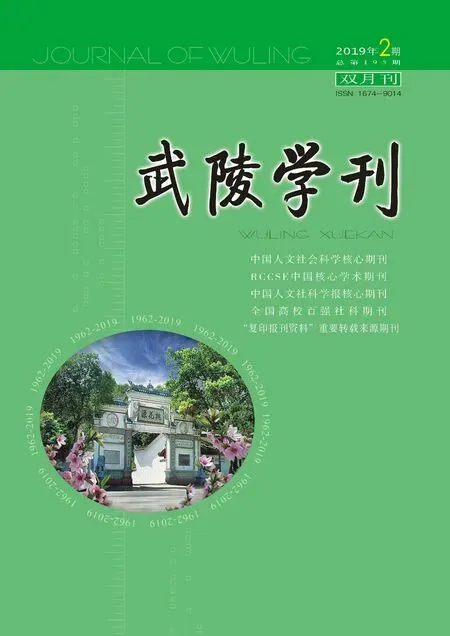梁元帝江陵焚书史事探微
左华明
(长江大学 图书馆,湖北 荆州 434023)
图书是文化的载体,图书兴废与政权盛衰紧密相关。隋文帝开皇初,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并列举了历代典籍的“五厄”,分别是秦始皇焚书、新莽之乱、东汉末董卓之乱、西晋末永嘉之乱和梁元帝江陵焚书。“五厄”中,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统一文化和思想,中间三次是王朝末年官方藏书毁于战乱。梁元帝江陵焚书虽然也是发生在梁末,却是元帝自己主动焚毁的,“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1]1299。这是梁元帝江陵焚书与其他“四厄”的不同之处。
梁元帝“及长好学,博极群书”[2]243,对图书极其热爱,何以在城破之前做出焚书举动?学界对梁元帝藏书的途径、来源、焚书的数量[3],以及江陵焚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损失[4]多有研究,但对于梁武帝、元帝父子致力于礼乐和图书事业的动机,图书、衣冠礼乐与正朔观、国家统一等之间的辩证关系,梁元帝江陵焚书的心曲等问题较少措意,仍有待发之覆。
一、梁武帝父子的著书与藏书成就
梁元帝江陵焚书的具体数目,不同的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历来都有争论。《南史》卷8云“十余万卷”[2]245。《资治通鉴》称“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5]5219。胡三省注引用了《通鉴考异》对此所做的考订,言之有据。梁元帝在《金楼子·聚书篇》中称自己历年聚书八万卷,加上从建康运来的文德殿公、私藏书七万卷,共有十五万卷之多。因此,《资治通鉴》称梁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梁元帝聚集图书数量之多,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比较少见的。刘裕平定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到了北周、北齐,图书数量仍然较少,“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尤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即使到了隋朝初期,藏书数量仍然无法与梁元帝时期相比,“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轶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1]1299。由此可见,萧梁时期是我国中古时期图书事业发展的一大高峰。
梁代图书事业的鼎盛,与梁武帝父子均爱好读书、著书,蔚然成为家风有密切关系。武帝萧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其所著儒学类著作达二百余卷,诏铭箴颂等文集又一百二十余卷,“又撰《金策》三十卷”[6]96。简文帝萧纲“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壁》三百卷,并行于世焉”[6]109。梁元帝“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文集五十卷”[6]135-136。
赵翼《廿二史札记》有“齐梁之君多才学”条,对齐、梁之君多才学的史料进行了详细的搜求,称“至萧梁父子间,尤为独擅千古”,梁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梁元帝、南康王绩、邵陵王纶、武陵王纪,均热爱读书、著书,梁武帝“历观古帝王,艺能博学,罕或有焉”,元帝“好学,博极群书,才辨敏速,冠绝一时”;此外还有梁武帝诸弟南平王伟、鄱阳王恢、安成王秀,简文帝之子大心、大临、大连、大钧,元帝之子方等、方诸,南康王绩之子会理、通理,邵陵王纶之子坚、确,武陵王纪之子圆正等,均具有一定的才学[7]。
梁武帝不仅热爱读书、著书,还热衷于藏书事业。“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1]907。由于梁武帝重视图书事业,江南又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至武帝末年,官私藏书都有大幅度增加。侯景之乱中,曾经起火延烧到文德殿藏书。在平定侯景之乱后,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藏书和在建康收集到的公私藏书运往江陵,仍然有七万余卷之多。可见梁武帝时期建康官方和民间藏书数量庞大,图书文化事业兴盛。所谓“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1]907。
梁元帝也热衷于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图书,且对自己的藏书成绩颇为自得,在《金楼子·聚书》中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8]梁元帝还记述了他收集图书的过程,包括他任会稽太守、丹阳尹、江州刺史、领石头戍军事、荆州刺史期间搜集以及从乐彦春、刘之遴、南平嗣王萧静、雍州刺史张瓒、桂阳王萧慥、留之远等处辗转得到的图书,共计八万卷。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绩。
二、江陵焚书原因再探讨
梁元帝作为一个嗜书、爱书之人,何以能忍痛将自己辛苦收集来的图书十四万卷付之一炬?江陵焚书的直接原因,当然是西魏的入侵和江陵城被攻破。但西魏入侵和焚书又没有必然联系,梁元帝完全可以不采取焚书的过激行为,西魏则可能像历代那样把江陵图书作为战利品运回长安。曹操击败袁绍、西晋灭孙吴、刘裕灭后秦、北周灭北齐,都有收其图籍的记录。梁元帝没有把图书留给西魏,而是主动焚毁,必然有另外的原因。
对于焚书的原因,梁元帝也有陈述。梁元帝焚毁图书,“将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5]5218;在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元帝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5]5220
从梁元帝的言行至少可以看到两点:第一,梁元帝将图书看作文道,与宝剑所代表的武道同为国家统治的两大支柱,即所谓文武之道。江陵的陷落,意味着他的文武之道都失败了。但在图书和宝剑二者中,元帝更愿意与他喜爱的图书一起葬身火海,而不是与宝剑同归于尽,即元帝更偏重于文道。第二,梁元帝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那么在元帝心目中,读书万卷又应该是有什么样的结局呢?换言之,在梁元帝看来,读书万卷之因与江陵城破之果不相匹配,应该有不同的结局。或许,在梁元帝看来,读书万卷、大兴图书文教事业的文道,至少应该使国家繁荣昌盛,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与武道相互配合,收复中原,攻破长安、邺城,完成国家统一,而不是自己被攻破。这就涉及到图书、文道与政权兴亡、国家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
梁元帝大兴图书文教事业,可以追溯到梁武帝对图书文教事业的大力提倡。对于梁武帝大修文教,传统史学家大加称颂。魏征称梁武帝:“既悬白旗之首,方应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悦近来远,开荡荡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饰礼容,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介胄仁义,折冲樽俎,声振寰宇,泽流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6]150
从魏征的评价看,梁武帝大修文教,包括礼制的完备、清谈玄学的鼓扇、儒家思想的提倡,取得了以下效果:一是“布德施惠,悦近来远”,即受到梁朝统治区域内人们的欢迎并对梁朝疆域之外和境内边远地区人们产生吸引力;二是对于移风易俗的作用;三是以仁义、文教作为手段,在外交上取得胜利,使萧梁声振寰宇,不使用武力就能维护和平局面。从这几点效果来看,梁武帝父子热衷于图书、礼乐制度的文教事业,不仅仅是个人爱好,其背后更有深层次的政治动机,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外交、国家统一之间的逻辑关系。
魏征称赞梁武帝大修文教,“悦近来远”“声振寰宇”,并非虚言。高欢就曾经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做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大夫悉奔萧衍。”[9]347梁武帝大修文教,专事衣冠礼乐,注重图书事业,在北方士大夫心目中树立了梁朝为正朔所在的正面形象,以至于高欢会担心如果法令过于严苛将使东魏境内的士大夫都投奔萧衍。同时,从高欢的言语中可以看到衣冠礼乐与正朔观、士大夫人心所向及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
三、衣冠礼乐与正朔所在
高欢指出梁武帝萧衍专事衣冠礼乐,可谓眼光犀利,准确地揭示了梁武帝统治政策的本质。衣冠礼乐,包括衣冠制度和礼乐制度,是儒家思想以礼治理天下的制度体现,是封建王朝用以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隋书》卷49《牛弘传》载:“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杨素所说“衣冠礼乐”指礼仪制度,牛弘为献皇后所定丧礼仪注属于礼仪制度中的凶礼。
衣冠礼乐制度也是传统史学著作的重要内容。董巴撰《大汉舆服志》一卷。司马彪著《续汉书》有《舆服志》,后被刘昭补入范晔《后汉书》。沈约作《宋书》,称“礼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飨,匪云别事,旗章服物,非礼而何?今总而裁之,同谓《礼志》”[10]204,将舆服制度归入《礼志》,将音乐归入《律历志》。《隋书》有《礼仪志》《音乐志》和《律历志》,其中《礼仪六》《礼仪七》对衣冠制度做了详细记述。
关于梁武帝制定礼仪制度,史籍载之甚明。“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耿。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1]107东魏的礼仪制度沿用自北魏孝文帝,与梁的礼仪制度不同[11]13。总体而言,梁武帝制定的礼仪制度比北魏、东魏、北齐的更完备、更先进。
对于礼制与中古士族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史家已有论述。陈寅恪先生认为:“礼制本与封建阶级相维系,子敦之说是也。唐以前士大夫与礼制之关系既如是之密切,而士大夫阶级又居当日极重要地位,故治史者自不应以其仅为空名,影响不及于平民,遂忽视之而不加以论究也。”[11]7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又称衣冠,如衣冠南渡即指士族南迁,且当时士族以熟悉礼乐制度、重视家庭伦理教育著称,衣冠礼乐一词也反映了士族与礼乐的紧密关系。
梁武帝制定的礼仪制度既是南朝后期继续完善之产物,又与东魏、北齐继承的吸收了南朝前期宋、齐成果的北魏孝文帝太和礼仪制度不同。当时南北士族极其重视礼仪制度,高欢担忧北方士族本来就受到梁武帝制定的衣冠礼乐制度的吸引,如再严苛法令则北方士大夫尽投江南,就不是毫无道理的杞人忧天,而是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
至于高欢说梁武帝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则涉及到衣冠礼乐与正朔观之间的关系。
正朔,本意指中国传统历法中每年正月的第一天,又指历法。司马迁曰:“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12]正常情况下诸侯应奉天子正朔。《宋书》卷12《律历志》中载:“汉兴,袭秦正朔。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废坏,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于天也。”汉初沿用秦的正朔,至汉武帝时改正朔,制定《太初历》,目的在于表明王朝受之于天,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此后,东汉有《四分历》,曹魏有《景初历》,西晋改为《泰始历》,刘宋时期何承天撰修《元嘉历》。对于改正朔,高堂隆曰:“按自古有文章以来,帝王之兴,受禅之与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10]329
历法对于统治阶级安排祭祀、朝聘等重大活动,对于农业活动和民众生活,都具有指导作用,因此由政府颁布历法就显得极为重要。政府可以通过颁布历法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正如司马迁所说,正朔不仅是历法信息,更是一种政治信息,诸侯需遵行天子的正朔,附庸政权也要通过奉其所依附政权正朔的方式表明其依附关系。后梁建立后,“赏刑制度并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则称臣,奉其正朔”[5]5224。
正朔问题,在大一统王朝时期没有争议,但在分裂时期,多个政权并立,就产生了以谁为正朔的问题,即正朔论,又称正统论、正闰论。南北朝后期,东魏、西魏、梁三足鼎立,正朔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高欢所说,北方士大夫因为对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心驰神往,进而以梁为正朔所在,涉及到士大夫阶层对南北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不同认识,自然会威胁到东魏的统治,所以高欢才会担忧“士大夫悉奔萧衍”。在这里,衣冠礼乐与正朔所在即正统观之间紧密相连。士族阶层由于所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影响和大家族宗法制度的需要,对衣冠礼乐制度特别看重,对于专事衣冠礼乐的梁武帝萧衍甚是服膺。文化成为决定士大夫对正朔所在认定的关键所在,对正朔所在的认定即是对政权合法性和正统性的认可。
四、正朔观与国家统一
正朔观也体现在史家修史上。特别是在分裂时期存在多个政权对峙的情况下,以谁为正统,以谁为攒伪、偏居,是史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延寿修《南史》《北史》,面对南北对峙诸政权,也有其正统观。《十七史商榷》卷55“大举北侵”条载:“愚谓梁与魏为敌国,而《南史》于‘北伐’改为‘北侵’。……李延寿之意以北为正,南为伪也。”[13]683又“北周为正”条载:“李延寿意以北周为正,北齐为伪,盖唐承隋,隋承周故也。”[13]692与东魏士族以萧梁为正朔所在不同,由于魏周、隋唐相承继,李延寿为唐人,遂以魏、周为正统,以梁为偏居。何德章进一步对《南史》《北史》的正统观做了详尽研究[14]。
学界对于正朔观、正统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李珍梳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正朔论的理论探讨[15]。董恩林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起源于华夷之辨、尊王攘夷的需要,进而产生了君权神授的“历数”“正朔”等政治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包含民族正统、政治正统和文化正统三种内涵[16]。胡克森将中国古代正统观的发展和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中原地域正统观、汉民族正统观、中华民族统一正统观[17]。
就梁武帝所处的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之争而言,涉及到华夷之辨的民族之争、中原与边缘的地域之争、功业大小和实力的强弱之争。沈约《宋书》称北魏为“索虏”,萧子显《南齐书》称之为“魏虏”,《魏书》则称南朝诸政权为“岛夷”。南北双方立足点不同,认识不同。南朝立足于华夷之辨、民族立场,强调自己的华夏民族血统,称北朝为“虏”,强调其夷狄身份;北朝立足于地域的中心和偏居、功业的大小、实力的强弱,强调南朝偏居于“中国”之外、栖居于荒岛之上,突出自己占有中原地区的地域之正及实现北方统一的功业之大。南北双方都立足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突出自己的优势,攻击对方的弱点。
梁武帝在民族、地域、实力的正统之争之外另辟蹊径,大力推进图书文教事业,专事衣冠礼乐。梁武帝的新举措,意在突出其文化的正统性,即梁是中华正统文化——儒家礼制文化的继承者。这是梁武帝萧衍专事衣冠礼乐的背后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争取正统地位的措施在孝文帝时期也发生了变化。孝文帝之前的北魏帝王并不讳言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他们的视角更多地立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和完成北方统一的事功。孝文帝则进一步从地域上突出北魏的正统地位,将都城从偏远的平城迁往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域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以摆脱对正统之争不利的夷狄身份,同时将鲜卑贵族门阀士族化,改革官制和礼制。孝文帝的迁都和改革,其目的在于一举实现北魏在地域、民族和文化三个方面的正统性,以最终实现国家统一。
南北朝正统之争,在民族、地域之外,不约而同地重视文化,说明民族交往的发展使文化融合的条件逐渐成熟。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突出文化正统,或许正是对孝文帝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的回应,即在地域正统之争不利、民族正统之争淡化背景下的一种战略调整。
现实政治中的正统之争,主角是政治家,是为现实政治目标服务的。有关政治家的正统考虑,还可以从石勒与徐光的对话中略窥一二。“他日,光承间言于勒曰:‘今国家无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吴、蜀未平,吾恐后世不以吾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汉运,刘备虽兴于蜀,汉岂得为不亡乎!孙权在吴,犹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荡八州,帝王之统不在陛下,当复在谁!’”[5]3033石勒担心后世不以其为正统,徐光则认为东晋、成汉是偏居,后赵占据长安、洛阳和八州的中原之地,帝王之统必在石勒。
政治上的正统之争与修史中的正统之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上的正统之争,包括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与北魏孝文帝迁都、改革,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沈约、萧子显、魏收等人在修史上的正统之争,是现实政治上正统之争的反映,是服务于政治的,更多是为自己所处的政权争夺正统之名。这与后世学者欧阳修、朱熹等人基于儒家思想而对以往朝代的正统进行评判不同。
梁武帝、梁元帝父子热衷于读书、著书、藏书,专事衣冠礼乐,大修文教,北方士大夫以为正朔所在,体现了古代史中传统文化与正朔观、国家统一之间的密切关系。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能否弘扬儒家文化,成为判断王朝统治正统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发扬儒家文化,重视礼制和典籍的建设并以之教化百姓,即可获得史家称颂,被认为符合中国文化正统;废弃礼乐文化,不重视以儒家典籍教化民众,就会被史家批判,被认为背离中国文化的正统。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君主,如果能重视儒家文化,大兴文教,也可获得士大夫阶层和史家的称赞,如苻坚、北魏孝文帝。
由于文化在正统之争中的影响力,南朝非常重视使臣的挑选,希望在外交活动中展示己方的文化实力。“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琊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6]664北魏孝文帝一方面向南朝使节展示北魏文化改革的成果,“十年,上遣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北使。宏西郊,即前祠天坛处也。……次祠庙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观视”;另一方面对南朝使节大加称赞,“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义。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18]。
在与北朝的交往中,梁武帝并非只是依靠文化,而是与军事手段结合起来。“大通初,北海王元显以本朝大乱,自拔来降,求自立为魏主。高祖纳之,以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送元显还北。”[6]461梁武帝一方面依靠衣冠礼乐的文化软实力吸引北朝人士,另一方面依靠军事手段,如接纳北海王元显并派陈庆之率军护送其进入洛阳,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统一。王鸣盛称:“梁武一意取魏,奄有南北,当天监中尚未锐志于此,及后魏事日衰,而帝心日侈,一改普通,二改大通,三改中大通,四改大同,五改中大同,观其号,其心可见。无奈魏衰而齐周并兴,梁不能取,陈庆之丧师,单骑逃回,复加封赏,如此用人,岂能成功?”[13]685梁武帝的多次北伐虽然都失败了,但其致力于国家统一的目的却是明确的。
五、梁元帝江陵焚书再评价
梁武帝大修文教、专事衣冠礼乐,不仅获得了后世史家的称赞,而且在当时也对北方士族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为梁在南北之间的正统之争中赢得了优势。梁武帝以文化争正统、争人心与军事征伐相结合的国家统一战略,一度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由于“魏衰而齐周并兴”,梁武帝最终未能成功,萧梁也在侯景之乱中走向衰亡,萧衍本人惨死。
梁元帝继承了梁武帝的事业。萧绎喜欢读书、著书、藏书,藏书量巨大,文教事业兴盛。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登上帝位,事业达到顶峰。但不久后江陵被西魏攻破,梁元帝主动焚毁所藏图书十四万卷,随后被杀。兴衰成败转变如此之快!梁元帝在焚书时发出“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的感慨,是向上天的发问,深深地反映了梁元帝的困惑与不甘。
对于梁元帝之问,王夫之认为:“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19]王夫之将梁元帝的失败归于不仁,如对兄弟子侄的剪灭,但也基于读书经世致用的立场,对梁元帝丧失读书的目标和方向,无志而以读书为志,继而沉迷其中,与宋元小儒一样寻章摘句、为文章而文章提出了批判。
现代西方的软实力研究或许可以为梁武帝父子专事衣冠礼乐、大修文教和梁元帝的失败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角度。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认为软实力是吸引力和同化力,依赖的是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国家软实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同时软实力也有其局限性,“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更加依赖自发的解读者和接受者。此外,吸引力通常具有扩散效应,产生的是一般性影响,而不是某种具体可见的行为效果”[20]。
中国古代先祖在很早就已经注意到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并在实际政治中应用。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对北方士族阶层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引起高欢的担忧。齐、梁挑选优秀的文学之士作为外交使节也获得了北魏孝文帝“江南多好臣”的赞许。这些都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文化软实力对北方士族的吸引力成为萧梁推进国家统一事业的一大优势,梁武帝多次组织北伐,企图混一南北,但最终都失败了。可见,文化软实力固然重要,但也有其局限性,即它虽然可以产生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和同化力只是一般性影响,不足以使北方士族付出具体行动来支持梁武帝的统一。
国家统一最终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文化因素外,民族融合的进程与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对比也十分重要,软实力和硬实力二者缺一不可。在当时,民族融合尚未完成。在经济上,南方虽经过孙吴、东晋、南朝的长期开发,但经济水平仍然落后于北方,而且南方的开发地域仍然十分有限,更广大的南方地区仍然未得到开发。在军事实力上,由于骑兵和步兵的差距,北方仍然强于南方。梁武帝有志于混一南北,较好地运用了南朝礼乐、典籍领先于北朝的文化软实力优势,并将其与外交、军事等手段结合,一度取得了较大成功,虽然最终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和硬实力上的差距而失败了,但其策略是基本明确的。
梁元帝过于相信文化的力量,相信读书的功能,没有看到文化软实力的局限性。文化软实力只有与经济、军事硬实力及外交手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国家的强盛不是单方面的文化力量所能决定的,需要的是综合实力。梁元帝热衷于读书,即使得知西魏军队将要进攻,仍然讲学不缀,但在政治上猜忌残忍,在外交上任性而为,在军事部署上犯错,致使江陵陷落,导致政权败亡。元帝却仍然执迷不悟,将失败归罪于读书,愤而将十四万卷图书焚毁,发出“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的感叹,不仅给中国文化典籍造成巨大损失,也为历史留下了无尽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