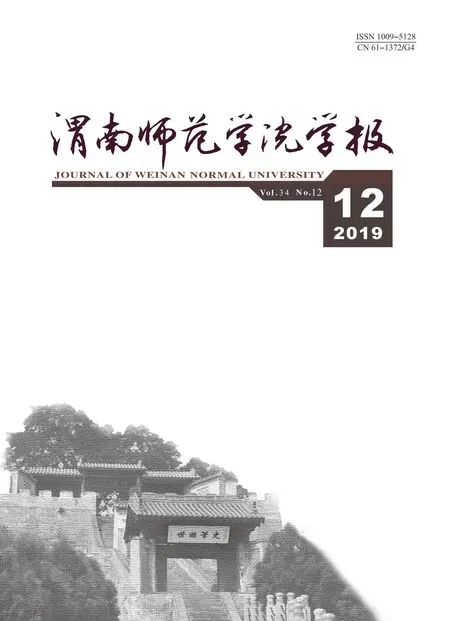拟实为体 表意为用
——党益民《石羊里的西夏》艺术实验论析
李 险 峰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长篇历史小说《石羊里的西夏》是著名军旅作家党益民的代表作之一。2011年,《石羊里的西夏》更名《屠城》,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再版,发行30万册。这部长篇历史小说问世后,被文坛誉为“再现西夏王朝覆灭的史诗”,著名学者雷达、李建军、孟繁华、白烨、胡平、贺绍俊等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荣获陕西省第二届柳青文学奖。评论界一般视《喧嚣荒塬》为党益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但就作品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论,以笔者的管见,《石羊里的西夏》无论思想价值还是艺术品位均超越了前者,在党益民的所有小说文本中更具代表性,也是21世纪长篇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创获。
从小说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反映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小说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即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1]。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主体重客观,重再现,他们试图用文学笔法还原具体的历史场景,唤起群体性的历史记忆并服务于历史。现代主义历史小说具有“历史的主观化”“超越历史”和“自指性”三个特征,创作主体把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作为探讨主题,他们把自己放在与历史同样重要的位置,看重个体性历史经验的书写。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重虚构,随意歪曲历史,动辄颠覆由来已久的群体性历史记忆,把历史置于附庸的地位。从文本的形态来看,《石羊里的西夏》总体上属于传统历史小说。然而,这部历史小说又分明借鉴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用穿越式的情节设计、繁复而清晰的视角转换、多层次的历史仿真、虚实相生的魔幻情调使文本焕发出别是一番滋味的艺术张力,彰显出拟实为体、表意为用的独特风致。
一、穿越式的情节设计
近年来穿越题材愈来愈受到网络小说写手的青睐。尽管穿越小说的内涵尚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但已初步形成了基本的模式:“小说主人公(一般是一位当代青少年)由于某种原因从其原本生活的年代离开,穿越时空,到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空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2]党益民既非网络写手,也不是刻意追求艺术技巧实验的先锋派小说家,而是一位操持传统文学艺术经验、深具现实情怀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家。但是,作为一位立足武警部队重要岗位的高级政工干部,虽然他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惜时如金地从事艺术创造,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却并不墨守成规,对于文学艺术的钟爱使他不仅如饥似渴地汲取经典文学艺术的养料,也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经典文学艺术素养跟大众文化兼容并蓄的审美意识结构从《石羊里的西夏》开头部分“我”与夏雨富含时尚元素的对话以及《一路格桑花》等文学文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这样的秉性和学养使他从日益勃兴的网络文学以及借此改编的影视剧作中得到一定的艺术启示和借鉴。
如前所述,《石羊里的西夏》的情节主体必然受历史本事的框束,不能像纯粹的穿越小说那样对客观的历史走向无厘头地臆想和虚构,因为读者对历史小说和穿越小说的阅读期待显然是不一样的。但作者在情节设计上借鉴了穿越小说或穿越影视剧的艺术技巧,给小说叙事和文本的接受都产生了积极意义。小说中的“我”本是现实生活中钟情于曾经辉煌一时而后神秘消亡了的西夏文明的党项后裔,在元大都遗址公园散步时,偶然从一个参与修筑地铁十号线的民工那里得到了藏匿着《白高大夏国秘史》的石羊,后来在夏教授家里发生自石羊的一系列神秘奇异之事使“我”在“恍惚中”由当下穿越到八百年前的西夏,而“我”即是西夏最后一个国王李睍(小名尕娃)。于是,“我”成为西夏王朝被蒙古铁骑屠灭前20余年忧愁风雨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诉说了西夏王朝从纯佑到末代皇帝李睍的末世苍凉。“我”从少年到青年一直到在风雨飘摇中当上皇帝以至最终被托雷用弯刀劈死的生命轨迹演绎了西夏王朝的内讧史、衰败史、灭亡史。而夏教授的女儿夏雨则是阿默尔的孙女阿朵的转世,阿朵“喜欢光着脚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夏雨也“喜欢光着脚丫在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夏雨脖子上挂着的玉羊竟是阿朵脖子上的玉羊几经辗转,被一个考古学家发现后送给夏教授的。这样,“剩女”夏雨也经历了一次生命的悲情穿越。因此,“我”跟夏雨两个当代人通过梦幻般的穿越完成了对西夏王朝末世动荡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建构。
就作者的创作动机而言,穿越式的情节设计至少产生了两重艺术效果。一方面,《石羊里的西夏》因融入了网络穿越小说的艺术技巧从而使作品激发了更多青年读者的接受兴趣——“穿越小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青春文学的气质。穿越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是以35 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为主”[2]。在“拥抱数字媒体,放弃阅读能力”的“后文学时代”[3],唤醒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成为传统历史文学的接受主体是历史小说家们不得不承担的文学使命,不得不深入探讨的一个文学话题。读者意识的缺席向来不过是书斋里的文学自慰。另一方面,穿越式的情节设计也为小说繁复而清晰的视角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只有当“我”穿越800余年的历史时空成为西夏王朝的亡国幼主,才能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西夏王朝衰亡的历史故事。
二、繁复而清晰的视角转换
徐岱在其《小说叙事学》中对小说的“叙事的人称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人称意识”的产生是现代小说迥异于古代传统的一个重要标志,人称选择的背后存在着叙事主体对叙事文本的总体效果和全盘结构的考虑,叙述的人称意味着一种叙事格局的确立,这种格局关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4]304-305对长篇历史小说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都明白这样的事实,由于时间跨度的深长、历史场景的宽广、人物数量的众多、故事情节的丰富等诸多因素,长篇历史小说作家很少选择把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视角,这是由第一人称固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但党益民在《石羊里的西夏》中却主要采用“我”(即“尕娃”李睍)的视角叙述二十余年西夏王朝的内忧外患,而且,在艺术构思上更为大胆的是,作品中还有另外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我”,即购买石羊、与夏教授一起破解石羊里所隐藏的秘密的“我”,这个“我”实际上是作家——叙事主体的视角。这两个“我”时分时合,亦幻亦真,使故事穿梭于“真实我”与“假想我”,“古代我”与“现今我”的两重境界之中,从而强化了表意的真实感和亲切感。
评论家李鲁平对《石羊里的西夏》中两个“我”的双重视角作了精当的解读:
小说把“我”与夏教授对石羊的不断解密穿插在“尕娃”对西夏王朝的历史叙述中。在“尕娃”的叙述中,尕娃既是西夏王朝最后一段时光的见证人,也是西夏历史的追寻人,因为尕娃自身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咨询本民族的历史记录人阿默尔了解西夏的历史。作家与作品中的“我”则是通过弄清石羊的秘密来探寻西夏的历史。作品中这两个叙述层面上的“我”具有某种同一性。作家“我”有时事实上把自己幻化成了历史中的“我”(尕娃),比如作家“我”想象“我”与教授的单身女儿的爱情,就是“尕娃”与“阿朵”的爱情。[5]
但是,第一人称视角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它难以展现悠长广阔的历史时空,无法叙述“我”作为历史在场者视角之外的生活场景,无法以“我”的口吻描摹他人的心理活动。为了弥补第一人称的局限,作者采取了转换视角的策略,小说常常通过叙述“尕娃”的梦境或者直接将叙述视角由第一人称转换为第三人称来补充叙述“我(尕娃)”个人经验以外的西夏往事和历史细节。比如在追叙党项先祖自隋末唐初以来历经拓跋赤辞因战败被迫归附唐朝受唐朝赐李姓、两次内迁、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夏国公”、李继迁中吐蕃人毒箭身亡、李德明施行“东和西战”战略、元昊登基这一系列历史进程时,小说采用的便是全知全能式的第三人称视角。又如在叙述德仁向安全提出关于修改《贞观玉镜统》的二十三条意见那个场景时,一者“尕娃”当时不在场,再者以“我”的口吻不宜刻画有些大臣特别是遵顼的内心活动,于是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现实生活中的“我”对当下生活图景和“尕娃”在场的历史场景的第一人称叙事与“尕娃”不在场的第三人称叙事迭次登场,构成了小说繁复而清晰的叙述脉络和独特结构。
《石羊里的西夏》这种独特的叙事格局仿佛幽灵叙事,历史中的“我”早在八百年前就被托雷砍掉了脑壳,但他的魂魄却附在了现实中的“我”身上,两个“我”合而为一,向读者讲述西夏王朝最后二十年的悲凉故事。同时,又通过尕娃的梦境让那些尕娃未曾经历的历史场景一次次“闪回”,让尕娃的列祖列宗一个个显灵,从而建构了相对比较完整的党项民族秘史和西夏王朝全貌。可见,党益民是一位有着强烈的“人称意识”的小说家,他非常重视自己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方式,为了使对话方式达到最佳状态,他不断地转换叙述视角,拉近了与读者之间心理距离,为读者呈示了清晰而又多样化的历史景观。
三、多层次的历史仿真
时至今日,人们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由于“写史出于政治和道德的目的或迫于政治和道德的压力,不从实而书或不敢从实而书;史家的历史观;语言固有的修饰性”[6]331-334等诸多主客观原因,历史书写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虚构”现象。从哲学上讲,一切存在一旦逝去,就不可能有“克隆”的可能,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妇孺皆知的论断,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从接受的角度而言,对历史文本毫不怀疑照单全收的态度显然是幼稚可笑的。历史书写尚且存在“虚构”,那么,作为文学艺术的历史小说更不可能还原历史本真,历史小说家既没有复现历史事像的可能,也不必持有再现历史原貌的创作诉求,他至多只能将史有所载的历史人事作为骨干题材并附之以虚构和想象来造成历史感。曹文轩站在哲学的高度深刻指出,“世界上没有再现的艺术,只有表现的艺术。”[7]81这个观点虽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层面上使之绝对化,但对于试图“克隆”历史真相的小说家来说具有警策的意义。然而,即便从艺术的角度考虑,历史小说家如果无视一切历史文本,肆意解构基本历史框架,不顾常识地进行自我臆想中的历史叙事,这样的产品就不能贴上历史小说的标签。另一方面,读者面对历史小说时一般会产生获得一定历史知识、走进历史情境的阅读期待,因此,一切历史小说家首先应该使自己成为所书写的那段历史的专家,必须在尊重历史总体面貌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艺术想象力,描绘历史的仿真世界,为读者营构“历史的”氛围,从而使人物鲜活起来,场景“逼真”起来,细节生动起来。
由于历史资源的丰厚、历史本身所散发的故事性以及“借古喻今”这一表达技巧的相对安全,书写历史向来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叙事传统,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影视作品等一直是中国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类型。进入21世纪,人们讲述历史的热情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呈现着持续升温的态势。但是,不同朝代的历史被讲述的程度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相对而言,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被关注得最多,其次为秦、汉、唐、宋、明,再次为先秦、魏晋南北朝、元等,像西夏这样以边地和少数民族历史为题材并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文艺作品几乎缺席。西夏的历史景观既然在大多数读者的史实结构中比较模糊,那么描述西夏历史的小说更应在历史情境的营造上作出更多的努力,由此而来的陌生化效应方能激发读者的接受兴趣。在研读西夏历史的过程中,党益民对自己身为党项后裔的民族身份有一定的认同,他是一个自觉的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追寻者、叙述者。为了把《石羊里的西夏》打造成精品历史小说,他收集研读了大量的有关西夏和党项人的历史文献资料,向有关专家学者虚心请教,深入到四川汶川、茂县、北川一带的羌族地区走访调查,“那里美丽的风光、古朴的民风、神奇的羌寨和古碉楼,还有神秘的‘释比’老人深深地吸引了我”[8]136。通过艰辛的文献研读、多方请教和田野调查,党益民无疑已成为西夏和党项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这一方面为小说搭建了牢固的艺术框架,另一方面也为他的再造想象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资源。
在《石羊里的西夏》中,党益民借阿默尔之口表达了他的历史叙事观:“正史里粉饰过的内容太多,不可信;《秘札》里的内容又很琐碎,太啰唆。所以我要写一部有血有肉的秘史,要给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白高大夏国的历史。”[9]65正是基于这样的识见,他在《石羊里的西夏》中多层次地进行历史的仿真,建构了一部“有血有肉”的西夏秘史,让我们仿佛进入了八百年前的西夏生活场景。这里有对西夏草原风光的描摹。比如雨后的西夏美丽而诱人,“雨终于停了。早晨的空气很好,天空晴朗。站在山坡上,能清晰地看见远方低矮起伏的沙丘,像一个丰满的女人躺在那里晒着阳光。沙丘后面是敌人密密麻麻的营帐,隐约可见的炊烟,如同女人呼出的气息”。有对西夏风俗的展示,比如党项人的占卜风俗“炙勃焦”“听弓”“咒羊”,祭神仪式,不食马肉的民族禁忌,复仇风俗,婚俗等等。有对西夏饮食的、服饰的、建筑的等物质文化的描述,比如“尕娃”家(国相府)早餐吃的是奶茶、粟米羹、荞麦饼、奶酪、腌制的沙葱、野韭菜,盛食物的盘子有菊花盘、牡丹盘、银莲花托盘;党项人的穿着、饰品、发型也跟汉人不同,男人要把头顶的头发剃光;他们冬天为了取暖烧“地龙”,行军打仗住的是毡房,贵族家里铺有滩羊皮垫子、毡毯。有党项人的方言土语和他们的草原牧歌,最典型的是他们把“什么”说成“甚”,党项人管皇帝身边的巫师叫“厮乱”,负责传递情报的士兵叫“急脚子”,步兵叫“步跋子”……这些“都流淌着西夏文化特有的地域色彩和异域风情,这既使作品平添了一重历史的真实,又使作品增强了文化的底蕴”[10]。相较于那些文明延续至今、拥有较多民族文化视像和遗存的边地和少数民族比如苗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关于党项这一神秘消失了的民族的历史想象更其艰难。因此,《石羊里的西夏》显示了党益民搜集素材的极大付出精神和非凡的艺术想象能力。
从题材上来看,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雪祭》是典型的藏地书写,《喧嚣荒塬》《阿宫》是纯粹的渭北叙事,《根据地》呈现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历史文化风貌,跟前述作品相比,作者在《石羊里的西夏》的创作中表现出了竭力去西藏化和渭北化的自觉,我们既看不到以“格桑花”为地标符号的雪域风情,也看不到氤氲着厚重农耕文明的关中格调,更看不到照金、南梁的梢林和台塬,眼前涌动着的是八百多年前党项人的毡房和蒙古王子托雷的弯刀。
四、虚实相生的魔幻情调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这一时代大潮的冲击与裹挟,中国文学自觉不自觉地向世界文学敞开了门户,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文学的视域,其中影响最大以至融入不少作家自主的文学观念的首推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正如新时期文学的亲历者、见证者、著名作家王蒙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一些作家对马尔克斯极佩服。当然在写到心理变态时又受卡夫卡的影响,在写到人道主义情感时,又受到艾特玛托夫的影响等等。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最大,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受马尔克斯影响的痕迹……”[11]386-387党益民也深受其影响,他曾告诉笔者,他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至少看了五遍,他的成名作《喧嚣荒塬》里九十多岁长出满口新牙每天夜里咬碎核桃活了一百三十余岁的太婆显然就是中国版的乌尔苏拉——《百年孤独》中活了近一百二十岁的马孔多的开拓者和奥雷里亚诺家族的经营者。对魔幻现实主义的钟爱和熟稔为他在梳理和构建党项民族的秘史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资源。
党项是西夏王朝的主体民族,随着西夏王朝的覆亡,党项民族也从人间“蒸发”了,这一事像本身就带有较强的神秘色彩,因而,使《石羊里的西夏》这部具有现实情怀的历史小说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魔幻氛围就成为文本审美情调合目的的必然选择。“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魔幻叙事方式与技巧有多种,对新时期中国小说产生明显影响的主要有神话叙事、冷静叙事等。”[12]151走进《石羊里的西夏》,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作者显然借鉴了魔幻叙事中神话叙事的艺术技巧——受职业及身份(现役武警高级政工干部)影响和约束在文学创作中亲近主旋律并且对党项民族怀有深切认同情感的党益民当然不便也不愿操持余华式的零度叙事。
小说的总体结构框架就是叙述了尕娃的一场梦,在历史“本事”展开之前的第一部分“地铁里的石羊”(相当于元杂剧里的“楔子”)的最后一段,作者这样写道:“恍惚中,我仿佛看见了八百年前的自己,那个叫尕娃的男孩。我也看见了夏雨,那时她不叫夏雨,叫阿朵。”在历史“本事”结束后的最后一部分“远去的党项羌人”的末尾,作者这样写道:“我惊呆了,脑袋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真的拥有过一部西夏秘史,还是仅仅只是刚才的一个梦……”小说以梦始,又以梦终,从而使西夏历史的演绎披上了一袭梦幻的外衣。不仅如此,对小说里的若干人物,作者也做了神话式的处理。主人公尕娃就带有超人式的魔力,每当蒙古人兴师而来边关告急时,他能听见羊胛骨发出的奇异叫声,他的梦里常常出现列祖列宗的鬼魂显灵,从而渲染了小说的神秘氛围。厮乱阿默尔是小说中另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巫师的身份本身就给人以神秘感,他能预测吉凶,他是党项人的先知,西夏王朝的兴衰、党项人的存在与消亡他都了然于心,但是他改变不了“天意”,只能默默地撰写神秘的《白高大夏国秘史》,然后将它悄悄地藏在石羊里等待八百年后的“我”来发现和揭示。从阿默尔的身上似乎能看到《百年孤独》里的乌尔苏拉、《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和《喧嚣荒塬》中太婆这些带有神异色彩的人物的影子。
如果说尕娃和阿默尔扮演的既是历史又带有神话色彩的角色从而使小说显示出对现实的幻化,那么,那些离奇怪诞的事像则是幻化的现实。比如,“汶川那边的羌族聚居地一地震,北京这边的元大都遗址下面就发现了可能跟党项羌人有关的石羊,难道真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又如,“我疑疑惑惑地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把石羊仔细刷洗干净。我嗅到了一股腐朽的羊血的味道,惊奇地发现石羊的肚皮下面有一行字,竟然是西夏文。我的心一阵狂跳。”再如,“我和教授准备将《白高大夏国秘史》送到北京文物局去,可是这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它们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堆粉末。”石羊及其所散发的腐朽的羊血味,石羊肚脐下面的西夏文及文字所记载的《白高大夏国秘史》这些事纯属子虚乌有,纯然是历史讲述者幻化的现实,但将其置于汶川大地震的现实语境中,竟给经历了那场巨大自然灾害的读者信以为真的错觉。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使小说的历史叙事氤氲着神秘而略带恐怖的魔幻情调,从而书写了一部有血有肉的西夏秘史。
20世纪末以来,跟非历史小说现代后现代思潮迭起的空前盛况相比,历史小说显得颇有些老态龙钟,不苟言笑,在诸多文学大奖评审中难入专家们的法眼,这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固然与受历史“本事”的束缚不便施展拳脚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历史小说家创作观念滞后的掣肘。从历史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西方现代派除去意识流、新感觉派和结构现实主义曾用于拟实,其余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均属表意艺术范畴。幻诞、象征与黑色幽默在拟实小说中或偶尔一用,但只能作为个别手法,不能成为全局性的艺术方法,否则就走向奇幻表意”[13]。无论“穿越”还是魔幻,在《石羊里的西夏》中都只是作为个别手法、而没有成为全局性的艺术方法,没有因为借鉴了这些方法而改变文本“现实性拟实类”的基本色调,“尕娃”所经历的那段西夏内讧史衰亡史得到了全景式的建构。历史本身有其存在的样态,这是一切历史讲述者都不能违背的,但怎样讲述则可以有各自的选择。从这层意义上来看,《石羊里的西夏》对当下历史小说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发。
有论者指出,“党益民除了军旅作家典型身份表征之外,还有他无法‘割舍’的‘秦之子’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14]。其实,论及党益民作为颇具实力的“业余”作家的身份表征,集中笔墨雕塑西藏高原军魂理所当然是典型的存在,但在这一典型身份表征之外,除了“秦之子”即陕西地域文化身份,还有作为西夏党项后裔的族裔身份,这也是党益民把自己书房命名为“三西堂”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党益民是拥有西藏、陕西、西夏三套笔墨的知名作家,而长篇历史小说《石羊里的西夏》则是他西夏族裔身份唯一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