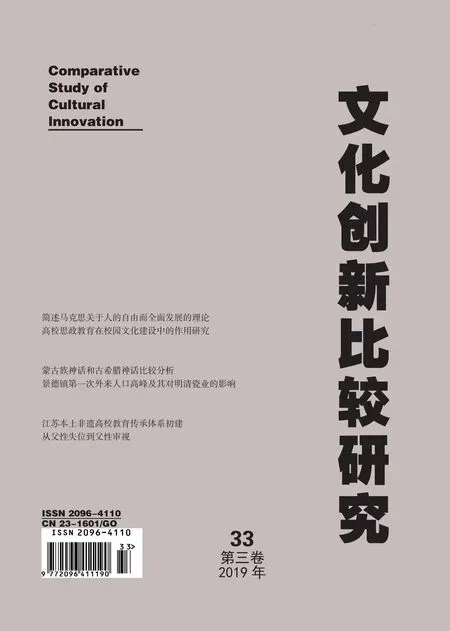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红军在雪山草地的粮食供给问题研究
李 星
(四川省团校,四川成都 610100)
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在此期间,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红色革命圣地,就长征精神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爬雪山过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行程。在雪山草地,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粮食问题成为红军亟需解决的首要难题。
1 解决粮食问题的必要性
长征途中,粮食供给匮乏问题一直存在。在雪山草地,此问题尤其突出,成为红军能否继续前行的关键。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的粮食困难状况,当时的电报、文件记载颇多,现择要佐证。
1935年7月15日,红六军在绒玉向红军总部报告说:“我大部尽吃野菜及干皮,现表现严重饥饿状态,死亡30余。”同日,《陈伯钧日记》中也记载:“是晚模范师、十八师及十六师之一营均到绒玉。此次行军,我军主要问题,就是缺粮、缺帐篷,以致影响工作。”7月25日,红六军在阿坝向红军总部报告说:“全军缺粮,从鱼头寺到阿坝死亡约300人。”
邓颖超曾回忆:“长征中除了作战外,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而部队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时……粮食就更困难。”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也提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肖锋在《长征日记》中写到:“在部队行动过程中,粮食日渐成为威胁我军生存的大问题。”可见,当时粮食问题已成为困扰红军的难题,并引起红军部队的高度重视。
2 红军在雪山草地筹集粮食的方法
2.1 筹集粮食的总体措施
2.1.1 拟定粮食分配计划,加强粮食宣传工作
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上级动员部队严格节约粮食,互相调剂,彼此帮忙,优先照顾伤员,连队把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定量食用,禁止粮食煮酒和出口。要求:“必须严守阶级路线,发动群众没收反动头人的粮食和牛羊,分一部分给群众,大部分供给给红军。在家未反动的头人,可用借粮证给他。在家群众的粮食和牛羊要出钱收买,跑了的穷苦群众,我们如吃了他们的粮食,群众回家时仍归还他钱。如穷苦群众地里的粮食我们割了,应当还一部分给他吃,另一部分我们给钱收买。禁止不分阶级路线的举动;不准用粮食喂牲口,不准抛散一粒粮食。”
针对粮食紧张的情况,红军加紧了粮食的宣传工作。指出:“动员一切力量拥护战争。各地党部要动员大批群众参加红军拿粮食打草鞋拥护红军。”着重提到:“应该尽一切可能少牺牲群众的利益,节省粮食,把负担加在剥削者身上……”1935年6月2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的《筹办、节省及携带粮食办法》指出:“我野战军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各部队除五天休息所需的粮食外,应筹足七天的粮食准备携带,以后不论向何地行动或休息,都应有七天的储粮,并规定了各军团的筹粮地区。还规定了每人每天食量”此外,由地方机构号召发展生产,提倡多种生长快,周期短的作物。
1935年11月,粮食问题更为突出,大金省委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第一,调查金川的粮食数量和分布情况。第二,预算粮食开支;第三,印制粮食购买证,粮食集中由粮食部管理;第四,粮食供应统一运输,建立粮食纪委、粮食巡视员,加强粮食纪律,节约粮食。第五,在各县、区成立粮食委员会,粮食一律要过称,严格注意收集和保管粮食。
2.1.2 缴获战利品
红军在川西北地区攻占了近10座县城和官寨,缴获了部分粮食、军需品。程世才在《包座之城》中回忆到:“敌主力被歼灭,后勤部队企图逃跑,我军以一部兵力猛追,缴了七八百头牦牛和马匹,这些牲口驮的粮食和弹药也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红军在懋功县接管了国民党的仓库存粮。当时,在县城禹王宫有一存粮仓库,名称“济仓”,存粮在20万斤左右。
通过缴获战利品获得粮食的数量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成为红军筹集粮食的主要途径。
2.1.3 通过苏维埃政府没收劣绅、地主的粮食;向商人和当地群众购买粮食
由于各级苏维埃普遍建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普遍展开,筹粮工作迅速开展起来。筹粮时,由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以地主豪绅为对象,开仓开窖筹集的粮食,予以没收,不给钱。懋功县两河口苏维埃主席罗永忠先后两次率领50余名游击队员在两河口大板昭一带筹粮,没收土豪赵洪发、何万福的藏粮5000余斤。
红军在各处都设有国家商店,用现金或实物收购粮食。金川苏区的国家粮店初期每天能收买粮食数千斤,红军在当地群众家里筹集的粮食,用川陕苏维埃发行的银元、铜元、纸币、布币等购买。
红军在茂县收购粮食,每斗玉米(约40斤)付给银元四至五元。茂县苏维埃每天在县城附近为红军筹粮,有时一天可筹集四五千斤。在黑水售粮的群众中,最多的一户筹粮400斤。懋功县的苏维埃组织还协助红军在群众中购买粮食。据老红军谢新华回忆:“1935年春天,粮食问题很严重,前方需要供应,我们在后方也没有吃的。那时我在负责筹粮工作,马尔康一带的苏维埃成员,藏民们帮助我们买了不少牛羊和粮食,牛、羊关了一条山沟,最少也有几万头,粮食约有40万斤。”
可见,通过苏维埃政府没收劣绅、地主的粮食,向商人和当地群众购买粮食是当时最主要的筹粮方式,也是获得粮食的重要来源之一。
2.1.4 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和窖藏,留下银元或欠条;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插上木板借条
筹粮过程中,红军不得以运走当地群众藏匿起来的粮食,都要留下欠条。红军每次挖窖藏时,都要通知群众将自己窖藏的粮食认领回家自用,只取走地主家的粮食。肖锋在《长征日记》中提到:“8月5日:各单位找粮的办法很多,尤其是工兵连,挖地窖的办法多,各单位筹集的粮食足以吃20天。8月6日:我同警卫连去青山借粮,途中,在半山坡看见四个人留下四袋青稞,我们打了一张借条。8月15日:经过十天筹粮,我们共借到几十斤青稞麦和一些盐,还借到四头猪。”
除了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和窖藏,留下银元或欠条,为了筹集粮食,红军迫不得已展开了大规模的割麦工作,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原总政治部于1935年7月18日专门发布了《关于收割麦子的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区收割已成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割麦办法是由军团与师政治部作大体的分配,再回各团政治处分配麦田给各单位去割。”
由此可见,运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粮食和窖藏,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是红军在筹集粮食过程中迫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但是红军在运走粮食和收割麦子的过程中,都留下了欠条,表明红军严守纪律,不以强征硬抢的方式筹集粮食。
通过以上措施,初到川西北时,红军用粮基本能够得到解决。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大部队的不断挺进,缺粮问题日渐突出。
2.2 成立筹粮机构,加强统一管理
1935年11月11日《西北联邦政府与大金省委联席会议》提出:“成立粮食委员会。督促各县、区、乡粮食工作有组织做起来,统一管理,区、县都要组织粮委。粮食要过称,成立粮食纪委;粮食权集中在粮食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的《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指出:“由当地驻扎的党、政府、红军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粮食委员会,统一收支。”
据载,红军共成立了芦花和毛尔盖两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开展筹粮活动。其中“黑水、芦花粮委担任筹集60万斤粮食的任务,计划在几个出产粮食的中心区域分头进行。”在汶川县威州宝子巷和涂禹山设有两个粮食集散处,由红军后勤部派人掌管。在懋功,红军组织了苏维埃“筹粮队”(俗称“打粮队”,实际上是后勤部派出的人员),深入到村寨筹集粮食。
红军通过建立各类筹粮组织,统一筹粮思想,规范筹粮行为,保证筹粮工作有序化开展,避免了在筹粮过程中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局面出现,也缓和了“与民争食”的矛盾,是红军成功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
在每一层次上对该层的因子进行逐个对比,对各个影响因子彼此间的重要程度量化,通常采用9 标度法进行赋值,构造相互比较结果的判断矩阵。层次分析法的判断矩阵模式,方便决策者进行不同指标之间的两两比较,有助于决策者明确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判断矩阵时,通过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各个影响因子指标进行比较评分,以一级指标影响因子重要关系为例建立判断矩阵见表3,其他每个判断矩阵依次类推。
2.3 红军筹粮措施的改进
红军在川西北地区的筹粮工作,并非一直都很顺利。除了当地粮食本来就很缺乏外,由于一些筹粮措施不正确,引起了当地一小部分群众的恐慌与反感,以致采取一些消极的方式加以反对,使筹粮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据当时总后勤部王政柱副部长谈红军长征在阿坝地区有关情况:“那时候部队那么多,大山区里出产很少,番民不懂我们的话,筹集粮食要讲民族政策才行。开始我们对大头人的粮食财务采取没收的办法,这样一搞很紧张,他们就把粮食藏起来了,人也躲到深山里去了,部队的粮食、供给困难了,就只有借粮。”
可见,在筹集粮食的过程中,办法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强制征收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会引来当地人的反感和恐慌,一些人只有用躲避的方法和其他消极方式反对,这样就加大了红军在当地筹集粮食的难度。
针对在筹集粮食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红军适时调整,改变了部分筹粮办法。
2.3.1 颁布政令,改进筹粮办法
1936年7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在《红军目前在西北地区筹取粮食资料办法》中指出:“根据当目前新的策略路线,过去红军中一般用“打土豪”、“打发财人”等口号来筹集红军给养军需与发动群众斗争的方法,现在是不适合了。在少数民族区域,不论主人是百姓或地主军阀与头人,在家或跑了,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拿粮食、取东西,而是应该采取下列方法》:1、向富有者交涉借贷或购买,一般群众的东西实行公买公卖,不得有所强迫。2、如果那些富有者或者财产的主人跑了,则应号召其回家,与之交涉。但若需要甚急,红军又无法待主人回家,则应由政治机关或应由部队政治首长批准向富有者家里借取一部,并留下收条或说明书。3、对武装抵抗我军者,则在其投降后吗,提出赔偿损失的办法以取得红军的需要。4、对大小商店的货物只能经过购买手续,不得用没收与强买的办法。5、倘若当地粮食物资都下了窖,或藏在山上,则应号召山上的群众回家,向其交涉购买。不得以要进行挖窖时,则应注意不可毁坏经书、庙宇及坟墓,以免伤及少数民族的宗教感情。”
2.3.2 筹集粮食转变为筹集可食物
到了无粮可筹的时候,红军组织工作队到边远牧场购买牦牛,买回来后,将大部分分给当地群众。据勒乌乡梁全国老人回忆:“当时他们是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缴获牦牛30多头。虽然缺粮很久,但这些战利品还是分给了群众,红军自己一个分队只分到一头牦牛。”据壤塘跃武村、吞都村和卧龙村村民牛旺、徐洛等回忆(1984年5月18日):“红军在该村筹粮时赶走羊300多只,牦牛300多头。”
1936年7、8月间,红军二、四方面军过草地时,为了生存,部队常常是遇见牛羊、即“围而筹之”,甚至派出部队专门到偏远的草地深处寻觅游牧的牛群、羊群。到了后期,粮食问题越来越尖锐,部队只好到周边地区去筹集粮食。
2.3.3 熬制土盐
除了筹集粮食以外,盐对红军的生存也有重要意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红军缺盐现象严重,所以熬制土盐也成为红军筹集粮食的一项重要工作。
红军请来会熬制土盐的藏羌师傅作指导,将含有盐分的盐石、泥土用水浸泡,取汁熬盐,约每200斤盐土可熬盐三四斤。当时,理番县的四门关、薛城,茂县的石大关、赤不苏,黑水的瓦钵梁子、色尔古等地都是产土盐的地方,至今还留有红军和群众挖的盐洞。
据肖锋《长征日记》中回忆:“红军经过大力开展筹粮、熬盐活动,部队有了粮食,有了盐,大家行军的劲头更大了……”
3 红军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因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面对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交锋、光明和黑暗两种前途的抉择,我们党始终植根于人民,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指示》指出:“上山宣传队应该很好地组织起来,细密的检查和督促他们的工作,使之成为喊群众回家的有力武器。必须利用一切可能使群众回来安居,纵然遇到一个群众,也必须不放松的给予优待和宣传,利用他喊群众回家。政治机关应注意收容投诚土司、通司及一切活动分子等,委以相当名义,这些人在号召群众方面,常起到很大作用,在行动中,先头部队应该组织武装的先遣工作队,专门做宣传群众的工作。”
在雪山草地,红军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许多书写、篆刻、标语、布告。选择的地方有院墙、碉楼、住房、门柱、城门等醒目的地方,树干上、草地上都有红军留下的标语。据党坝、松岗、卓克基等地的群众回忆,红军在岩石上、路边、墙壁刻写、贴满了标语,用藏汉两种文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纲。
红军还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番民代表大会等,向各族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部队中的宣传队、剧团等单位,在军民联欢会等场合,给群众演出歌舞、川剧、话剧等,用革命文化的形式来扩大影响,以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
红军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有效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成为成功解决粮食问题的关键。在雪山草地解决粮食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民族工作的经验,增强了群众工作本领,体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当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