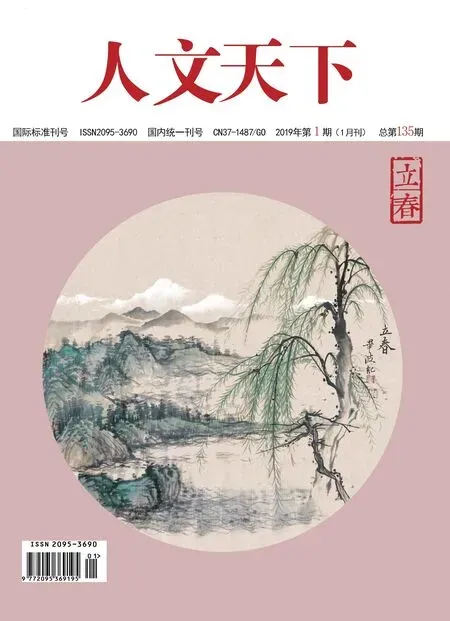休闲经济视角下的 “理性”供给与需求
——以电影产业为例
刘瑞祥
休闲产业是一个“泛产业”,只要能为消费者的休闲活动提供服务的行业均属于休闲产业的范畴。休闲经济产生于人们“有钱有闲”的背景下,强调“以人为本”,关注消费者体验、情感表达与满足感,认为幸福是人们的最终追求。本文以休闲经济中的影视产业为例,从“理性”角度浅析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中的供给与需求。
一、激励与供给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休闲时间、休闲需求、休闲意识逐渐提高,休闲产业蓬勃发展,休闲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具体到电影产业,大量社会资本的涌入使得电影市场空前活跃。从2011年到2017年的6年间,中国银幕数量从9286块增加至50776块,观影人次从3.7亿增加至16.2亿,电影总票房从131.2亿增加至559.1亿。毫无疑问,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票房粮仓之一。
“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是经济学的重要原理之一。激励是指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某种事物,诸如惩罚或奖励的预期。那么,中国电影创作者们面临着怎样的激励?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获得国际认可为标志,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1988年,张艺谋凭借《红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1993年,陈凯歌凭借《霸王别姬》荣获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影片。受此影响,此后一段时间的中国电影大多循此主题,但效果却不甚明显,甚至还引发了争议,批评者认为其通过展露中国人的丑陋以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落后来取悦外国人。在这种境地下,想要获得西方世界认可,中国导演的选择似乎只剩下一个,即展现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文化和优秀的民族特性,但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时至今日,即便《战狼Ⅱ》在国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从其惨淡的海外票房成绩与评价来看,结果不言而喻。
在市场激励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创作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现象。一是鲜有导演愿意触碰历史文化及民族题材,而架空世界独受青睐。二是在商业片与艺术片的博弈中,前者完胜,文艺片举步维艰。三是喜剧电影格外受到关注,特别是新进的社会资本。上述现象无可厚非,无论电影产业带有怎样的社会属性与意义,既为产业,其第一目的终归是盈利,而“理性人通过比较成本和利益做出决策”。
以2015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为例,喜剧片票房经过几年酝酿一路走高,至15年已呈井喷之势,《万万没想到》 《恶棍天使》 《夏洛特烦恼》 《港囧》 《煎饼侠》等电影皆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分别为3.22亿、6.49亿、14.41亿、16.13亿和11.59亿。与高票房相对应的是低评分,以豆瓣电影为参照,上述影片除《夏洛特烦恼》达到7.5分外,其余评分皆在5分左右,属中下水平。观众口中的“烂片”依旧能斩获不俗的票房成绩,人们对喜剧电影的偏爱可见一斑,由此带来的喜剧片票房水涨船高也是意料之中。同年,台湾导演侯孝贤创作七年、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艺术电影《刺客聂隐娘》仅收获六千多万的票房,与上述影片形成鲜明对比。创作者、投资商们热衷于商业片与喜剧片,是出于经济的考量,是对市场激励做出的必然反应。如何处理好艺术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找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有机融合的平衡点,成为当代中国电影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偏好与需求
“理性”的不仅有制片商和导演们,消费者也是如此。消费者的偏好影响产品供给,而休闲消费正是一种以精神消费为核心内容的、知识限定性的、体验性的、个性化的、受时间约束的消费,这就决定了休闲经济对消费者的关注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阶段,精神享受成为其核心要素。
为什么选择电影,为什么偏爱喜剧片,人们的休闲动机是什么?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中,时间正逐渐成为稀缺资源,现代人希望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寻求安慰和放松,喜剧片无疑是最有效的选择。即便笑点尴尬、包袱生硬,也能让人们在舒适的环境中轻松度过两个小时。但总有些电影晦涩难懂或是阴暗压抑,在微博等社交网络自媒体的影响下,也能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讲述“慰安妇”的纪录片《二十二》票房过亿,关注社会热点的《嘉年华》也取得2000万的票房成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上述提到的新现象正是观众主动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懒于选择的结果,这种“懒”助长了买数据、买热点、偷票房等现象,也体现了我国目前重娱乐性、消遣性消费,轻发展性、智力性消费的休闲消费结构。
人们总要面临选择,通过比较以在不同目标之间权衡取舍,这一过程即是决策。选择电影也就意味着要放弃学习、运动,选择某部影片也就意味着相同的时间内要放弃其他事情。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诱发“选择困难症”,口碑则成为重要的筛选器。口碑来自电影本身,是基于演员、导演、出品、发行的群体价值判断,在人们难以或懒于选择时发挥作用并左右战局。大鹏的《煎饼侠》在骂声中拿到了11亿票房,新作《缝纫机乐队》即便颇有成长也只能在与《羞羞的铁拳》的抗衡中铩羽而归。《人在囧途》只有3690万的票房,但其良好的口碑是《泰囧》12.5亿票房最有力的保障。
电影领域同样存在着休闲制约,休闲制约是指限制休闲偏好形成或阻碍人们参与并享受休闲的因素。其不仅与电影供给的结构和数量有关,还受个人知识水平和人际关系影响,如看一部晦涩电影的“补课”经历,或是顺从朋友看一部不想看的电影。电影从业者们深知这一规律,《我不是潘金莲》微博骂战、《爵迹》导演哭诉等炒作手段,抑或是频频出现“挂羊头卖狗肉”的偷票房现象,即是为了利用并扩大休闲制约的影响,提高曝光率以吸引消费者关注影片。
随着休闲教育的普及以及人们技能知识、欣赏水平的提高,上述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人们必然会舍弃快餐式的休闲消费转而更加追求文化内涵和品位,观众会更加注重一部电影所能带来的价值。
三、盲目的 “理性”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正如经济学中对于“理性人”或者“经济人”的假设,现在这一说法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认知。毫无疑问,在人类社会的光辉旅途中,在现代科学的体系构建中,“理性”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抑或是现代心理科学研究都证明:人类经常会做出不理性的、具有偏见的甚至是非常“愚蠢”的决策和行动。非理性与不可预期是休闲消费的常态体现,这不仅表现为个人决策,有时甚至是组织或群体行为。
电影艺术诞生以来,基于理性判断与大众选择的结果,不乏有名垂影史的经典佳作在其产生时不受待见。诸如《银翼杀手》和《肖申克的救赎》,如今前者成为影史上最伟大的科幻电影之一,后者则长期占据IMDB资料库Top250排行榜第一名。再如只收回成本六分之一票房的《美国往事》,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大话西游》,虽然其发行公司因此破产但却受到大陆年轻一代人的极力追捧,这或许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时间性”。在文化消费中,“理性”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人们也并非一直渴望追求理性,休闲消费受到时空与文化的限制,寄托的仅是对精神与情感的倾诉。
在现代物质社会的价值追求引导下,当然也是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人们往往为了物质享受而忽略了人生的意义与休闲的价值,娱乐活动也常常具备目的性,休闲的意义转变为社会服务,而电影也表现为一种社交手段。尽管开始就受到国内影迷的一致排斥,海外电影执着于找国内“明星代言人”的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与之相似的,漫威中国举办复仇者联盟3“国内明星见面会”的笑柄仍历历在目。从效果上看,与电影毫无关联的明星推广对电影票房的影响程度仍是无法确定的未知数,但这显然离不开对中国市场与受众的分析和妥协。
“追求利润最大化”毫无疑问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因此我们看到抹杀了事物间本来的差异、抹杀了特殊、抹杀了个性。当《阿凡达》席卷全球时,3D热在中国一发不可收拾,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电影都转制为3D格式,但由于转制技术及设备不到位,“伪3D”适得其反地带来糟糕的观影体验。《钢铁侠3》等在北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仅发行2D版本的电影,也只是针对中国市场投放特殊的3D版本。而到了以晃动镜头闻名的《谍影重重5》上映时,国内观众也终于陷入寻找2D版本而不得的哀声怨道之中。这既是电影票价与补贴带来的逐利陷阱,也是观众们消极放纵姿态的“自食其果”。即便卡梅隆曾断言:“数字3D技术带来的观影革命就跟默片时代走向彩色电影时代一样,局势已定。”但从本质上而言,电影在于对艺术的创造,是集合剧本、导演、演员等多方面因素的文化表现形式,电影的内容、形象的塑造仍是最至关重要的。3D技术是一种先进的艺术表现方式,但其仍然要以丰富的艺术内涵为基础。时至今日,北美电影市场逐渐呈现出“去3D化”趋势,而中国的“3D热”却仍未消散。
结语
本文对电影领域的供给和需求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在市场拓展与科技创新的激励下,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同时由于社会环境和休闲制约的作用,消费者的偏好也更加趋向于迎合这些特点。结果是,供需双方同时存在着不太“理性”的现象,也由此引发了电影领域供给与需求相互关系的争论。简单来说,即关于“观众埋怨没有好电影,创作者埋怨没有好观众”的争论。导演冯小刚也曾以“导致中国电影垃圾是因为一批垃圾观众”“垃圾观众养活垃圾电影”的言论参与其中。如果说电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足够理性,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争论?进一步说,当一个不健康的市场出现时,生产者和消费者谁又该承担责任?
供给与需求是使市场经济运行的力量,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决定供给量、价格、资源配置。因此,尽管这个问题有其特殊语境,但本质上并无过多讨论的价值,如果执意探讨,也应是“观众和电影谁更垃圾”的问题。更进一步说,当一个好的转机出现,需要探讨的也不是“观众和电影谁的功劳”的问题,而应是“谁的功劳更大的问题”。因此,随着观众知识水平、欣赏水平的提升,电影的供给也必然会在利润杠杆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以此共同决定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方向与未来。现在的问题是,谁率先迈出这一步,而另一方又会给出多大的回应。
撇开剧本、演员、导演等电影自身要素不谈,之所以造成“观众埋怨没有好电影”还与大量社会资本涌入电影市场有直接关系,这确实增强了电影市场的活力,但同时也降低了电影行业的准入门槛。电影产业利润丰厚、前景广阔,2007年的票房冠军《变形金刚》仅为2.8亿,10年后的《战狼Ⅱ》已达到惊人的56.8亿。但过多觊觎这块肥肉、想来分一杯羹的投机者的加入,便很有可能将这本是活跃电影市场的好现象变成乱象。“创作者埋怨没有好观众”则是在于多数观众并未把电影上升为审美活动,无论是娱乐消遣还是单纯的社交需求,电影的质量与艺术性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备选项,享受轻松愉悦的观影氛围才是关键。从这个角度说,也就不难理解当前喜剧电影的特殊意义,同时这也成为电影炒作会对票房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力佐证。
乔布斯曾提出:“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他们就发现,这是我要的东西。”这是一种对自身产品绝对自信的表现,而作为当今好莱坞最为著名的中生代导演之一,克里斯托弗·诺兰也有着极为相似的理念,在诺兰执导的电影结束的第一时间,会立刻出现导演诺兰字样以提醒你刚刚观赏了一部“诺兰电影”,其含义不言而喻。高阶段的休闲消费是“求新求奇”的,休闲产品的供给或许并不需要完全以消费者需求为基准,而是更加注重创造需求、引领需求。这也是在好莱坞电影日益类型化、电影创作者们越发急功近利的社会大背景下,执着于叙事结构和创新的诺兰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