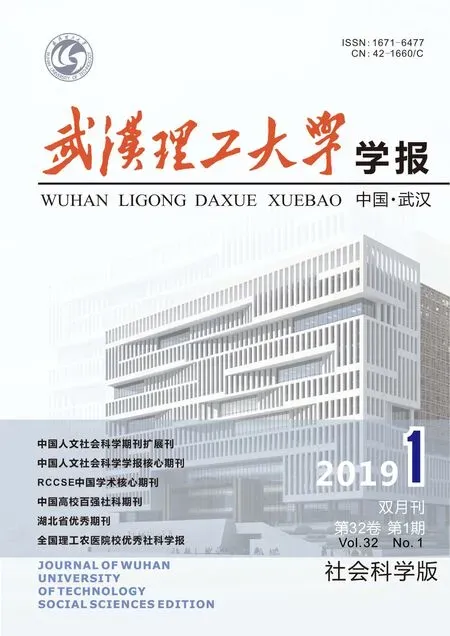禅宗“多视角”叙事对传统“全知视角”的解构*
邱紫华, 余 杰
(1.华中师范大学 东方美学与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2.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叙事视角”又被研究者们称之为“叙事角度”(narrative perspective)、“视点”(point of view)、“视觉角度”(angle of vision)、“眼光”、“透视”(perspective),“叙述焦点”(focus of narration)。无论是“视觉角度”、“眼光”、“透视”、“叙述焦点”,都包含有观察者的视角,叙述人对于人物、事件有着观察和理解上的切入点,叙述的重点和细节的选择等要素。叙述视角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叙述人称总起来说有四种情形: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第二人称叙述以及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叙事作品所采用的“人称”和“视角”变换的叙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结构主义批评家对叙述视角的形态作了比较精细的区分和多方面的研究。例如,法国的兹韦坦·托多洛夫把叙述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其中,所谓叙述的“全知视角”(Omniscient perspective),直译为从“无所不知的角度观看”,指叙事者的观察视野大于故事中所有人物的视角;而“外视角”与之相反,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一切比所有人物知道的还要少。这是禅宗“公案”叙事常常采用的叙事视角。由于佛教宣扬的“因缘和合”的真理观以及禅宗“公案”故事叙述时采取“多视角”方式,即“非全知视角”。因此,我们集中探讨佛教禅宗叙事的“非全知视角”特性。
一、 禅宗“公案”故事的叙事特点
禅宗著作的叙事特点可以通过慧能的《坛经》《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和其他“灯录”中的故事加以总结。禅宗故事往往采取“第三人称视角”和“外视角”叙事。
所谓“外视角”叙事,是指叙述者所持有的依然是“个人的角度”,其观察的视野远远小于某个人物全部的活动和经历。这种叙述视角同“全知全能”视角截然相反。叙述者对其所叙述的内容不仅不是“全知”,反而比故事中的人物知道得更少。他很像是赛车比赛中的解说者,既不知晓比赛过程中每一个选手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情况,又不可能洞察和预测比赛的结果。
相比较“全知视角”的叙事,“外视角”的叙事是“不知”和“无知”。它既是叙事者的“不知”、“无知”,又是听众或读者的“不知”、“无知”。叙事者无法解释或说明故事中人物内在的隐秘及其心理活动,又无法知晓事情的真相,无法预测事件的结局。“外视角”叙事的特点是具有客观展示性。它的叙事直观而客观,显得真实、生动而引人入胜,具有一定的戏剧性意味。“外视角”叙事所具有的“不知性”带来另外两个优点:一是富有悬念而耐人寻味;二是显得神秘莫测。
“外视角”是禅宗“公案”常常采用的叙事视角。
第一则故事:“世尊(释迦牟尼)在灵山(灵鹫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都外别传,付摩诃迦叶。’”[1]
这则故事的叙事采取的是叙述者的“单一视角”,它显得客观而逼真。叙事过程中,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所传达出来的思想情感是模糊不清的,让人感到神秘莫测,不可捉摸、不可确定。这则故事的叙事特点就是“不知”。首先,参与灵山大会的“众人”都“不知”“佛祖拈花”是什么意思,“迦叶破颜微笑”又是什么意思;其次,作为叙述者本人,对于佛祖和迦叶之间的思想情感交流也是“不知”的,因为,在叙事文本中,叙述者只有客观的叙述而没有任何的解释;再次,阅读者、接受者在看完、听完这则故事的叙述后,同样也不明白为什么“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这说明,禅宗故事的叙事,似乎故意地让人们面对事件、场景、人物、思想而不得其解,使其“不知”。
第二则名为《亡名道婆》的故事:“昔有婆子供养一庵主,经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饭给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么时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举似婆。婆曰:‘我二十年只供养个俗汉!’遂遣出,烧却庵。”[2]
这则《亡名道婆》故事也突显出禅宗“公案”的叙事特色。它故意营造出“不知”——即“不可知晓”或者说“不让人知晓”的叙事效应。其中,老婆婆借用“女色”企图来考验庵主哪一方面的德行?如果是为了考验庵主对于“色戒”遵守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庵主表现出强烈的拒斥“女色”的态度后,反倒被老婆婆斥之为“俗汉”而遭到驱逐,草庵被烧毁。读者对老婆婆考察庵主的动机是“不知”的。当事的庵主更是“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而被老婆婆逐出草庵?同样,人们不禁要问,庵主严格遵守佛教的“色戒”有什么错误?
阅读者看完这则故事,也陷于“不知”的状态中。这种“不知”必然造成多种猜测、多种解释。按照禅宗的观念,自然万物和多元化的精神思想,正像高天流云瞬间即变,不可确定。这正是禅宗叙事通过“不知”的叙事效应,来达到其所要表达的哲学理念:“一切皆不确定”。
第三则故事说,百丈怀海禅师跟随马祖道一禅师学禅已达三年之久。有一天,百丈随从马祖道一大师外出时,听到野鸭子的叫声。马祖大师问:“这是什么声音?”百丈回答:“是野鸭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马祖大师又问:“刚才的声音到什么地方去了?”百丈回答说:“飞过去了。”马祖回过头来对着他的鼻子用力拧了起来,百丈痛得连声大叫。马祖说:“还说‘飞过去了’吗?”百丈一听这话,刹那间在痛彻中开悟。
当百丈回到了寺里自己的房舍后,便哀声大哭起来。同事们回道:“你想念父母了吗?”百丈回答:“不是。”同事们又问:“是被谁打了吗?”百丈回答:“不是。”大家又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事哭呢?”百丈说:“我的鼻子被马祖大师拧得痛极了!”同事们又问:“你同马祖大师闹了什么别扭吧?”百丈回答说:“你们去问马祖大和尚吧!”同事们问马祖大师:“怀海师兄同您闹了别扭吗?现在他正在住房中大哭呢!请大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怀海师兄为什么大哭。”马祖大师说:“是他开悟了!你们去问他吧!”同事们回到房舍对百丈怀海说:“和尚说你开悟了,叫我们来问问你呢!”顿时,百丈怀海哈哈大笑起来。同事们说:“刚才还在哭,现在又为什么笑起来了呢?”百丈说:“刚才哭,现在笑。”同事们听到百丈的回答,都满脸困惑,感到茫然不解[3]。
这则故事叙事采取的也是叙述者的“单一视角”,它显得客观、逼真而生动。这则故事的叙事特点也是“不知”、费解。首先,马祖道一大师为什么突然用劲拧百丈怀海的鼻子,百丈怀海不知道,所以痛得大叫,乃至于回到房舍后还伤心痛哭。其次,同事们也不知道百丈为什么痛哭。再次,叙事者也不知道马祖道一禅师为什么突然紧拧百丈怀海的鼻子。最后,除了马祖道一禅师和百丈怀海禅师之外,谁也不知道百丈怀海为什么在师傅拧痛了鼻子之后就开悟了?百丈怀海悟到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这则故事的叙事视角也是单一的“外视角”。其叙事真实生动,情趣盎然,但同样让人感到神秘莫测,不可捉摸。
第四则故事说:宣鉴和尚一直在四川修行。当他听说南方禅宗风行,很不以为然,便说道:“出家人几千劫学习佛教礼仪,几万劫遵守佛教的戒行,还不能成佛。南方魔子竟敢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就要捣毁他的巢穴,消灭他的同类,以报答佛教的恩赐。”于是,他担着手抄的佛经《青龙疏抄》走出四川。当他来到了湖南澧阳地界,在路上遇见一位老太婆在卖饼子。宣鉴便卸下担子买饼子吃。老太婆指着宣鉴的担子问道:“这是些什么书?”宣鉴回答说:“《青龙疏抄》。”老太婆说:“它抄的是什么经呢?”宣鉴回答说:“《金刚经》。”老太婆说:“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回答得出来,便送点心给你吃。如果回答不出来,请到别处买饼子去。《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道上座你点的是哪个心?”宣鉴回答不上来,也没吃上饼子。他径直来到龙潭崇信禅师的寺庙里。
宣鉴到龙潭禅师的法堂上就说:“我很久以来一直向往龙潭,但是现在来到了,潭看不见,龙也不现身。”龙潭禅师伸出身子问道:“是你亲身来到龙潭了吗?”宣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回答,就留下来了。
有一天晚上,宣鉴侍立在龙潭禅师身边。龙潭禅师说:“夜已深了,为什么你还不下去?”宣鉴告别龙潭禅师后,刚出门又回头说:“外面太黑。”龙潭禅师将点燃的灯烛递给宣鉴。宣鉴刚伸手去接灯烛时,龙潭禅师却将灯烛吹灭了。宣鉴刹那间有所领悟。宣鉴立刻跪拜在龙潭禅师面前。龙潭禅师问他:“你悟到了什么?”宣鉴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怀疑老和尚说的话了!”第二天,龙潭升座后就对大家说:“这里有一个汉子,牙齿如剑树,嘴巴如血盆,一棒子打不回头。将来会在孤峰顶上宣扬我的道法。”听了龙潭禅师这些话,宣鉴就将《青龙疏抄》堆在法堂前面,举起火炬说:“穷究所有的玄言理论,仅如太空中的一根毫毛;研探世上的关键机要,只似万丈深壑中的一滴水。”宣鉴禅师说完这些话后,就把这堆书烧毁了[4]。
首先,宣鉴和尚挑了两筐子的佛经,却不知怎样回答一个卖饼子的老太婆所提出的问题,这是宣鉴的“不知”;也是叙事者的“不知”;当然也是读者的“不知”。其次,叙述者和读者都不理解和“不知”:为什么龙潭禅师在把灯烛递给宣鉴的瞬间,故意把灯烛吹灭?这师徒之间到底表达了什么思想意蕴?
这就是禅宗公案故事采取的“外视角”叙事所追求的叙事效应——云遮雾绕的“不知”效应。
最后,我们再看小说《红梦楼》第91回中“林黛玉、贾宝玉参禅”的故事:
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
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撅着嘴道:“讲来。”
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又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爱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
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
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
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
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
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
宝玉道:“有如三宝。”
黛玉听了这话,低头不语。[5]
这则“林黛玉与贾宝玉参禅”故事中,参禅的林黛玉和贾宝玉采取“借此而言彼”的象征、暗喻的手法,传情表意。他们俩人心有灵犀,心心相印,所以,非常清楚对方在“弦外之音”的话语中所表达的意思。在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对话中,没有一句谈情说爱的话语言辞,却没有一句不是深情的爱情表白。在作者的叙述中,读者是不知晓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真切思想的。
上列的五则故事的作者都是采取“单一”的、“外视角”的眼光去观察对象,并且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描述。它们共同追求的叙事效果都是“不知”。
这就是禅宗的话语特点——其目的在于故意采用“云遮雾绕”的话语,让人“不知”。禅宗“绕路说禅”的话语决定了禅宗“公案”叙事的特点——通过各种象征、暗喻、比喻手法,采取扑朔迷离的、似是而非的话语,故意营造神秘莫测的语境,让人捉摸不透,把握不住人物的思想意蕴。一句话,禅宗“公案”叙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叙事具有“不确定性”,二是追求叙事的“不可知”。
二、 小说《竹林中》和电影《罗生门》所演绎的禅宗故事的“多视角”叙事
禅宗“公案”故事叙事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两个特点,在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和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里得到了集中体现。
芥川龙之介是禅宗信徒。他运用佛教哲学“因缘和合”和“真理就是全体”的观念创作出了短篇小说《竹林中》。黑泽明把小说《竹林中》与作者另一篇小说《罗生门》加以拼接组合,改编成了电影《罗生门》。1950年上映后轰动世界,成为20世纪世界电影的经典。
人们在看了小说《竹林中》和电影《罗生门》之后,有种种猜测、推理和评论。人们不仅在人物的评论上差异很大,在思想观念和情感倾向上也无法取得统一,甚至连事件的真像和经过都难以认定,这是读者和观众最感困惑的地方。因此,人们一般都把小说《竹林中》和电影《罗生门》的叙事称之为“各说各话”的难解之谜。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取材于日本古代平安朝末期的民间传说故事集《今昔物语集》卷29中的两个故事:《在罗城门楼上发现死人的盗贼》和《携妻同赴丹波国的丈夫在大江山被绑》。
《罗城门》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盗贼来到战乱中的京都,他登上了罗城门。在城楼上,他窥见了一个白发的老妪正偷偷地从一个死去的妇人的脑袋上拔下一根根长发。这个盗贼看到老妪的怪异的行为而感到毛骨悚然。他持刀逼问老妪。老妪说:死去的这个妇人生前是她的主人,主人的长发可以做成假发卖钱,所以,她就拔下主人的长发去卖钱。这个盗贼听了老妪的坦白后,就毫不犹豫地剥下了死去的妇人和老妪身上的衣服,抢去了老妪拔下的死人的头发而逃走了[6]1165。
《丈夫被绑》故事讲的是:京城里的一位男子陪同妻子回波丹国娘家去。妻子骑着马,男子手持一张弓,身背了十来支箭,跟在马后前行。在路上,他们碰上了一个身挎大刀的剽悍汉子,便一同前行。汉子向这个丈夫炫耀自己宝贵的大刀,并提议用宝刀换这个丈夫的弓箭。这个丈夫欣然同意了。到了吃午餐的时候,这个汉子说,我们在大路边吃饭很不雅观,我们到树林中去吃饭吧!来到树林中,这个汉子趁男子把妻子抱下马来的时刻,就张开弓箭,对着这个丈夫厉声吼叫说:不许动!你若一动我就射死你!然后汉子逼迫夫妇俩走进密林中。汉子逼迫丈夫交出了身上的佩刀、匕首,就用绳索把丈夫紧捆在树干上。然后,汉子就动手强奸这个女人。女人挣扎不得,只好任汉子任意摆布,恣意轻薄。事后,这个汉子背上了弓箭、手提大刀,骑上了大马,临走前他对女人说:“我感到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实在无法压抑我的淫心。为了你,我饶他不死。为了快逃,我只好骑马走了!”汉子走后,女人在惊恐之余,暗自庆幸这个强盗还没有剥光自己的衣服,把衣服抢去。女人一边松开了丈夫的绳索,一边责骂丈夫无能。最后,夫妻俩只好步行回到波丹国去了[6]1171。
第一个故事中,作者描述了人性之恶的可怕。如果有的人抱着“人人都在作恶,我也不妨作恶”的信条,倘若人们要在犯罪或恶行上进行比赛,那就非常令人恐怖了。第二个故事描述了如果人们对恶人没有充分的认识,对恶行缺乏高度的提防,就要吃亏遭殃。两则故事原本是平安朝时期佛教徒用来教诲世人的“劝世良言”,有一定的哲理。
芥川龙之介把这两篇小说分别加以再创造,大大深化了原来故事的“劝世”思想。在小说《罗生门》中,芥川龙之介深刻揭示了人性之恶的心理原因:这就是人类的自私本性,人们总要为自己的恶行寻找依据和借口。那位家将认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要从无办法中找办法,便只好不择手段。”那位老妪也为自己拔下死去的女人的头发卖钱的肮脏行为辩护。老妪说:“拔死人头发,是不对,不过这儿这些死人,活着时也都是干这类营生的。这位我拔了她头发的女人,活着时就是把蛇肉切成一小段,晒干了当干鱼到兵营去卖的。……她干那营生也不坏,要不干就得饿死,反正是没有法干嘛。你当我干这坏事,我不干就得饿死,也是没法子呀!我跟她一样都没法子,大概她会原谅我的。”芥川龙之介赋予这篇小说的哲学寓意在于:人性的自私、贪欲是让人变得罪恶、丑恶的根源;如果人们仿效罪恶,鼓励罪恶,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罪恶,以致罪恶滔天。因此,作者的寓意是既不能仿效罪恶,更不能用罪恶去对付罪恶。
短篇小说《竹林中》描写了古代日本发生的一个抢劫、强奸、杀人案件。一个名叫多襄丸的江湖大盗在大路上窥见了武士妻子的美色而顿生淫心,他将武士和他的妻子诱骗到竹林中。他捆住了武士,强奸了武士的妻子。然后杀死了武士,并抢走了马匹和武器。武士的妻子径直逃跑掉了。后来,多襄丸被官府抓住。故事的叙述就是从审讯开始的,小说的结构也就以各位叙述者所讲述的情节来营构的。
其中,罪犯在官府的审讯中,对犯罪事实、犯罪经过有详尽的描述,并且承认自己强奸了武士的妻子,在决斗中杀死了武士。
武士的妻子被污辱后,逃到了寺庙里。她在寺庙中深深忏悔受到的污辱和自己犯下的罪行。然而,她在官府中所描述的事件经过同罪犯的描述大不相同,她忏悔自己竟然在丈夫的眼前被强盗强奸,她认为,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最大的耻辱。她受不了丈夫对她无比憎恶的眼光,因而在极度悲痛中用匕首杀死了丈夫。
死去的武士的灵魂借巫师之口,叙述了事件的经过。武士的叙述与罪犯和妻子所说的又不同。武士说:在妻子逃跑后,强盗割断了捆住他的绳索放了他。在强盗掠去马匹和武器离开后,武士深感自己受到的奇耻大辱,没脸再活在人间,就慨然用匕首自杀了。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从两个方面深化了原来的《丈夫被绑》的故事。
首先,作者把原来故事“劝世教益”的性质,改变为对“人性恶”的揭露。小说中通过不同的人物来揭露人的恶劣本性,来刻画人物的心理和行为。例如,强盗借着控诉官府的机会,来为自己抢劫、强奸、杀人的罪行辩护:“我杀人用的是腰上的大刀,可你们杀人,不用刀,用的是权,是钱,有时甚至几句假仁假义的话,就能要人的命。……要讲罪孽,到底谁个坏,是你们?还是我?鬼才知道!”
武士则是为了贪财而受骗,以至于妻子被强盗强奸,马匹被抢走,自己被杀。但是武士却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在他看来,妻子不仅失去了贞洁,而且居然从感情上也归顺了强盗,甚至鼓励强盗杀死自己的丈夫。武士声称,他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才自杀的,这是他最体面的结局。
武士的妻子是丈夫贪财欲望的直接受害者,是强盗所犯罪行的承受者。所以,她声称,由于内心中对丈夫的气愤和失望,以及遭受污辱后的悲哀和羞愧,不得不杀死丈夫。
有一个樵夫来到树林中的杀人现场时,杀人事件已经结束,凶手已逃离。樵夫因为自己贪小利而偷走了杀人现场的匕首而惹上了官司。他在官府供述时也说了谎:“没有看见刀子!”
在这个故事中,每一个人的陈述都是站在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利益的角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隐瞒和歪曲了事实。他们“各有异见,争论斗争,以如矛之口,互相刺击。”[7]最终,他们都堕入了虚假不实的叙事之中。可见,人的本性是自私而贪欲的,这是罪恶之源。这是佛教对于人性恶的根本判断。
其次,作者要说明的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正因为自私,才会有掩饰、隐瞒自己恶行的言行;也因此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了事实。由于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叙述都充满了自私的动机,都为了维护自己的虚荣心和利益,他们所陈述的都是虚假的谎言。谎言的聚集让人们无法获得事实的真相。佛教哲学说:“相由心生”、“心生万法”。在社会生活中,任何叙述都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利害性,这就是“主观的真实”、“片面的真实”。如果每一个人的叙述都是“主观的真实”的话,那么就不存在所谓客观的“真理”了。所以,尼采说历史“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以是小说《竹林中》的情节事件为主干,以小说《罗生门》中的个别情节和场景作为电影叙述的时代环境。
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中,增加了一个叙述者。这人是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的砍柴人。砍柴人说,武士的妻子在被凌辱后,强盗恳求她随他远走天涯。这女人却对丈夫和强盗说;“你们俩人中,必须死去一个!”她随即用匕首割断了捆住丈夫的绳索,让丈夫同强盗决斗。在决斗过程中,女人仓皇逃走了,她并不知道丈夫和强盗谁生谁死。最后,强盗在决斗中杀死了武士。由于砍柴人偷走了匕首,就使他在官府的呈堂供述中,不敢说明全部的事实真相,他的叙述中也存在着片面的“主观的真实”。
小说《竹林中》和电影《罗生门》的叙述方式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多个人拼凑而成的“多视角”叙述,也可以称之为“散点叙事视角”。每一个人都是用“单一”的“视角”观察事件,每一个都根据自己的“主观态度”来陈述事件经过。因此,每一个人的叙述,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甚至完全相反的一面。它们的陈述都是“主观叙述”,就像佛经中“瞎子摸象”中瞎子们各自不同的说法一样。
电影《罗生门》通过各个人物“不同视角”的叙述,这一悲剧性的事件大体上是清楚的:一个叫多襄丸的强盗在大路上,见到美丽的女人和她的丈夫一起赶路,顿时生起淫心。他欺骗武士,他们可以在树林中找寻到财宝而进入林中。强盗借机把武士捆在树上,然后奸污了武士的妻子,掠走了马匹和武器。最终,武士被杀死了,武士的妻子逃进了寺庙之后当了尼姑,强盗被抓住并受到审判。
多年来,人们受传统“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唯一”的思想观念限制,面对《竹林中》和《罗生门》的场景,总是执着于追寻“事实的真相”,总是认为这个故事中,“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并想通过“事实真相”去给故事或人物加载某些道德评价,力图在人物中区分出谁善谁恶、谁对谁错、谁高贵谁卑贱等等。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传统的“一元化真理观”所宣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佛教哲学及禅宗坚持的“不二之法”,后现代哲学的多元本质观所批判的正是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人类对外界的感知和印象永远都是主观的。主观性是人类认知的本性。由于人类所具有的强烈的主观性,甚至使我们经常出现“眼见并不为实”的错觉。例如,木棍在水中变弯曲;日常常见的种种魔术等等。20世纪西方的“实验心理学”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奥秘:任何叙述都是主观的叙述,都在某种程度上歪曲或改变了原来的事实。例如,实验证明:非常贫穷的孩子们描绘他所见到的“馅饼”和“金币”都比真实的“馅饼”和“金币”要大得多;处于极度惊恐中的人们所描述的暴徒往往比真实的罪犯高大得多!这就是心理学所揭示的“潜在的心理动机必然要影响人的行为和语言表述”的原理。
这说明,主观性的叙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真实。
在小说《竹林中》和电影《罗生门》的各种主观性的叙事中,同一个事件经过不同的人物的叙述,使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使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使人物的品性显得复杂、诡谲。这就是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在洞察到的“人的主观性叙述的非真实性”特征之后,所采用的“叙事技巧”。这种叙事技巧,被历史学界称之为“《罗生门》式的历史阐释方法”。这是指“同一个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的阐释”。而这些“不同的阐释”可以有着不同的“历史叙事”,可以生成不同的“历史故事”。这正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美学家克罗奇所说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刻内涵。
芥川龙之介和黑泽明所要表达的观念,就是“真理都是相对的”,“任何真理只是有限范围内的真理”;“没有绝对的、客观的真理,因缘和合才是事情的本真。”这就是佛学和禅学的真理观。也就是说,小说《竹林中》和电影《罗生门》通过运用“多视角”叙述,就是佛经“瞎子摸象”的现代版,颠覆了叙事文学中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