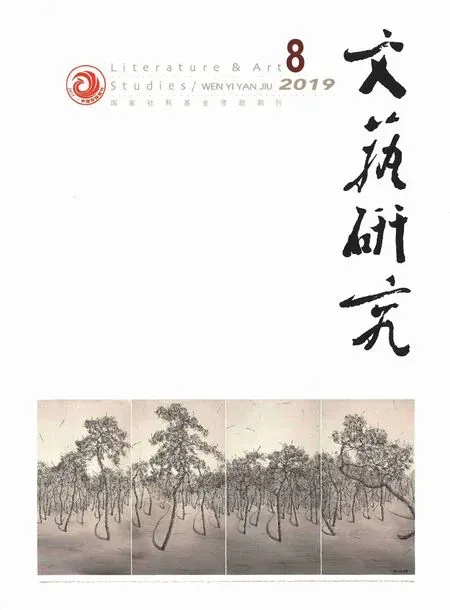“以射喻怨”与“诗可以怨”命题的意义生成
袁 劲
中国文论经典命题“诗可以怨”的题眼是“怨”字。因之,解诠“诗可以怨”命题离不开对“怨”的考察。鉴于“怨”是一种普遍而又潜藏着巨大能量的情感类型,先秦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将其纳入理论视野,遂形成诸子论“怨”的思想谱系。而“以射喻怨”①正是诸子论“怨”思潮中独具特色的一环。无论是孔子的“射有似乎君子”(《礼记·中庸》)②、墨子的“杜伯之鬼射周宣王”(《明鬼下》)③、孟子的“越人关弓而射之”(《告子下》)④、庄子的“游于羿之彀中”(《德充符》)⑤,还是孙膑的“弩之中彀,合于四”(《兵情》)⑥、韩非子的“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难三》)⑦,儒、道、墨、法、兵诸家均用射箭之喻来言说“怨”与“不怨”之理。在“以射喻怨”的总题下,学派的整体思想特色与学者的个人言说智慧如何一一呈现?“以射喻怨”作为公共知识话语的历史依据究竟何在?这一譬喻说理模式,与我们更为熟悉的“诗可以怨”命题又存在怎样的关联?本文将循此线索,勾连先秦两汉思想史中的“以射喻怨”与文论史上的“诗可以怨”,从而为考察“诗可以怨”命题找寻互文本,绘制“辅助线”。
一、从“越人关弓而射之”看孟子对“诗可以怨”命题的诠释
钱钟书曾站在比较诗学的立场上,较早梳理了中国文论及文化传统中的“诗可以怨”,称其为“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和“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⑧。此后,随着陆文虎《原“怨”——释钱钟书的〈诗可以怨〉》、周振甫《诗可以怨》、赵成林《“诗可以怨”源流》⑨等文章相继问世,中国文学批评史里“诗可以怨”命题的承衍线索日益清晰:自孔子在教学过程中提出“诗可以怨”(《阳货》)⑩命题而后,屈原“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⑪、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⑫、刘勰“蚌病成珠”(《才略》)⑬、钟嵘“离群托诗以怨”(《诗品序》)⑭、白居易“惟歌生民病”(《寄唐生》)⑮、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⑯、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⑰、李贽“不愤则不作”(《忠义水浒传序》)⑱、金圣叹“怨毒著书”(金批《水浒传》第十八回回首总批)⑲、黄宗羲“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后世哀伤、挽歌、谴谪、讽谕皆是也”(《汪扶晨诗序》)⑳、梁启超“熏、浸、刺、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㉑等等论说,共同勾勒出一条代不乏人的言说脉络。相较于上述贴近文学发生论、创作论、鉴赏论、文体论、功用论的相关表述,经学与子学视域中的“诗可以怨”诠释史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孟子·告子下》所载孟子与弟子公孙丑围绕着“《小弁》之怨”与“《凯风》何以不怨”的探讨便是典型一例: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㉒
在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里,这段师徒对话多被当作“以意逆志”的佐证材料,遂不在“诗可以怨”专题中论及㉓。以文论家为中心的顺叙书写,固然有利于凸显孟子文论思想的创新性和实践性,而对于“诗可以怨”接受史来说却缺失了重要一环。考虑到孔子只言“诗可以怨”而未论“诗为何可以怨”,于此语义空白,孟子师徒的对话实乃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文献可征的首次“完形填空”。
《论语·阳货》记载的孔子教导是一个反问句加祈使句:“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㉔考虑到孔子在更多情况下教授的是“不怨天,不尤人”(《宪问》)㉕、“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㉗,弟子们恐怕也会产生困惑——诗为何可以怨?诗如何怨?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怨?什么情况下又不可以怨?……倘若再结合《论语·里仁》中夫子所言“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㉘之“不怨”与《诗·小雅·小弁》中“何辜于天,我罪伊何”㉙之“怨”的尖锐对立,孔门弟子中好学如颜回、直爽如子路者,恐怕会忍不住提问。
相较于《论语》的戛然而止,《孟子·告子下》的多轮问答填补了这一语义空白。大致说来,孟子师徒对话的前半部分围绕着《小弁》之“怨”是否属于“小人之诗”展开,孟子以“亲亲”和“仁”释“怨”,捍卫了“诗可以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后半部分通过对“《凯风》何以不怨”的辨析,孟子又具体以“亲之过”是大是小来为“诗可以怨”确立必要的限度。置入文论史观之,孟子对“怨”之必要性及其限度的论说意义至少有三:
其一,接续孔子“诗可以怨”思想,倡导内心的“诚”而反对外在的“固”。相较于高叟“机械地传述孔子中和思想而丢掉了‘诗可以怨’的传统”㉚,孟子通过“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辨析了“可以怨”和“不可以怨”两种情况,捍卫了“怨”情流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所谓“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礼记·经解》)㉛,这对于纠正当时如高叟一般“固”守“不怨”“无怨”“远怨”主流论说,以致一味“温柔敦厚”而陷入“愚”者,无疑是必要且及时的。
其二,突破传统的“君子不怨”命题,标举“浩然之气”与“大丈夫”作为人格典范。“孟子那种善于养‘浩然之气’,并且能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大丈夫’与孔子心目中那种‘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君子’也有着很大区别。”㉜高叟之所以批评《小弁》为“小人之诗”,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怨亲”有违于《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㉝的顺从,乃至《礼记·内则》所要求的“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㉞。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㉟的关联,高叟们还由“君子不怨”反推出“怨即小人”的观念,视“怨诗”为“小人之诗”。与之相对,孟子言“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告子下》),正是张扬主体“浩然之气”的表现,亦与其从“道”不从“势”的“大丈夫”气概相一致。这对于后世文人敢于、继而善于写“怨”(甚至是“愤”和“怒”),对于中国悲怨、讽谕传统的兴盛,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三,在捍卫“诗可以怨”必要性的同时,又为“诗如何怨”设置必要的限度。在弟子的追问下,孟子区分了“《小弁》之怨”与“《凯风》何以不怨”,即君父有大的过错才“可以怨”,这种情况下的“不怨”反倒成了疏远;而当君父的过错不大时,再去“怨”便是不可取的过激反应。在中和思想的影响下,孟子将“怨”纳入“亲亲”和“仁”的正统框架,颇似刘安在《离骚传》中以“《小雅》怨诽而不乱”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担保㊱。孟子认为,“怨”是必要的,“诗可以怨”为“温柔敦厚而不愚”提供了保障;同时“怨”又是有限度的,毕竟“骂詈非诗”㊲。在“诗可以怨”的接受史上,有此补笔,才不至于矫枉过正。
孟子对“《小弁》,小人之诗”的驳斥,对“《凯风》何以不怨”的辨析,均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从修辞角度看,这多半要归功于“以射喻怨”的成功运用。分析“喻”的特质与功能,除了依据本体、喻体、喻词,明喻、暗喻、隐喻等现代语言学范式进行,还可由《说文解字》中“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㊳的释义来加深认识。“比,密也”的义训和“反从为比”的形训,是许慎在训诂层面对字义的说解。结合孟子的“以射喻怨”来看,它们又何尝不是对其修辞功用和运作原理的精当概括?
先看“比,密也”。这里的“密”取亲密义,指比喻具有密切联系本体与喻体、辅助认知的功用。在孟子用“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与“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的对比中,本体“怨”与喻体“越人/其兄关弓而射之”的匹配,能够拉近抽象事理与具体情境的距离,使“怨”与“不怨”的讨论语境化。不唯如此,“比,密也”还能由亲密更进一步而至细密、深密和精密。孟子指出,面对毫不相干的“越人”,即便是他要引弓射杀自己,也不会心生怨恨,故能从容劝导之;可一旦换成了有亲缘关系的“其兄”,便难免“言之迫切,出之以号泣,欲泣兄之必听”㊴。在这则解释复杂事理的说明性比喻中,两种“以射喻怨”揭示了人际亲疏对“怨”情生成的影响,可谓加深了认识。
再看“反从为比”。这里的“反”有打破常规之义,揭示比喻运作的深层机制。《说文解字·从部》云:“从,相听也。从二人。”㊵在今天看来,许慎由“二人为从”推导出“反从为比”,不符合古文字实情。甲骨文“比”字从二“匕”,此“匕”看似与“人”呈轴对称关系,实乃取跪拜之形而非侧立之体。当然,“反从为比”之“反”失之于形,却得之于义。在比喻修辞中,需要的不是常规的听从、跟随或一致,而是与之相反的陌生化与新奇感。此中奥妙,正如胡范铸所言:“‘从’意味着群体的习惯,对习常认识、日常视野、惯常用法(‘从’)的反拨,才是‘比’的生命。任何‘比喻’,只要一成立,便已经意味着‘反从’;而这日常思维习惯被猛烈突破而来的‘远距’的比喻,这种双倍的‘反比’,更是‘比’中之‘比’。”㊶关于此点,不妨比较孟子“以射喻怨”与同时期其他思想家的“近亲造怨”说。
兄弟反目、父子怨噪、慈母操箠,都属于“怨”的极端情况,因其反常而更能说明问题。《管子·形势》有言:“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㊷又曰:“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㊸这是具有道家“自然”“无为”色彩的情感发生说。《墨子·尚同上》云:“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亦有类似的说法:“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故父子或怨噪,取庸作者进美羹。”㊺墨子言父子离散、兄弟反目,是为了强调不能“尚同”的严重后果;韩非子取父子亲情与雇佣关系对比,则旨在揭示功利对亲情的胜出。多方比较,只有孟子以“仁”释“怨”,正面认肯了“怨”的正当性。借助“以射喻怨”中“比”的精密化与反常化,孟子在孔子更偏重于“怨而不怒”的主流言说以外,开启了文论史上重视“浩然正气”与“怨而怒”的另一脉㊻。
二、诸子论“怨”中的“以射喻怨”
在文论史上,孟子的“以射喻怨”有新意也有意义。不过,结合当时的文化语境来看,“越人/其兄关弓而射之”并非孤明先发,而是属于先秦两汉诸子“以射喻怨”思潮中的一环,在当时还拥有为数不少的互文本。
“怨”不只是个人心态的表征,还关乎世风民情。由此,“怨”之发生与因应也就自然进入先秦诸子的视野。诸子百家“遭直世变。本其所学,以求其病原,拟立方剂”㊼。面对群己关系中的“怨”,儒、道、墨、法、兵诸家皆予以不同层面的关注,并在其中寄托了“救世”或“治世”的主张。通观先秦两汉诸子论“怨”,可知其所思所言不仅是学者的个人智慧,还汇聚成学派的鲜明特色。大致说来,儒家将“不怨”的理想诉诸“仁义”,故有《论语·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㊽的反问。面对《老子》第七十九章“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㊾的难题,老庄以“自然”和“天道”彰显了“不必怨”的达观。墨家的“举公义,辟私怨”(《尚贤上》)㊿和法家的“私怨不入公门”(《外储说左下》)在“公—私”框架内或以“义”为准则,或以“法”规范之。兵家的智慧则表现为攻守转换中的于己“止怨”以“守气”和对敌“兴怨”以“攻心”。
若说“怨”所蕴藏的丰富意涵在儒家之“群”与“己”、道家之“天”与“人”、墨家之“兼”与“别”、法家之“法”与“情”、兵家之“令”与“心”等不同视域下,以及学派攻讦辩难的语境中得到充分彰显,那么,“以射喻怨”便是会通诸子论“怨”的一个整体视角。
先秦两汉之际,有作为君子礼乐展演的“射艺”,也有用于仇敌武力杀伐的“射术”。在礼乐文化的流风余韵下,射箭的结果是“发而能中”,还是“失诸正鹄”,成为儒道两家“以射喻怨”的焦点话题。《礼记·中庸》载孔子曾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孟子为之作注“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这是儒家倡导的自省。其内在理据是,把“发而不中”的结果进行内向归因,便可“不怨胜己者”。孔子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八佾》)的认识,孟子也以“射”为喻,申说智巧与圣力之异:“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万章下》)同样在谈到“不中”的问题时,《庄子·德充符》巧设寓言,通过身残却不怨天的申徒嘉阐明立场:“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这种“归于天命”代表了道家的态度。孔、孟、庄的三则譬喻均抓住射而不中的典型情境,以小见大,或放在“社会人”的范畴内强调“不应怨”,或置入更具超越性的“自然人”框架中来凸显“不必怨”。
墨、法、兵诸家也参与了这场“以射喻怨”的大讨论,与儒道两家相较,他们更关注仇怨射杀的因果与效果。《墨子·明鬼下》提到杜伯无罪受戮后“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这固然是为了“明鬼”,却也点出时人对“怨”与“报”的认识。《明鬼下》讲的是杜伯因“怨”而射杀周宣王,《墨子·非儒下》和《韩非子·难三》还进一步讨论了面对别人的射杀,是“接箭还射”,还是“揜函弗射”,抑或是“忘射钩之怨”的问题。墨子批评了儒家倡导的“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认为这将导致“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焉”。这是墨子对儒家“仁战”思想的批评,却也暗合了孔子对“以德报怨”的反思——“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换言之,在家国仇怨面前,战场上的“揜函弗射”无异于“以德报怨”,将导致是非紊乱、报应失衡,是不可取的。法家一面强调明公利而释私怨,称许“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难三》);一面又青睐射中目标的效果,故《商君书·外内》还有“赏多威严……以此遇敌,是以百石之弩射飘叶也,何不陷之有哉”的类比。与之相似,兵家的“弩之中彀,合于四”(《兵情》)同样关注军事战争的系统性,并发现君、将、兵、民之间“无怨”的“和气”,可凝聚成势如破竹的“锐气”。
先秦诸子勾连起行为之“射”与心理之“怨”,巧设譬喻,多方观照,既彰显出学派的理论特色,又寄托了学者“救世”或“治世”的智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救世”与“治世”不同,若说前者(以儒家为代表)仍寄希望于重振“礼乐刑政”和“王道政治”的传统,那么后者(以法家为代表)则走上了改弦更张的道路。不妨比较“救世者”孟子与“治世者”韩非子相似的两则“以射喻怨”:
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离娄下》)
解狐荐其雠于简主以为相,其雠以为且幸释己也,乃因往拜谢。狐乃引弓迎而射之,曰:“夫荐汝公也,以汝能当之也;夫雠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拥汝于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门。一曰:解狐举邢伯柳为上党守,柳往谢之,曰:“子释罪,敢不再拜。”曰:“举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外储说左下》)
在孟子和韩非子看来,庾公之斯和解狐均很好地处理了公与私的冲突。庾公之斯“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看重的是仁义,故象征性地去掉矢镞再弯弓射箭;解狐出于公心举荐仇人,却又对登门拜谢的仇人引弓欲射。前者不以“君事”废道义,是乱世中对“仁义”的可贵坚守;后者不因私怨废公事,则彰显了法家明辨公私背后的效力。在歆慕礼乐王道的“救世者”看来,弓弩不只是杀伐的利器,因为“器”上有“道”,“器”中藏“礼”。而在推崇霸道的“治世者”眼中,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善射”才是头等重要的。在“以射喻怨”的思潮下,以“善射”为标志的“射术”和“弓矢藏礼”所代表的“射艺”,构成先秦诸子不约而同却又同中有辨的两种阐释路向。
三、“射术”与“射艺”:“以射喻怨”的历史文化语境
诸子在“以射喻怨”上的会通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先秦两汉的历史文化语境。钱穆曾言:“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若要深入解诠“诗可以怨”命题,还原“以射喻怨”的历史文化语境,同样需要“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而所求者至少应包括先秦两汉征战频仍的客观现实和礼乐蜕变的思想状况。因之,作为器物的“弓弩”、用作杀伐的“射术”和象征礼仪的“射艺”三者交织,或投射为“以射喻怨”的现实底色,或沉淀为诸子论“怨”的思想背景。
频仍的战争以及弓弩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为先秦诸子留下深刻的记忆。“中国古吴越文化期之民族,在甚早时期,似已知制造弓矢及弋弩等器。”据中国古兵器研究者周纬推测,矢镞脱胎于矛头——华夏先民取铜或更早的蚌、骨、石之锐利者,“安长柄以刺者为矛,安半长柄以投掷者为标枪,安短柄以射者为箭”。作为先秦射远器的典型代表,弓弩与同一时期的长兵、短兵、防御武器相较,其优势在于增加对敌攻击的范围和减少己方受伤的可能。由是之故,先以弓弩远射,继之长兵冲锋、短兵杀敌,成为当时常用的战术。时至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太史公自序》)。在此形势下,如何改良弓矢与培养善射之士,自然会成为诸方势力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根据远近、攻守、火战、车战、野战等不同需要,时人注重研制不同类型的弓矢。《周礼·夏官司马》载“司弓矢”之职能曰:“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依郑玄注,弓之“枉矢”与弩之“契系矢”,“前于重,后微轻,行疾也”,因速度快而适合火射、守城与车战;弓之“杀矢”与弩之“鍭矢”,“前尤重,中深,而不可远”,其杀伤力大,故可用于近射和田猎;弓之“矰矢”与弩之“茀矢”,“前于重,又微轻,行不低也”,因其射程高而利于弋射。其名类愈多,分化愈细,愈可证明是时弓弩应用之广泛。
良弓需射手,怎样培养善射之士也成为先秦诸子关注的问题。《墨子·尚贤上》就旗帜鲜明地主张:“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若说“尚贤”属于直接的引导,《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载李悝断讼以射,则是通过间接的刺激:“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射也。”
随着“良弓”与“善射”成为战争纪实和社会的焦点话题,以“射”为喻(“以射喻怨”属于其中的一种)也就自然进入先秦两汉诸子的公共知识话语。兹举数例以为证: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管子·参患》)
赏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敌,是以百石之弩射飘叶也,何不陷之有哉?(《商君书·外内》)
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韩非子·用人》)
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无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吕氏春秋·孟春纪·本生》)
夫人之射也,不过百步,矢力尽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万里数,尧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尧之时,天地相近,不过百步,则尧射日,矢能及之;过百步,不能得也。(《论衡·感虚》)
除了充满剑拔弩张气息的“射术”,以儒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还关注到“以文化之”的“射艺”。在礼乐文化语境下,弓矢作为思想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载体,具有“辨尊卑、别贵贱、表祈祷、达礼敬、明约信、示敬奉、喻征伐、彰德行、抗天命、蕴威仪等丰富的礼仪内涵”。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先秦“弓矢藏礼”文化现象还涉及王官之学转向诸子之学过程中的六艺教学、选贤任能、游于艺等方面。
相较于战场上的“射术”,先秦士人的“射艺”已进入日常礼仪而更加生活化。“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正如《礼记·昏义》的概括,射礼与成年(冠)、婚姻(昏)、慎终追远(丧、祭)、出仕为官(朝、聘)、协和邻里(乡)一道,共同规范着周人的衣食住行。《论语·述而》将孔门师徒教学宗旨概括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于礼、乐、射、御、书、数之传统“六艺”,儒家推许的状态是“游”。如朱熹所言:“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射艺”在孔门教学中与“道”相通,是君子成人的必备素质。《论语·宪问》即言:“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儒家如此,道家亦然。《庄子》中多以“艺”论“道”,借谈“射艺”而阐发“忘我”“凝神”“合天”的道理。例如,《田子方》中“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的“不射之射”,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百发百中的“射之射”。
于此不妨作一小结,先秦诸子不约而同地“以射喻怨”,主要原因有两点。从喻体上看,无论是战争,还是个人的争执或竞技,“射”都会触及小到胜负、大至存亡的问题,因而极易产生怨恨。同时,与《韩非子·显学》所谓“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相似,结怨双方又会以弓弩作为报复的武器,这就涉及“关弓而射之”“接箭还射”“揜函弗射”“忘射钩之怨”“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等多种可能。再从比喻的使用者来看,“射”作为六艺教学、立身成人、选贤任能与协和乡里的重要内容,早已成为先秦士人的公共话题。于是,原本属于武力的“射”经过教育、礼仪、制度等不同层面的“文化”,很自然地进入诸子论“怨”的视野,最终形成先秦两汉“以射喻怨”的特定知识范畴。
四、作为“辅助线”的“以射喻怨”
通过对思想史传统中“以射喻怨”和社会史视野下“射术”与“射艺”的考察,可为文论史上的“诗可以怨”提供众多互文本。同时,沿着“以射喻怨”这条线索探幽穷赜,还能发掘出“怨”与“直”“和”“礼”“乐”“正”“让”“节”等传统文化范畴的呼应,进而串联起“诗可以怨”与“诗可以群”两大诗学命题。这条可以将分散现象集中化、把不规则论说有序化的线索,正像几何学中的“辅助线”,对中国文论研究的“解题”大有裨益。
那么,通过绘制“以射喻怨”这一在通行批评史教材中并不存在的“辅助线”,可以获得哪些新见呢?如前所述,在文本语境中,孟子以“越人/其兄关弓而射之”辨析“《小弁》之怨”和“《凯风》何以不怨”,既捍卫了“怨”情抒发的正当性,又为其设置必要的限度,从而奠定了中国文论中“怨而怒”与“骂詈非诗”的基础。在文化语境中,孔孟教导弟子的“诗可以怨”,本身就是“诗可以群”之“群居相切磋”的典范,而礼乐文化中的“射礼”更是处理“群”与“怨”关系时极具代表性的制度设计。换言之,“以射喻怨”既可“连点成线”,呈现“诗可以怨”与“诗可以群”两大文论命题的关联互动;又能作为“延长线”引出具有原型意义的“射礼”,从而为“诗可以怨”与“诗可以群”命题溯得礼乐文化之源。
“诗可以群”,孔安国称其为“群居相切磋”,朱熹解释为“和而不流”,两说分别着眼于诗的沟通思想、乐群和合属性。《论语》所载“子贡之悟切磋”和“子夏之悟礼后”便是师徒互相启发,实现意义增殖的“诗可以群”。孟子与公孙丑的问答亦属此列,如果没有公孙丑“《小弁》,小人之诗也”的提问和“《凯风》何以不怨”的追问,恐怕就不会引出孟子对“诗可以怨”的正名,以及对“可以怨”与“不可以怨”的具体辨析。一千年后的南朝,钟嵘《诗品序》有“离群托诗以怨”的概括,可视为“诗可以怨”命题的回响。以反题推之,“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似乎隐含“合群则不需托诗以怨”的意思。这也代表了“个人之发见”后南朝士人的认识。不过,在先秦礼乐文化语境中,偏于个体的“诗可以怨”与更具社会性的“诗可以群”并不冲突。
《礼记·乐记》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语境中的“不争”与“不怨”都是“群”的题中之义。傅道彬曾指出,返回周代乡里、乡人、乡乐的历史语境,并结合乡饮礼、乡射礼的具体制度,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诗可以群”命题的丰富内涵。顺此接着说,在乡饮、乡射礼制下观照“诗可以群”,还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隐藏其中的“诗可以怨”命题。《诗·小雅·楚茨》云:“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殽既将,莫怨具庆。”奏乐、肴馔与“莫怨具庆”的理据何在?细读《仪礼》中《乡射礼》和《大射》的记载,以及《礼记·射义》的相关阐发,可发现无论是王室之“大射”,还是乡民之“乡射”,这一群体性的礼乐展演都在积极地防范和疏导“怨”。该过程通过演奏《肆夏》即席、升歌《鹿鸣》燕宾、合乐《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蘋频》献宾、奏《驺虞》或《狸首》以节射、奏《陔》而送宾等一整套流程,彰显出“诗可以群”的礼乐盛况。
大致说来,“射礼”及与之相关的“燕礼”和“乡饮酒礼”在处理“群”与“争”(包括“怨”)之关系时,所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有三。
一曰“正”,即摆正自己的心志、形体和身份。《礼记·射义》谓:“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平心静气、形体端正、遵守规范才能命中目标。当然,射箭不单纯是技艺比拼,还有仪式展演的性质,所以“心平体正”其实兼具技术要领、经验总结与比德教化等多重内涵。《仪礼·大射》规定“公射大侯,大夫射参,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获”,《礼记·射义》亦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角度解释“大射”先行“燕礼”,“乡射礼”之前有“乡饮酒礼”。诸如此类的规定与设计,均出于归正伦理秩序和身份地位的考虑。
二曰“让”,恭敬揖让而不唯胜败是取。《礼记·射义》引孔子之语:“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借助“让”的改造,射箭争胜的功利色彩消退而“争也君子”的礼仪和“辞爵”“辞养”的德义增强。无论是宫廷“大射”,还是民间“乡射礼”,宾主赠答百“拜”不厌。不仅主宾、主人、大夫、众宾、司射、司马等皆需行礼,就连一耦(“射礼”搭档)之中的上射与下射也要彼此相揖。
三曰“节”,即射时配乐,或奏《狸首》,或演《驺虞》,以音乐节制射箭,“不鼓不释”(《仪礼·乡射礼》)。这种礼乐设计在“中的”之外另立“节奏”作为评价标准,从而兼顾识礼重文与尚武恃力。《狸首》已不可考,今本《诗·召南·驺虞》中所咏叹的“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其节奏从容舒缓,而非激烈亢进。郑玄注解天子之射以《驺虞》为节,也强调其并非赞美猎人善射,而是喻指“乐得贤者众多,叹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
通过内外规范,“射礼”用礼乐仪式展现了“君子之争”和“虽争不乱”的可能。《荀子·王制》谓“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以“射礼”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正是为了解决“争”的问题。胜者袒左袖、执张弓,负方穿上左袖、执弛弓、饮罚酒以示象征。故《礼记·射义》有言:“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在中和思想影响下,“无怨”与“可以怨”殊途而同归于“群”。“诗可以群”的规范与主张是从社会层面入手,实际上是将“无怨”的个体融入群体。孔子的“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孟子的“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都属于这一脉。与之相较,孔子的“以直报怨”(《宪问》)、“诗可以怨”(《阳货》)与孟子的“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告子下》)则属于借道“可以怨”而最终回归“可以群”的另一脉。
这是因为在以“群”化“怨”的同时,更具社会性的“群”还为偏于个体的“怨”保留了空间。“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孔子认为,“群居”只是形式,言行举止能否遵从仁义才更为重要。“群居”可能带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问题,也能够砥砺切磋、彼此启发而达成“礼后”(《八佾》)与“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的共识。这多半也是孔安国以“群居相切磋”注解“可以群”的用意——通过“相切磋”来标识群居形式之上的价值尺度。与孔安国注并称的是朱熹的“和而不流”,其论取自《礼记·中庸》的“君子和而不流”,又照应《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与“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之说。通观“群居相切磋”与“和而不流”,将不难发现前者主外在言行,后者重内在精神。两者结合,一方面申明“和”与“不争”的理想,从而实现“群”对“怨”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强调“不流”“不同”与“不党”,指出“群”与个体的独立性并不矛盾。
借由“诗可以群”的参照,“诗可以怨”还在情感流露的真实性以外,彰显出对价值与信念的可贵坚守。《易传·系辞下》“三陈九卦”章有“《困》以寡怨”说,大意是孔颖达解释的“遇困守节不移,不怨天不尤人”。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太史公取《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和“子路愠见”之事,就特意在中间加入“孔子讲诵弦歌不衰”的细节,强调“诗”对“君子固穷”品性的塑造。又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载,刘邦在垓下战胜项羽后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这种“不怨”需要定力。《论语·八佾》载孔子看到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僭越礼制,一边吟唱《雍》诗一边撤除祭品时,借诵《诗》“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来表达不满之情和讽刺之意。《论语·阳货》载,孔子托辞有疾避见孺悲,却又故意取瑟而歌,让使者知其并非真病。这种“怨”更需要魄力。所以,在“诗可以群”的映衬下,有魄力的“怨”与有定力的“不怨”同样难能可贵。所谓“诗可以怨”,还会超越情感层面“怨”与“不怨”,以及“怨而怒”与“怨而不怒”的形式区分,直指个体在困境中对坚定信念、独立人格、批判精神的葆有。
① “射”在先秦两汉有两解,本文讨论的是射箭,而非射覆。后者如《荀子·解蔽》所谓“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2页)。
③ 事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24—226页。
⑧ 钱钟书:《诗可以怨》,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⑨陆文虎:《原怨——释钱钟书的〈诗可以怨〉》,载《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3期;周振甫:《诗可以怨》,载《孔子研究》1993年第2期;赵成林:《“诗可以怨”源流》,载《中国韵文学刊》2001年第2期。
⑪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
⑬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9页。
⑭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⑮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8页。
⑯ 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0页。
⑰ 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3页。
⑱ 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8页。
⑲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03页。
⑳ 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58页。
㉑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352页。
㉓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即选录此章,并言:“孟子根据以意逆志的方法作了具体分析,认为作诗可以怨亲,也可以不怨亲,关键在于是否违背‘亲亲’‘仁’‘孝’等原则。”(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也指出孟子对《小弁》和《凯风》的评释兼用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两种方法(参见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8页)。
㉚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第119页。
㉜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㊱ 参见洪兴祖撰《楚辞补注》,第49页。
㊲ 古代文论家多反对诗文中的过激行为,如争执、攻讦、骂詈等,此即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所谓“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殆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
㊳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86页,第386页。
㊴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33页。
㊶ 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㊻ 参见刘文勇《价值理性与中国文论》,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54页。
㊼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5页。
㊾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