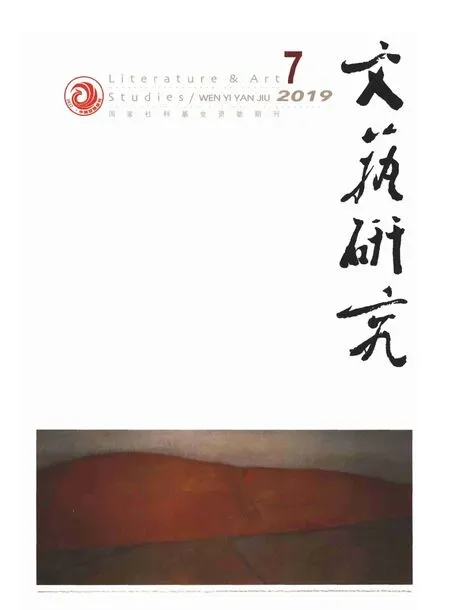好莱坞影响下中韩跨国商业电影的主体性问题
——张艺谋与奉俊昊的跨国大片比较
罗 婷
2002年《英雄》在本土和北美票房的大获成功燃起了中国电影、也燃起了张艺谋本人的一个热望——中国制造,出口全球。通过制作《金陵十三钗》(2011)和《长城》(2016),张艺谋试图以跨国商业大片来面向全球观众,他又一次成为中国电影“摸着石头过河”的先行者。再将目光转向近邻韩国。21世纪之交,韩国电影迅速崛起,并极具竞争力地抢占了东亚地区的电影市场。奉俊昊的跨国商业电影《雪国列车》(2013)和《玉子》(2017)更是以浓重的好莱坞色彩使这位韩国影人成为电影全球化时代新一轮跨国电影浪潮的弄潮儿。
以奉俊昊为代表的韩国电影从本土走向全球市场的过程与张艺谋所引领的中国电影跨国实践之间构成了颇有意味的镜像关系。本文将在检视中、韩电影“大片策略”的背景下,比较张艺谋与奉俊昊的跨国商业电影在类型征用、意识形态改写、主体建构等方面的共性与不同,透视民族电影的跨国电影实践在走向由好莱坞主导的全球市场中,是如何处理民族性与好莱坞的关系,又是如何在好莱坞的阴影下建构自身主体性的。
一、大片策略:好莱坞阴影下中、韩电影的自救与逆袭
不论是张艺谋还是奉俊昊,他们都是21世纪以来中、韩电影的“大片策略”及其跨国实践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所谓“大片”,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好莱坞,通常指情节简洁紧凑、易于理解,且具有大制作、大明星、大场面、多特效等特点的影片。这类影片通过大规模的市场营销和浸透式的上映带来高票房收入。作为产业及文本策略,大片成为好莱坞抢占全球电影市场的主要利器。
在韩国,好莱坞电影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然强势占据着其电影市场70%左右的份额。韩国电影市场的拐点出现在1999年。在叙事、场面、明星等诸多方面模仿好莱坞电影的韩国动作大片《生死谍变》,以六百四十多万的观影人次打破了《泰坦尼克号》之前创下的历史纪录。此后,一系列韩国本土大片如《共同警备区》(2000)、《实尾岛》(2003)、《太极旗飘扬》(2004)等接连告捷,使得韩国电影赢得了本土市场份额的50%以上。2006年,奉俊昊的大片《汉江怪物》成功地将当年本土电影市场份额史无前例地推高到64%。可以说,短短几年间,韩国电影在本土市场完成了对好莱坞的逆袭,大片也在韩国电影的创作格局中获得了主导地位。不过,高昂的制作投入和韩国有限的国内市场容量,使得拓展海外市场成为韩国大片继续生存的必然需求。尽管在以日本、中国为主的亚洲市场上韩国大片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好莱坞大片的物美价廉的“替代品”,然而,或许因其显著的民族主义内容,在进军欧、美市场时却未能如愿。
在中国,自1994年中国以分账制每年引进十部好莱坞大片到2001年入世后每年引进二十部,好莱坞大片以每年50%以上的票房占有率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格局。不过,2002年《英雄》的问世,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模式”,这一模式也成为迄今中国电影抗衡好莱坞的主要手段。之后出现的《十面埋伏》(2004)、《无极》(2005)、《夜宴》(2006)、《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投名状》(2007)、《集结号》(2007)等国产大片,开始进入票房排行榜的前列。到2005年,在国产大片的强力冲击下,国产电影票房占有率已达到68.5%,至今仍较稳定地保持着每年5—6成的市场份额。
在与好莱坞的关系上,21世纪以来中、韩两国电影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面对如何阻击好莱坞在本土市场的强势占领,中、韩电影都在世纪之交不约而同地借助于好莱坞的“大片策略”。尽管在投资成本、制作规模上中、韩两国的大片与平均成本超一亿美元的好莱坞大片有着相当的差距,但它们在确保本土电影票房的市场份额上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不同的是,韩国大片从一开始便有着浓重的好莱坞类型印记,以外来的形式承载着民族主义关切。韩国大片与好莱坞电影之间有着一种既整合又颠覆的“矛盾关系”①,这在奉俊昊的作品序列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与他的同龄人一样,青少年时期的奉俊昊通过驻韩美军的电视网络观看了大量的好莱坞影片,对好莱坞的类型电影语法熟稔于心。在《杀人回忆》(2003)、《母亲》(2009)等罪案悬疑片中,奉俊昊始终将对韩国社会的审视、批判与类型片结合在一起。他的大片《汉江怪物》尤其突出,影片一方面准确地运行了好莱坞怪兽片的类型公式:怪物出现→怪物作恶→人类设法斗怪→怪物被消灭或被驱逐;另一方面,本土身份与民族情感叙事强力地穿透了该片好莱坞类型的表皮和肌理,表层的斗怪故事之下是对导致怪兽出现的始作俑者美国以及对美国唯命是从的韩国政府的批判。
与韩国大片不同,张艺谋所引领的中国大片潮更明显地晕染了民族电影的底色和叙事传统。仅从武侠片、古装动作片是其中的主导类型来看,中国大片直接承接的是本土电影的谱系,我们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的《双旗镇刀客》(1991)、《东归英雄传》(1993)、《秦颂》(1996)、《荆轲刺秦王》(1998)等影片看到21世纪初国产大片的影子。可见,好莱坞对于当下中、韩民族电影的影响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与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便施行的“清除好莱坞”运动不无关系。正是在与好莱坞长久的隔绝中,以非商业类型片为导向构建的艺术教育环境培养了以张艺谋为代表的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艺术观念和趣味。张艺谋前期电影生涯中仅有一次算是对商业类型片的探索(《代号美洲豹》,1989),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尽管从类型角度来看《英雄》是一部武侠片,但“罗生门”式的现代主义多视点叙事以及延宕叙事的纯视觉机制的采用让这部影片显得颇为艺术化。《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古装动作片包裹着《雷雨》式内核的悲剧故事。可以说,国产大片在诞生之初的几年间(约2002—2006),其特点更多表现为对带有明显的艺术化表达倾向的民族类型——武侠功夫片的借用。
张艺谋、奉俊昊隔离与亲近好莱坞的殊异以及在创作中艺术片与类型片的分野所折射出的正是中、韩民族电影大片发展路径的微妙不同,但是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张艺谋与奉俊昊则不约而同地以跨国大片的制作方式瞄准了全球的电影市场。
二、从类型征用到意识形态改写:白人拯救、女性身份与东西方政治
类型电影在重复性与变异性、固定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平衡使其成为跨国流通的理想载体,同时也是好莱坞全球统治力确立所依靠的重要的艺术方法和市场策略。对于民族电影的跨国商业实践来说,类型电影目前看来依然是抢占全球商业电影市场的合理路径。
在奇观式的武侠功夫片热潮过后,张艺谋显然是想借助典型的好莱坞“重工业”类型片——战争片与怪兽片——重返北美市场,赢得更广大的全球观众群体。《金陵十三钗》的投资据说高达9400万美元,是当时成本最高的中国电影。影片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故事讲述了假扮为神父的美国人约翰,将12个风尘女子以及一个教堂男管事伪装成女学生,赴日本军队的死亡之约,同时将真正的女学生安全地送出了南京城。似乎是为了彰显影片作为好莱坞战争片的类型属性,《金陵十三钗》在诸多方面凸显了自身与好莱坞知名大片导演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之间的渊源关系。二者同属“二战”战争片,共有人道主义的拯救主题;张艺谋聘请了负责《拯救大兵瑞恩》的特效团队操刀该片的战争场面;无法仅仅视为巧合的是,两部影片的男主角竟然都叫约翰·米勒。不过,周学麟在比较了《金陵十三钗》与《拯救大兵瑞恩》后发现,在更为核心的叙事、场景、情节设置和视觉语言等方面,这两部影片有着本质的不同:《拯救大兵瑞恩》严格遵循传统好莱坞类型片叙事上的“因果律”,并一一对应贝辛格所提出的“二战”战争片的16条标准情节元素,以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清晰地讲述一个营救故事;《金陵十三钗》在镜头语言上则显得更为风格化、抒情化,更倾向于表现主义式地呈现人物、场面的壮烈及美感,可以说,艺术“景观”才是张艺谋的心之所系②。由此,《金陵十三钗》应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产大制作电影的艺术化的影像机制和好莱坞类型的有限结合。
在艺术电影与类型片结合的表相之下,不少论者都揭示了潜在于《金陵十三钗》中的“白人拯救”叙事。作为一个主要发生在教堂里的故事,假扮神父的白人约翰同时是现实与象征意义上“救世主”,他完成的是一次双重救赎,不仅在现实层面上营救了教会女学生,而且在道德层面上救赎了秦淮河妓女——以高超的化妆术使她们重返“纯洁”的处子状态,安排她们替年轻一代从容赴死。虽然影片中也出现了某种意义上中国人自己的协助拯救——“十三钗”主动的自我牺牲才使得美国人最后的拯救成为可能,不过,这样的设置并未使《金陵十三钗》突破“白人拯救”的叙事框架。马修·休希(Matthew Hughey)在分析当代好莱坞电影(1997—2009)中出现的一系列黑人形象时发现,黑人角色常以底层的形象出现,他们的重要使命是帮助失落的白人恢复道德的纯洁与正常的生活。黑人在完成这样的使命后,通常会以各种方式“消失”(离开或死亡),以此来表明他们在情节设置中的辅助位置。这种对于种族间友好和合作关系的描绘,虽然巧妙地避免了公然的白人至上主义的渲染,但是他们依赖的仍旧是白人家长式的控制以及黑人刻板式的顺从逻辑③。《金陵十三钗》(还有之后《长城》)里的人物与情节设置几乎就是对休希所描述的修正了的好莱坞“白人拯救”叙事的移植。当然,《金陵十三钗》中“白人拯救”成为主导叙事,这不能仅从西方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施行的人道主义救援的史实来加以解释④。其实,“白人(男性)拯救”叙事曾出现在一系列传统好莱坞电影的中国想象中,从《中国少女》(1942)、《中国门》(1957)到《苏丝黄的世界》(1960)、《大班》(1986),概莫能外。说《金陵十三钗》所透露出来的“白人拯救”神话是一种历史想象的延续和好莱坞叙事逻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为过。
不过,除了“白人拯救”叙事,《金陵十三钗》更凸显了一个中国古老的文艺主题——女性的牺牲。在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个主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被压迫与被牺牲的女性成为孱弱国族的直接象征。与这样的女性形象一同出现的是无力的男性形象,是被西方阉割的女性化男性。苏珊·布劳内尔(Susan Brownell)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作品反复出现的还是男性无法带领女性步入现代化这样的主题。她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借用的是受苦的、牺牲的女性形象,但它事实上完全是关于男性的,女性受苦也是因为男性无力纠正他们的女人给他们带来的不公。”⑤在20世纪的不同阶段,造成男性无力的原因依次是殖民主义、国家父权制以及当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带着这样的视角审视《金陵十三钗》这部关于国族危难的影片,我们发现影片中的中国男性或“消失”或“转换”,始终处于“缺席”的状态:国军李教官在战斗中牺牲,书娟的父亲孟先生因汉奸身份而处于一种“去势”状态,教堂管事陈乔治则由约翰的化妆术完成了“男变女”⑥。白人约翰成了影片中唯一的男性,他完成了从被迫扮演的假神父到积极投入营救的真神“父”的转变,并带领女学生们成功地逃出了南京城。正如贺桂梅指出的,约翰这一角色显得颇为暧昧:“他以某种精神之‘父’的形象植入影片关于中国人的国族想象之中。”⑦是否可以更直接地说,《金陵十三钗》为缺席的中国男性构建了想象中的替代者——约翰,曾经的西方帝国主义如今成为拯救国族之“父”。在这个意义上,约翰也成为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电影语境中好莱坞的绝佳化身。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全球体系的十年,新自由主义塑造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也重塑着中国在这一秩序中的自我定位和认知。中国电影中的西方人与中国人、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无疑深植于这种秩序以及自我认知中,是对当代全球文化秩序中权力关系的投射。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以及奥斯卡奖所构成的文化政治又是这种全球秩序具体而微的体现。《金陵十三钗》邀请好莱坞知名男星出演主角,在北美圣诞节档上映,制片方甚至在上映前便声称将申报角逐奥斯卡所有的单项奖,这些都显示出制片方是在打造一种等量齐观的“好莱坞商品”。从张艺谋“武侠三部曲”作为奥斯卡“外语片”到《金陵十三钗》试图成为“好莱坞电影”而角逐奥斯卡单项奖,这个由“外”而“内”姿态的转变也是中国大片接受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等级关系并将其文化逻辑内化的过程。
然而,“白人拯救”叙事主导下的消费人类灾难中情色与暴力的故事,放置在今天的好莱坞看起来也颇有些“政治不正确”,这或许是《金陵十三钗》在北美市场折戟沉沙的原因之一。不过,张艺谋并未放弃他的好莱坞之路,他接受邀请,执导了有着突出的好莱坞大片“血统”的《长城》。《长城》由中、美共同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而且与《金陵十三钗》改编自华裔作家严歌苓的小说不同,《长城》的剧本出自好莱坞六位知名编剧之手,并由张艺谋做出修改;作为怪兽电影,其特效与道具由业界顶级的工业光魔(ILM)与维塔公司(Weta Workshop)制作;影片邀请了好莱坞一线男星马特·达蒙出演,英文对话比例从《金陵十三钗》的40%上升到了该片的80%;当影片于2017年2月在北美上映时,更是以3326块银幕的好莱坞大片级规模开画。
《长城》的故事发生在时间模糊的古代中国,一伙来自欧洲的雇佣兵到中国寻找黑火药,其中的威廉·加林逐渐为驻守在长城上的中国军队勇敢无私的精神以及保卫家国的情怀所折服,他帮助女将军林梅统领中国军队打退了怪兽饕餮。这看起来是个典型的好莱坞式“打怪”故事。从文化症候角度看,怪兽片中的怪兽通常反映了特定时代或社会的潜在焦虑。不论是20世纪50年代怪兽片如好莱坞的《原子怪兽》(1953)、《X放射线》(1954),日本的《哥斯拉》(1954)中所折射的“冷战”时期对于核爆的普遍恐惧,还是1986年的《异形2》对于苏联式集体主义的隐晦暗喻,这些影片都通过对怪兽起源的探寻、对怪兽活动的展示,将现实的焦虑具象化并加以释放。对于《长城》中的怪兽形象,张艺谋将其设置为意喻贪婪的中国古代神兽饕餮,不过,对于饕餮的缘起,剧情仅以史料记载的信息——上天为惩罚古代一位贪婪的皇帝而降下饕餮——简单带过。事实上,《长城》中饕餮所隐喻的贪婪与对无度皇权的批判无涉,而是更多地指向西方雇佣兵试图盗取黑火药的贪念——一种西方对东方的掠夺欲望。不过,故事中的西方人由于加入了中国军队打退饕餮的战斗,象征性地完成了与异类(怪兽)的区隔、与同类(中国人)的认同。因此,与其说《长城》是一个关注异类和人类之间对立、冲突的故事,不如说是在异类出现的危机下“我们”是否为“同类”的故事。“我们是否一样”是影片中串联起男女主人公关系的核心问题。
正是由于《长城》着力于完成认同,其影像呈现的中心不再是怪兽片类型惯例中的“毁灭美学”。苏珊·桑塔格曾在《灾难的想象》中指出,包括了怪兽片在内的科幻电影的本质不是关于科技,而是关于灾难。科幻电影关切的是毁灭的美学,是在毁灭的创造和混乱的制造中发现独特的美。一部出色的科幻电影的精髓正在于毁灭的意象中⑧。原子怪兽在曼哈顿横冲直撞,金刚爬上帝国大厦与战机对抗,哥斯拉从海上闯入东京城肆意破坏,知名城市地标被怪兽轻而易举摧毁,人群四散逃窜,高楼倾圮崩塌,可以说,正是毁灭美学赋形于怪兽电影,毁灭的过程正是恐惧与焦虑被唤醒又被极大释放的过程。反观《长城》,除了在长城脚下挖了条通向京城的暗道,饕餮并未给长城造成实质破坏。皇宫即使被密密麻麻的饕餮爬得水泄不通,宫廷建筑也没有被大规模毁坏。无怪乎,有论者注意到张艺谋甚至没有给以贪食人命见长的饕餮几个肆虐都城、吞噬百姓的镜头⑨。在科幻片或怪兽片的类型传统中,与视觉层面的“毁灭美学”一致的是其精神内核上对“科技的怀疑”⑩。自有怪物诞生的科幻电影作品《弗兰肯斯坦》(1910)始,不论是制造怪兽的核试验、化学品的危害,还是消灭怪兽过程中对科学手段的审慎或嘲讽,对科技的深度怀疑总是若隐若现地贯穿其中。这在之前日本的《哥斯拉》、韩国的《汉江怪物》等东亚怪兽片中皆已有所表现。反观《长城》,黑火药、磁铁、热气球等古代“前沿科技”纷纷亮相。《长城》背离“毁灭美学”,成为一场幻想中展示古代中国军事与科技力量的嘉年华。这种对怪兽片类型的反转恰恰是影片“认同政治”的重要一环。张艺谋试图将处于危机中的国族从《金陵十三钗》中作为被拯救的客体转而打造成《长城》中被认同的主体,影像文本内意识形态的转变呼应着文本外的张艺谋在商业电影的全球政治中与好莱坞的暧昧关系:借用好莱坞类型试图确立主体意识,却又无法跳脱“我们是否为同类人”的焦虑,而只有通过与他者的镜像关系才能获得自我的确立。因而,我们看到,影片最终指向的无非是旧有秩序(帝制)的恢复。《长城》充满了对东方的肯定与赞美,却仍然无法逃逸出对于文化的刻板印象——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东方的集体主义以及白人男性与东方女性之间关系所映射出的文化与国族的寓言。张艺谋竭力避免重蹈覆辙,将《金陵十三钗》中的异国情爱恋人转而设置为《长城》里惺惺相惜、共同抗敌的战友,但对于依旧堕入这种二元逻辑的作品来说,这种修正在更多意义上反倒成为一种现实和文化中的幻象。对于影片所暗含的对中国与北美这两大世界电影票仓的双重献媚,市场也并未买账。
与张艺谋相似,奉俊昊的《雪国列车》《玉子》以其英文对话、美国明星主导的阵容彰显着进军全球市场的野心。《雪国列车》的剧本由奉俊昊改编自法国同名漫画,投资约四千万美元,是彼时韩国影史上投资最大的影片。《雪国列车》有着明显的好莱坞“面孔”,由影星克里斯·埃文斯与蒂尔达·斯文顿领衔主演,特效由曾制作过《复仇者联盟》等大片的Scanline VFX公司负责,讲述了一个好莱坞热衷表现的反乌托邦故事:在地球发生极寒灾难之后的2031年,一列载着幸存下来的人类的环球行驶的火车上,下等车厢的乘客试图以暴力革命推翻上等车厢的统治。这是一个有着全球化背景的人类寓言——全球气候灾害、环球旅行、不同国别的各色人种生活在密闭空间。因而,《雪国列车》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全球语境中的东西方关系、白人与其他种族的关系等问题。《雪国列车》的“革命”故事饶有兴味。当下等车厢的底层民众在白人男子柯蒂斯的带领下以巨大的牺牲攻入了头节车厢、柯蒂斯正要改朝换代之际,却发现整场“革命”只不过是火车统治者威尔福德与底层的精神领袖吉列姆之间早有的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适当的暴力革命“保持火车人口生态”,柯蒂斯的反叛也成为了该计划的一部分。这是好莱坞科幻片中典型的“后末世”叙事,也是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统治力和封闭性的言说。《雪国列车》中作为反叛者的白人男性也只是对火车生存体系做出有限修正而非反抗体系本身,深植于好莱坞类型中的“白人拯救”神话不再。韩国人、火车安全设计工程师南宫民秀,在火车引擎室边上炸开了一扇打破旧体系、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南宫的女儿尤娜,类似在革命叙事中通常待拯救或被忽视的少数族裔青少年女性形象(如《金陵十三钗》中的女学生),与她的父亲一起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影片的最后,尤娜比白人男性领袖柯蒂斯更为决绝地对抗列车系统的罪恶,带着黑人小孩逃出了爆炸的列车,走向了已显露出一丝生机的冰雪世界。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结尾。《雪国列车》完全拒绝了“白人拯救”叙事,挑战了好莱坞类型模式中对于种族和性别身份的刻板呈现,也对资本主义体系及其自我修复机制进行了深刻批判。《雪国列车》的结局不再是混乱的平息与原有秩序的恢复,而是一个人类社会新纪元的可能出现。
《玉子》没有《雪国列车》对于突破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明朗基调,但它依然以改写好莱坞类型的方式去魅“白人拯救”神话,打破了对资本主义的幼稚幻想。在《玉子》中,韩国少女美子和爷爷在大山里为跨国生物寡头米兰达公司养大了一头转基因猪——玉子。米兰达公司认为玉子是全球投放的品质最佳的种猪,于是欲将玉子送往美国总部进行大肆宣传。美子不愿玉子被带走,便与一个西方动物保护组织展开了一场营救玉子的行动。作为奇幻冒险类影片,《玉子》的类型起源可追溯到1933年的《金刚》,定型于40年代的《巨猩乔扬》。这类好莱坞影片有着稳定的类型模式:白人女性+巨兽的组合,从异域来到西方大都市经历了一系列冒险,结局是巨兽或死亡或重返异域。从异域到西方文明都市的空间位移使得这一类型具有了明显的跨文化属性。以《金刚》为例,辛西娅·埃尔布(Cynthia Erb)认为“《金刚》的文化价值源于它作为大众流行文化对民族志式的遭遇或是第一与第三世界接触的戏剧性呈现”⑪。白人女性代表着西方文明,是欲望的对象,而像金刚之类的巨兽“其本身巨大的杂交性承载着大部分西方思想中的二元结构特征——东方/西方,黑人/白人,女性/男性,原始/现代”⑫。《玉子》借用这一类型模式,同时它的改写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主体+异域他者”的组合被异域文化所代替,异域文化不再是充满威胁的巨兽,而是(有色人种)少女+(人畜无害的)母猪。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的跨文化电影中通常被情欲化的亚洲女性(如《金陵十三钗》中的玉墨等)不同,不论是《雪国列车》中的尤娜,还是《玉子》中的美子,都被设定为未成年少女形象,有着果决、行动力强等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男性才有的特质。不同于《巨猩乔扬》中白人女性协助猩猩回到非洲丛林式的拯救模式,《玉子》中美子营救玉子的行动是一场从资本主义世界的逃逸,而作为当代西方文明化身的动物保护组织因其对抗中的天真与无力也在影片中被善意地嘲讽。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的资本主义,传统的或修正的,严苛的或温情的,其不变的只有金钱法则,而美子正是在洞悉了这一法则之后,悖论式地用一只金猪赎回了屠宰场里的玉子。《玉子》含而不露地暗示着,人类世界已不存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世外之地,纯真少女和可爱动物间的真挚情感则是对世外桃源必然逝去的童话式挽歌。
《雪国列车》和《玉子》都明显地借用了好莱坞电影的类型配方,然而这种借用又暗藏玄机。通过对类型元素的置换和重新配置,两部影片不仅重估并挑战了植根于类型系统的美国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而且暗度陈仓地批判了好莱坞全球垄断所依赖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三、主体性构建:全球语言与民族符号使用中的分野
制作跨国商业大片,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是如何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以及全球(尤其是英语)观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张艺谋与奉俊昊的不同立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们各自影片对于语言的使用上。对于追求全球文化商品属性的大片来说,英语作为对话语言可以说是先决条件,这与好莱坞电影长久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英语对话占到近一半比例的《金陵十三钗》中,为了让中国人与美国人约翰的沟通变得“自然化”,影片将女学生、陈乔治、玉墨设置为受过教会教育因而英语交流无障碍,汉奸孟先生、日军将领也展现了流利的英语。正如有论者发现的,“影片每一处剧力的转折,都靠英文在起承转合,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剧情,冲决矛盾”⑬。事实上,《金陵十三钗》隐秘地将英语表达与阶级身份相勾连,良好的英语表达意味着良好的出身与教养,妓女中唯一会英语的玉墨在影片后半段道出自己的前史——作为曾经的教会学生,她的英语是班里最好的,这个细节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洗刷”了玉墨作为妓女的身份“污点”,将她归入了更体面的社会阶层。《金陵十三钗》中,被“白人拯救”的叙事如此紧密地与是否掌握通往西方文明的钥匙——英语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只有会英语,从而进入“父”秩序之象征界的角色,才能真正被“听到”、被拯救。充满隐喻意味的是,临近影片结尾处,妓女“小蚊子”不愿假扮女学生随日本人走,她以南京方言发出了拒绝赴宴的呼喊:“我不是女学生!我不去!”结局却是被压制、被拒绝,最终被约翰顺势推上日本军车。上帝的福音似乎是用英语说出的。为英语交流扫除一切剧情障碍的设置,象征性地标识了东西方文化的等级秩序作为《金陵十三钗》的意识形态肌理,也与文本之外好莱坞所确立的全球秩序遥相呼应。到了《长城》,80%的英语对话终于使其脱离了好莱坞“外语片”的身份,而张艺谋如何处理80%英语和20%汉语的兼容则是电影跨文化交流的症候式问题。有趣的是,让古代中国人说英语对于张艺谋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影片交代了女将军林梅的英语乃一位假扮传教士的西方人所授,至于另一个角色王军师为何会说英语则语焉不详。对于一部致力于表现“我们是同类人”的影片来说,张艺谋显然不想让语言不通成为问题。然而,在大众文化产品中,行一切方便让来自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显得交流顺畅、毫无障碍,这本身即构成问题。相比之下,奉俊昊并不刻意消弭不同种族、信仰、语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不回避跨文化交流中的沟通不畅及互相理解之困难,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语言不通在《雪国列车》和《玉子》中均成为影响故事走向的重要因素。
《雪国列车》的英语对话约占到90%,但这并不意味着奉俊昊对英语作为主导语言无条件的接受。在影片的前四分之一,火车作为幸存的人类已经生活了十八年的唯一空间,其“官方语言”显然是英语,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不论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均操一口流利英语。对于这种设定,作为观众,似乎觉得天经地义,毕竟在现实语境中,英语确乎享有“全球语言”的地位。不过,当反叛者将南宫民秀从单人监狱中救出时,南宫的一口韩语以及翻译机的使用突然为车厢的同质世界打开了异质的文化空间。南宫通过翻译机首先纠正了白人对他名字的错误认知和发音。不过,翻译机无法翻译出他话中附带的粗口——“您所使用的词语不能识别,请使用正确的词汇。”这个戏谑的情节暗示并强调了英语及其代表的文化与其他语言及其所属的文化之间事实上并不具备必然的通约性,“我们不一样”是其中的潜台词,南宫“正名”的举动更像是象征性地通过特定语言来宣告并强调自我的主体身份与文化的多元,从而抵制单一、同质的文化诉求。韩语的使用打破了英语作为一种(好莱坞类型片的)常态的语言环境。英语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并非理所当然,它与好莱坞的“白人拯救”叙事一样是一种文化霸权的建构。语言不同的背后是思维的差异,与柯蒂斯试图在体系内部进行革命不同,南宫看到了打破车厢体系、进入更大世界的可能。在影片高潮处,南宫与柯蒂斯通过翻译机进行的一番无法真正沟通的对话,正是这种思维差异的体现,而故事的结局恰恰证明南宫作为(语言、文化)体系的异质分子所提供的另类视角成为拯救人类社会的关键。
奉俊昊在语言上的用心之处远不止于此,《雪国列车》在美国上映时,奉俊昊有意不为影片的非英语对白配上字幕,也就是说,南宫和尤娜之间的虽不多却对情节推进举足轻重的对话,对于英语观众来说完全是不可知的。由此,与影片中说英语的角色相似,影片同样将英语观众放置在了由于言语不通而无法完全了解关键线索(比如,南宫通过一架坠毁的直升机被雪掩埋的体积的变化,判断出火车外的冰雪世界已经开始消融)的懵懂境地,语言的理解障碍会引导长期处于(好莱坞电影所提供的)母语舒适区的英语观众突然注意到存在英语之外的(有时甚或是无法翻译的)文化和文本世界的事实,从而意识到他们所不熟悉的、异质的语言与文化对理解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同样不可或缺⑭。文化是一组隐藏的假设,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承载体。多数时候,特定文化中的人们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属于某种文化,但当这些隐藏的假设受到挑战时,人们便会经历一种模糊的不安。正是在英语电影中以外语隐藏关键信息这样颇具挑战的方式,奉俊昊在文本内外均颠覆了世界秩序中支配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等级秩序,也打破了英语作为支配性的全球语言和其他地方语言之间的文化等级。当《雪国列车》2014年在北美上映时,负责发行的韦恩斯坦公司要求奉俊昊删除主角说韩语而没有英语翻译的片段,遭到奉俊昊的坚决拒绝。在2017年的《玉子》中,奉俊昊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在继续,英语和其他语言间的沟壑依然被刻意强调,英语与韩语间的语言不通在剧情推进中仍起着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玉子两次从美子身边被带离,皆因美子不懂英语而被蒙骗。到了影片的高潮处,当美子面对即将被宰杀的玉子、第一次以初学的英语喊出了“我要买玉子,活的”时,美子最终明白了,要想拯救玉子,就必须以资本主义的话语(英语)和方式进行。语言霸权和经济霸权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玉子》所呈现的既是对当下现实中基于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准确勾勒,又可以视作奉俊昊对于跨国电影创作的一种自况。
显然,张艺谋与奉俊昊在对待西方强势文化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周蕾在分析张艺谋的电影《菊豆》(1990)时,曾以影片中天青偷看菊豆洗澡、菊豆却毫不回避地展示自己的伤疤这一场景为例来揭示张艺谋电影与西方之眼的关系。她说:“转过身来的菊豆将自己‘引用’成物恋化了的女人,并向她的偷窥者展览她承负的疤痕和伤痛,这一民族志接受东方主义的历史事实,但却通过上演和滑稽模仿东方主义的视觉性政治来批判(即‘评估’)它。以其自我臣属化、自我异国情调化的视觉姿态,东方人的东方主义首先是一种示威——一种策略的展示。”⑮如果说在《菊豆》中菊豆将自我“引用”为物恋化的女人——在“客体”的位置上戏仿了东、西方之间的视觉政治,从而对这一视觉关系形成了挑衅甚或是某种程度上的颠覆的话,那么到了《金陵十三钗》,影片将约翰、玉墨、书娟这三人的关系做了颇具精神分析意味的呈现:玉墨曾是书娟般“纯洁”的教会女学生,书娟对玉墨的窥视显示其潜意识里渴望成为玉墨般成熟的女性,以她们共同渴望(崇拜)的男性对象约翰为中介,二者构成了一个互补的客体。客体的策略性示威与挑衅性展示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模仿主体建构的“表演”⑯:假扮女学生的“十三钗”在赴日本人的死亡之约后未有下文,而在影片中真正完成“表演”的“主体”只有约翰——在对客体的双重拯救中实现了从假神父到真神“父”的转换。在文本内,影片通过作为主角的美国人对“主体”的“表演”来确立其主体位置;在文本外,《金陵十三钗》则通过对好莱坞类型和白人拯救叙事的移植,模仿了在全球体系的等级关系中好莱坞电影的主体性。在《金陵十三钗》与《长城》中,危难中的国族,不论是作为被拯救的对象还是作为被认同的对象,都呈现出自我客体化的东方欲与西方合一或同一的渴望——玉墨对约翰说“带我回家”⑰,林梅对威廉说“我们是同类人”⑱。这种渴望,与霍米·巴巴所讨论的被殖民者渴望变得和殖民者一样的心态或许别无二致。
张艺谋的两部跨国大片有着对于民族元素的刻意强调,国族历史、服饰、建筑、科技在影片中比比皆是。《长城》对于民族符号的赞美式呈现甚至打破了类型叙事的惯例,充溢《长城》的是文化本质主义式的“民族性”。《雪国列车》和《玉子》中虽有韩国人及韩语、韩服等民族元素,但更多是作为全球秩序中边缘的身份象征出现。《玉子》更是反讽地揭示了民族符号使用背后所暗藏的文化政治——作为一种宣传策略,跨国资本巨头米兰达公司在安排美子和玉子重聚的公众见面会上,特意让美子穿上了此前她在韩国本土都不曾穿过的韩服,以彰显她的异文化身份——原本的文化主体成为被资本消费的符号化客体,跨文化传播中的“差异化”策略在此以戏仿的方式被解构。
张艺谋与奉俊昊在处理民族符号时的不同,事实上折射出的是在跨国电影制作与传播中对于民族性及其作用的不同理解和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讨论,将思想史对于“民族”或“国族”的认知从民族是什么转向了对于民族的想象是如何形成的,这意味着“民族”“民族性”“民族传统”等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建构⑲。对于民族性的理解,一种恒定、纯粹和绝对意义上的认知让位于充满历史流变、动态竞争、正在进行中的构建。然而,与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流动性和生成性的认识相悖,在影视创作中,民族性却常有被狭隘地等同于僵化的民族符号和民俗标签的倾向。例如,与《长城》类似,韩国导演沈炯来2007年的英语跨国商业片《龙之战》便是基于韩国古老传说里常出现的“龙”(Imoogi)来构建的怪兽灾难电影。这部实际总制作超7000万美元、意在全球市场与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下的影片,口碑糟糕,总亏损达一千多万美元⑳。可见,在当下更大规模的跨国电影浪潮中,对民族性囿于老套、浮于表面的理解和表述已经不再能必然地转化为市场的卖点与跨文化的接受。一个文化体系的古老形象或意象,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文化阐释作为支点,很容易只成为好莱坞所寻求的差异化的点缀,而无法形成表达新语境下生成的价值体系的主体。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跨国跨文化的交往、竞争与沟通导致了新形式的文化出现,被民族国家话语所遮蔽的个人和群体的其他文化身份——阶级、种族、性别、技术、区域等渐次浮出地表。奉俊昊则很好地捕捉了这些新的文化身份,对于《雪国列车》和《玉子》的观众来说,其观看与情感投射的基础不再是国族和人种,而是对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的认同,是一种基于泛无产阶级性的世界主义身份认同机制。奉俊昊的跨国商业片在好莱坞的类型限定中打开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空间,在跨文化对话中创造出一种“未被强加等级的不同文化”㉑,成功建立起跨国大片的主体性。
结 语
张艺谋和奉俊昊的跨国电影实践分别是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与韩国“韩流”这两个民族国家文化输出战略的重要体现。电影的跨国制作和传播潮流已经挑战了以往我们在理解好莱坞与民族电影关系中惯常的全球/本土、西方/东方、霸权/反抗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现在或许应该转变为:对外输出的跨国电影制作不再单纯地抵抗好莱坞,而是与好莱坞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跨国商业电影竞争,用一切可用之资源,成为全球市场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事实上,好莱坞已经先做出了策略调整,美国联美影片公司前主管丹尼尔·瑞斯(Daniel Reese)曾这样分析到:“2000年,美国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票房收入大体相抵,但此后美国票房收入只占到了40%……很久以来,我们都没有打造严格意义上的美国电影,因为我们毫无选择。为了与全世界对话,新时代的好莱坞应该制作全球化的电影。”㉒在将自身打造成超越文化与国界的全球性商品的过程中,好莱坞不仅以普适性面孔行销世界,也将不同国家的人才、文化元素和民族符号视为原材料库,在其中予取予求,借以抢滩各国电影市场。《花木兰》《功夫熊猫》《功夫梦》《木乃伊3》等主打中国元素的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成功曾给中国电影人带来巨大的冲击。像李安这样的华人导演在好莱坞不仅拍摄了由英国名著改编的《理智与情感》、美国西部爱情片《断背山》,还拍摄了《绿巨人》式的超级英雄片以及具有浓郁印度文化色彩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可见,在电影的全球化制作与传播的语境中,民族文化和民族元素已与特定的国族身份或地理区位分离,可被任一资本所提取、转化、征用。
与好莱坞对其他民族文化元素的迅速吸纳并转化成商业卖点不同,民族电影在走向跨国电影制作、尤其是与好莱坞产生深入交集的过程中,还时常纠结于“民族性”的存续问题。采用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美学,是否就意味着民族电影的好莱坞化和自身主体性的消解?事实上,好莱坞电影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国家大众想象与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在电影语言、类型、技术等诸多方面对好莱坞的借鉴已清晰地表明,中国电影的民族性里显然早已融入了好莱坞的色彩。克里斯蒂娜·克莱因(Christina Klein)提出,我们应该重新看待好莱坞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将好莱坞视为全球化的代理人,而是一个目标对象、一个象征资源的存储库,民族电影可用以构建它自己文化经济的全球化之路㉓。在今天电影的跨国制作、传播的潮流中,民族国家的跨国商业电影对好莱坞在全球市场千锤百炼过的类型美学、故事策略、技术特效继续实行“拿来主义”已成为普遍策略。因此,我们看到,中、韩电影不约而同地以跨国大片的制作进军全球电影市场,尝试通过复制好莱坞所开创的模式积极参与到影像的全球流动中。这也是目前看来民族国家的电影最有可能在世界商业电影的版图中夺城拔寨的战略路径。
① “矛盾情感”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概念,意指个体在面对同一个欲望对象时,有两种相反(通常是爱与恨)的情感和行为倾向。在英语学界,学者们普遍认为当代韩国商业电影对于好莱坞电影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关系。Cf.Kyung Hyun Kim,Virtual Hallyu:Korean Cinema of the Global Er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2-13.
② Cf.Zhou Xuelin,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Zhang Yimou’s Genre Films,Singapore:Palgrave Macmillan,2017,pp.65-79.
③ Cf.Matthew Hughey,“Cinethetic Racism:White Redemption and Black Stereotypes in‘Magical Negro’Films”,Social Problems,Vol.56,No.3(2009):543-577.
④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出现了一系列由西方面孔出演的战争题材影片,如《红河谷》(1996)、《红色恋人》(1998)、《黄河绝恋》(1998)等,尽管这些影片已经开始模仿好莱坞的类型叙事(《红色恋人》就曾邀请好莱坞编剧合作),但其中的西方人形象在叙事中仍处于中国人的庇佑下,或是受到中国人精神的净化、感召。
关于游侠盟的文字,现在完成的有《燃犀》一篇,即游侠盟后期的盟主周然为了给盟中一名普通帮众肖通复仇,追杀武功远高于己的秘教左使云梦犀的故事。而现在正在写作的,则是游侠盟后期,两名来自异域的盟主之一,罗林斯的故事。
⑤ Susan Brownell,“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in Tyrene White(ed.),China Briefing2000:The Continuig Transformation,Armonk,NY:M.E.Sharpe,2000,pp.210-224.
⑥ 这与以往经典好莱坞电影在表现亚洲形象时将亚裔男性或描绘为色魔或刻画成性无能的惯常设置又是一致的。Cf.Eugene Franklin Wong,On Visual Media Racism:Asians in the American Motion Pictures,New York:Arno Press,1978,p.109.
⑦ 贺桂梅:《记忆的消费与政治:〈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的变奏》,载《文化研究》2013年第15辑。
⑧ 参见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⑨ 郭松民:《〈长城〉:张艺谋的“恒王”情节》,http://wemedia.ifeng.com/6499821/wemedia.shtml。
⑩ Susan Napier,“Panic Sites:The Japanes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from Godzilla to Akira”,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Vol.19,No.2(Summer,1993):331.
⑪⑫ Cynthia Erb,Tracking King Kong:A Hollywood Icon in World Cultur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5,p.5.
⑬ 赛人:《〈金陵十三钗〉:商女恨与国家仇的想象性共振》,载《电影艺术》2012年第2期。
⑭ 有英语观众在线讨论关于《雪国列车》无字幕的问题,https://www.reddit.com/r/movies/comments/22mcvb/is_snowpiercer_supposed_to_have_subtitles_no/。
⑮ 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孙绍谊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48—249页。
⑯ 在朱迪斯·巴特勒看来,“表演”(performance)是“先于主体”的,在表演的过程中,主体得以确立。在巴特勒对福柯的解读中,她指出,主体在被模塑的过程中,“被理解为在身体‘之内’的这个内在灵魂的表征,是通过它在身体上面的铭刻而被意指的”(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6—17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金陵十三钗》中约翰穿上神父常服、玉墨等穿上女学生服的情节元素,皆可象征性地被视为主体“在身体上”被建构的过程。
⑰ 在《金陵十三钗》进行到1小时58分左右,约翰与玉墨之间的对话。
⑱ 在《长城》临近结束的1小时30分左右,林梅用英文对威廉·加林说“We are more similar than I thought”。
⑲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⑳ 参见《沈炯来的〈龙之战〉损失超一千万美元》,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05/22/200905 2201433.html?related_all。
㉑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5.
㉒ 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刘成富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1页。
㉓ Cf.Christina Klein,“Why American Studies Needs to Think about Korean Cinema,or,Transnational Genres in the Filmsof Bong Joon-ho”,American Quarterly,Vol,60,No.4(2008):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