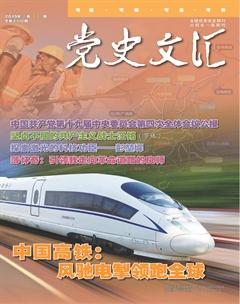薄怀奇:引领我走向革命道路的良师
陈源 丁逸枫


薄怀奇老人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的老师,他引导着我走上革命道路,并且一步一步精心培育我,让我在前进的道路上,脚步更坚实,走得更远……
一
我第一次见到薄老,是在1948年的河南商城县。那年12月下旬,我和一批青年学生被固始县党组织送到正在筹办的鄂豫公学。他是鄂公的教育长,也是筹备者之一。
薄老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早在1943年,他就是太行二分区一专署主管教育的科长,1945年又任太行二中校长。1946年,平汉战役后,他又调到由范文澜在河北邢台筹办的北方大学担任行政学院主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他带着部分学生随军南征。根据刘、邓首长“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抵达河南的薄怀奇就地铺摊子开始工作。
1948年10月,商城、固始相继解放。为了把鄂豫地区建成中原野战军的后勤基地,区党委、军区和行署进驻商城,薄怀奇调任行署教育处长。11月上旬,薄怀奇到任后,行署领导向他讲明中原局关于创办一所抗大、陕北公学式的鄂豫公学的决定:创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组建各级政府机构,开展巩固基层政权工作,为新区准备大批干部。学校由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任校长,薄怀奇任教育长。
鄂豫公学的筹备从当年12月份开始,校址就定在原私立雩娄高中校址。筹备组只有八九个人,薄老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不仅要筹划学校的机构设置,制定学校编制和教学计划,还要编讲义、准备开学、授课事宜。学校各项工作尚未准备就绪,学生们就开始陆续报到。我们这批固始学生是第二批到达的,被安排在行署招待所,后面陆陆续续来了邻近商城的潢川、金寨、霍邱、叶集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学校生活很艰苦,学生没有宿舍,就住在教室里,把课桌拼起来当床铺,吃饭也是“有亲投亲,无亲投友”,但前来投考的青年人仍然络绎不绝。1949年春节过后,就达到近200人。
1949年2月23日,学校正式开学,薄老主持开学典礼。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薄老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鄂豫公学的办学宗旨就是培养一批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要求我们在经过长期的学习、改造、实践后,彻底转变立场,建立新的人生观,树立起革命的新信念。他用一个“诚”字将革命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希望我们诚心诚意参加革命学习。只有诚心诚意参加革命学习,世界观才能通过革命理论指导的革命实践得到彻底转变,才能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他告诫我们要用诚实的态度来接受革命教育,用诚实的劳动进行革命实践。薄老讲话善于古今结合,并赋予新的内容,与时俱进,对启迪我们学习革命理论的积极性和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薄老本身就具有待人以诚、执事以信的品德。多年后,他在给《鄂豫公学校史》 领导小组办公室同志的来信中,自谦地写道:“我这个人很平凡,要说有点什么好处,就是对党还忠诚,对人还诚恳,对革命还坚定……”
薄老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在鄂公,他给我们讲授《中国革命史》 ,从鸦片战争一直讲到解放战争。他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研究历史,讲课时条理分明,逻辑性强,既有知识性,又有鼓舞性。本来他的课是两节,各40分钟,结果一讲就是一上午,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国家教委的意见,组织编写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湖北“革大”)校史。1993年6月,成立了编写《鄂豫公学校史》 的工作班子,历时3年,直到1996年5月23日,在庆祝校史出版发行暨鄂公校友南下47周年的紀念大会上,薄老深情地说:“鄂豫公学虽然从筹备、开学、剿匪、南下、支前,到办‘革大,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但同志们对它的怀念,对它的感受却是那么深!为什么?因为大家在鄂公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方向,另一个是工作作风。鄂豫公学的凝聚力、吸引力,或者说感召力、穿透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个上面。”
可以说,我和我的校友们都是在鄂公接受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革命洗礼”。我们在那里接受党的传统教育,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建立了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团结友爱、追求进步的革命精神,坚定了跟党走的革命信念。而薄老就像一位不辞辛苦的园丁,传道授业解惑,精心培育着校园中的这些幼苗,剪杈修枝,让所有的营养都输送到主干,茁壮成长。
尽管我们在鄂公学习的时间很短,但无论老师还是同学,都对他满怀深情。在编写校史的3年时间里,薄老担任编写领导小组组长,他远在广州,仍4次给校史办公室写信,具体指导如何开展修史工作;召集办公室的校友去广州商议,对书稿的内容、出版,都作了详细规划;对最后30万字的校史清样,他更是逐字逐句地看,连一个标点都不漏过。
编写校史时,校友们一方面是积极写稿,有妻子代故夫写稿,夫君代故妻写稿;另一方面是踊跃捐款,有些校友家境清贫,也捐了50元,一些故世校友的子女也代父捐资,薄老和夫人薛英,更是屡次捐助,在他和夫人相继住院做手术期间,仍然寄来捐款。据编写校史财务小组最后统计,薄老的捐款前后累计达3000余元。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1996年5月23日,在武昌的桂子山上,84岁高龄的薄老与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名鄂公师生,欢聚一堂,举杯同庆鄂公校史出版发行。
鄂豫公学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校友之间的感情却是永存的。
二
1955年,我转业到湖北省教育厅工作,意外地见到薄老,再次成为他的“学生”。1949年6月,鄂公奉命从河南商城南下湖北武汉的途中,我和另外38名同学一起在麻城投笔从戎,加入湖北军区独三师文工团。那年别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薄老。
办理好工作手续后,我心里有些想不通:薄老是北大的高材生,有文化有水平,早在1934年就参加革命入了党,是老党员、“老资历”,为什么却只是一个在非党员厅长(柳野青)领导下工作的副厅长?
谈话中,薄老敏锐地发现了我思想上的波动,他很严肃地给我“上课”:“柳厅长之所以没有成为党员,是组织认为他在党外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他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和恽代英同志一起工作,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革命资格,他都是我的前辈……”
薄老的一席话,令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大约是看出了我的难堪,薄老又笑起来,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小鬼,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你应该知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哟……”我使劲点点头。
对我这个当年的“小鬼”,薄老始终像园丁一样,给我修枝剪叶,帮我吸收更多的阳光雨露,顺利成长。
我到教育厅工作后,时逢全厅组织理论学习,学习按干部级别划分小组,尽管我只是主任科员,却成为负责辅导处级干部学习的小组长。小组成员多是一些重点院校的校长,包括本厅的厅长,薄老也是组员之一。小组每周组织两次理论学习,一次半天。
虽说我是小组长,却当得战战兢兢。那些校长、教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管是文化水平还是理论水平,都令我高山仰止,而我只读过信阳女子师范,充其量也只是个高中水平。后来虽在鄂豫公学学习了半年时间,理论水平哪能和这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领导们相比?
果然,一次学习结束后,薄老将我叫到办公室。他问我对中国近代史了解多少?在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薄老面前,我的历史知识近于小学生水平。薄老严肃地说:“你没弄清楚的东西,就不要轻易下结论。辅导也是一种引导,所以,你要先学!”接着,他耐心地给我进行历史“扫盲”,从鸦片战争的起源讲到清王朝的退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北洋政府的军阀割据,直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其间穿插着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大事件,使我对各個不同历史时期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讲完了近代史,他又讲起近代革命史,着重阐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的区别和成败原因,他都烂熟于心、娓娓道来。他甚至给我讲《三国志》 《三国演义》 《水浒》 ,同样的历史人物,哪些事件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
课上完了,薄老说:“认识由模糊到清晰,学习由不自觉到自觉,都有一个过程……在学习讨论过程中,也是一样,先摸清哪些观点大家认识模糊,然后找难点,抓焦点,找准切入点,就观点讨论,不要轻易地表扬或批评任何人,注意求同存异,通过学习明晰观点,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就是辅导。”
听完薄老这一堂深入浅出的历史课,我顿时醍醐灌顶,感觉他给了我一把打开一扇知识大门的金钥匙。事实上,在此后的工作中,每走一步,薄老都会给我一把钥匙,不断地培养和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学习《反杜林论》 时,薄老告诉我:“《反杜林论》 是一枚酸果,既然你要带领大家去啃,就要自己先啃……”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时,他教我:“学习马哲,就要学理论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事物的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是矛盾在作用,矛盾暴露出来,先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再寻找解决的办法……”
知耻而后勇,好学近乎知。薄老让我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热爱学习的种子,我在工作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理论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在后来的辅导学习中,再未出现过失误。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开始整风。整风整什么?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自己的思想。在学习小组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揪出不少的“小我”。但是从5月中下旬至6月初,国内政治生活的气氛突然变得十分紧张,社会上极少数人趁“大鸣”“大放”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自此,中共中央正式改变决策部署,全党由开门整风转入了反右派斗争。
由于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主要是来自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因此,教育系统的很多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被扣上了帽子,并且运动还在扩大化。
我在独三师文工团的战友冯文锦,也是鄂豫公学的校友,比我年长10岁。投考鄂豫公学时,她坦言自己因在抗战时期参加过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参加过一些宣传、演戏活动,因此被管制。薄老当即派学校的齐瑞棠去商城公安局查阅档案,公安局所提供的材料说她的身份是国军系统,而她的活动是宣传抗日,并没有劣迹。薄老从事统战工作多年,知道在国共合作期间,许多文艺团体是以国军面目活跃在正面战场的,而“青年军团”也有一部分人是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所以,决定收她入学。鄂公南下时,公安局不准冯文锦离境,薄老又派人与公安局反复交涉,她才得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南下途中,她和我们一起参加了独三师文工团,因为演技很高,还获得过军区会演的“优秀演员”。不幸的是,因档案中的记载,冯文锦与丈夫都被戴上了帽子,蒙冤而逝。薄老自责地说:“那时候,我要是让组织科长在她的档案中把调查结果写清楚,就不会给她的生活留下后遗症了。”他说因为自己的粗心,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薄老爱护同志的政治生命,我深有体会。1956年7月审干开始时,首先抽我到厅审干办公室任第二组小组长,看到其他同志都是工农出身,我是小商出身,父亲身份不清楚,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有一天,薛英大姐交给我一张复印纸,打开一看,是薄老在我的“审干”调查上的批示:“她没跟其父生活过,对他一无所知,所以他对她没有任何影响……”短短的几行批示,令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薄老这盏指路明灯的引导下,此后在各种运动中,我对群众工作都做得得心应手。
1964年,我随共青团湖北省委“四清”工作组到麻城蹲点,推广试验田、改良品种,刚开始受到农民的抵触。我想起薄老曾经教过我:“教任务的同时,还要教工作方法,分析他们工作中的难处,关心他们,并尽力去解决……”我和一些小队干部具体分析情况后,知道农民是希望提高生产力的,如果能给国家多贡献点、集体多留点、自己多分点,他们何乐而不为?摸准了大家的心理,再细致地工作,将政策与实际相结合,农民很快就接受了改良的新品种和试验田。
薄老自1964年离开武汉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也再未见到他。如今,他故去也有19年了,但我从未忘记过他,于我,他不仅是老领导,更是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至今,他和我们大家的合影,我一直珍藏着。
(责编 申世杰)
相关链接
薄怀奇(1912-2000),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4年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毕业后回到山西,曾任高平县县长。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高教厅厅长,中共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等。“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下放到粤北干校。1972年回到广州。1981年至1988年,任广州市第七、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