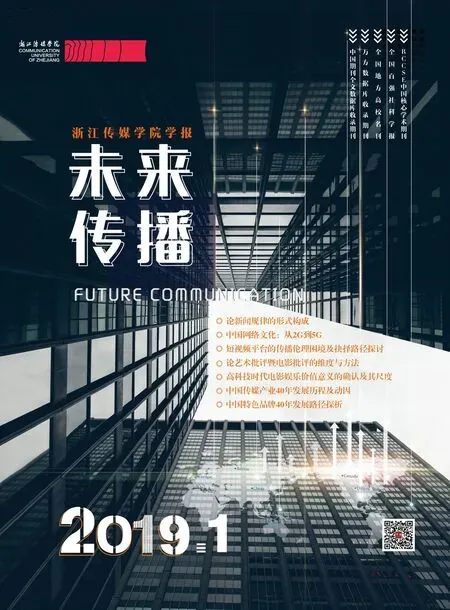高科技时代电影娱乐价值意义的确认及其尺度
李建强
一
当下电影所处的时代,名之曰“高科技”,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现代电影工业制作和生产体系与高科技的发展犬牙交错、互为表里,开创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影像创造和创意的崭新格局。其实,当我们回过头去省察,电影植根于工业化时代,一部电影史,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带动电影艺术进步的历史,就是艺术和科技嫁接交互的历史。科技对于电影的重要作用勿庸置疑。影像艺术形态的每一步发展,特别是它所呈现的虚幻时空,超常角色、神魔鬼怪、奇特造型等等,从一开始就根植于科技强有力的支撑。乃至本雅明提出,与精神革新相比,首先应该提倡技术上的革新,因为只有实现了技术上的革新,才可能有精神创新。他进而号召从事艺术生产的艺术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生产条件,认识到生产技术对艺术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自觉地更新和改造艺术生产工具,通过它们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1]卡尔维诺则要强调,技艺是你能在世界上存在的最重要的东西。面世100多年来,电影从未摆脱技术的束缚,也从未错过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电影的历史也即与科学技术媾和联姻、携手共进的历史。大体说来,电影从发轫至风靡数十年,艺术与技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敬如宾,在互惠互利、携子之手的和睦共处中,电影的表现手段和方式方法日渐丰腴多彩,推助“第七艺术”后来居上,以百变丰盈的姿态,给身处变动不羁、焦虑躁动的人们带来诸多精神抚慰和生活梦幻,电影的生命娱乐意义与价值也籍此得到伸张和确认,并为世所公认与体察。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末以来,《星球大战》发其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一批所谓国际主流大片脱离原先艺术发展的轨道,热衷以制造视听奇观为能事,以猎取资本增殖为圭臬,以形塑新一代观众口味为导向,肆意渗入特技手段、工业编码和暴力元素,寻求用各种超能力的高概念/大制作取代实际生活,用更多感官刺激挑战叙事情理,使电影发生了从现实到悬置、从“叙事电影”向“景观电影”模式的突变。从此,高科技大片高举高打,日渐占据银幕主导位置。在这些电影里,玄幻奇观无所不在,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超级英雄无所不能,生命的切身体验开始让位于视觉感官,肉体的刺激享受登堂入室替代了精神愉悦。由是,电影的形式日渐铺张扬厉,电影的内容日趋怪诞和空泛,电影的观众则日见低龄化和对象化。更可怕的是,好莱坞大片作为一种“文化激素”和价值示范,挟裹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金融、媒介霸权和软实力风靡全球,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仿效的对象和摹本。世界电影格局为之生变,优孟衣冠纷至沓来,神魔鬼怪接踵而至,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深为其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受其扰。好莱坞成为当代电影高峰的代名词,也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角力的前哨与阵地。应该承认,中国在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路途中,也未能完全规避这种路径“依赖”和“锁定”。一些电影人受其所诱,自觉或不自觉地跟从依傍,心甘情愿地为之张目,渐致模糊和失去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记得2016年5月,好莱坞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来中国,看过《捉妖记》《美人鱼》《寻龙诀》等一批中国热门电影后,麦基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影坛存在着当代现实题材少、故事复杂却不深刻、异想天开地逃避现实等弊病。他直言:“中国电影是好莱坞的二流模仿者”,为什么要玩那么多技艺?为什么不多做些现实题材?[2]问题直截了当、尖锐到位,完全超出了陪同人员的预料。连一个美国电影人都看出了其中的奥秘,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加以搪塞和隐瞒。
二
笔者这样说,并非要完全否定好莱坞高概念科幻大片的影像创意和创造价值。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的:“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3]科学上的突破总是同步地带来工业技术上的发展,并渐次覆盖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具体到电影,我们无法遏制电影科技的发展,也无法阻挡影像艺术的进步,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进化发展一样。毫无疑义,电影嫁接高科技概念和最新技术成果,既维系了传统影像作品的形式基因,又理所当然地带来了新生的影像介质,并以新的影像仪态挑战电影原先的生产程序和制作模式,体现了新世纪影像艺术的美学内涵和架构,丰富了电影语言的方式和手段,使电影更出彩、更好看、更富有表现力。同时,审美视野的变化和审美经验的更新,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内容的扩张,使得电影的疆域在有形、无形中得到极大延伸,开拓出森罗万象的艺术新天地,缔造出波澜壮阔的文化新景观。新一代观众群的形成和汇聚,其实是电影艺术更新换代的随行物,是带有某种必然性的。但不容回避的是,凡事有度,过犹不及,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旦脱离艺术的制约和规范,电影“高概念”就像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并凭借科技强大的冲击力和人们求新求异心理的双重红利,跑马圈地,攻城略池,直抵电影艺术的要津命门,颠覆传统艺术的精髓蕴藉。我们看到,从《星球大战》,到《黑客帝国》《V字仇杀队》,再到《变形金刚》《星际穿越》,技艺日新月异,改弦更张;世界弱肉强食,暴行肆虐;英雄不食烟火,超人酷炫——千奇百怪的景观、无厘头的预设、神与怪的博杀牢牢盘据银幕“头条”,人类生活所必需面对的实际问题却退居其次,现实主义和人文精神呈若有若无,已经不可遏制地走向视觉和奇观的极端。环顾电影新近40年的经历,高概念大片如入无人之境,高歌猛进,野蛮扩张,成为全球化时代一道难以抗拒的社会景观。指称其形成了某种文化寡头垄断,恐怕也是不为过的。
当然,电影应该出新,可以造梦,长于夸饰,没有定式,但对生命娱乐意义的体验一旦让位于单纯的视觉感官享受,并且不断冲刷底线,走向极端,它的负作用负能量也就难以回避,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释放出人世间的各种不端和邪恶:超级英雄逞性妄为,妖魔人渣法力无边,物欲肉欲无所节制,人欲情欲冲塞弥满,恶化了正常的艺术生产环境,扰乱了人类健康的精神成长需求。不是吗,在高科技的遮蔽下,低俗、恶俗司空见惯,暴戾、凶蛮大行其道,怪诞、诡异屡见不鲜——资本为了在被诱导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利润,无所不用其极,金钱本位全然替代艺术本位,工具理性完全超越价值理性,甚至不惜荼毒善良人们的心性,吞噬千禧一代主体观众的灵魂(美国儿科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2015年、2016年上映的10部好莱坞超级英雄影片中,正派角色平均每小时有23场暴力戏,反派角色每小时则有18场暴力戏,男性角色的暴力戏是女性角色的5倍,对成长中的青少年造成极大负面影响)。[4]这种影响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通约、一种时尚。就以国内上映的《毒液》为例,观众趋之若鹜,票房一路狂飙,单日票房破3亿,连续登顶票房冠军,但就其本身内容看,不过是故弄玄虚、人兽纠合的老套而已,血腥、暴力、重口味则借尸还魂、变本加厉。可以说,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联袂的电影生产已经和正在造成人与自然、人与艺术、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许多年来,国际国内不断有艺术家慷慨陈词,呼唤批判好莱坞,抵制好莱坞,道理正在于此。
三
人类的艺术生产活动必须遵循精神生产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资本编织的电影观念,“重新对人类生命中娱乐的意义与价值,对电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艺术和社会整体精神文明的关系进行确认,也已成为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绕不开的重大命题。”[5]
笔者以为,这里有两个尺度必须得到重视:
一是,从作品的文化逻辑说,怎样摆正科技与价值的位置。如前说,一部优秀的影像作品,最引人入胜和打动人心的常常并不是技术做的多玄妙、场面有多壮观、特效有多神奇,更多的是由于跌宕起伏的剧情、以情感人的故事内核、鲜活可爱的人物形象,以及人性内在精神的深刻阐发,只有这些核心元素、基本语言才是真正支撑起电影艺术的根本条件。无论是传统叙事作品,还是高概念大制作,都是通过视听语言来讲述故事、传达情感的。好的创意、好的故事、好的形象在根本上决定了影像作品的精彩程度。换句话说,电影科技的最终目的是为内容服务的,故事、人物、情感才是作品的灵魂,技术、手段的使用只是为了更完美、更贴切、更有力地体现作品的主旨内容。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说就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脱离了故事的技艺,难免无所依傍;过度的技术包装,常常会损伤人文内核。因为电影毕竟是一种讲究创意、承载思想、抚慰人生的艺术,技术手段尽管能增光添彩,但代替不了故事的叙述、人性的张扬和人文的渗透。因此,摆正技术与内容的位置,调节科技手段与人文创意精神的关系,将技术与艺术紧密结合,让技艺手段自觉为内容服务,是电影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忽视了对“基本问题”的关注,往往只能成为工匠式的专才,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只能停留在某些技术的层面。这位大科学家晚年一直有两大担忧:一是资本主义的无节制发展可能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阻碍,二是科技的无序发展可能对人类生存带来的灾难。他为此强调,“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6]“如果没有活生生的精神作依托,所有的手段都只不过是迟钝的工具……在涉及人性问题时,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态度,不能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6][106]显然,爱因斯坦的忧虑和思考对于今天同样具有警示意义。电影艺术与电影科技的联姻,是电影有生以来的元命题,是电影的宿命,也是电影赖以立身定命的根据。它们的关联是自然生成的,它们的秩序和规约也是与生俱来的:当电影驾驭科技时,可以使影像如虎添翼、神采熠熠;当科技凌驾于电影之上时,影像就可能丢失命门而趋向于衰亡。位置不能颠倒,逻辑需要自洽。必须明了的是,高概念/大制作跨世纪的风行走俏,并未根本改变电影的本质功能,完美拉升影像艺术的内涵品格,因此,不过是、也只能是特定阶段的一种替补性的应对,一种偶然性的选项。
一个信手拈来的例证是亚洲一些邻国的电影。先说长期被我们轻看的印度电影,完全走的是一条与好莱坞背道而驰的路线,就是和中国大部分影片相比,它们的科技含量也要逊色不少。但由于坚持用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讲述印度故事,主题深刻,选材多样,直面生活,情趣盎然,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的灵活性,一些中小成本电影常常稳扎稳打、以小博大,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近年在中国上映的《摔跤吧,爸爸》《起跑线》《鬲鬲老师》《老爸102岁》《护垫侠》等,无不获得强烈反响,在票房、口碑以及文化影响力上全面刷新,一点也不输给偌许竭力仿制好莱坞的中国电影。科技的“短板”不仅没有妨碍这些印度电影艺术功能的阐发,反而因为删繁就简、朴实无华,专注思想情感价值的开发,而将影像的各种可能性发挥到极致。由此可见,从作品的文化逻辑上说,有一些艺术观念需要澄清,有一些认识盲点需要校正,并非迎合“国际电影潮流”才有出路,只有适合自己的表达才是最好、最有力量的选择。伊朗、日本和韩国的电影也都提供了这样具有说服力的确证。伊朗电影的淳朴厚实,日本电影的东方韵味,韩国电影的现实干预,弦歌不绝、久久为功,数十年如一日,不改初衷,各自形成了具有民族化特征的电影序列和核心竞争力。老杜诗云:“颠狂杨柳随风舞,无情挑花逐水流”。说的是“杨柳”和“桃花”,对自身的岁月印迹无动于衷,满足于乘风乱舞,随波逐流,它们是永远也领略不到春暖花开之盛景的。笔者籍此强调的是,自然界和艺术界的生存规律常常是相通的,杜甫的倾情抒发本身就是人格化的,泾渭不分地盲从好莱坞,趁波逐浪地追踪高科技,很可能遮蔽我们的精神视野,撼动我们的艺术根基,使我们远离,而不是切近电影艺术的本质。近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波折、反复多少都与此相关,揠苗助长,事与愿违,欲速不达。恰如已故著名华人科学家张首晟所说: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的伟大,乃在于它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尤其值得我们警醒的是,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电影产业的发展,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入地介入电影的创作和制作(网络化、数字化的走势不可逆转),在此新的情势下,我们一定要对科技和艺术的文化逻辑始终保持清醒意识,对艺术人文情怀的力量维系足够的战略定力。这不仅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也是影像艺术持续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是,从艺术家内心说,怎样保持内心价值的稳定。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各级政府、社会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发展,电影生产能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三,电影市场容量跃居世界第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表面上看,电影的主流和自主意识已经成为稳定的价值系统,其实这个价值系统还没有成为业界全体成员内心自觉认同的价值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影视艺术领域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碰到了许多新问题。一方面,思潮涌动、价值多元,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产业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对电影资本增值和票房利润的过度关注,导致了影像文化艺术属性的大面积散失。特别是在向电影强国的进发中,我们对于好莱坞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认知时常失之偏颇,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众所周知,艺术的进步并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模式与方法,好莱坞类型电影的成功套路也已不再是什么隐私秘诀,但我们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还是摇移不定,甚至神情恍惚、走火入魔,不是在观念上奉若神明、亦步亦趋,就是在制作上曹随萧规、因循守成,加之商业上锱铢必较、唯利是图,常常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走向比“好莱坞”更“好莱坞”的歧路。从近年生产的一些作品看,盲目仿效、甘遂人后的多了,发乎情意、本乎地道的少了;摆弄技术技艺的多了,重视思想承载的少了;高概念、大制作的多了,有温度、接地气、走心动情的少了。我们有些电影人太实惠太追逐功利了,眼睛只盯着市场和票房,一旦某个样式、类型、获得成功,便一拥而上,大量繁殖复制,直至耗尽它们全部的生命力(号称花费了7.5亿元人民币的《阿修罗》,始则高调亮相,放言赶超好莱坞,以营收30亿元人民币为标的,最终全线撤档、暗淡收场只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制作的影片,如果不能表现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行为逻辑,以及中国人对于现实和未来世界的深沉思考,就很难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在这个过程中,金钱崇拜自然罪责难逃,价值游弋也难辞其咎。如果说前者是外因,是缘由;那么后者就是内因,是本源。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主体的迷茫和焦虑导致客体的异化和走样。这虽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更多地属于消费主义时代的全球通病,但在强调文化自信,在亟待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当口,这种现象还是非常值得警惕的。说到底,无论是游离艺术本心,还是放逐娱乐价值,体现的都不是文化自信,都不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义。不断膨胀的物质主义正把我们引入高度异化的时空结构之中,金钱拜物教也好,票房决定论也罢,并非只是市场逼迫的结果,也是一种精神向度的自我选择。
应该承认,当下的中国电影既面临极大机遇,也面对严峻挑战。从宏观上说,文化发展空间还多有不足,体制制度环境还有待完善;从微观上说,艺术的潜质有待开掘,市场的能量尚待释放。在这样一个转型发展时期,市场、票房、利润三箭齐发,区域的、集团的、个人的利益相互交织,我们的价值判断遭遇到了空前复杂的环境,可以和可能诱惑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作为艺术家本身,是否同样也有一个坚守精神价值、保持内心稳定的问题。傅雷先生曾强调:艺术的力量,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是艺术家世界观、文化学养、艺术思想、性格特质、塑造能力的一种投射。[7]按照他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心理底色,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呈现;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品貌。“社会把特征印在艺术家身上,艺术家把特征印在作品上。”[8]在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境氛围中,我们不仅要接受生活给与的馈赠,更要守住精神灵魂的疆域,洞悉社会人生的本相。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艺术家,还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推进技术工具和人文理性的协调发展,维系健康友好可持续发展的艺术生态系统的责任。那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渊薮,也是我们存身立命的根基。为什么好莱坞能够振臂一呼、统领世界,高概念可以越厨代庖、畅行无阻,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基本价值发生了动摇,我们的内心出现了焦躁吗?反过来,为什么印度电影、伊朗电影、日本电影可以不为“好莱坞”所动,不被“高科技”牵制;能够坚守民族文化的精神根底,顽强地体认本国的影像特色,不就是因为尊重自己的历史、维系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对本民族历史文化抱有足够的自信吗?实际上,只要我们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就会发现,人类自有文字创造的几千年来,希冀在艺术镜像中观照和展现自己精神力量的夙愿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社会和物质形态瞬息万变,精神和艺术价值亘古不移。更进一步说,人类之所以得以从自然界、生物界脱颖而出,依据的不正是这种须臾不可或缺的精、气、神吗?正如美国著名杂志编辑威廉·德莱塞维茨不久前在斯坦福大学的开学演讲中强调的:在艺术生产中,比想象力、创造力更难更重要的,是按自己的价值观行动的勇气,是守成人文理想的硬度和韧性。[9]在商业大潮、物质主义、技术至上、炫耀性消费、娱乐至死等现代社会思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各种乔装打扮浸润、干预我们生活的当下,如何保持内心价值的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而又现实地摆在各位艺术家面前。我们唯有气场恒定、心无旁骛,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如爱因斯坦所期待的那样,将“实现这一目标的渴望有力地存于我们的内心”,[6](19)才有守正胜算,才不至于在高科技至尊的电影新时代迷茫失范、狼狈地败下阵来!
四、结 语
总之,坚守电影的艺术本性,强调电影艺术家的心灵存放,直面创作者精神宣示的价值维度,在人心与物化的世界间搭起桥梁,应该成为高科技时代确认电影娱乐价值意义的出发点。从此出发,技术和工具的张扬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影像的创意和创造也才有了本质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