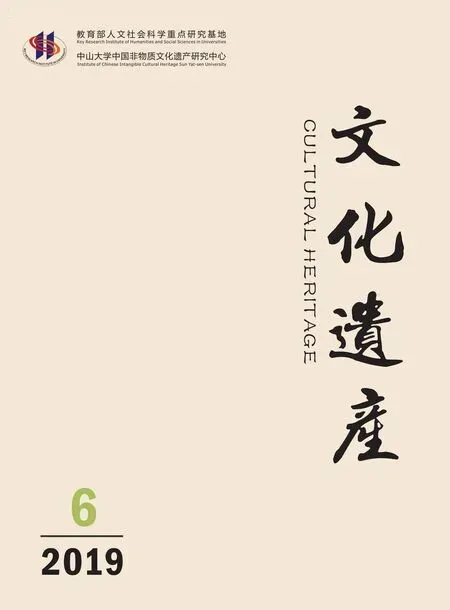从粤剧剧目发展史的遗留问题看林榆剧作的示范意义*
董上德
一、 粤剧剧目发展史的遗留问题与今天研讨林榆剧作的“由头”
粤剧的保护和发展,是这一影响巨大的剧种如今相当需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它被列入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周年之际,如何保护,怎样发展,粤剧行内以及关心粤剧的社会人士均共同关心。
在众多的头绪中,笔者比较关注的是粤剧的剧目和剧本创作,曾先后写过两篇相关的论文,分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粤剧论争及其启示》(《广东艺术》2014年第4期)和《试谈戒虚妄——商榷若干新编粤剧的剧情逻辑》(《广东艺术》2016年第2期),前者主要聚焦于粤剧剧本的“改革”问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戏改”语境下展开论述;后者主要是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认为某些新编粤剧剧本片面追求“戏剧性”而超越了生活逻辑和历史逻辑,导致出现某种“虚妄”的剧情。笔者肯定不少新编粤剧剧本的成绩和贡献,但也不必讳言,有不少新作尚嫌粗糙、生硬,上演之后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没有出现可以“唱到街知巷闻”的重点唱段,总体上还没有达到前辈粤剧编剧已经达到的高度,如杨子静、莫汝城等的《搜书院》(1956)和《山乡风云》(1965),如林榆的《伦文叙传奇》(1985年)和《花蕊夫人》(1986)等,可以跟谢宝、刘琴、伦文叙、花蕊夫人等相提并论的立体化的艺术形象也真不多。
回顾粤剧剧目发展史,行内专家郭秉箴先生曾经指出,就粤剧的剧目而言,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添油加醋、随意发挥的改编和臆造”,并举例说明:“例如,马师曾模仿京剧《虹霓关》的故事,改头换面,先是将剧中的人物现代化,取名《古怪夫妻》,后来再将现代人物穿上古装,改名《佳偶兵戎》,成了他的首本戏。又如,廖侠怀,把文明戏《棒喝自由女》加上少妇被逼疯的情节,改编成了《花王之女》,演出时却是穿古装的。还有一些取材于重大历史题材编就的戏,其主要关目是以形同儿戏的表现方式来处理的,如《淝水之战》写的是苻坚投鞭可以断流的著名历史战役,戏中把谢安打败苻坚的关键写成由苻坚的爱姬张子慧作为内线,派丫头小红女扮男装向谢安报信,趁苻坚与张歌舞行乐之时,夜袭取胜。这等于开历史的玩笑。”(1)郭秉箴:《粤剧风格论》,见郭著《粤剧艺术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78-79页。而笔者之所以写出《试谈戒虚妄——商榷若干新编粤剧的剧情逻辑》一文,正是有感于粤剧剧目史上的这一“遗留问题”在当今的粤剧剧本创作中并未绝迹,提出了一点批评性的意见。
郭秉箴先生还说:“粤剧的老大难问题,概括起来不外是:剧本质量低,特别是陈词滥调多;四功五法的功能不全,只能唱,不会做和打(包括舞)。”(2)郭秉箴:《粤剧改革的里程碑——论〈山乡风云〉戏曲化的经验》,见郭著《粤剧艺术论》,第262页。当然,郭先生已经辞世多年,他未能看到如今新一代的粤剧艺人正在克服“只能唱,不会做和打(包括舞)”的弱点,积极练功,奋起直追,并努力向兄弟剧种学习,在“做手”和“唱”等表演艺术方面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可话说回来,“剧本质量”的问题依然突出,剧本的文学品味有待提高。
说及有成就的粤剧编剧,除了杨子静、莫汝城等著名人士外,林榆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打算以林榆先生的粤剧剧本创作为话题,探寻林榆剧作的示范意义。在上述背景下,今天研讨林榆剧作的“由头”也就显得有一定的针对性。粤剧的生存环境在它被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10年里是越来越好,人们在高度重视和期待着粤剧会有越来越多、越来越高质量的剧目上演。我们借由对林榆粤剧剧作的研讨,以便突显林榆剧作既与时俱进又不失粤剧“本色”的价值所在,或许对粤剧剧本的认知会有所推进。相信如此选题,对回应粤剧的“怎样发展”问题也不无裨益。
二、 戏剧评论界尚未注意到的“林榆价值”
林榆(1920-),广东东莞人。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干部、戏剧工作者和剧作家。2015年,荣获第二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戏剧评论界已经对林榆粤剧剧本有过不少论述,《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一书之第二版块“众说林榆”已经收录得较为齐备。(3)《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慎海雄主编,林榆、林西平编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本文引用林榆粤剧剧本的相关评论均见此书,下文只注书名和页码。这一版块再细分为“记人”和“评剧”两个部分,二者的内容其实互有交叉,综观这些成果,约有数端:第一,论及林榆的导演实践与其编剧的关系,如李小瑛《林榆:新中国粤剧的幕后推手》记述了林榆戏剧活动中很值得关注一个“事件”:“1964年,中国京剧院来广州演出《红灯记》,给粤剧注射了强心剂。陶铸说粤剧也要搞一个‘绿灯记’,于是有了《山乡风云》。林榆参加了《山乡风云》从创作剧本到导演、演出的整个过程,1965年底上京演出。……《人民日报》《戏剧报》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赞扬。”该文还指出,林榆十分重视粤剧的剧本,强调新编粤剧要以简代繁、以虚代实、以少胜多。(4)《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61-62页。第二,论及《伦文叙传奇》的艺术成就,如李门《〈花蕊夫人——林榆剧作·论艺集〉序》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伦文叙传奇》的剧本特色:“《伦》剧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掌故作为基础,却加强了它的人民性、文学性,使主人公变得更加可爱:不慕虚荣,面向民间,而令人忍俊不禁的对联斗句,更突出了《伦》剧的本色,说是推陈出新的佳构,绝不是泛泛之词。”(5)《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64页。霍大寿《〈伦文叙〉的艺术魅力》认为林榆重新塑造了伦文叙的形象,突出了“卑贱者最聪明”的题旨。(6)《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75页。而陈仕元《戏剧要多写观众爱看的戏——评粤剧〈伦文叙传奇〉》一文用三个“关键词”称赞此剧的成功之处:脱俗,好看,有益。(7)《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84页。第三,论及《花蕊夫人》的艺术成就,如李门《〈花蕊夫人——林榆剧作·论艺集〉序》高度评价了《花蕊夫人》一剧的改编思路:“该剧取其历史大事,以艺术虚构手法抒写之,务求去却枝蔓,树立以花蕊夫人为中心的,包括耽乐无能的蜀主孟昶、大宋开国之君的赵匡胤、好色跋扈的大将军王全斌等鲜明形象,称为新编历史剧是适宜的。”(8)《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64页。又如韦轩《后蜀名花带泪看——试谈粤剧〈花蕊夫人〉》指出该剧处理“人”与“戏”的关系颇有特点:“把历史上史料甚少的花蕊夫人写成一个大型长剧,写出一个比较丰满而才貌双全的花蕊夫人,又写出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开国之君、大宋王朝的赵匡胤及其一段缠绵哀怨的恋情,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面貌又能有戏可看,应该说是粤剧创作中一朵脱颖而出的新花。”(9)《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92页。肖甲《试谈粤剧〈花蕊夫人〉》分析了该剧的美学特征:“剧作者面对史籍、传说、话本演义、民间散记和各种不同的考证推断,却从容地关照其大端,在符合历史大事件中,撷取和择用适于表现剧作主题的情节和细节,推衍出一出极明快的悲喜剧。”(10)《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99页。
以上的评论,均各有见地,值得参考。而笔者写作此文的动因是,林榆剧作还有人们尚未注意到的“林榆价值”。笔者认为,不宜就林榆论林榆,孤立地去看林榆剧作;应该在粤剧剧目发展史的“维度”上观察林榆其人以及他的剧作的“存在意义”。
早在中学时期,林榆开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里,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社会活动和舞台演艺的诸多经验。笔者将此三点联系起来看,可以说,如果“三缺一”都不是“这一个”林榆。一个成功的编剧,绝不是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就足以点染“纸上春秋”的,绝不是仅靠翻阅古书、资料就可以写出传世之作的,绝不是只懂得一点“编剧技巧”就能够“笔下生风”的。没有深刻的阅世经历、高度的美学修养、丰富的“场上历练”,要想做一个成功的编剧几无可能。林榆先生能够成为一位取得了颇高成就的粤剧剧作家,与他的这些积累是密不可分、高度相关的。在粤剧发展史上,林榆就是独特的“这一个”,他创作的剧目的原创性值得珍视。
我们不妨客观地看到,粤剧史上,粤剧剧目数量相当庞大,公开出版的《粤剧剧目纲要》(一)和《粤剧剧目纲要》(二)(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编印于上世纪60年代,羊城晚报出版社于2007年重新出版)已经有较为充分的展示,但属于粤剧“原创”的剧目并不多见。郭秉箴先生认为,过去的粤剧剧目大体有几种类型:一是木鱼书、小说、笔记的戏剧化,一是外国戏剧电影的粤剧化,一是添油加醋、随意发挥的改编和臆造;再有就是生命力不强的“直接针砭时事的改良新戏”和作为“案头剧本”的文人作品等。(11)郭秉箴:《粤剧风格论》,见郭著《粤剧艺术论》,第71-80页。其实,郭先生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还有为数甚多的粤剧剧目是从兄弟剧种长期传演的剧目中“移植”过来的。如果我们不是盲目乐观的话,丰富多彩的粤剧史有一块明显的“短板”,就是粤剧剧本“外来的”多,“原创的”少(粤剧史上有一个相当长的“提纲戏”阶段,可称之为“无剧本演出”;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不重视剧本或胡编乱造成为“惯例”)。传承和发展粤剧,不仅要创作出更多的新编剧目,而且,还要下大力气提升剧本的质量,后者更具有“战略”意义。而林榆,他的丰富的人生阅历、杰出的粤剧剧本创作,以及已经取得的众所公认的艺术成就,恰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郭秉箴先生还有过一个尖锐的批评,指出粤剧剧本有“四大病状”:“满(不精炼),散(不集中),平(不感人),折(不连贯)”。(12)郭秉箴:《粤剧改革的里程碑——论〈山乡风云〉戏曲化的经验》,见郭著《粤剧艺术论》,第263页。这是一位深爱粤剧的评论家的肺腑之言。这四点之中,笔者认为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平(不感人)”。这是戏剧创作的“牛鼻子”。戏剧,可以写“平凡”的生活,也可以写“不平凡”的人生,前者如《伦文叙传奇》,后者如《花蕊夫人》,可不管如何,感人的艺术魅力是二者都必须具备的。笔者试图聚焦于“感人的艺术魅力”这一点来解读“林榆价值”。
三、 林榆剧作处理故事题材的若干特色
林榆的粤剧剧本尤其是《伦文叙传奇》和《花蕊夫人》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要“破解”其中奥秘,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笔者想从林榆剧作处理故事题材的若干特色入手,得出三点看法:一是林榆善于对比人性之劣与人性之善,而以人性之善作为“平凡生活”中最具诗意的“戏眼”;一是林榆善于突显主人公的悲悯情怀,使之成为“不平凡人生”中最夺目的“亮点”;一是林榆的粤剧剧本富于“粤式”的机趣,既有雅俗之辨,又能雅俗共赏。下面分别加以具体的论述:
1. 人性之善与“平凡生活”中最具诗意的“戏眼”
写“平凡生活”,是对戏剧家极大的考验。比如,流传广府民间的伦文叙故事,故事主人公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卖菜仔”,读过几本书,牙尖嘴利,鬼马机灵,满身“急才”而不免“古惑”,有不少令人解颐甚至是“喷饭”的情节,其故事一度以浓郁的“市井味”而受到底层民众的喜欢。可林榆的学养和追求使他不甘心于将一个不无“低俗”趣味的人物和故事搬上舞台,他说过:“伦文叙是广东南海人,因为出身贫贱,生活坎坷异常。过去的粤剧把伦文叙写成一个恃才傲物、捉弄乡人的浪荡子。要写这个人物就要摆脱这些俗套、旧套,还他质朴的、乐天的穷不夺志的本性,表现他聪明过人,才气横溢以及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情操。务求达到‘脱俗’。”(13)林榆:《也谈雅俗共赏》,见郭秉箴《花蕊夫人——林榆剧作·论艺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5年,第283-284页。林榆的着力点固然是“还他质朴的、乐天的穷不夺志的本性,表现他聪明过人,才气横溢以及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情操”,可他深谙戏剧的底蕴,戏剧是在人物的关系、角色的互动中“出彩”的,能够打动人心的是人物内心的“善”,“善”能生“美”,尤其是在“难能可贵”的情景里表现出的人性之“善”,更是感人至深的,这是戏剧的一条规律,故此,林榆没有“拔高”伦文叙,而是在一个“善”字上做文章,写出“善”与“善”的相遇和碰撞,即以伦文叙与阿琇的相遇和碰撞为主线,呈现的是一对心地善良、纯洁无瑕的年青男女在毫无“机心”的前提下不期而遇,在几乎“不可能”的环境里双方凭着一颗善良的心越走越近,从而激发出一段凉薄人世中的温暖而奇巧、意外而合理的真挚情缘。这是《伦文叙传奇》一剧的“主要戏脉”。
“改造”固有的伦文叙的形象而使之以“新面貌”出现于舞台之上,林榆的一个“高招”是用心塑造好阿琇的形象来与之“配戏”。这样一来,就为重新塑造伦文叙形象“开拓”出一个富有意味的“戏剧空间”。伦文叙内心的质朴、善良、风骨等性格要素均可以在此“戏剧空间”里得以展现。写好阿琇,是为了写好伦文叙;可反过来说,写好伦文叙,也是为了“挖掘”出阿琇在全剧中不可缺少的“戏剧功能”。试想,如果阿琇只是一个过去旧戏里的“梅香”,纯粹跟随小姐上下场,做些“斟茶递水”的小动作,其“戏剧功能”极为微弱;可是,整部《伦文叙传奇》不能没有阿琇,而阿琇正是以“第一女主角”的身份出现于林榆笔下的,这是其“神来之笔”。阿琇的“戏剧功能”是双重的,一重是她确系卑微的“梅香”,在伦文叙与胡蓉(小姐)之间、伦文叙与胡员外(胡蓉之父)之间、胡家与伦家之间,均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此作用类似于《西厢记》里的红娘;另一重是她不仅仅做“梅香”,更是剧作家要重点塑造的“女一号”,她本来是真心希望胡蓉小姐不要“错过”了伦文叙这一个难得的“婚姻对象”(有善心,有才学,有“前途”,热诚朴实,侠义助人;而且胡员外对伦文叙的才学尤为看重,并寄予厚望,一心想招为“东床”),她对伦文叙的为人、为学极为敬佩(阿琇不是一般的“下人”,而是读过书、有眼光而因遭遇不幸才被迫沦为婢女的,她亲眼目睹小姐被疯狗狂追、伦文叙仗义“救护”的情景,她亲眼目睹伦文叙在胡家“招亲”时力压其余竞争者的出众才华,她亲眼目睹伦文叙孝顺娘亲、勤苦攻书、辛劳养家的种种“行状”),她乐于帮助胡员外,还出主意设法让伦文叙对胡蓉小姐产生“好感”,以便完成胡员外的嘱托去“撮合”伦文叙和胡蓉的婚事。她除了敬佩伦文叙之外,并无“非分之想”,满腔热情地为胡蓉小姐“效劳”,以此作为自己的“本分”。她越是无“机心”,就越是显得大方得体,善良可爱,纯洁无瑕。这就是“平凡生活”中最具诗意的“戏眼”。
林榆懂得戏曲是“剧诗”的原理。《伦文叙传奇》的剧情一路曲折发展,顺着剧中的“诗意”蜿蜒而来。试想,如果阿琇内心是平庸的,形象是扁平的,气质是低俗的,她怎么可能打动伦文叙以至于这位男主人公在获取状元后要执意迎娶呢?须知,在金銮殿上,皇帝已经“打了招呼”:“母后有言,谁中状元就招驸马。”(第六场)(14)本文引用林榆剧作,均据《花蕊夫人——林榆剧作·论艺集》,不另出注。于是,经过轮番比试,“结果”马上“出炉”,皇帝面对伦文叙唱道:“(滚花)卿家穷不夺志,积健为雄。不但激励人心,孤亦为之感动。赐你鳌头独占,人来速报后宫。”伦文叙却出人意料地说:“陛下,慢,慢……”他要婉拒“状元”的名分,为的是“臣有妻,虽未娶,难变初衷”;如果一旦接受了“状元”头衔,就马上陷入后宫的“预设”,自己就难以和阿琇成亲。一边是成为驸马的“荣耀转身”,一边是与婢女结婚的“平凡之举”,两相对比,似有云泥之别,可伦文叙只是喜欢并钟情于阿琇。这就是“平凡生活”中最具诗意的“戏眼”!伦文叙怎么能够忘记:在第三场,自己穷居之时,是阿琇“帮伦母把水挑进屋去,倒入水缸”;自己在“识破”阿琇送来的小姐的“诗作”之时,阿琇还在设法帮小姐说话:“我小姐知错了,她很内疚,一晚都睡觉不着!所以‘垂泪到天明’。”如此聪明灵巧,如此“尽忠职守”,如此天真无邪;伦文叙向其母耳语之后,伦母对阿琇说:“姑娘,刚才文叙对我说,这是一首唐诗,是唐朝才子杜牧的诗。”阿琇“随机应变”,说:“借唐诗表情意,小姐正聪明得很。一来怕羞,免直抒情感,二来藏拙,免见笑才人。”其随机生发的应对虽是“谎言”,却显得机智可爱。伦文叙怎么能够忘记:阿琇看着掩饰不了,就主动招认“自作主张”替小姐选了一首唐诗:“明人不做暗事,相公请谅,实是我的主意。”其一片真诚和善良,将自己的母亲也打动了:“不应错怪姑娘。”伦文叙怎么能够忘记:阿琇自述悲惨身世,自幼饱经困苦,幸得一位落魄的教馆先生认作义女,才会“识字断文”,可一场大水吞没了整条村庄,自己孤身一人,不得不“大户为奴至于今”,听到此处,伦文叙也忍不住激动和感叹:“此女身世凄凉无倚凭,饱经灾劫剩孤身。冰雪聪明伶俐甚,却屈居奴痛沉沦。”阿琇的善良、聪明和悲苦,令饱读诗书的伦文叙产生自然而然的“情感审美”,当面对阿琇说:“姑娘不同流俗,慧眼识人。小生他日有成,一定不忘援引。”这还不至于说是“爱的宣言”,却是伦文叙心地善良、同样“慧眼识人”的具体表现,可以说是惺惺相惜。转到第四场,伦文叙和阿琇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伦文叙准备上京应试,上船之前,在渡口等候阿琇,两人相见,依依不舍,含情脉脉;伦文叙感激阿琇前来送行,更感动于阿琇的深情表白:“相公不要将人看扁了,就算你失意归来,(唱滚花)我也为你将家务操持,糟糠同命。”好一个“糟糠同命”,这是最能打动伦文叙、也是最能打动观众的十分朴素的“金句”。全剧的“诗眼”正在于此。所以,站在金銮殿上,伦文叙所言“虽未娶,难变初衷”,发自肺腑,是义无反顾的。
戏演到这里,戏剧张力极强,伦文叙和阿琇这两个人物是在一系列“饱满的剧情”中互相“成就”着对方,他们的“戏份”相互依存,二人关系的变化和行为的互动构成了全剧“情感戏”的主线,而伦文叙的“功名之路”成了一条为之“服务”的副线。这是林榆的剧本构思不同凡响之处。
2. 悲悯情怀与“不平凡人生”中最夺目的“亮点”
林榆的《花蕊夫人》选择了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做“女一号”。花蕊夫人生活于“残唐五代”时期,这是一个乱世,乱世“故事多”,何况花蕊夫人有特殊的身份、经历和遭际,所有的“特殊”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人生故事的“传奇性”。这绝对是跟《伦文叙传奇》里的阿琇相互迥异的人生。
林榆将花蕊夫人的出场安排在后蜀将亡而未亡之际。这是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后蜀君王孟昶的宠幸和依恋、后蜀“母后”的鄙夷和冷眼、后蜀民众的困苦和不幸,这种种的“戏剧元素”丛集于花蕊夫人的心中。她是孟昶的妃子,是“母后”的儿媳,更原是民众的一份子(第二幕写孟昶彻夜难眠,等候回乡省亲的花蕊夫人返宫,这一戏剧情景,正是剧作家想要强调的花蕊夫人身上的“平民底色”,在她登场之前,有意借情景的渲染而将此“平民底色”加以“放大”),如果是一般的美女,没有什么思想,也无什么情怀,她不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困难,反正此刻的身份只有一个:“妃子”。可是,花蕊夫人不是一般的美女,她有思想,有情怀,她的身份认同是复杂的:她固然已经是“妃子”,可是“母后”的冷眼并非没有来由,“母后”将自己的“被宠幸”看在眼里,内心大概时刻在想着“红颜祸水,女色误国”,花蕊夫人明白自己在“母后”的眼里不是一个“好儿媳”;更为揪心的是,她虽然是孟昶的“妃子”,身处宫禁之内,有如笼中之鸟,但是她知书达理、察言观色、耳听八方,时时关心宫禁之外的世界,关注家乡父老的安危,尤其是眼下这一次家乡之行,耳闻目睹“宫廷一席宴,农户十年粮”的残酷现状,亲身感受到“民不聊生衣食欠,繁苛租税苦相缠”的悲惨事实,她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为君王身边的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规劝君王“改弦更张”、关心民瘼、改善民生。她还生怕“口说无凭”,特地将故乡的一束只有空壳的稻穗带回宫中,让孟昶“目验”,让他知道天灾加上人祸是如何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度日如年。她的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急迫、痛心以及不无内疚与自责的心态。孟昶毕竟与花蕊夫人相处日久,两人声息相通,花蕊夫人的眼神、语气和急迫的情状,一一直抵孟昶的内心;花蕊夫人手持空壳稻穗递与孟昶,说:“这就是乡下的收获,正好比如今的蜀国!”不待她细述,孟昶当即知其用意,说:“哦哦,我明白了,夫人是为家乡父老,恳求减免钱粮,孤王恩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孟昶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他有一定的同情心,可是,他这么爽快地“恩准”,主要的目的在于“拥花蕊欲下”,免得花蕊继续“啰嗦”。剧作家这一舞台指示,一下子将花蕊夫人和孟昶二人的人生境界区别开来:孟昶的“恩准”带有自私性质,他急不可待要和花蕊夫人“亲热”以慰多日的相思之苦;而花蕊夫人还没有从家乡的苦况中走出来,剧作家赋予她的戏剧动作是:“(叹息)唉!……”她对于孟昶的重私情多于重民情感到极为不满,又觉得无可奈何,可是尽管如此,还是想进一步劝说一番,剧本里的那一个“叹息”之后的“省略号”就显得意味无穷,而那一声“唉!”更是表明她哪有心情去“寻欢作乐”呢?剧作家笔下的花蕊夫人,在接着出现的一连串犹如惊涛骇浪般的剧情中,其悲悯情怀是她的“不平凡人生”中最夺目的“亮点”。
随着剧情步步展开,花蕊夫人的悲悯情怀与家国情怀合而为一。林榆的独创性在于,他写出具有悲悯情怀的花蕊夫人在动荡而不凡的人生中与“屈辱”随行,而这些“屈辱”又与家国的命运相连。
面对一连串的“屈辱”,要是没有“定力”和“主见”,很容易变成自怨自艾或随波逐流。可是,剧中的花蕊,既坚贞不屈,又独立自守,不屈服于任何的淫威和权力。先是在后蜀将亡之际,花蕊不仅遭受“母后”的白眼,还无辜遭到“母后”的痛斥和指责:“累皇儿骄奢失政,都是你!(顿足下)”花蕊听到此言,无比委屈、痛心和克制,她只有一句台词:“太后严词切责,教人有口难言!”(第二幕)她不得不克制,这不是与太后争辩的时候;她不得不痛心,事实上太后的话没有“全错”;她不得不感到委屈,太后哪里知道自己曾几何时苦口婆心劝说过孟昶?这对于花蕊而言,是她所遭受的第一重“屈辱”。
她所遭受的第二重“屈辱”来自“破剑门南侵”的王全斌。王全斌是一个极为好色的将领,他以夺得花蕊作为人生的一个目标。此刻,夜已渐深,孟昶已经给王全斌呈递“降表”。王全斌并不满足,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无法接受的要求:“花蕊夫人我要定了。限明天一早送来,过时不送,我便杀入成都,屠城三日。”可在孟昶这一方,国中已无“勤王师旅”,也无“卫国之臣”,时间一点一滴过去,王全斌催促“交人”的“魔咒”一声高似一声,花蕊夫人誓不低头的心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高亢,甚至猛然间拔出孟昶的佩剑自刎,幸得孟昶及时将剑夺回。情势越来越紧迫,戏剧张力越来越“绷紧”,孟昶在自怨自责,却束手无策,而一众大臣则急于等候“投降”。花蕊看在眼里,悲愤难忍,执笔题诗,以抒发其内心激愤:“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在“屈辱”中的花蕊,没有畏缩,面对王全斌毫不示弱,且厉声唱道:“在成都,烧杀抢,刀下多少冤魂;灭吾国,辱我君,还要淫污妃嫔;虎狼心,禽兽行,正是你王文斌!”(第三幕)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花蕊夫人所遭受的第三重“屈辱”来自赵匡胤。赵匡胤以大宋皇帝之尊,也垂涎于花蕊的美貌,他虽然不像王全斌那样鲁莽露骨,却还是掩饰不住一片“色心”。林榆在赵匡胤和花蕊的关系问题上以“化实为虚”的方式来处理,写“精神恍惚”的赵匡胤在梦境中与花蕊“互动”,向花蕊表露欣赏之意,更对“更无一个是男儿”那首诗大为称叹。剧作家借幻境写花蕊的应对:“妾身哪懂诗,偶有感触与忧思,写几句俚语抒我心志。”接着对不能自持的赵匡胤正色劝告:“臣妾心常记,君臣有尊卑。愿君遵礼义,出言莫相戏。”这似乎也是借以“补足”花蕊早前在孟昶身边时的“苦口婆心”。而在现实里,面对赵匡胤的滋扰,她有礼有节,巧于应对,甚至视死如归,她的最终死去,真值得“全场痛切,下跪致哀”。
花蕊经受的三重“屈辱”,是全剧的“戏肉”所在。她被历史狂潮裹挟着,其载浮载沉的命运不可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她能够掌握、可以自主的是自己的人格、心志和悲悯情怀。她至死也感念曹彬对于国家的忠心:自己遭遇曹彬的刺杀,身受重伤,必定不久于人世,可没有必要让曹彬连带也一起“牺牲”。故而,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唱)庸臣害政残民,我有切肤之痛。忠良之士,应得天地宽——容!”此语一出,惊天动地,花蕊也随之气绝,令赵匡胤在内的众人深为感动并哀恸不已。林榆精心“打磨”出一部感人至深的悲剧。
3.“粤式”机趣与雅俗之辨
林榆是广府人,也是粤剧人。他在长年的耳濡目染中、在第一线的粤剧编演实践里深谙“粤式”机趣。粤剧史上有一个现象:凡是“收得”(粤剧界行话:指票房收入高)的剧目,每每是富于“机趣”的,它有“逗笑”的成分,可不是一般的“插科打诨”;它有很接地气的“市井味”,可又不是一般引车卖浆者流话语。林榆十分熟悉以马师曾为代表的粤剧表演艺术,已经注意到成熟时期的马师曾对于粤剧的“机趣”是有过雅俗之辨的,只不过,马师曾的舞台实践有的成功,有的不算成功,比如,林榆《马师曾生平及其艺术成就》一文就相当肯定马师曾改编京剧《四进士》为粤剧《审死官》的艺术尝试:“京剧《四进士》中的宋士杰是个深谋远虑的讼师,是用老生行当演的。他(马师曾)改写的《审死官》中的宋士杰却是个嬉笑怒骂,寓庄于谐的人物,……上述例子,说明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有大胆革新的气魄”。(15)林榆:《马师曾生平及其艺术成就》,《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396页。换言之,马师曾所改写及扮演的宋士杰比起京剧的宋士杰更为近“俗”,更接地气,而不无“市井味”,充满着“粤式”机趣。《审死官》因而受到粤剧爱好者的欢迎,也成为马师曾的一个重要剧目(近年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和广州粤剧院合作重排上演《审死官》,仍然大获成功)。如果与马师曾的一些其它剧目相比,《审死官》的“俗”是有分寸的,以符合人物性格的规定性为前提,不是一味求“俗”,可说是偏“俗”而不离“雅”、雅俗结合。可林榆也指出,马师曾的剧本“有好亦有坏,正如许多传统剧目一样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整理马师曾的剧作,必须经过一番去芜存菁,恐怕比一般的传统剧目还要花更大的气力。”(同上)实际上是说马师曾在雅俗之辨方面尚未“彻底自觉”,留下了进一步供后人探研的空间。
林榆对粤剧的雅俗之辨是相当自觉的,一来他是文艺官员,熟悉文艺政策,也经历过“戏改”的全过程,在雅俗之间掌握了适当的“寸度”;一来在导演和编剧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自己的“雅俗观”,形成自己的偏“雅”而不离“俗”的审美倾向,这与马师曾的偏“俗”而不离“雅”的审美倾向形成对比。
在《也谈雅俗共赏》一文中,林榆提出:“雅与俗,不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既然要共赏,就要把两者统一、结合起来。‘雅’不能高雅到群众不能接受,要像兰香一样,大家都能品尝的‘博雅’。‘俗’不能庸俗到专家摇头,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般的‘脱俗’。”(16)林榆:《也谈雅俗共赏》,《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385页。林榆所说的“博雅”是一个重要的提法,它不是高校的“博雅教育”的“博雅”,而是指可以博得广大群众能够接受和欣赏的“雅”;林榆所理解的“俗”,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与他们声息相通的生活描写和语言表达,此“俗”绝非低俗,而是具有“莲花”般的“内质”,洗去“浮艳”,质朴感人。
且看林榆夫子自道:“花蕊夫人是蜀主孟昶的一个妃子,由于才貌双全,善于诗词而闻名。中国历史不乏女诗人女词家,同是宋人的李清照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诗词造诣和知名度就大大超过花蕊夫人,为什么我选择后者而不选择前者,主要与‘博雅’有关。”他接着说,李清照的诗词虽是经世之作,但“过于高雅,广大观众一下不易理解”;而花蕊夫人的作品,“浅近易懂,憎爱分明,较为一般人所接受”。再有,《伦文叙传奇》,本来故事是“够俗”的,于是,为了“脱俗”,“对传说的原材料,引用时加以必要的筛选;……本来是民间的顺口溜,念起来是很有趣的,但有些文理不通,”于是,就只好自己加以“改作”,以求“博雅”。
看来,在处理“粤式”机趣方面,林榆紧紧抓住“脱俗”与“博雅”这两个关键词,“脱俗”而不离“俗”(大众认可的、声息相通的),“博雅”而不求甚“雅”(大众难以理解、不合大众口味)。前者保留、继承了马师曾等已经积累的好经验,后者则是力图克服马师曾等尚未克服的某些“舞台陋习”,在“博雅”的基础上“脱俗”,“博雅”和“脱俗”双管齐下,提升粤剧剧本的艺术品位。这就是不可忽视的“林榆价值”。
本文所论及的《伦文叙传奇》和《花蕊夫人》,均有丰富的“粤式”机趣,剧本均在,读者不妨自行品鉴,限于篇幅,不再缕述。此处着重点出林榆自觉的“雅俗之辨”,以补学界论述之不足。
林榆对自己的粤剧剧本创作是有较高期许的,简言之,他不写“研究专家不感兴趣”的戏,也不写“群众不爱看”的戏。他的戏剧认知是:“戏是给群众看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而专家往往掌握着质量的尺度,没有专家就难辨精粗、优劣。”(17)林榆:《也谈雅俗共赏》,《当代岭南文化名家·林榆》,第385页。所以,林榆追求的是观众和专家的共同认可。
本文试图将林榆的粤剧剧本创作置于“粤剧剧目发展史”的维度上来考察,思考林榆的成功之道,论述林榆剧作的若干特色,以林榆的剧作和林榆的自述相比照,以期引起粤剧界、学术界对于林榆及其剧作所具有的“粤剧史意义”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而其示范意义也自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