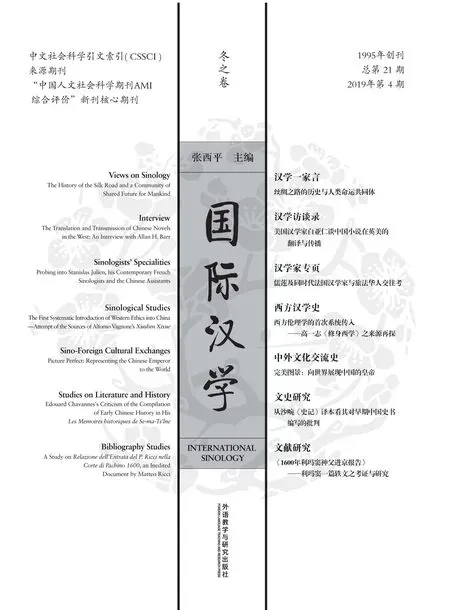情境喜剧《压迫》:丁西林编剧艺术札记
□ 刘绍铭 著
赵冬旭 译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没有哪位作家能像丁西林(1893—1974)一样,作品极少却又如此频繁地被人提起。即使在1939年后便中断了写作,①丁西林在1923—1939年间,共著有7个独幕剧、1个四幕剧,分别是:《一只马蜂》(1923)、《亲爱的丈夫》(1924)、《酒后》(1924)、《压迫》(1925)、《瞎了一只眼》(1927)、《北京的空气》(1930)、《三块钱国币》(1939)、《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39)。关于丁西林的书目信息,详见《中国现代戏剧图书目录》,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编印,1967年。同名补编于1970年出版。译者注:此处有误,丁西林在1940年写成四幕剧《妙峰山》后才中断写作。他仍然是戏剧技巧最为精湛的中国现代喜剧作家,无人能与之相媲美。当然,他并不是唯一一位写喜剧的作家。熊佛西、李健吾、袁牧之、陈白尘、袁俊等作家,往往误把喜剧艺术当作是简单的闹剧或者滑稽剧②丁西林自己曾针对闹剧与喜剧的区别做过较为中肯的评价:“年仅几岁的孩子们可以欣赏闹剧,而很难欣赏喜剧;为什么?能不能这样说呢:闹剧是一种感性的感受,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我喜欢卓别林,他是一位艺术家,他拍的片子是喜剧,而劳莱、哈代拍的片子就是闹剧了。”参见凤子:《访老剧作家丁西林》,《剧本》1961年第11期,第65页。(例如熊佛西的《洋状元》,1926年),而喜剧艺术的魅力在丁西林早期作品中已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利用喜剧来对当代中国风俗发表个人评论。
丁西林的第一部剧本《一只马蜂》写于1923年,亦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年,郁达夫发表《沉沦》后的第二年,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的第五年。不过奇怪的是,虽然《一只马蜂》同样由白话写成,却和同时代的文学作品大相径庭,并没有那种普遍的执念。丁西林在1939年前所写的多数独幕剧都是如此:没有对腐朽制度的声讨,没有对残暴军阀或外国侵略者的谴责,没有过分的多愁善感或顾影自怜,没有把个人的失败同国家的无能相提并论。身处于一个沉迷于社会改革和国家复兴的时代,他所创作的喜剧难免会被社会主义评论家认为是无关时代的。陈瘦竹便指责丁西林的早期作品有“凭空虚构而又缺乏现实意义”“追求市民阶级趣味”的毛病。③陈瘦竹:《论丁西林的戏剧》,《戏剧论丛》1957年第3期,第185页。
在一些社会主义评论家眼中,只要不是反映代际、阶级之间矛盾与斗争的艺术作品,都称不上是“现实主义”(realistic)。所以,陈瘦竹对《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峰山》这两部爱国主义作品的评价更高,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是这样解释的:“丁西林在这一时期中,面对着伟大的民族战争,他的视野逐渐扩大,密切注视当前形势;所以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要比初期喜剧更接近现实,更倾向革命,充分表现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汉奸卖国分子的憎恶,以及对人民积极抗战的歌颂。”①《论丁西林的戏剧》,第186页。
然而,无论这两部戏剧起到了多大的宣传作用,就艺术方面而言,由于需要用煽情的语言来激发国人的爱国救亡之心,它们的戏剧结构就被牢牢地限制住了。即便是曹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剧作家,在写《蜕变》(1940)一剧时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不同的是,丁西林作为业已成名的喜剧作家要向宣传家转型,只会比曹禺更加艰难。鉴于曹禺此前已经有《雷雨》(1934)、《日出》(1936)、《原野》(1937)这样的作品,要他在《蜕变》的结尾处发出疾呼——“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②曹禺:《蜕变》,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287页。——也不算过分。但是,观众却早已习惯了丁西林的喜剧伎俩。当梁治对他母亲说教道:“中国人打仗,向来以为只是军人的事。这是不对的。军人有军人的事,学科学的人也有学科学的人应该做的事。必定要大家齐心协力,才可以打胜仗。”③丁西林:《丁西林剧作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04页。台下观众一定摸不着头脑,甚至要揣摩一阵后才能意识到作家是期望这些宣言被严肃对待的。虽然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代沟”本该是绝佳的风俗喜剧素材,但在抗战期间,尤其是当父亲成了汉奸而儿子是爱国青年的情形下,这道“沟壑”就变成了一个不能被轻松处理的冲突和主题。所以,虽然作家宣称《等太太回来的时候》是四幕喜剧,但在喜剧这一意义下,它是名不副实的;在艺术上,它也以失败告终。即使人生中不乏泪中带笑的时刻,我们仍然难以想象出一个合适的场景能调和欢笑与憎恨这两个极端,而这便是该剧所设定的情境。因此,《等太太回来的时候》给人一种举步维艰的感觉,好像作者在尽力拖长剧情,好让每一个青年角色都有机会发表他们的爱国言论。可是,没有喜剧人物的戏剧是无法被称为喜剧的——虽然评论界对此还认识不足。由于梁家的冲突过于紧张,丁西林必须加入两位亲戚才能使得该剧呈现出一丝滑稽的色彩。然而由于内容的局限性,这些角色所能做的也只是时不时地贡献些“俏皮话”罢了。例如,在梁治对他父亲沦为汉奸感到不解时,许任远提出了他的看法:“饭碗与良心的问题。你如果要我分析汉奸的人品,我想我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等。第一等是虽有良心,没有饭吃。第二等是本无良心,又无饭吃。第三等是虽有饭吃,没有良心。”④同上,第62页。
其实我们不难解释丁西林早期剧作大受欢迎的原因。首先,它们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娱乐,而娱乐作为戏剧观众的最基本权利,却常常被那些比丁西林更知名的同代剧作家所忽视。大多数“五四”剧作家要么热衷于说教,要么沉浸在被他们视为燃眉之急的问题当中,而不屑于为观众呈现娱乐的享受。(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舞台上充斥着洪深笔下的残忍军阀、田汉笔下的悲情恋人、熊佛西笔下的无情父母和恶毒丈夫,以及无数即将出走的中国娜拉(Chinese Noras)。剧场里接连上演这样的话剧,几乎变成了强制社会教育的高台。因此,丁西林的出现不啻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也毫无争议地“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建立不可磨灭的功绩”①胡宁容:《谈丁西林独幕喜剧的特色》,《剧本》1963年第2期,第65页。。
即便不提其他,仅是阅读丁西林的白话文,就已经大为受益了。他运用白话语言的精湛程度(遗憾的是这一点无法在英语译文中体现),很少有同代剧作家可以达到:郭沫若过于直白露骨,熊佛西则是近乎歇斯底里的夸张,还有田汉那沉痛的感伤。丁西林的白话甚至比郁达夫、茅盾等颇负盛名的小说家还要略胜一筹,而后两位曾写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糟糕的白话文章。有人可能会误以为丁西林的白话属于“我手写我口”的风格,实际上,这些自然天成的对白却来之不易:它们是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与斟酌得来的。对于这位非表现主义戏剧作家来说,对白是他讲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唯一途径。所以,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说的那样,在写下人物对白之前,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思考人物在规定情境下的心情。②《访老剧作家丁西林》,第65页。例如,在《孟丽君》一剧中,他让皇甫少华在见到孟丽君丞相后发出赞美:“数年不见,你长得越发美丽了。”③同上。单看这句话,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然而一旦与语境结合起来,它就不仅揭示了两人之间的秘密,而且是说话人的一种表白,因为孟丽君丞相正是一位易钗而弁的美丽女性。丁西林对语言的追求,没有止步于贴切或流畅,他还苦苦搜寻一个合适的情境,能让看似毫无艺术价值的话语变得富有内涵。
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注重情节的设计。虽然有人提及丁西林的写作受到了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契诃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或A.A.米尔恩(A.A.Milne, 1882—1956)的影响,④洪深第一个指出丁西林可能受到了A.A.米尔恩的影响。参见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载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62年,第78页。乔羽则在文章《橄榄——读〈压迫〉札记》中,将丁西林与莫里哀、契诃夫作对比(《剧本》1957年第9期,第67页)。但在我看来,他的编剧技巧更接近于斯克里布(Eugene Scribe, 1792—1861)式的佳构剧(well-made play),因为他常通过剧情的转折来达到他所期望的意外效果。除《酒后》和《北京的空气》改编自同名小说外,⑤《酒后》和《北京的空气》分别改编自凌淑华和宇文的同名小说,参见陈瘦竹:《论丁西林的戏剧》。基本上丁西林所有原创的剧本都得益于佳构剧那精巧的戏剧艺术手法。《压迫》是他写得最好的情境喜剧,我们不妨以它为例。
《压迫》是为纪念一位病逝的单身朋友刘叔和而写的独幕剧。叔和曾与丁西林等人在北京同住。在书信体的前言中,作者回忆起有天晚上,叔和同他在火炉边聊天时曾随口提及想要搬出去另找房住。丁西林回应说,想要找房就必须得结婚,因为“北京租房,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铺保,一是有家眷”⑥丁西林:《西林独幕剧集》,香港:学林书店,1956年,第107页。。之后不久,叔和死于瘟热。虽然丁西林悲痛万分,但他并没有忘记那一夜的谈话内容,即房东对未婚租客的“压迫”,这其实是很好的喜剧素材。所以他写了这出戏,因为他知道叔和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不会责怪他“写一篇喜剧来纪念一个已死的朋友”⑦同上,第108页。。
《压迫》里有五个姓名未知的角色:房东太太、老妈子、巡警和两位单身的男女客人。剧情直接从事件的中间展开。在一个雨夜,男客人刚到房东太太家,就被老妈子告知太太要把租房的押金退还给他,因为她不愿租给单身的男房客。男客人觉得很费解,要求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老妈子答道:
你知道,我们的太太爱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边。家里只有我和小姐两个人。有人来看房,都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没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应,等到太太回来,一打听,说是没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①《西林独幕剧集》,第111页。
但凡男客人能“通情达理”些,事情应该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这房子是房东太太的私人产业。可男客人却不这么认为:他的理由事实上和房东太太一样荒谬:
房东 (渐渐的感到不快)你这话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说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应,是不是?
本次论坛由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农民日报社联合承办,以“落实精准帮扶措施,提升产业扶贫质量”为主题,分产业扶贫政策与部署、产业扶贫实践与创新2个专题,研讨交流产业扶贫的好经验好做法。论坛发布了产业扶贫十大机制创新典型。
男客 喔,不是,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应。不过,既然把房子租给了我,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答应。你知道,现在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问题,是退不退的问题。②同上,第114页。
房东太太听罢目瞪口呆,只得让老妈子去找巡警来,自己则气冲冲地回了屋。但在巡警到来之前,却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位女客人不期而至,也想要租这儿的房。男客告诉她虽然屋子已经租出去了,但她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女客 房子倒不错,房价也不贵。(想了一想)这房子真的可以让给我吗?
男客 自然是真的,为什么要骗你?
女客 不过今晚就来住,总不行吧?
男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来)不过——你结婚了没有?
女客 (跳了起来,挺了胸脯,竖起眉毛)什么?!
男客 (还要补一句)你结了婚没有?
女客 (怒了)你这句话问的太无道理!
男客 太无道理?
女客 简直是一种侮辱!
男客 (高兴起来)“侮辱”,对了,一点都不错,我也是这样说。但是现在有房出租的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结婚没有。
女客 我结婚没有,干你什么事?
男客 是的,一点都不错,我结婚没有,干她们什么事?可是她们一定要问,你说奇怪不奇怪?③同上,第123—124页。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似乎不能确定这位男客是否是故意要询问女客的婚姻状况,以此激起她的愤怒。他掖着自己的秘密,观察女客对这般荒唐情境的反应,并以此为乐,但他好像全然不知该如何化解自己与房东太太之间的分歧。当女客人问他一会儿等巡警来了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只能坦白说:“我把巡警痛打一顿,让他把我带到巡警局里去,叫房东把房子租给你。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就都有了住宿的地方。”④同上,第127—128页。
这个听起来绝妙的主意,却并不对他新朋友的胃口。这位女客人不仅是本剧的“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还是一位早期戏剧中较少受到注意的中国娜拉。⑤中国现代戏剧中较为有名的娜拉式人物,除了胡适《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还有欧阳予倩《回家以后》里的吴自芳、郭沫若历史剧《卓文君》里的同名女主人公、熊佛西《青春的悲哀》里的贾晓琴,以及曹禺《雷雨》里的蘩漪。她想给她的朋友一次“出那一口气”⑥《西林独幕剧集》,第128页。的机会,于是提议要作男客人的太太——当然只是假扮,进而彻底扭转了局面。这让她的朋友也始料未及。当然,故事最后正如丁西林所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战胜了“有产阶级的压迫”。⑦同上,第108页。《压迫》的结尾部分同《一只马蜂》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男客 (关上门,想起了一个老早就应该问而还没有问的问题,忽然转过头来)啊,你姓什么?
女客 我……啊……我……①《西林独幕剧集》,第133—134页。
通过以上分析,《压迫》是多么“佳构”的一部戏已是不证自明了。它和《雷雨》的不同之处在于,《雷雨》是一部佳构的“主题惊悚剧”(thesis-thriller)②弗朗西斯·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 1904—1986)用“主题惊悚剧”一词来形容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创作中期的戏剧作品,特别是《群鬼》(Ghosts, 1881)一剧。Francis Fergusson, Idea of a Theater.New York:Doubleday, 1955, p.162.,它的每段小插曲都是刻意而为,目的是要引出一个更大的悬念。而《压迫》中的意外之喜却被策划得如此巧妙,以至于看起来像是偶然发生的,是剧中人物事后聪明式的举动。在《雷雨》的结尾,当周家所有蓄谋已久的秘密都被揭开以后,我们可能只会勉强地夸赞作者用心良苦,设计了如此复杂纠缠的人物关系,来制造出其不意的结果。我们觉得勉强,是因为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和操纵。与此相反,丁西林笔下的人物总是急中生智,让我们觉得他们自身也是毫无准备的,他们做出的决定和说出的话常常是一时起意。在一出典型的丁西林式戏剧中,我们会欣然发现剧中人物和我们一样,对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意外情境感到猝不及防。在《压迫》一剧中,女客人一定也会对她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惊讶,在其他情境下,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在《一只马蜂》里,吉先生虚构出马蜂这个毫不相关的“角色”来掩饰自己的窘迫,在此之后他一定也颇惊讶于自己的临场机智。同样,在《三块钱国币》里,杨长雄在情急之下灵机一动,摔碎了吴太太的宝贝花瓶,他同样也会意外,自己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与吴太太的争端。
丁西林一方面能够让事情的发展产生戏剧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善于引导观众走进死胡同,而在他们山穷水尽、行将放弃之际,再突然呈现出一片柳暗花明。③凤子用“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描述丁西林的戏剧策略。参见《访老剧作家丁西林》,第67页。这可是了不起的成就,也是丁西林戏剧艺术的精华与魅力所在。“五四”时期的批评家中,似乎只有韩侍桁对丁西林的才华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他在四十多年前就曾写道:“在中国的剧文学上,有一个人总使我想着他,但这个人并没有写过很多的剧本……可是这少许的作品,使我不止一次重复地读了,而每一次都能给我以同样的愉快,——这种事,在我们现今文学的创造中是很独特的例子。”④韩侍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载《文学评论集》,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第106页。对于物理教授丁西林而言,这实在是相当高的赞美;而对于贫瘠的中国现代戏剧来说,却是十分悲哀的。或许《压迫》的作者从未想过自己会靠写“诙谐剧”(funny plays)而在文学史上留下美名。在这点上,他就像是混迹于“三藏法师”们中间的“孙悟空”。中国现代戏剧的“三藏法师”们(如郭沫若、欧阳予倩、洪深等戏剧权威)把自己求取真经的任务看得太过重要,他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世界,而忽略了在“公案”这种形式里,“与主题的无关紧要”才是构成喜剧性的重要元素。丁西林的贡献,恰恰在于他趁中国现代戏剧的《心经》还没被刻下之前,给我们留下了几出隽永的“公案”。⑤译者注:英文原文后附刘绍铭英译的《压迫》剧本,本译文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