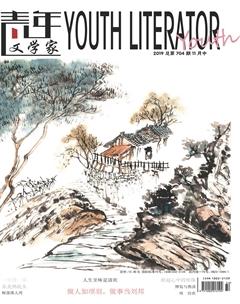重读《玫瑰门》
摘 要:《玫瑰门》以权力与身体的冲突书写文革时期女性身体体验、生命困境,解构了宏大的革命叙事,揭露了红色年代被遮蔽的女性血色记忆,其中以司猗纹、竹西、苏眉为代表的三代女性,各以身体注解了革命年代的女性命运史、心灵史、成长史。
关键词:三代女性;玫瑰门;身体叙事
作者简介:王粟玉(1996.9-),女,汉,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18级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32-0-02
作为灵魂的对立面,“身体”在早期东西方文化传统中承载着与灵魂相较更低下,更具世俗意义的价值,关于身体与灵魂的二元对立思维最早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灵肉说,19世纪伊始,“要以肉体为准绳”的尼采哲学首次为身体正名,此后西方思想界开始反思灵肉对立的命题,身体逐渐“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领域”。
长期处于封建男权文化压抑之下的女性身体被作为泄欲、生育工具,则更少具有表达身体欲望的权利。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女性作家真正崛起的时代,新时期文坛,张抗抗、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作家以对女性身体、欲望书写推进着文学叙事模式的转变。《玫瑰门》以权力与身体的冲突书写文革时期女性身体体验、生命困境,解构了宏大的革命叙事,揭露了红色年代被遮蔽的女性血色记忆,其中以司猗纹、竹西、苏眉为代表的三代女性,各以身体注解了革命年代的女性命运史、心灵史、成长史,以此生发出向历史反思的动力。
一、权力对身体的异化——司猗纹
司猗纹可悲的一生在于权利对身心的压迫和异化。在为革命献身的纯真年代,司猗纹在父权制家庭的逼迫下出嫁,受过优等教育的司猗纹看到了权力的无所不能,于是主动进入了贤妻良母的角色而服从权力的调遣,新婚之夜庄绍俭的摆布使她“不再认为这就是做人的图画”,灯光打开,粗鲁而决断的“拨开”、“劈开”和“攥住”使她彻底感受到身体与精神的分离。此后的司猗纹正式卸掉了“肉身的沉重感”而完全地进入了生命的“黑夜”。身体对司猗纹来说无异于客体,乱伦和裸体入睡宣示了身体的工具化,它被用来发泄权利所激起的侵凌欲望。
正是对身体的无限制的压抑和工具化,她不愿看到竹西洋溢着生命力的健康的身体,于是她窥视她的身体,想方设法瓦解它的完美,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权力。她强盛的权利欲却使她处处树敌,她掌控着苏眉童年的一切,在她成年后跟踪窥视她,强行介入她的生活,把响勺胡同变作谁也不愿踏入的坟墓。身体和权利在司猗纹这里是相悖的,要获得生存的权利,必须对身体发狠,控制身体欲望,要以权利主宰命运,毕竟权利曾经主宰了她的命运。
司猗纹的身体承受了权利的压迫、丈夫的侮辱,细菌的啃食,最后走向毁灭时留给苏眉一个微笑的答复,她的一生没有爱过任何人,他人对司猗纹来说是义务、责任和权力的象征,却唯独不是爱。
二、作为代偿性存在的身体欲望——竹西
竹西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她不用像婆婆那样为了担起家庭责任争生存。竹西的裸体从眉眉的视角看来无比完美,山似的脊背,“从脖子到腰覆盖着一层金色的汗毛”,“金色小溪”从“山上”直淌下来,乳房是“两个自己跳躍着又引逗你去跳跃的球”,臀部是“引逗你内心发颤的两团按捺不住的生命”。庄坦是个懦弱无能的丈夫,但他的死却使竹西彻底解放了曾处在司猗纹窃听和庄坦嗝声压抑下的性欲。大旗“挺直的”,多肉短粗的脖子和硬领间的摩擦在竹西是欲望的引诱和点燃,黑暗夹道里的偷会最终稳定了“流浪”多年的情欲。大旗给竹西带来了“清新和健康”,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具有街道主任儿子的优越政治身份。
情欲是竹西政治理想的替代性的存在,从大学时期紧跟革命大潮到响勺胡同时期被压抑在革命高潮之下,竹西在一直寻找着释放自己的出口,这一出口正是身体。叶龙北从乡下被调回北京喻示着新时代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人得脱俗”口号似地重新唤醒了竹西莫须有的冲动——大学时期紧跟时代和政策的青春冲动。而在文革时期拥有更高阶级身份的大旗已经落伍于“新粮食新粪”的新时代了,因此竹西的抛弃就具有了特别的意味:如同抛弃旧时代一样她离开了大旗,而从叶龙北身上找到了大学时期憧憬的新时代的“烟味儿”。
三、身体的反思和觉醒——苏眉
如果以权利对身体造成扭曲代表司猗纹,以沦为权利补偿的身体代表竹西,那么苏眉这一人物则体现了要求摆脱权利束缚的女性身体的觉醒,觉醒的动力则来自于精神的自我反思。从小苏眉就疏远斗争和政策,在生活老师的目光下憋小便、生活老师在学生的目光下尿裤子、爸的阴阳头……年纪尚小的苏眉开始感受到身份的自卑和权力对身体的摧残,
随着成长,各种各样的身体情境闯入了她的视线……姑爸被通条直插的血淋淋的下身,被猫毛缠住喉咙窒息的死亡,使苏眉不断噩梦;姨婆被儿子用热油烫掉乳头的乳房“像肉食店油亮的小肚”,身体成为获取政治权利的牺牲品,弑母般的身体摧残和泯灭人性的假情假意的同情使苏眉对恐惧感产生了麻木。作为旁观者的苏眉,“她的灵魂发生着震颤”,“这由人给予她的震颤使她不能不逃脱人类”,“哪怕是逃和飞的模拟”也使她必得把作为人的司猗纹甩在身后。
响勺胡同的童年生活千疮百孔,而青春期身体的萌发却使噩梦般的生活陡然迎来了春意。“她的胸脯开始膨胀”,“那隆起和舒展使她又惊慌又满足”,以至于希望引人注意。离别的车站里,初潮的意外到来使她重新感受到女性生命溪流的绵延,这是一曲哀歌,却更是一曲赞歌。“一般视角人物总处于一种被肯定的地位”,但作为作者视线聚焦点的苏眉并没有因此客观化,对过去十年的自我反思并未中断,关于人性本恶、谎言、欺骗、对自我生命的体验和心灵的剖析都是一次次私密的灵魂审视。
四、结语
新生儿头上带着手术器械留下的永恒的新月形疤痕,女性生命似又来了一个轮回,像司猗纹谜一般的微笑,作者在文末又替苏眉发出一个疑问,“她爱她吗”,没有体会过深刻母女之情的苏眉必须回答这个伦理问题,在铁凝的笔下,问题本身暴露出命运对于女性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捉弄。“门就是肚子,肚子就是子宫”,姑爸临死时看到的那扇“红彤彤的厚重的门”是母亲那“任何利器都不能戳破”的子宫,而子宫正是生命轮回之所,子宫的隐蔽以及所承担的孕育生命的繁重过程喻示了女性身体艰难的觉醒过程。身体仅是诠释女性的一个注脚,以身体为视点的《玫瑰门》最终回归女性作为存在本身,遥想和反思大时代下女性的命运、心灵和成长,正如波伏娃所说:“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以身体展示灵魂的痛楚,以身体回应灵魂诉求,“身体写作”成为认识女性自我,建构女性主体性的方式,在性别权利逐渐平衡的未来,身体写作将仍是书写女性特殊生命体验的主要场域。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上下)[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杨秀芝,田美丽.身体性别欲望[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梁盼盼.“革命”与“身体”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史”——重读《玫瑰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03.
[5]齐林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身体观念及其发展[D].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3.
[6]谢有顺.“要以身体为准绳”[Z].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