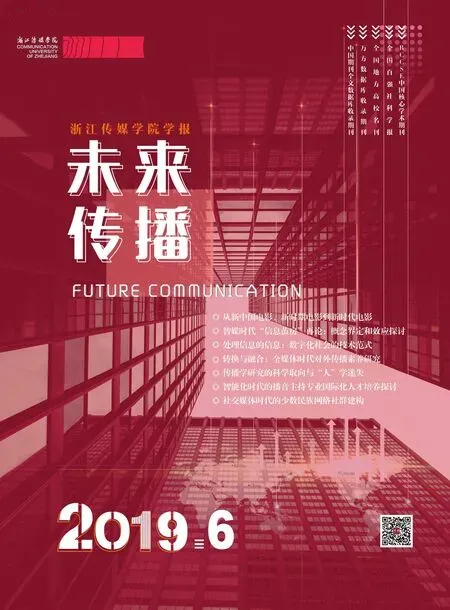国产喜剧电影的类型化与文化表征
吴鑫丰
类型电影作为市场主体,无论是在业界还是在学界都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电影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互联网企业在电影业的布局带来电影融资、生产和传播的日益互联网化,国产电影的类型化发展也表现出新的特征。在不同题材类型与叙事样式的电影中,喜剧片一直都是最受关注的一种类型。喜剧电影不仅在产量上占据较高的比例,在市场上也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和票房表现。在历史票房最高的10部国产电影中,有6部是喜剧片。从单个年度电影票房排行榜的情况来看,喜剧电影一直都占据着比较高的比例,甚至很多时候喜剧电影票房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当年国产电影的总体票房。
作为最具本土性特征的一种影片类型,喜剧电影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意义不仅仅只体现在市场层面。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电影产生的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化及其效应在喜剧电影类型创作和传播中得到了充分集中的体现,使中国喜剧电影在创作形态上进入了一个全面调整的阶段。”[1]观影人群的低龄化,互联网思维在电影创作和传播中的影响不断扩大,IP和粉丝效应持续主导电影创作等新出现的现象更是集中地在当下的国产喜剧电影中得到体现。继冯小刚贺岁喜剧、宁浩的“疯狂”喜剧、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和徐峥的“囧系列”喜剧之后,以大鹏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导演和以“开心麻花”团队为代表创作的喜剧电影成为市场新的热点。在电影市场快速变化和文化转型的双重影响下,喜剧电影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类型,喜剧电影创作的类型、风格也更加多元化。
一、国产喜剧电影的类型化发展
类型的出现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人类本能地就有把性质相同的事物进行归类的习惯。但任何的分类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任意性和模糊性,类型之间的区别并非总是界限分明的,类型和类型之间往往存在着模糊的缓冲地带。分类标准的不同也会增加类型划分的模糊性。就电影的类型化而言,传统的类型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们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总不可避免会引入新的理论和视角。在人们熟知的电影类型中,有的是按照形式来界定的,例如歌舞片中定会有歌舞元素,武侠片和动作片也一定会有武打和动作场面;有的电影类型是根据内容来界定的,例如爱情电影、灾难电影、喜剧电影等;有的电影类型则是依据更加多元的标准,比如都市电影依据的是故事空间,超级英雄电影主要是指根据超级英雄漫画改编的电影;还有的电影类型是和特定的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美国的西部片,日本的武士片和中国的家庭伦理情节剧。由此可见,常见的电影类型的划分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标准。
当我们在说电影类型的时候,实际上总是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在使用类型这个概念:即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类型电影被普遍认为是好莱坞大制片厂时代的发明,是制片厂制度下各大电影公司争相采取的电影创作模式。制片厂会根据观众的心理特点,在一段时间内以某种类型作为创作重点,新创作的影片在人物、情节和视觉影像方面会尽量遵循特定类型的一般特征,同时也需要在各个方面有所创新以满足观众追求新鲜感的需求。有学者借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和个别言语的论述来描述电影类型和类型电影的关系。“电影类型相当于语言系统,而类型电影相当于单一话语或个别发言,系统与个别之间存在相对的互动关系。”[2]但电影类型和索绪尔的语言系统之间仍然拥有本质上的差异。在语言系统中,单一话语不会影响整个语言系统,而个别电影虽然来自某种类型,其特殊的风格却可能会颠覆,甚至改写、重写该类型的成规(convention)。正如詹姆斯·纳雷摩尔所言:“每部电影都是跨类型或多元的。不管是电影工业还是观众都不会遵循结构主义的规则。”[3]
虽然由索绪尔所引发的结构主义的观点和列维·斯特劳斯、普洛普等人关于神话和原型的研究,都对类型电影的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这种研究进路都高度倚重归纳法,很容易忽略个体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和原创性。其次,这类研究几乎无视类型的演变与融合等现象。类型电影的创作总是处于一个十分奇特的困境中,他们必须不断地变化并重新创造类型的程式,类型电影在形式和文化主题等方面都处于不断的演变中。托马斯·沙茨指出:“类型对于某些基本文化议题的深层关切也许是原封不动的,但是为了保持生机和活力,它的电影必须跟上观众对于这些议题变化着的构想,以及跟上观众对于类型的不断增长的熟悉度。”[4]因此,对于类型电影的研究更应采取文化研究的进路,在具体的电影工业的背景中和与观众的关系中来探索类型化。
近年来,喜剧电影在国产电影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中小成本电影中,喜剧的产量更是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前几年国内电影市场上最抢眼的一个现象就是:一批中小成本的喜剧电影在票房上跑赢了很多重量级的好莱坞大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国产电影票房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单部电影的票房上,喜剧片的表现都不容忽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喜剧电影的类型化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类型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按照某一种电影类型的程式来进行创作。电影创作中的类型化首先是一个在电影产业或者工业的语境下出现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与观众的期待和观影习惯密切相关的概念。郑树森在《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一书中就指出,类型电影是一种商业化生产的产物,是生产者按照消费群体的口味精心制作的商品,是“带有文化性质的工业制作”。[2](10)因此,不同电影工业体制中的类型化肯定是不尽相同的。在美国学者理查德·麦特白看来,观众对于类型化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类型的规则与其说是一套文本的成规与惯例,不如说是由制片人、观众等共享的一套期望系统。”[5]麦特白把这一套期望系统也称为“类型元素”,即构成类型电影的关键元素。可见电影的类型化所描述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中国特定的电影工业(产业)体制和类型演化的历史语境下,创作者们根据对当下观众的了解,围绕着关键的类型元素来组织影片的生产。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的深入,电影的商业诉求日益突显,类型开始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正如饶曙光指出的:“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完善,决定性的力量在于物质性的方面(生产和消费体制、生产力水平、产业化规模),而非精神性的方面(电影观念、文化心理结构、精英文化意识和标准)。”[6]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不可能脱离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具体经验和现实。喜剧电影是最具有本土特色的一种电影类型,国产喜剧电影的类型化更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国产喜剧电影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与观众的互动中逐渐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也积累起来一些再三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因素,即我们所说的类型元素,这些类型元素成为组织生产新的影片的重要依据。
不可否认,类型元素仍然是一个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的概念。构成爱情片、警匪片、恐怖片、战争片等的类型元素显然是属于不同方面的。“构成类型电影的似乎是一个庞杂的大众文化范畴,在这个范畴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伦理、道德、艺术、历史等等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些角色几乎无一例外地跻身于电影的故事与形式之中,它们变成了某些人(或群体)喜爱的因素,变成了他们出钱购买的欲望,也就是变成了类型电影的核心元素。”[7]一般来说,喜剧片的主要特征是要产生娱乐大众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传递出严肃的精神内涵。但无论形式还是意义的呈现都是动态变化的。前几年,那些高度依赖网络上的段子和“热词”创作出来的喜剧片,在市场上也有不错的表现,但久而久之就不再奏效了,市场需要新的形式与精神内涵。因此,在确定喜剧片的类型元素时需要综合考虑形式与精神内涵及其呈现方式等多个方面。
正是由于较之其它类型,喜剧片在类型元素的界定上存在着更多的模糊性,创作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难度也会进一步加大。从商业运作的角度看,类型化就是创作者与观众在动态的博弈中达成共识,但这种共识的达成也是非常不易的。不同观众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绪支配下也会有不同的选择。为了使影片能够吸引最大数量的观众,喜剧片创作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资源、进行创新。相比于冯小刚的“贺岁喜剧”、宁浩的“疯狂喜剧”、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作者性”,当下的国产喜剧在喜剧观念、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更加丰富和多元。国产喜剧电影创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几种不同类型元素混合在一起,通过类型的糅合来达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如黑色幽默与情节剧的融合形成黑色喜剧,喜剧类型与爱情元素的结合形成都市爱情喜剧,用喜剧的形式对战争题材进行包装形成的战争喜剧,喜剧元素与动作片的融合形成动作喜剧,古装、历史题材与喜剧类型的糅合产生古装荒诞喜剧。无论是以喜剧元素为主导的糅合,还是以其他类型为主导的糅合,都极大地丰富了喜剧片的亚类型。类型糅合成了当前国产喜剧电影类型化的重要特征。
二、IP开发、粉丝效应与当前的喜剧电影生产
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高级编辑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在《流行制造者:娱乐时代的流行科学》(Hit Makers:The Science of Popularity in an Age of Distraction)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公式——“喜欢=熟悉+惊喜”。用于剖析人们对事物的喜爱背后的心理机制。笔者在对流行文化和流行行业中的热点产品和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一个事物能否成为热点很多时候受制于传播渠道,但人们喜欢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熟悉的基础上还能带来惊喜。德里克提出的“流行公式”不仅可以被用于分析苹果手机、畅销车型等具体的商品,对于分析像很多经久不衰的电影系列或类型等文化产品也同样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如前所述,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就是如何与观众互动的问题,我们显然也可以借用这个“流行公式”来对类型化的概念进行深入分析。类型电影之所以受到市场和观众的欢迎,主要原因是类型片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对于“熟悉”的要求,在“熟悉”的基础上还经常能够带来“惊喜”。
学者郝建在谈到类型电影时提出:“类型电影的概念可以这样限定:在美国好莱坞发展起来、在世界许多国家盛行、按照外部形式和内在观念构成的模式进行摄制和观赏的影片。”[8]这一观点的洞察在于提出了分析与研究类型电影的一系列辩证的维度:好莱坞与其他国家、外部形式与内在观念、摄制与观赏。这些看似对立的视角可以让我们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对类型电影的认识。如果把类型电影定义为按照外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模式进行摄制和观赏的影片,就可以发现不仅具体的类型是动态流变的,类型化的具体策略也是动态变化的。在好莱坞大制片厂时代,人们对电影类型化创作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公式化的情节、定型化的人物、图解式的视觉影像”。这种创作模式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创作者会力求在模式化的类型程式中加入新的元素,观众在熟悉的情节、人物和视觉影像的基础上也总能收获“惊喜”。在新的“惊喜”不断成为熟悉的过程中,不仅单一类型在不断改变,新的类型也随之涌现,类型的种类日益丰富。当我们这样来描述类型电影发展的过程时,我们所关注的都是类型元素的“内在观念”。在真实世界中,创作者们经常会引入电影之外的一些元素以提供给观众熟悉和惊喜的感受。这些电影文本之外的对电影的生产与消费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类型电影在国内发展的历史并不长,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类型电影的创作模式还未能获得学界与业界的一致认可,在国内喜剧也缺乏好莱坞那样具有深厚而悠久的文化积累,类型化发展的基础相对要薄弱很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产喜剧的类型化更多是通过“作者性”表现出来的,像冯小刚的“冯氏喜剧”,宁浩颇具个人风格的黑色喜剧,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都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导演对特定主题和题材的持续关注以及标识性的喜剧桥段、个人化的语言风格,一度是喜剧电影类型化探索的主要方向。近几年来,以硬件设施建设的跟进、电影市场空间的提升、新生创作力量的涌现与观影群体的变化为标识,中国电影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为喜剧电影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也深刻影响了喜剧电影的创作与生产。IP热潮、粉丝经济与“互联网+”生态的兴起,都对喜剧电影的类型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喜剧文化相对薄弱的背景下,从“外部性”方面寻求突破,以实现与观众的良性互动,成为当下喜剧电影类型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IP(Intellectual Property)从2014年开始成为了电影行业内经常被提及的高频词,基于IP开发的电影项目不断涌现。时至今日,IP在电影业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产权”的本意。在热门的国产喜剧电影中,虽然不乏《西游降魔篇》《西游伏妖篇》等取材自经典文学作品的影片,也有像《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和《李茶的姑妈》等改编自舞台剧、话剧的影片,还有像《煎饼侠》《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万万没想到》和《十万个为什么》等改编自网络作品的电影,甚至还有像《滚蛋吧!肿瘤君》这样改编自漫画的喜剧电影。基于IP导向的电影项目开发,是文化产品跨媒介经营的结果,被选中改编为电影的IP往往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在原生平台上也积聚了相当数量的粉丝,正是通过IP的中介,影片可以与观众,尤其是粉丝观众实现互动。IP为电影提供的不仅仅是成型的故事内容,更为投资者和创作者看重的还是内容本身所携带的“流量”粉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IP和传统意义上的改编也有很大的区别。IP电影成为热点,是和消费文化、“粉丝经济”的兴起密不可分的。在计算机科学领域,IP指的是一台计算机在网络上的唯一标识,每台连接网络的计算机都需要IP地址来相互区分、相互联系,因此也是网络设备通向目的端的唯一通道。在IP电影的实际运作中,IP在整个电影项目中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整个网络中一个有效连接的节点,通过这个节点,创作者、内容和观众得以有效地连接起来。
在当前的国产喜剧电影中,“开心麻花”团队的IP开发无疑是最为抢眼的。“开心麻花”创立于2003年,同年推出的话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获得了很好的反应,由此坚定了喜剧的创作方向,大概从2012年开始在影视和网络传媒行业拓展业务。2015年,“开心麻花”推出了面向大银幕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夏洛特烦恼》,这部改编自“开心麻花”原创舞台剧的影片上映后很快就成为当年国庆档的一匹黑马,最终斩获14.4亿的票房。接着“开心麻花”又推出了第二部同样是改编自舞台剧的电影《驴得水》,虽然票房还不到2亿,但影片在各个平台都取得了良好口碑。在连续成功案例的刺激下,开心麻花陆续推出《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和《李茶的姑妈》等影片,这些影片无一例外都是改编自舞台剧,在票房上都有不错的表现,“开心麻花”在喜剧电影的创作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模式,业已成为该领域一个很有影响力的IP。
虽然在当前电影界对IP有过很多的讨论和思考,但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过精准的界定,那些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电影生产要素在不同的论述中都被纳入到IP的范畴。针对《美人鱼》这部影片,有论者指出虽然片名所指向的意象符号代表着人类普遍的文化想象,此前也多次出现在电影中,但“与其说大众对奇幻生物趋之若鹜,不如说周星驰才是《美人鱼》观众的期待目标,事实上也构成了最核心的电影IP”。[9]周星驰不仅是影片商业成功最重要的保证,而且这个核心IP的光环足以让很多粉丝观众忽略影片在情节设计、情感处理和影像表达等方面明显存在的漏洞。事实上,建立在核心主创IP的基础上,通过粉丝经济最终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案例远不止《美人鱼》,《一出好戏》《疯狂外星人》等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类似模式的有效性。
IP和粉丝效应在电影行业的大行其道根本上还是源于资本的推动,这种创作模式不仅可以提升电影投资的安全性,也有利于缩短创作周期、较快获取收益。虽然很多影片的票房表现不俗,但影片质量还是经常被诟病,对此也有很多人进行了不乏深刻的反思。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IP的受众基础与票房之间还需要高品质内容生产的有效支撑”,[1]以热门IP作为与观众联结的基础的创作模式本身并非不可取,问题是在此基础上缺乏对影片内容的深耕。正如德里克·汤普森对商业电影流行原因的论述中所指出的,要打造一部流行的商业电影除了需要观众熟悉的元素,还要能够提供“惊喜”。当前的国产喜剧电影创作,在通过外部元素建立与观众的联系的基础上,更需要回归电影艺术的本体,在故事、结构、节奏和影像方面能够给观众带来“惊喜”的审美感受。
三、游戏化、网生性与互文性
近年来,由于银幕数、三四线城市电影院数量和电影传播渠道的增长,喜剧电影的市场空间大幅提升,同时观众群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镇青年、网生代等观众群体的快速崛起,并带动了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观影趣味。面对观众审美趣味的新变化,创作者们“纷纷把目光朝向各种前卫的、另类的、流行的、反传统的、挑战世俗的生活方式、事件和人物,从不同的层次和方面来展现新时代日趋时尚化的生活”。[10]在这种市场导向的驱使下,当下的国产喜剧电影创作更热衷于从游戏、网络内容和社会热点等青年人熟悉和喜爱的元素中寻找故事素材和灵感。
游戏是当下很多喜剧电影热衷的元素。法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让-米歇尔·弗罗东曾经预言:“电影正在或将要涉及电子游戏的领域,它或者将电子游戏翻拍成电影,或者创作一些以电子游戏迷为背景人物的影片,或者从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设计中汲取创作灵感。”[11]他的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得益于数字特效技术的进步,电影与电子游戏的融合成为了可能,并促成了游戏电影化与电影游戏化的双向融合。游戏化元素对当下国产喜剧电影的渗透不仅体现在游戏内容、技术手段和视听表现等方面,甚至在叙事结构、情节设计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17年上映的影片《傲娇与偏见》是近年来国产喜剧电影中游戏化特征体现得很明显的作品。影片一开头用动画加独白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这既是男主角朱候对正在精心准备的“求爱仪式”能够获得成功的美好幻想,也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首先,网络游戏的玩家们会很自然地将这种漫画加解说的方式与很多网络游戏中的开篇动画联系起来;其次,可能是为了强化观众的这种联系,在文字的解说中看似不经意,实则刻意地一口气抛出了“武动乾坤”“斗破苍穹”以及“吞噬星空”等热门网络游戏和网络小说的名字,并借此在影片和观众,尤其是游戏玩家观众之间建立起“熟悉而又陌生”的互动关系。在屠楠楠被主编逼着更新网络小说和“小鲜肉的十种吃法”等桥段中也采用了类似的处理,影像也一改常规,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游戏感。2018年上映的影片《唐人街探案2》的开篇也设计了一个古装的探案情节,而后揭示了其实是主人公秦风在排队等候时玩的游戏里的情节,这似乎在暗示观众这款“犯罪大师”(Crimaster)的游戏将会在整个故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游戏化思维当下在设计、教育等领域正成为一种潮流。所谓游戏化思维,指的是在非游戏的领域内引入游戏设计方法和游戏元素的思维方法。据报道,腾讯平台推出的两款热门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与《和平精英》的日活跃用户都在5000万以上。游戏化思维的盛行固然和游戏产业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不仅游戏的用户数量庞大,更为重要的是游戏用户的粘性普遍都很强。由传奇影业和暴雪娱乐出品的改编自经典同名游戏的影片《魔兽》上映后,很多游戏玩家都在第一时间观看了影片,甚至有玩家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要看10遍。为什么游戏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刘梦霏在一篇名为《游戏的精神》的网络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作者看来,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细化等方面的原因,个体对完整生活方式的认知是断裂的,而游戏可以让人跳脱现实世界的设定,暂时地回归到集体潜意识中,去感受狩猎采集式的完整生活方式。或许正是因为游戏所遵循的是人类身体底层的需求和思维模式,才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对游戏化思维进行更大范围的商业开发。
游戏化思维对电影的渗透主要还是体现在叙事结构和情节设计方面。诚如汤姆·甘宁所指出的:“每一个时期的电影也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建构它的观众。”[12]在数字化时代,游戏设计中的角色养成、探索模式、任务系统、奖励机制和排行榜等都对电影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体验。在影片《唐人街探案2》中,被唐仁以结婚的名义骗到纽约的秦风,最终决定留下来参加这场“国际侦探大赛”的重要理由就是这款“犯罪大师”的游戏。不仅在游戏排行榜上靠前的重量级玩家都参与到了这场探案比赛中,而且真正的凶手就是在排行榜中排第一的Q,在对探案推理过程的叙述中也始终夹杂了“争排位”的成分,这种游戏化的叙事结构与情节设计让观众能够深度地参与到故事中,仿佛和影片的主人公一起在参与游戏的竞争,从而获得别样的观影体验。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上映之后,同名的网络游戏也立即面世了,成功实现了从游戏到电影、再从电影到游戏的双向流动。
当前国产喜剧电影中深受游戏影响的例子并不在少数,游戏化思维融入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所带来的不仅是类型的拓展和素材的充实,且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电影的叙事结构、情节设计、视听呈现和美学特征,并最终改变观众的观影体验。当前的喜剧电影对游戏化手法的探索还明显不够深入,游戏元素、游戏化手法与故事叙事之间经常存在断裂,很多时候游戏在影片中只是充当了唤起观众“熟悉的记忆”的功能,或者说是充当连接电影和观众的“界面”。事实上,很多网络平台和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和现象也经常被一些电影借用来承担类似作用。如董成鹏导演的首部大银幕作品《煎饼侠》几乎可以看成是之前搜狐自制网络剧《屌丝男士》的衍生品,得益于网络剧积累的庞大受众,这部投资成本仅2000万的影片最终以11.59亿票房收官。2017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羞羞的铁拳》,是“开心麻花”团队继《驴得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改编自舞台剧的喜剧电影,首周票房突破10亿元,一举超越成龙主演的中美合拍动作片《英伦对决》、王晶导演的《追龙》等被市场普遍看好的作品。影片在“男女身体互换”的主线之外,还涉及了打假拳、虚假新闻、网络直播、明星炒作等热门的社会话题。从游戏、网络和社会话题中寻找创作素材已经成为当前喜剧电影创作中的常见手法,虽然这种创作模式能非常有效地和观众建立起“熟悉”基础上的连结,但也会使影片陷入故事叙述断裂,甚至碎片化的风险。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就曾批评电影《夏洛特烦恼》就是一部杂乱的综艺短剧,“是导演对电影艺术、电影美学的不尊重”。[13]
作为当下国产电影版图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喜剧电影也是国产电影中类型化程度最高的片种之一。在整体社会环境、媒介环境、电影生态尤其是观众结构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当下的国产喜剧电影继续沿袭着荒诞离奇的情节设计、草根人物、黑色幽默的场景叠加等近年来逐渐形成的大方向,同时通过跨平台的IP改编等方式不断拓展喜剧创作的素材空间。这一方面导致喜剧与其他类型元素之间的不断融合,使得喜剧的亚类型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生产出来的喜剧电影带有很强的游戏性、网络性和互文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在创作过程中过于强调题材的拓展和形式的新颖,而忽视了在喜剧思维和喜剧精神层面的深度挖掘,虽然喜剧电影整体的票房表现很抢眼,但总是被评论和媒体诟病艺术层面的诸多缺失。诚然,当下喜剧电影的创作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但如果回到电影创作与观众互动的视角,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观众观影经验的提升,仅仅通过题材开发和形式创新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创作者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寻求改变。媒体和评论也不妨对国产喜剧多一点耐心,“让子弹再飞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