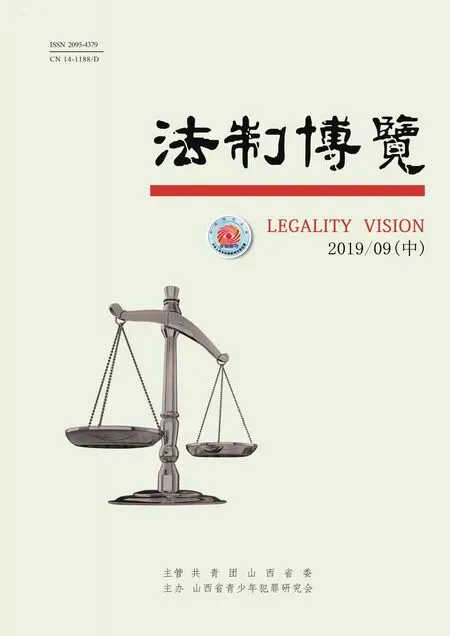不正当竞争行为解读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
罗玲苑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2017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颁布并实施24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旧法)作首次修订;2019年4月23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一次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了修订。
《反不正当竞争法》两次修订基本维持了旧法的立法体系和结构,修改内容包括:完善相关概念界定,如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秘密;调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厘清了与包括《反垄断法》、《商标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等部门法的关系,对原有不正当竞争行为做了细化;完善了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加大了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力度。
总的来说,旧法列举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但规定较为粗略,适用起来还有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至第12条共列举了7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删除了旧法中企业限制性交易行为、行政性垄断行为、搭售行为、低价排挤行为和串通勾结投标行为的法律规定,增加了关于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
一、厘清了与《反垄断法》、《招标投标法》的关系
众所周知,《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共同肩负着维护我国市场竞争秩序的使命,共同构成我国竞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价值取向却各有侧重:反垄断法主要关注竞争的自由性,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更注重竞争的公平性。没有竞争的自由就谈不上竞争的公平,因此自由竞争是公平竞争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反垄断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效实施的基石。[1]然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在先,《反垄断法》颁布在后,导致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可能存在的垄断行为都要放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进行调整。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前,两部法之间必定存在交叉和重叠,2017年修订该法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厘清和切割两部法在调整对象和法律上的竞合,从而实现内容上的相互衔接。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删除了旧法第6条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条款、第7条关于行政性垄断条款,第11条关于低价倾销条款以及第12条关于搭售条款的规定,将这四个条款回归《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厘清与《反垄断法》的法律竞合问题,成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体例上的独立性。同时,考虑到《招标投标法》对串通招投标行为已作规制,删除了旧法第15条关于串通招投标条款的规定,厘清了与《招标投标法》的关系。
二、衔接《商标法》,修订完善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定,更好地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法》内部条款之间的逻辑对接
(一)衔接《商标法》,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删除了旧法第5条第(1)项有关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行为的规定,因《商标法》第57条、第60条对此已作规定,将其回归《商标法》调整,厘清与《商标法》的关系。
(二)将旧法第5条第(二)项规定的“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修订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同时在新法第6条第(二)和第(三)项中新增加了社会组织名称、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其他内容。既扩大了受保护商业标识的范围,也不再限定以知名商品作为前提,将其修改为“有一定影响”。
(三)删除旧法第5条第(4)项关于“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的规定,直接将该内容衔接到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关于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中对其进行调整,从而在条款内部实现了逻辑对接。
三、修订完善商业贿赂行为
(一)删除了关于回扣的规定
回扣是商业贿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旧法第8条商业贿赂条款将回扣作为一项单独的贿赂行为予以规定和明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的手段得到了升级和演绎,虽贿赂手段更隐蔽和多样,却掩盖不了行贿之实。故2017年修订摒弃回扣作为单独的贿赂行为方式,转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来概述,这种表述既将回扣纳入财物的范畴,又能将其他通过隐蔽性贿赂手段实施的贿赂行为加以调整,更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
(二)将商业贿赂的受贿主体细化界定
一般来讲,在商业贿赂行为中,行贿主体通常是经营者,受贿主体则不特定。旧法将“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认定为商业贿赂的对象。2017年修订将交易相对方排除在商业贿赂的对象之外,将商业贿赂受贿主体细化为三方:一是交易相对方的工作人员;二是受交易相对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三是利用职权或者影响力影响交易的单位或者个人。
(三)将经营者的员工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纳入规制范围
旧法并未明确经营者的员工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新增一款,“经营者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的,应当认定为经营者的行为;但是,经营者有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的除外”。据此,将经营者的员工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纳入该法的规制范围。
四、厘清与《广告法》的关系,明确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内涵外延,对虚假宣传的具体内容予以细化,规制电子商务领域的虚假宣传行为
(一)厘清与《广告法》的关系
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8条规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明确在此种情况下,优先适用广告法,厘清了与《广告法》的关系。
(二)明确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内涵外延
旧法的表达中将引人误解用来修饰虚假宣传,在实务操作和理解过程中容易误以为虚假宣传的前提必须是引人误解,缩小了打击的适用范围,此并非立法本意。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此作了重新阐释,该行为既包括虚假宣传,也包括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如此一来,既避免了适用上的混乱理解,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打击虚假宣传行为,维护正当的竞争环境。
试验用土取自南京市某基坑场地,取土深度6~8 m.该土的主要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见表1.试验前将土在60℃下烘干至恒重,粉碎过2 mm筛,向过筛后的土壤中添加Pb(NO3)2,Pb在干土中含量为5 000 mg/kg,5 000 mg/kg为我国工业污染场地Pb污染典型含量值[10],选择Pb(NO3)2作为污染介质是因为Pb(NO3)2具有较高溶解度(较强的阳离子活动性),且硝酸根具有惰性,对水化反应干扰很小[11].再向污染土中添加去离子水使土含水率为22.34%,拌合均匀后密封,在室温下焖土30 d,使Pb(NO3)2与土壤反应充分.
(三)对虚假宣传的具体内容予以细化,经营者刷单,炒信和虚构交易等行为得到规制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该领域的虚假宣传问题也日益凸显,甚至出现了专门组织虚假交易帮助他人进行虚假宣传的情形,严重损害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细化了虚假宣传的具体内容,把对商品的“销售状况”和“用户评价”也纳入进来调整,经营者对此亦不能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此更好地打击电商领域的虚假宣传行为。在此基础上,新增一款专门用来规制组织虚假交易以帮助其他人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此外,在该法的第20条对于其责任做了衔接:“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以此更好地规制电子商务领域的虚假宣传行为。
五、完善商业秘密的含义、手段,扩大该行为的责任主体范围,强调监督检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其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
(一)完善“商业秘密”的含义
2019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对商业秘密作了更完善的界定: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对比之下,新的概念删掉商业秘密的营利性要件,修改为“具有商业价值”。同时,给予商业秘密的概念一定的适用空间,不再局限于列举出来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而是用“等商业信息”来概括,扩大了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领域。
(二)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
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一)项保留了原来的盗窃、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将利诱修正为贿赂和欺诈,利诱并非法律概念,适用的时候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贿赂和欺诈则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以及《民法总则》中都有界定,通过修正可避免在司法适用中对利诱一词理解的非统一化,也能很好地与其他部门法中的相应概念做好衔接。同时,考虑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适应信息化发展需求下商业秘密的保护,2019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9条,将以电子侵入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也纳入该条调整和规范。
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留了旧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手段的第(二)和第(三)项,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项作为第(四)项:“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扩大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责任主体范围
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保留原有的经营者和“明知或应知”的第三人作为责任主体的同时,扩大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责任主体范围,增加了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工、前员工、其他单位或个人,员工侵犯经营者商业秘密的行为得到规制,更有利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同时,2019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加了“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扩大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责任主体范围。
(四)强调监督检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
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5条规定:“监督检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强调监督检查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加大监督力度,保守商业秘密,全方位规制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将更多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
(五)加大了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该法两次修订都加大了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增加了法定赔偿数额。
根据2017年第一次修订的第21条规定,侵犯商业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般情节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其罚款数额也由旧法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增加到了“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根据2019年第二次修订的第21条规定,一般情节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其罚款数额由2017年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增加到了“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其罚款数额也由2017年的“五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增加到了“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六、完善不正当有奖销售的表现方式
(一)丰富完善有奖销售的表现方式
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完善了不正当有奖销售的表现方式,“利用有奖销售的手段推销质次价高的商品”被修正为“所设奖的种类、兑奖条件、奖金金额或者奖品等有奖销售信息不明确,影响兑奖”。这一规定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不断演变的有奖销售形式。按照新法对该项内容的修改,理解如下:经营者对有奖销售的信息有明示的义务,依此保障消费者在消费之前的知情权,尽可能地避免因经营者对有奖销售信息模棱两可产生的消费误解甚至欺骗性的消费,从而扩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
(二)将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提高至5万元
2017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将抽奖式有奖销售最高奖的金额提高至5万元。这主要是结合旧法实施24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消费水平、物价水平的提升等方面的因素考虑修改的。[3]
七、完善细化诋毁商誉行为的手段,增加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完善细化诋毁商誉行为的手段
旧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把捏造、散布修改表述为编造、传播,将旧法的虚伪事实修改为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修改后的表达逻辑上更协调,避免了虚伪事实内部逻辑的矛盾冲突,事实一般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现象,与虚伪存在词意上的冲突,相比之下,虚假信息一词表达显得更为严谨妥当。对诋毁商誉行为的手段和对象做更明晰的界定,也利于实践中司法部门对该行为的认定。
(二)完善了商业诋毁行政责任的规定
旧法仅对诋毁商誉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却并未对该行为的法律责任作出相应的规定。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3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11条规定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行为增加了法律责任的规定,改变了旧法对该不正当竞争行为没有罚则的尴尬局面。
八、新增对互联网领域利用技术手段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款
(一)“概括”+“列举”+“兜底”的立法模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涉及互联网不当竞争的案件也越来越多。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的其中一个亮点便是增加互联网方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将其归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起规制调整。
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经营者利用网络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本法的各项规定。”此处的本法各项规定,不仅包括该互联网专条,还包括该法其他条款。该条第二款列举了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方式包括“流量劫持”、“修改、关闭、卸载他人产品或服务”和“恶意不兼容”。同时考虑到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可能会出现当前不正当竞争类型所涵盖不了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故在本条的第二款第(四)项增加一条兜底条款,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更好地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对“恶意不兼容”的争议
有关“恶意不兼容”被认定为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此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网络产品与服务之间的不兼容,既可能是因为技术原因导致的,还可能是因为经营者根据竞争关系特意设置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在未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参与市场竞争的经营者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市场竞争者并无“兼容”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义务。“从法律上来说,对“恶意”的认定,一般以是否故意为标准。而事实上,所有的竞争手段,归根到底其实都是经营者故意而为之的。将“恶意不兼容”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难免会将一些正当的商业策略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到底如何适用“恶意不兼容”条款,笔者认为还有待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践对“恶意”作进一步的司法界定。
综上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接连历经两次修订,本身已是一大进步。虽两次修订基本维持旧法的立法体系和结构,事实上也确实厘清了与《反垄断法》、《商标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等多个部门法之间的内在衔接,也对原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了细化;同时完善了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至于两次修订没有兼顾到的内容,可以结合日后的司法实践,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抑或当新问题层出不穷,必要时再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做大修。作为法学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我们仍须不断探讨和研究《反不正当竞争法》,力求弘扬法治精神,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