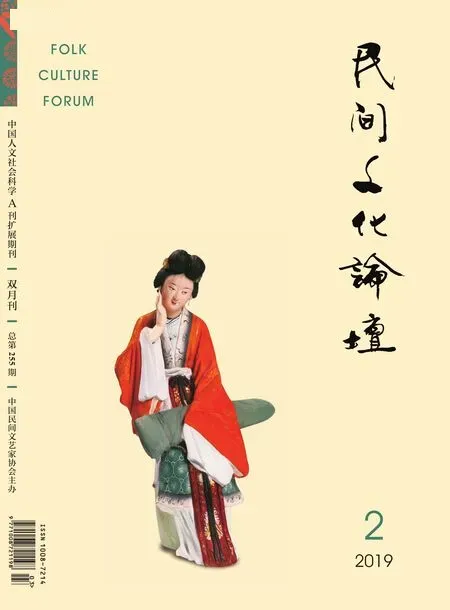生态的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视域下的“非遗”
萧淑贞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区别于大自然的人类所有活动及其产物都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狭义的文化则指除了经济以外的活动及其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是“道”不是“器”、是“体”不是“用”,它渗透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其他可持续发展的维度之中。有的传统文化形式如建筑,人们可以看见;有的如道德、风俗等是看不见的。传统文化的力量虽然无形,但更深刻、持久,它蕴藏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在乡土中、乡村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如果说乡村是国家的基础,那么乡土传统文化则是基础的基础、根本的根本。
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与中华文明的复兴实际是一体三面。中华文明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母体和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灵魂和根脉。对传统文化自信,才会有振兴乡村的国策。振兴乡村是综合的系统工程,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目标一定伴随乡村振兴。只有乡村生机勃发,中华文明才能实现真正复兴。
那么,文化自信应对传统文化中的什么自信?我们现在占据主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知识体系?传统和乡土文化对于转向生态文明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生态文明视域下“非遗”的价值和可能的发展方向如何?
一、传统与乡土:另一种文化和知识系统
在近三四十年间,出现频次最高、广为大家熟悉的词汇莫过于“发展”和GDP。在工业化背景下,人们对于乡土的印象多是落后、愚昧,乡土与传统所代表的知识和文化体系也被贬抑。我们目前主流的文化、知识体系和系统①参见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还是“西化”的工业化体系,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和发展道路,也是近代以来“中西之争”的延续,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的战略和国策其实是对于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的一次重新选择和再出发。
在工业社会中,伴随全球化的快速蔓延,基于工业化的“科学”知识以压倒性的优势碾压在地的本土知识和文化。从文化的视角看,我国工业化的知识体系自近代以来在远离本土、传统和乡土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力文化多样性》报告指出:“科学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环境的互动、价值系统和世界观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然而,“科学只是诸多知识系统的一种知识,其他的许多知识体系根植于不同的文化,滋养、支撑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知识遗产,它们对实现国际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性的作用仍然被低估了。对在地知识应持一种更加复杂和细致入微的态度,应该认识到,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没有单一的、同质化的‘知识’,如果我们要面对当前的环境挑战,就需要跨文化、代际间不同的知识体系共同参与,并根据性别、职业和种族有差别地去处理”,而“利用当地和本土知识的部分困难在于,它们往往是隐性知识”。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世界报告,2015年,第三部分“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第225页。隐性知识难以证明给人看。比如,民间和中医都有在端午节当天太阳出来之前采摘艾叶的惯习,这样做出来的艾条和艾香才有疗效。用现代科学的手段目前无法证明这短暂的时间与疗效之间的关系。此外,对于中医、中药的认识也体现了隐性知识的被忽略,以及“科学”知识对本土文化的挤压。与西医依赖于生硬、冰冷的指标不同,中医重视生命的过程和联系。真正高水平的中医廉价、高效,但中医长期被贬低、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解决百姓的医疗健康问题,需要走出对于西医的简单迷信,走出对于科学主义的迷信。在本土和乡土文化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在“科学”的思维参照下,这些隐性知识都被当作愚昧的迷信,被边缘化,从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和教育中消失了。
因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不同,在两种文明的理念和形态下,文化和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显著特征。从工业化转向生态文明不只是简单的生产方式的转型和改变,而是系统的改变,需要重新确定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将发展目标转向以人的发展和幸福为主,从重“物”向重“人”转变,“人”的发展将取代以“物”为中心的理念,被置于较高的地位。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将被日益重视,支配工业化的理念和工业化的伴生物如人类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价值中立以及注重竞争、成功的观念,将向以人文主义和精神为基础的合作、互助转变,因为人文精神是“意义”和幸福的源泉,也是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生态文明的理想图景中,社会成为重视联系、情感、团结互助的生态的社会;多样性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和人的精神发展;人自身不再陷于身心的分裂之中,身心合一尤其是人的精神和道德素养的提升,会使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而生态的环境是实现以上三个维度的目标之后的自然结果。
因此,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不亚于一场革命,一次新长征。这个转型除了显性的体制、机制的转变,更需要内在的思想、认知方式的根本转变,本质上是文化、知识体系的全面转型。到哪里去寻找整体转型的文化资源和动力?那部分曾经被视为落后、愚昧的本土、乡土文化能够帮助实现这一转型。
本土、乡土化的知识和文化体系因具有互助、包容和尊重的人文主义特征,具有修复、疗愈工业文明背景下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弊端的资源和力量。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系统性问题,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文化和知识的系统转型,需要回到本土的知识和文化体系中寻找疗治的源泉和力量。工业化的危机与问题更加凸显了乡土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维度上的价值,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重估本土和乡土在社会、文化、教育和精神层面对世界、国家和个人的价值和意义。在生态文明的革命和长征中,本土和乡土文化将重新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以乡土文化的复兴作为载体支撑我们向生态文明转型。
其实,不只中国如此,全球都有类似需求。在工业化的深重危机中,乡土自身也在不断觉醒,焕发自信和力量,更多的本土文化和知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力量而重获新生,它们在教育中的价值也被重新认识和重视。“被赋能的个人和社区参与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也能够体现他们的文化形态和团结一致,这种方式以他们的文化表达、价值观和看法为基础,因此可以恢复个人和社区尤其是土著居民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自豪感……然后‘认同’(identity)就可以从防守性的站位转化为有利于实现他们自主定义和可持续的发展目标的‘赋能’(empowerment),在这个意义上,‘有认同感的发展’就会变成‘有尊严的发展’。”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世界报告,2015年,第三部分“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第225页。
因此,乡村振兴的意义不只在于为了乡村自身的发展,也是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础。当中国在工业时代的巨大影响下开始转向生态文明的时候,需要特别专注乡村社会的文化和技艺的复兴。在这个角度和意义上,在乡土中蕴藏的“非遗”就属于这部分文化和技艺,“非遗”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将会起到独特的作用。
二、生态文明视角下“非遗”的价值
如果从经济效益和直线史观的视角看,“非遗”好像注定会被历史淘汰,但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中,“非遗”会获得自身价值的新定义,因为它们蕴含着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
鉴于生态环境、有机农业、食品安全等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人们对于高质量、有品位的生活的追求也日益高涨,在衣、食、住、行、游、购、娱等跟人们生活和乡村息息相关的领域,未来可能会出现以下变化和需求:
(一)纺织品和衣物:化纤→棉麻丝、布鞋;
(二)(农用)肥料、药剂:化学制剂→天然有机的菌肥、生物制剂;
(三)(农副产品)食品加工:工业化→绿色加工和手工酿造:酒、面粉、豆腐、酱油、醋、茶叶等;
(四)日化洗涤:化学品→手工酵素及其制品;
(五)护肤和化妆品:化学品→植物纯露、精油等;
(六)乡村手工技艺:布艺、陶艺、木艺、竹艺、铁艺、蚕艺、绣艺等;
(七)居所:乡居、山居;
(八)教育:自然教育、灵性教育、生命教育、游学体验、夏令营等;
(九)精神和灵性成长:禅修、静修。
以手工技艺为例,它是乡村拥有的独特资源优势,也与乡村振兴高度相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的五项“非遗”的第五项是“传统手工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传统技艺”列在第三项。手工技艺不仅是一种绿色技能,还蕴藏着精神、审美和生态生活的重要特质,具有发展生态文明必需的社会建设、文化教育、精神和审美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
首先,手工技艺是一种绿色技能。手工制品大多在大自然中就地取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环境的惊扰。在制作过程中,倾注、传递着制作人的心性和温度,这种生命与生命的交流保留了大自然向人类馈赠的能量,因此,手工食品给人们带来的食物本来的美好味道不是精细加工的工业化食品所能匹敌。食物的品质和功效也大多与时间和地域有关。药食同源的“九蒸九晒”系列蕴藏着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智慧,花很少的钱就能自己调理身体,可治未病,防治各种病症。而到大医院去治疗,小毛病也动辄需要花费上千,还疗效甚微。在草木染中,各种染料取自天然的植物,用植物替代化学染料,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而植物不但可以染色,也可疗愈身体。
第二,手工技艺中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的劳动本身也是社会建设的一种方式。在乡村,主要的产业和劳动形式是农耕和手工,这些劳作主要靠手,且耗费体力较多,通常需要几个或一群人通力协作才能完成。比如制作麦芽糖,为了最大限度地做出地道的美味,需要大家轮流上阵,反复推拉盘缠,最后,趁麦芽糖还有温度、没有变硬以前,大家一起剪成小段。如果没有集体的力量,麦芽糖很快变硬,就无法剪成小段,类似这样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能够培养人们团结、亲密的社群关系和集体力量。
第三,与很多工业化、标准化的产品不同,“非遗”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也是宝贵的文化传承和教育的资源,也会在满足人们对生态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中得到活化。美国著名作家温德尔•贝瑞说:“我渐渐读懂了土地真正的需要:在每一个角落,它需要的就是多样性。我所见识的每一片美国乡村,最需要的就是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农作物和牲畜品种的多样性、人的技艺和方法的多样性,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以更加敏锐、更加优美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善用一方水土。”①[美]温德尔•贝瑞:《为多样性而辨》,汪明杰译,《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11期。
第四,“非遗”具有难以替代的艺术审美特质,可以弥补工业化的“审美匮乏”。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人类将来一定会不断提升精神、艺术和审美修养。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精神高度发展的“生态人”,其中,审美是培养生态素养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能力,而审美只有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才能培养、展现出来,“审美能力(esthetic appreciation)的下降是不利于生态素养的第三个因素。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丑陋处之泰然,也不能有效抵抗丑陋的提供者:城市开发商、企业家、政府官员、电视制片人、木材和矿产公司、水电公司和广告商等。但是,丑陋并不只是审美问题,更是人与人、人与土地的关系失调的信号。”②[美]大卫•W•奥尔:《生态素养》,萧淑贞、汪明杰译,《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11期。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手工技艺在修身养性、培养“生态人”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降低物质欲望的“生态人”,手工制作是人与心灵联结的过程,感官内收,心才能够更沉静地感受世界,“非遗”手艺人大多很安静就是这个原因。手脑心的配合协调、左右脑的平衡对于儿童教育以及人们健康、幸福、灵性发展的重要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揭示。
三、“非遗”技艺的复兴、传承与乡村振兴
“非遗”中有很大一部分手工技艺源自农耕生活,因此,“非遗”的转化和再生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关切。
传统和乡土文化中蕴藏着基于“天人合一”的生活常识和生活技能,传达了有关农业生产、健康医疗和教育的知识和技能,这一部分知识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也是传统文化中有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但是,除了一部分农耕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地方,在很多地方这一大部分知识目前已经被遗忘,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振兴乡村,首先要复兴乡村赖以繁荣的文化和知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地实现这一目标。
振兴乡村,文化先行。文化不仅带来自信、认同,也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赋予人们生活的“意义”和“意思”。在这个主题下,乡土记忆和技艺在乡土的觉醒、自信中会不断展现自己的意义和力量。只有这样,多年来被抛弃的农村才能提振信心,聚拢人气,积蓄力量,找回自己的精气神。令人欣喜的是,社会各界的人们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方言电影、村史、农耕博物馆等挖掘、坚守乡土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传统和乡土文化越自信,乡村振兴就来得越早,乡村的发展就越好,因为在人们心中培养一种地方情结、归属感和共同的愿景,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让人人拥有基本的生活条件。
以足够的自信相信这部分文化的价值,经改造再生,充分挖掘它的价值,无形的文化可以创造难以计数的经济效益。①参见萧淑贞:《发现人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0页。跟土地和乡村有关的产业,自身会形成一个生态链条,撬动一个,就会带动其余,由点及面,激活整个生态产业和生活系统。我们将在那些被人遗忘的手工制品、没有添加剂的有机食品等衣、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全方位地展望未来的产业变化,看到乡村产业复兴和“非遗”活化的希望。
“非遗”的手工技艺是传统文化和乡土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的宝贵的生态生活和文化、教育资源。相比教育的方式、方法和载体,乡村教育的目标、主题和内容更重要。做到这一点,以振兴乡村为目标的教育必须改变现有的教育观念,让被忽视多年的源自乡土的手工技艺通过进入教育体系得到传承,让成人教育重新走上前台。找回这些丢失的本土、乡土文化和技艺,需要通过教育传承来实现,为乡村培养人才,而不是只让乡村输出人才。乡村振兴一定伴随着有机农业和手工业的复兴,“非遗”手工技能的传承培训培养的正是乡村产业复兴和乡村建设需要的人才。
而乡村的振兴和重生不单单是为了乡村自身的发展,还将帮助人们提高生活品质,提升审美和精神品位,为城市更新提供资源和动力。四川明月村以古窑的修复为切入点,吸引了若干文创人士和文创项目,形成文创产业,带动了生态农业的转型以及附带而来的乡村旅游,激活了整个村庄。四川明月村的艺术审美正是通过手工艺、手工业,通过生活和产业,在当地村民的身上实现的,此为乡土文化和技艺是乡村振兴的根和魂之一例。通过文创和乡创,明月村把传统的、生活的、实用的手工业提升为艺术审美的生活,将乡村变成了满足人们艺术审美需求的场所,无论对于市民还是当地村民,都是一种艺术审美和精神的提升,真正将乡村建设成了人们精神的故乡。
四、生态的生活:“非遗”活化的内生动力
在工业化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人们对“非遗”的印象多是在博物馆中安静得有点落寞、落后的旧时记忆,“非遗”的现代活化面临如何从博物馆走向生活的挑战,“非遗”未来的发展是否能够突破这个困扰?
“非遗”和乡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面临多重问题的时候,被遗忘多年的乡村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知识分子不断呼吁乡村复兴,市民中则出现了乡村旅游和乡居的热潮。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复兴是一种徒然无力的怀旧、乌托邦式的幻想还是基于理性思考的客观认知?在应对现代性问题层面,如何重新思考定义乡村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认为,乡村的吸引力不是生产,是生活,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乡村生命力的所在。①张孝德在2017年4月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在浙江省乾潭镇胥岭举办的“生态乡村建设案例”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萧淑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乡村启航——生态乡村建设浙江胥岭研讨会报告》, “三生谷生态村” 微信公众号,2017年5月24日。
因为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我们常常见到有市民群体来到近郊,自己种粮种菜,由被动消费变为主动地参与到生态生产的实践中,也有人渐渐看透了所谓学历精英竞争背后的焦虑或成功背后的无意义,认识到正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的隔膜疏离让人们渐渐失去了幸福的感觉,“一种极为物质理性和短视的人生观主导的城市文化正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在思想和情感上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因为身心的分离而陷于种种疾病困扰”②金振豹:《中国需要再来一波上山下乡运动》(一),“静修与读书”微信公众号,2017年12月14日。。那么,在什么地方,还能够重新找到这些联系?有一群人找到了乡村,祖先在几千年前为我们创造的一群人的聚居地。
这个新村民群体是在精神和心灵上都有需求的自觉、觉悟的人群;他们在乡村找寻、获得了当今城市现代生活中缺失的部分,不同于资本追求快速套现的资源掠夺,他们带着尊重、欣赏与乡村良性互动,代表一股善意的建设性的力量;他们多半喜爱传统文化,携带了乡村文化链条上能够激活乡村、为乡村注入生机活力的技能;他们自带城乡间的联系,能够促进城乡结合、互通有无的资源流动;最后也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自己成为乡村的一员,生活在村里。因此,在他们身上集合了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的要素和文化融合,结合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优势和联系,在两种文明的交融中,正在尝试创造一种新文明形态下的新生活。这种生态的新生活,生活简朴,却精神充实,集成了既平民又贵族的生活方式,是乡村激活、创新的源泉和力量——形成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式,本身成为改变乡村的动力,同时也是被工业化破坏之后的社会重新建构社会的努力。
这样的生活选择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自救:“当人们不再迷信城市所谓优良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当越来越多在城市里受过理性启蒙的知识青年和中年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对更为合乎人性之需求及尊严的生活的向往,回到因为中国历史上种种运动和分隔城乡的政策陷于经济及文化上的双重贫困的乡村当中去施展自己的创造力,去办学校,去发展有机农业,去创造富有文化和艺术水准,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环境和社区,让科学和艺术为富有精神性的传统文化注入活力和生机,让每一个偏远的角落都因为其独特的美和更大范围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也让不堪人口和环境之重负的城市得以缓解压力,并效仿乡村去重建自己的生态,这将使中国社会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和兴盛,也将使中国的文化真正向整个世界呈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并有力地推动这个世界的持久和平和繁荣。的确,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也正在迎来一大波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只是这一次,它将不是因为某种片面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专断决策,而是出于人心的觉醒以及广大受过良好教育,而又未丧失对于真正合乎人性之生活方式的觉知和想象的人们奋起自救的努力”。①金振豹:《中国需要再来一波上山下乡运动》(一),“静修与读书”微信公众号,2017年12月14日。
如果说来自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都是外部的推动力量,追求美好的生活可否被视为一种内生的动力——一种经原本外在的力量转化而来的内生动力?数亿民众生活方式的转变能否成为“非遗”活化和乡村振兴的保障?在这个日渐扁平、平民化的时代,可否由普通民众改变思想观念,自发、自觉地去改变生活方式,进而倒逼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游、购、娱能否成为推动历史变革的力量?
回答是肯定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和世界一定是人人参与、人人贡献的平民运动,同时又对个体的精神修养有着较高的要求。生态文明需要的价值观和知识类型也不是强势的资本和权力主导的为大工业服务的知识和价值体系,而是惠及大多数人的多元、包容、互助的知识体系。民众创新生活方式、向生态文明转化的身体力行的生活会在深层次更加根本地促进社会的知识更新和转型,产生新的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的知识。国际生态村在青年当中很有吸引力和影响力,表面看貌似是一群人离群索居、寻找远离尘世的桃花源,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省思:世界七十亿人口如何才能和平融洽、不破坏生态地共同安居在地球上。生态家园可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解放原有的固执的、人们视为当然的思考和生活模式,从重视生态环境、友善农法、蔬食低碳的生活观、身心灵的喜悦与自由、互助合作,迈向自给自足的永续可能性,这是对于“我们这一代最光明的愿景”的描绘。在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中,民众的觉醒和社区的参与会使人人参与、人人贡献的平民性、在地化和普及性得到可能前所未有的彰显。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民享、民有的平民化运动。
因此,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成为乡村建设和“非遗”活化的新动力,追求一种生态的生活方式让新村民成为了乡村的新主人、新主体的一部分,这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并不仅仅只是身份、态度的不同,而是决定了这股力量的性质具有一种内在的主体性,不是外在的客体。与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的不是义无反顾悲壮的激情、理想、牺牲的高尚,也不是政府推动容易出现的强势、隔膜,他们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乡村的空间自然融合,从容、轻松地来到乡村生活。四川明月村的新村民说,“我到乡村就是来生活的,我自己的生活好了,乡村自然就建设好了”②明月村代表陈奇在2017年4月1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在浙江省乾潭镇胥岭举办的“生态乡村建设案例”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萧淑贞:《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乡村启航——生态乡村建设浙江胥岭研讨会报告》, “三生谷生态村” 微信公众号,2017年5月24日。。“非遗”可以充当乡村振兴的引擎和发动机。明月村有古窑、染织这样传统的手工艺,在古代它只是一个手艺,烧的都是老百姓日常用的碗和泡菜坛子等,古代也没有文创的概念。通过“非遗”与现代文创结合,吸引了一批城市来的新村民,复活了传统文化的产业链条,使手工、草木染的衣服、鞋子、琴棋书画、篆刻等等都处在活化的状态。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多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间,多是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一种文明形态对应一种生活方式,农耕文明的生活条件不太便利,但人们勤俭、节约,少数贵族的艺术审美、精神生活达到过很高的水准;工业文明的生活舒适、便利,但不生态,消耗、奢侈、炫富、浪费。我们期待的生态文明的生活一定是吸取了二者之长的兼容并包,既要兼顾舒适、便利,还要有艺术、精神意义上自由的内在品质。
回到乡村的人群能够成为建设乡村的直接力量,远离乡村的人们的生活其实也并未真正远离乡村,如果人们能够在衣食住行游购娱的诸多方面主动、自觉地选择生态的生活方式,“非遗”活化和乡村振兴都会在人们重新自觉选择的生活中获得深刻、持久的内生动力。人们对于生态生活的追求向往正是“非遗”活化和乡村振兴的动力所在,改变生活方式可以促进实现生态文明,“非遗”也会以一种新的面貌重新活在我们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