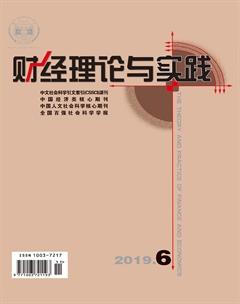生育选择、人力资本和中等收入陷阱
徐达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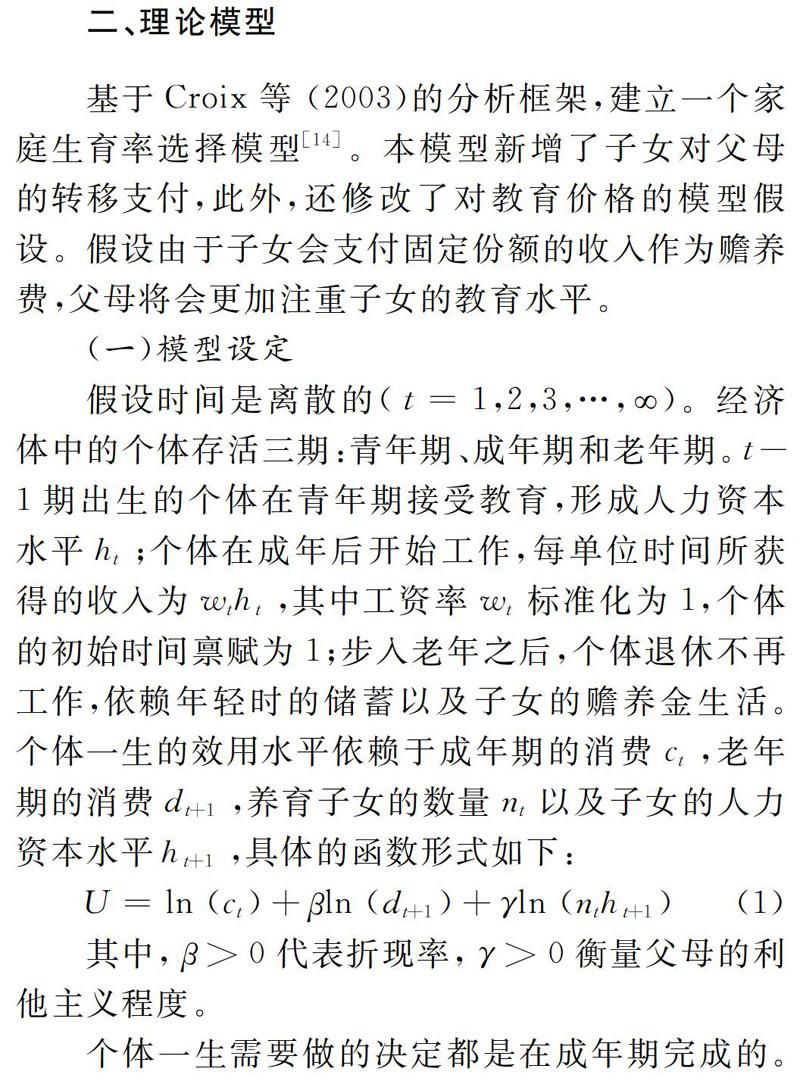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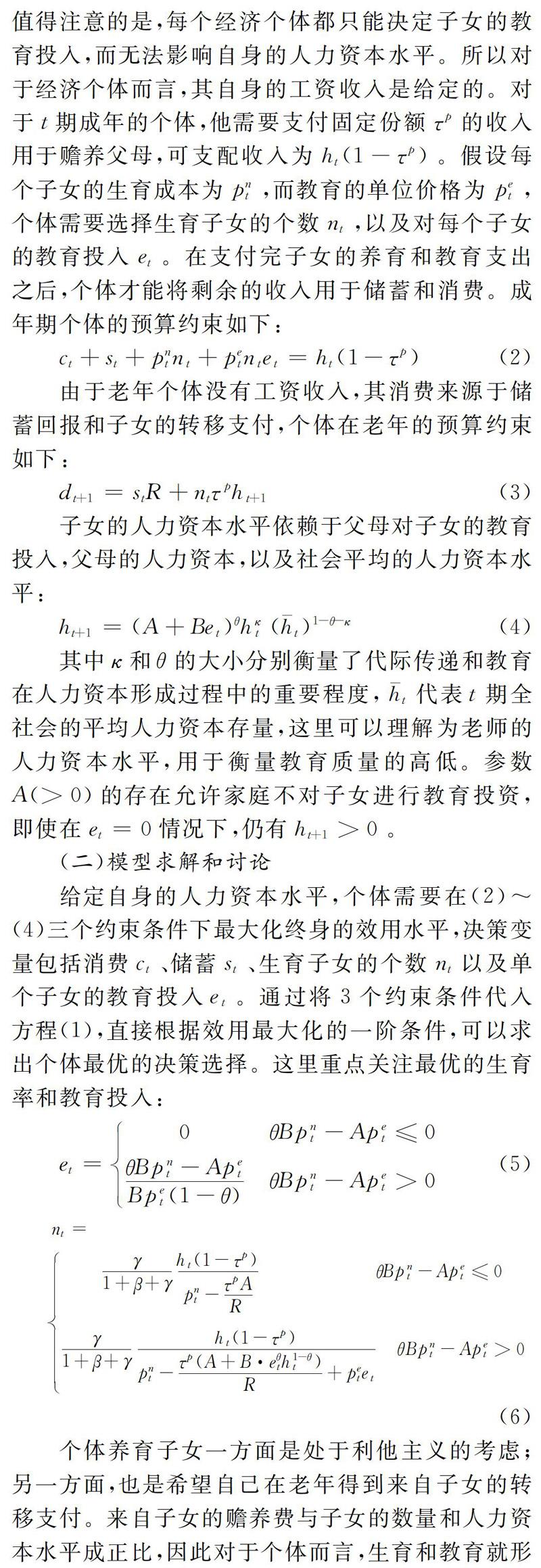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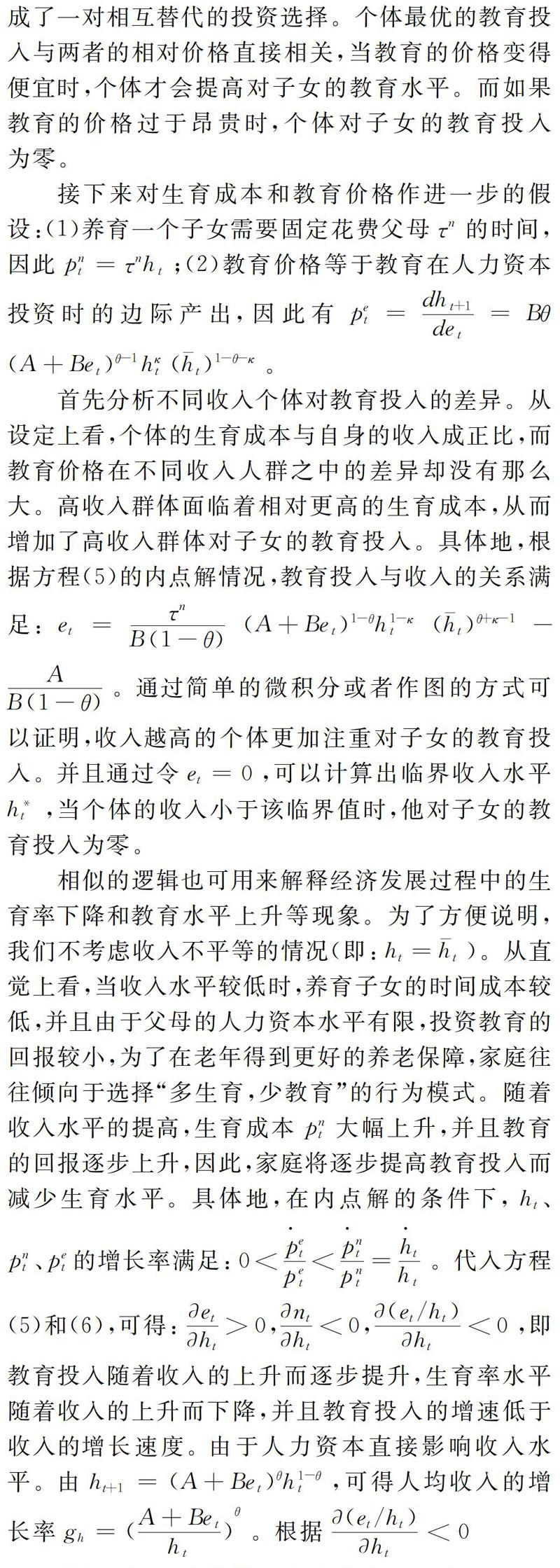
摘 要:通过建立一个内生的生育率选择模型,研究收入水平与教育投入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生育成本的增长速度高于教育价格的增速,家庭会逐步降低生育率,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在模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会逐步下降,但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使这种增长放缓的现象得到缓解。结合36个国家近50年的面板数据,统计了“增长放缓”现象在不同收入区间的分布情况,结果发现:“增长放缓”现象的确集中出现在中等收入国家,形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根据probit回归的结果,中高等教育的普及能够有效降低增长放缓出现的概率,同时,贸易壁垒较高、基础设施陈旧以及制度评分落后的国家更有可能遇到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关键词: 生育选择;教育投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6-0135-06
一、引 言
二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它们通过引入外资等方式刺激经济,迅速跳出了低收入陷阱。根据“条件收敛假说”,发展中国家理应具有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使得各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在1960年的近100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只有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能够在201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拉美等主要经济体在50年之后仍未成为发达国家。世界银行将这一类现象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根据韩、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它们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生育率的大幅下降以及教育水平的迅速提升,而且他们更加注重加强产权保护、政府监督以及降低贸易壁垒。这些因素是否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此外还有哪些因素可能阻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文将从模型和实证的视角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近年来,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归纳为增长问题的一种特例,利用模型的多重均衡和实际数据来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一些文献将中等收入陷阱与人口因素关联起来,如Funke 等 (2000) 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必须经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创新[1]。Galor (2005) 进一步提出了“统一增长理论”。通过考虑家庭微观层面的效用最大化决策,他将人口结构的改变与经济的长期增长结合在一起,从而揭示经济增长与生育率以及教育水平的关系[2]。Lee (1997) 详细介绍了1945-1992年韩国的发展史,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3]。但工人的教育程度必须与产业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相符。Kim 等 (2010) 研究了墨西哥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教育投入情况,发现墨西哥每年的公共教育支出与韩国一直不相上下,但当时墨西哥缺少足够的高素质就业岗位,大批高等人才失业,使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4]。
另外一些文献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如Eichengreen 等(2013) 发现增长放缓容易出现在11000 ~ 12000美元和15000 ~ 16000美元之间,同时靠投资驱动经济以及通过贬值本币以促进出口的经济体往往更容易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5]。Agenor (2010) 和Agenor 等(2015) 分别建立了由公共基础设施驱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6,7]。他们利用模型的多重均衡,证明了基建支出份额的提升可以使得经济体跳出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境。 Papageorgiou 等 (2012) 认为出口种类过少是低收入国家的典型特征[8]。而Hausmann 等(2007) 则发现出口商品的精细化程度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9]。随着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步上升,Mishra 等 (2011) 发现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在经济增长中同样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10]。Jankowska 等 (2012) 从经济转型方面解释了拉美国家的增长问题[11]。对于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韩国),其高效的现代产业在转型过程中可以从传统产业吸收足够的劳动力,使得总体的TFP迅速上升,而拉美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通过将人均产出进一步分解,Restuccia (2008) 发现劳动生产率和TFP水平的差距是拉美国家增长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12]。Cole 等 (2005) 将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拉美国家具有较强的贸易保护措施和进入壁垒,这阻碍了市场竞争,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下 [13]。
綜上文献可以发现,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实证方面,相关的理论模型较少。基于“统一增长理论”的思路,本文建立了一个生育选择模型。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长能提高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而教育水平的提升反过来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然而,这种良性循环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和教育投入均存在上限,经济增长最终会陷入停滞,这就体现了政府鼓励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了教育促进增长的结论,并且发现贸易壁垒、基础设施以及制度等因素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直接的联系。
二、理论模型
基于Croix 等 (2003)的分析框架,建立一个家庭生育率选择模型[14]。本模型新增了子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此外,还修改了对教育价格的模型假设。假设由于子女会支付固定份额的收入作为赡养费,父母将会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水平。
(一)模型设定
个体一生需要做的决定都是在成年期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每个经济个体都只能决定子女的教育投入,而无法影响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所以对于经济个体而言,其自身的工资收入是给定的。对于t期成年的个体,他需要支付固定份额τp的收入用于赡养父母,可支配收入为ht(1-τp)。假设每个子女的生育成本为pnt,而教育的单位价格为pet,个体需要选择生育子女的个数nt,以及对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et。在支付完子女的养育和教育支出之后,个体才能将剩余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消费。成年期个体的预算约束如下:
由于老年个体没有工资收入,其消费来源于储蓄回报和子女的转移支付,个体在老年的预算约束如下:
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依赖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父母的人力资本,以及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
其中κ和θ的大小分别衡量了代际传递和教育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程度,t代表t期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存量,这里可以理解为老师的人力资本水平,用于衡量教育质量的高低。参数A(>0)的存在允许家庭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即使在et=0情况下,仍有ht+1>0。
(二)模型求解和讨论
给定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个体需要在(2)~(4)三个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终身的效用水平,决策变量包括消费ct、储蓄st、生育子女的个数nt以及单个子女的教育投入et。通过将3个约束条件代入方程(1),直接根据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求出个体最优的决策选择。这里重点关注最优的生育率和教育投入:
个体养育子女一方面是处于利他主义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在老年得到来自子女的转移支付。来自子女的赡养费与子女的数量和人力资本水平成正比,因此对于个体而言,生育和教育就形成了一对相互替代的投资选择。个体最优的教育投入与两者的相对价格直接相关,当教育的价格变得便宜时,个体才会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水平。而如果教育的价格过于昂贵时,个体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为零。
接下来对生育成本和教育价格作进一步的假设:(1)养育一个子女需要固定花费父母τn的时间,因此pnt=τnht;(2)教育价格等于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时的边际产出,因此有pet=dht+1det=Bθ(A+Bet)θ-1hκt(t)1-θ-κ。
三、实证分析
接下来,将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考察国际贸易、基础建设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一)数据来源及其初步分析
表1给出了实证部分选取的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变量及其数据来源,具体由以下五大类构成:(1)人口特征。人口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生育率(fertility),即妇女在一生中生育的子女个数;人口抚养比(dependence),用低于15岁与15~64岁的人口数量比来表示;初等和中高等教育年限(primary、secondary),即全国25岁以上受初等和中高等教育年数的平均值。(2)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水平(Ratio),以及投资支出、外商直接投资和债务分别占GDP的比重(invest、FDI、debt)。(3)国际贸易。关于国际贸易的指标包括:贸易-产出比(trade),即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关税(tariff),用以进口商品价值为权重的平均关税水平来表示;高科技出口(Tech_exp),用研发密集型商品在制造业出口中的比重来表示。(4)基础建设,这里用铁路长度(rail)来衡量。(5)制度。关于制度方面的指标包括:政府规模(government),用于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产权保护(property),即产权所有者维权的难易程度;监管(regulation),用于综合衡量政府对金融以及劳动力等市场的监管程度;金融开放度(finance),即一个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接下来,选取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来代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高收入经济体,并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来代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表2分别给出了这两类经济体在1970年和2010年各指标的均值水平。可以看出,虽然两类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在1970年相差无几,但40年之后,韩日等高收入经济体的相对人均GDP发生了显著的提升,而拉美等国家却不升反降。尽管两类经济体的生育率和人口抚养比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但韩日等高收入经济体的下降幅度更大,且数值更小。因此,它们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在子女的教育之上。虽然两类经济体的初等教育年限相差不大,但对于韩日等高收入经济体,它们对中高等教育的普及明显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果。拉美等国家的贸易-产出比较低,不过这可能是它们经济体量较大的原因。但是韩日等高收入经济体具有更低的关税和更高的高科技出口比重,这说明它们具有更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从而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能够大规模生产高科技产品以供出口。此外,拉美等国家在制度方面的评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比如它们在产权保护和政府监管方面的表现就明显不如韩日等高收入经济体,并且在监管方面的差距在进一步放大。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拉美等主要经济体在某些人口特征、对外贸易以及制度方面的确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可能抑制了这些国家的增长潜力,使得它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
(二)样本选择和“增长放缓”的识别方法
接下來本文将通过回归分析来进一步验证中等收入陷阱与上述变量的相关性。与已有文献相似,本文同样将中等收入陷阱视为“增长放缓”现象的一种特殊情况,并采用Eichengreen 等(2013)所提出的识别方法。本文的样本由欧、亚、拉丁美洲等36个国家和地区用1960-2010年的数据组成①。如果某个国家的人均GDP满足以下3个条件,本文则认为该国家发生了“增长放缓”的现象:
方程(7)意味着,在“增长放缓”现象出现之前,该国6年内的人均GDP增长率需要不低于3.5%,这说明该国过去几年中经历过高速增长;方程(8)则说明,在“增长放缓”现象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内,人均GDP的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大于2%),并且这种情况没有在短期内得到好转;方程(9)将样本限制在中高收入国家。由于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与中等收入国家不同,因此,将低收入国家的增长问题排除在本文的研究目标之外,以免对最终的结论造成影响。
图1给出了数据样本中关于“增长放缓”现象在不同收入区间的分布直方图,其中横轴代表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水平,纵轴表示“增长放缓”现象在该收入区间一共出现的次数,直方图上方的曲线则代表根据样本均值和方差估计所得的正态分布。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5月提出的最新标准,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NI介于1005 ~ 12235美元之间。如果不考虑GDP和GNI的微小差异,那么根据图1,“增长放缓”现象集中出现在中等收入区间。当然,图1并不能揭示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真实原因,因此,接下来将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以验证与“增长放缓”现象相关的影响因素。
(三)回歸分析
利用probit回归模型来检验表1所示的人口、教育、制度、宏观经济环境、基础建设以及国际贸易等一系列因素与“增长放缓”现象的相关性。probit回归模型满足的性质如方程(10)所示,其中Y代表模型的因变量,当发生“增长放缓”现象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X1,…,XN代表模型的解释变量。由方程(10)可知,在回归模型中,“增长放缓”现象发生的概率与模型的解释变量呈线性关系,通过检验参数 β1,…,βN的显著性,可以判断对应解释变量与“增长放缓”现象的相关程度。
考虑到解释变量种类较多,无法将相关的解释变量一次性全部加入回归模型之中,因此,只能将解释变量分为4组,分别估计它们对于“增长放缓”现象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第一列的回归结果,由于变量Ratio代表各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GDP水平,那么“增长放缓”现象出现的概率将在本国人均收入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1/3时达到顶峰,这与图1所描述的结果相近,也与表2的数据相符。由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位于世界前列,该结论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容易遇到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生育率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高生育率会提高发生“增长放缓”现象的概率,这与统一增长理论的结论类似。投资-产出比和FDI的系数同样显著大于零,这说明由投资驱动经济的国家往往更可能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加大投资来迅速提高人均产出,但长此以往终将面临投资效率下降、产能过剩以及内需不足等问题,从而造成增长动力不足的现象。
为了验证理论部分关于教育促进增长的结论,表3第二列新增了关于教育的两个解释变量。从表3第二列可以看出,在引入新的解释变量之后,相对人均GDP、投资-产出比、FDI以及人口抚养比等变量的系数显著度并未发生改变,但生育率不再显著,而教育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教育才是阻止经济增长放缓的直接因素。而在两个教育变量中,只有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可以显著降低“增长放缓”出现的概率。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两类经济体初等教育年限的差距不大,拉美国家的中等教育年限明显低于韩日等发达经济体。根据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经验,要想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需要逐步转型生产更加精密的、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通过产业升级以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这不是初等教育人才能够胜任的,因此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就显得至关重要。表3的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给出了关于贸易与制度因素的回归结果。由贸易产出比的系数可以看出,除了闭关锁国之外,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同样可能提高“增长放缓”出现的概率,因此,保持适度的贸易产出比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同时,关税水平较高、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但高科技出口与“增长放缓”的关系与预期的结论相反。至于制度方面的因素,监管和政府规模分别在5%和1%的显著度水平下显著,而金融开放度和产权保护则不然。这说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削减冗余的政府部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转而加强对市场的监管,那么该国发生“增长放缓”的概率将会大幅降低。
四、结 论
通过建立一个内生的生育率选择模型,研究收入水平与教育投入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由于生育成本相对教育成本的增长幅度更大,家庭会逐渐向“少生育,重教育”的方向转变。尽管人均收入的增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但教育的存在能够使得增长放缓的现象得到缓解。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数据,“增长放缓”现象集中出现在中等收入区间,这也许暗示着“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增长问题的一个特例。通过建立probit回归模型,证实了中高等教育的普及的确能够降低“增长放缓”出现的概率,而投资产出比较低、适度对外开放、具有良好基础建设以及制度完善的经济体可以更少地受到“增长放缓”现象的困扰。
注释:
① 欧洲国家包括德、法、英、意、西、葡等15个发达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印、菲、泰等11个增长迅速的经济体;剩余的10个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经济体。
参考文献:
[1] Funke M, Strulik H. On endogenous growth with physic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and product variety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 44(3): 491-515.
[2] Galor O. Unified growth theor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Lee J W.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R]. Working Paper, 1997.
[4] Kim C S, Hong M K. Educa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2010, 17(2): 21-30.
[5] Eichengreen B, Park D, Shin K. Growth slowdowns redux: new evidence on the middle-income trap [R]. Working Paper, 2013.
[6] Agenor P R. A theory of infrastructure:le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10, 34(5): 932-950.
[7] Agenor P R, Canuto O. Middle-income growth traps [J]. Research in Economics, 2015,69(4): 641-660.
[8] Papageorgiou C, Spatafora N.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LICs: stylized fact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R]. Working Paper, 2012.
[9] 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7, 12(1): 1-25.
[10]Mishra S, Lundstrom S, Anand R. Service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 Working Paper, 2011.
[11]Jankowska A, Nagengast A, Perea J R. The product space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comparing Asian and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s [R]. Working Paper, 2012.
[12]Restuccia D. The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problem [R]. Working Paper, 2008.
[13]Cole H, Ohanian L, Riascos A, Schmitz J.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rview mirror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5, 52(1): 69-107.
[14]Croix D, Doepke M. Inequality and growth: why differential fertility matter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091-1113.
[15]Barro R, Lee J.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2010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 104: 184-198.
[16]Abbas S, Belhocine N, Elganainy A,et al. A historical public debt database [R]. IMF Working Paper, 2010.
[17]Canning D. A database of world stocks of infrastructure, 1950-1995 [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12(3): 529-548.
[18]Chinn M, Ito H. What matters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pital controls, institutions, and interaction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81(1): 163-192.
(責任编辑:铁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