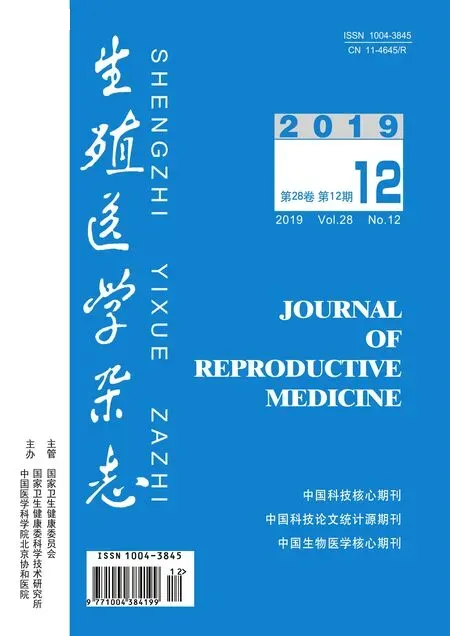老来得子,忧患实多—辅助生殖中高龄男性的伦理思考
沈朗,谢利嘉,史潇,秋晓,华芮,陈东红,王志坚,全松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生殖中心,广州 510515)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医疗水平的提高及婚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夫妇结婚年龄及生育年龄均大幅推迟,伴随着高龄生育问题的逐渐凸显和加重。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ART)的飞速发展及生育新政策的出台,许多高龄夫妇借助ART圆了为人父母的梦想,而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伦理乃至法律问题。目前,高龄女性患者的助孕问题已成为生殖医学领域焦点伦理问题。针对目前社会上关于高龄女性行辅助生殖所产生的医学、社会及伦理问题,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综合中国生殖医学领域各专家的意见,形成了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指南。然而,此前人们伦理关注的重点只在高龄女性上,而对于ART中的高龄男性患者的伦理关注甚少,亟需引起广大ART工作者的思考及重视。因此,有必要对ART中高龄男性患者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二、辅助生殖中高龄男性生育现状
多数研究认为男性年龄超过40岁是生育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子代的健康风险相应增加[1]。研究显示,美国高龄男性生育后代比例在过去30年间明显增多,2014年30岁以下生育男性比2013年下降12%,30~44岁年龄段生育的男性比例上升2%~3%,45~49岁上升高达6%,50~55岁上升4%[2-3]。英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近10年间35岁以下男性婚内生育率从74%下降到60%,而35岁至54岁的父亲从25%上升到40%[4]。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男女结婚年龄推迟1.5岁,男性平均结婚年龄近27岁,生育年龄也相应推迟[5]。有数据显示,国内ART中心就诊男科患者中,40岁以上患者所占比例从19.5%(2015年)大幅增长到27.0%(2016年),超过50岁的患者门诊就诊率也显著增加[6]。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开放及ART的发展,加之国内离婚率、再婚率的飙升及婚育观念的改变,“老夫少妻”的现象在各ART机构数见不鲜,有生育意愿及成功生育子代的高龄男性患者越来越多。此外,我国传统观念认为“老来得子”是福气,是男性能力乃至社会地位的体现,许多六七十多岁老年男性通过ART成功得子的报道更加刺激了社会上关于高龄男性生育的冲动及意愿。对于超过一般生育年龄的男性来说,他们不仅担心自己的生育能力,而且更加关注ART的妊娠结局和孩子出生后的健康问题。然而,关于ART中高龄女性的研究及伦理关注较多,许多ART机构也常规开展高龄女性生育的咨询及评估,但对于高龄男性患者,其助育的生殖结局及子代健康风险研究甚少,也没有专门针对高龄男性患者的咨询、告知和评估体系。事实上,高龄男性患者的精子不仅存在质量显著下降、DNA损伤及突变率增加、染色体非整倍突变增高及表观遗传学变异等问题,且其子代出生缺陷及认知神经疾病等发生风险也较高[6]。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道德、伦理乃至法律层面的问题。
三、辅助生殖中高龄男性引发的伦理问题
(一)高龄男性自身权益的问题
生育权是指所有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的自然人所拥有的决定是否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的自由或资格[7],是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对于高龄男性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睾丸功能下降,精子数量、质量及功能明显降低,成功妊娠所需时间显著延长。研究表明,超过35岁男性生育力较前略有下降,而39岁以后其生育力每年下降21%~23%[8]。虽然高龄男性患者生育力的下降可通过ART以实现其生育权,但这个过程中涉及到许多伦理问题。
首先,高龄男性在ART助育过程中出现健康风险的机率大幅增加。因心脑血管功能下降、肝肾功能不良、代偿及应激能力减低等身体机能的改变,许多高龄男性在助育过程中进行身体检查时发现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乃至肿瘤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对于这部分高龄男性而言,这些健康风险的增加并不会促使其审视自身健康权与生育权之间的平衡,反而进一步刺激了其尽快生育的想法和决心。其次,随着男性年龄升高,其精子遗传及表观遗传学发生变异,导致其助育结局相对较差。有研究显示,超过40岁男性其女方IVF受孕失败的风险是小于30岁男性的1.7倍;研究认为,男性年龄超过40岁与女性超过35岁类似,也是生育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9]。通过分析接受卵子捐赠的ART结局发现,随着男性年龄升高,其胚胎着床率、妊娠率、活产率明显下降,而流产率上升[9]。高龄男性患者助育的高风险和低成功率,及反复治疗和不良妊娠结局将给夫妻双方带来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创伤。最后,高龄男性一般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基础,但较差的助孕结局决定了多次助孕耗费不菲,且如助孕成功,其子代未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又是另一个严峻的挑战。故此,这部分高龄男性患者将不得不在严重的经济及生活压力下继续努力工作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利于其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
由此可见,由于高龄助育的高风险及养育子女的艰难性,高龄男性需以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为代价以实现其生育权,导致其生育权与生命权、健康权及幸福权等产生冲突。
(二)高龄男性妻子权益的问题
研究显示,高龄男性精子的DNA碎片率、突变率、染色体非整倍突变率均上升,且存在表观遗传学改变[6]。这些改变使基因组复制过程中对碱基交换、微缺失和微重复等错误更加敏感,从而影响蛋白质翻译及功能,导致胚胎发育不良、流产及其他负面影响[10]。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控制女方的年龄及其他相关因素后,随着男性年龄的增加,其妻子的自然流产率也随之增加[11]。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男方年龄是其妻子发生自然流产概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年龄大于45岁男性是小于25岁男性的2倍[12]。
助育过程中高龄男性患者精子的遗传及表观遗传学变异引起的胚胎发育不良、自然流产等不良妊娠结局主要由其妻子承担。不仅如此,其妻子还需要承担后续医疗处理(如清宫术)、反复促排治疗、多次手术等后果。这无疑会对其妻子造成身体及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不利于其妻子的生命健康权及幸福权,也给家庭关系带来隐患。
(三)高龄男性子代权益的问题
1. 子代的健康风险:近期研究显示,高龄男性子代近期及远期健康风险包括:认知神经疾病(如孤独症、双向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如软骨发育不全、阿佩尔综合征、成骨不全、眼癌)、先天性疾病(如无脑儿、大血管错位、先天性心室间隔缺损、房室间隔缺损、神经管缺损)及其他疾病(如神经性失调、神经系统肿瘤)等[4]。国内亦有文章综述了高龄男性生育增加子代健康风险,如出生缺陷、染色体遗传病、精神认知障碍疾病、肿瘤、多发性硬化及肥胖等[13]。
高龄男性患者子代健康风险的增加,使得生殖工作者在解决高龄男性患者生育权问题的同时,更要从伦理方面着重关注保护子代安全性及子代权益的问题。保护后代原则作为辅助生殖伦理学中核心要素之一,在出生之前其子代权益体现为胎儿权益。胎儿因具有发育成人的潜能而被界定为潜在的人,作为潜在的权益主体应当享有最基本的生命权和健康权[14]。而在出生后,子代权益则表现为儿童权益,儿童作为国际上公认的特殊保护群体,应享有优先于成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及发展权。由此可见,高龄男性患者生育权的实现是以其子代近期及远期的健康风险增加为代价,造成高龄男性生育权与其子代出生前后的生命健康权益和发展权之间的矛盾。
2. 子代的社会问题:高龄男性生育不仅会造成子代健康风险的增加及子代权益的损害,也会给子代的亲子关系、成长环境、心理健康、情感障碍乃至自杀倾向等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显示,高龄父母和孩子的感情距离可能会加大,交流也会出现障碍,当父母亲年龄大于45岁时,亲子关系更容易受到冲击。父母与子代间年龄差距过大可能会加剧亲子间价值观、信念、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子代更容易误解和不满其父母,评价也更消极。有研究报道,与父亲年龄差距大于40岁的子代在青少年时期对父亲的评价要比年轻父亲(30~39岁)的孩子对父亲的评价低[15]。高龄才成为父亲势必面临着子代还未成年,父亲就已垂垂老矣,可能无法保证将其抚养成年的困境,这也影响了子代正常的成长环境,影响其发展权。
我国传统观念及法律法规均规定子代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高龄男性的子代在上大学或工作时,一方面要兼顾其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又要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亲,这对于其子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过度的心理负担。有研究指出,一个高龄父母的孩子不得不照顾他们年长的父母,导致其比同龄人成熟得更快,有更高的抑郁和行为问题的几率,同时更容易受到压力和焦虑的影响[16]。作者指出,高龄父母的孩子对父母健康状况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并引起其他许多情感障碍,如孤僻、社交问题和感情问题等。
此外,有学者认为,孩子20岁之前失去父亲的风险在父亲初次生育孩子的年龄大于55岁时急剧增加[17]。对于孩子来说,失去双亲是难以磨灭的创伤,对其日后的教育、健康、寿命等的影响非常重要。研究发现,幼小学龄前失去父母是其成年后需要心理健康咨询或者治疗的高风险因素[18]。还有几项研究发现子代自杀率和自杀倾向的增加与父母的死亡有关[19]。一般来说,子代在学龄前失去父亲与年老时失去父亲相比,造成其自残或服毒住院的风险更高;学龄前失去母亲会增加男性子代的自杀风险,尤其是非自然死亡情况下,风险会更大。但无论是失去父亲还是母亲,另一个父母的存在并没有被证实对孩子有保护作用从而降低风险[20]。
(四)高龄男性与社会公益的问题
在1994年开罗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中提出:个体或者夫妇在实现生育权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他们自身及孩子将来的生存问题,以及他们对社会应尽的义务[21]。这从社会公益性角度规定了个体或夫妇对孩子及整个社会的义务。高龄男性在享有生育权利、做出生育决定的同时,更应该谨记及衡量伴随而来的自身能否履行“为人父”的义务。同时,还应从社会公益性方面考量是否会给社会增加额外的负担。一方面,高龄男性助育结局较年轻男性差,势必会更多地占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医疗资源,如生殖医学中心、产前诊断、新生儿监护病房等,这将影响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不利于医疗资源的社会分配;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高龄男性助育增加了子代健康风险,影响出生人口素质及质量,危及人类未来的利益。此外,高龄男性的子代成长环境存在变故,生存压力较大,不仅影响子代个体的发展,也会带来沉重的社会负担。上述问题都不利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健康发展。因此,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公众利益角度,为合理配备珍贵的医疗资源,辅助生殖医疗机构在应对高龄男性进行助育治疗时应充分权衡利弊,避免高龄男性生育权与社会公序良俗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四、辅助生殖中高龄男性助育的伦理对策
(一)做好充分告知及知情同意
目前,各ART机构在高龄女性进行ART助孕之前,会进行详尽的关于成功率、妊娠结局、子代风险等的知情告知及评估,而对于高龄男性患者,一般只要精液检查结果无显著异常即认为其生育能力保存良好,而忽视了高龄男性生育导致的自身权益、配偶权益、子代权益乃至社会公益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因此,ART工作者要积极提高自身素养,在尊重高龄男性患者生育权的同时,为患者进行个体化的生育风险评估、伦理评估及知情同意,帮助高龄男性患者权宜生育权与自身、配偶、子代及社会之间的平衡。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高龄男性患者进行告知和咨询:(1)失去父亲对其子代带来的潜在负担;(2)其子代在相对年轻的成长阶段照顾年迈的父母所带来的情感和其他负担;(3)高龄男性精子增加子代已知和未知的遗传和健康风险。此外,正如美国生殖医学会伦理委员会关于育儿能力和提供生育服务的文件中所概述的那样,生殖工作者可依据他们对未来子代的评估,而具有拒绝提供治疗的权力[22]。
(二)遵守伦理原则,完善伦理监督
在对高龄男性患者进行助育的过程中,ART工作者要恪守辅助生殖伦理原则和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按规定流程进行切实有效的诊疗操作,防止ART技术走入歧途,危害婚姻、家庭和社会。首先,从有利于患者原则出发,尽可能帮助高龄男性患者实现生育权。其次,贯彻知情同意原则,对高龄男性患者进行详尽的知情告知,充分告知其助育成功率、妊娠结局、子代风险等。再次,从保护后代原则出发,应对高龄男性患者子代的健康风险、成长环境、心理健康等进行评估,必要时保留拒绝提供治疗的权力。最后,在对高龄男性患者进行助育时,要兼顾社会公益性原则,避免有限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目前,因我国辅助生殖伦理原则较为笼统,社会各界对此的解读各异。例如,“有利于患者原则”并未指出当父亲的生育权与子代生命健康权益相冲突时,该如何进行衡量和选择,这就使得ART工作者在具体如何维护患者利益的问题上感到困惑。因此,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需要充分发挥其伦理监督的作用。首先,当患者生育权与生命健康权益不一致甚至矛盾难以调和时,医学伦理委员会应该以优先生命健康权为原则,指导ART实施。其次,在实现高龄男性患者的助育要求时,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充分考虑到患者之外其他主体(如其配偶、子代、社会等)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要以利益最优化为目的,以公平公正为准绳,在充分讨论、全面考虑、综合衡量的基础之上,本着对患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指导医疗机构做出合理的决策[23]。另外,我国各ART中心生殖伦理委员会的水平参差不齐,相关伦理知识及培训不足,其内部成员发挥的作用也不平衡[24]。为提高生殖伦理委员会伦理监督及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成员中应配备一名资深的生殖医学专家,同时加强各委员的辅助生殖伦理知识培训,从而保障伦理监督的公平和客观性,充分发挥生殖伦理委员会职能。
(三)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
目前,我国ART可循的规范仅限于十几年前原卫生部制定的相关办法、法规和原则,法律规章尚不完善,局限性日益凸显,亟待发展。如未明确该技术是否可用于高龄乃至老龄男性等生育主体,由于无据可循,ART机构难以拒绝这些患者的助孕要求。其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规章制度不完善,约束力薄弱,无法有效约束地下试管机构乃至ART机构及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也没有一部详实的针对ART管理、实施以及权益保障等各个具体层面的法律[25]。由于立法层级较低,无法在赋予公民生育权的同时,有效约束生育主体做到“负责任地生育”,尽到其对子代、配偶及社会的义务。最近,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出台了高龄女性行辅助生殖的专家共识及指南,规定行ART助孕的女方年龄不得超过52岁,但对于ART中的高龄男性,却并无相关指南或共识规定其年龄限制。因此,在法律法规或行业规范上,应对高龄男性生育主体的资格有所规范,促进高龄男性患者ART助育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