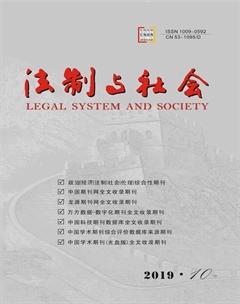普罗塔戈拉的“时代”性
黄陆璐
关键词普罗塔戈拉 美德 技术 功利 民主
《普罗塔戈拉》篇纪录了古雅典时期以普罗塔戈拉为首“智者派”的言论与主张,其所代表的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为何在古希腊政治变革时期如此流行,普罗塔戈拉的主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呼应关系?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苏格拉底和后来的柏拉图又为什么要将他的主张和观点视为辩驳对象?是本文想要展开,进行探究的问题。
一、“智者派”的兴起
《智者运动》一书中对“智者”崛起的背景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首先就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兴起。梭伦和伯里克利时期,社会正处在变革的蓬勃期,政治权利的行使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法治原则。希腊民主政治制度意味着自由民拥有在公共事务方面发表见解及参与处理的权利,实践权利的能力对公民而言必不可少。公民在参与政治生活时,往往需要通过与分歧者辩论,不断明确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当时背景下,城邦公民产生了学会如何辩论,提升政治参与能力的教育需求。人们开始重视用于政治生活的专业知识。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教授修辞学、论辩术为职业的“智者”应运而生。他们针对公民参政需要四处游学、收费授徒,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拥有大批的追随者。
第二教育体制无法跟上制度变化。希腊传统的教学体制赋予部分青年政治权利,然而教授体育、玄琴及文法技艺的课程内容与实践目的不符。“自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进入城邦时代。在长达3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教育领域并不是统治者改革的重点。由于青年们没有获得政治知识和辩论艺术,渴望学到能够提升他们在公共事务中展现个人能力的道德与政治课题。希腊原有的教育并不系统,智者们的出现顺理成章的带动了这方面的改革。梭伦确立了系列的教学体系,合格的学员可获得参政议政的权利并成为正式的城邦公民;从而在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参与公共事务中彰显个人能力与获得政治权利的倾斜。教育改革成为日益迫切的实际需要。传统教育体制的无力在制度上促进了智者运动的兴起。
第三个原因则是伯里克利对于智者及其群体的重视与倚重。在他执政期间,伯里克利扶持学术和文化活动,并对多项与文化教育及参与其中的公民与平民提供政府津贴,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在这样的氛围下,智者们应市场需求在雅典四处讲学,“他们与统治阶层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得智者运动在统治者们的推崇下遽然兴起”。。
显然,史实的概况勾勒出了普罗塔戈拉“智者”群体成为当时雅典城邦的潮流,这个潮流的基础是城邦民主政治的兴起;伯里克利和权贵家庭对普罗塔戈拉的青睐,也为当时的“智者”群体起到了背书作用。在《普罗塔戈拉篇》中记录了贵族希波克拉底。听说普罗塔戈拉的到来,兴奋的要求苏格拉底前去共同拜访时,看到多个贵族子弟排在普罗塔戈拉身后,亦步亦趋地、安静的陪伴他沉思的场景:“当我们(指苏格拉底和希波克拉底)进屋时正巧碰上普罗塔戈拉在门廊下踱着方步。那些跟在他身后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一边是希波尼库斯的儿子卡利斯,他的继弟、伯里克利的儿子帕拉路斯,格劳孑L的儿子卡尔米德斯;一边是伯里克利的另一个儿子克珊提普斯,菲洛麦路斯的儿子菲力庇底斯和普罗塔戈拉最著名的学生曼地的安提莫路斯。他正从事专业性的学习,以成为一名智者。他们大多是外邦人——普罗塔戈拉经过每个城邦时把他们吸引过来,带在身边,他就象奥福斯(0rpheus)一样用自己的嗓音征服他们,使他们虔诚地跟着——当然,那儿也有一些雅典人。“就在我(指苏格拉底)看到他们时,我惊喜地发现:每当他们转头回走时,学生都井然有序地分开,围着普罗塔戈拉绕一圈又回到他们各自的位置跟在后面。有趣的很,他们就是这样如此小心,以致于害怕走到普罗塔戈拉前面或挡着他的道。”权贵与“智者”的结合有彼此的需求,“智者”将“美德”可教作为其所掌握的“技术”,以此标榜可以使人们具有参与政治获得话语权利的公民素质。因此,深究普罗塔戈拉的主张,是了解他受到当时时代推崇原因的必由路径。
二、完整的伦理相对主义体系下“美德”成为“智者”掌握的“经验”形成的“技术”
于乌戈·齐柳利。为普罗塔戈拉的相对主义倾向做出的辩护。他试图将普罗塔戈拉从感觉知识论中分离出来,建构体系完整的相对主义的阐释。他立论的出发点是指出普罗塔戈拉是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之后运用“不可通约性”原则解决了普罗塔戈拉建立在“主体”经验的认知与其他“主体”经验之间因缺乏“客观性”标准和框架难以进行比较、沟通的断裂问题,这个论述直接将普罗塔戈拉纳入经验主义的鼻祖的行列。
“普罗塔戈拉相信满意的人获得的感知比那些不满意的人获得的感知更为真实。智者的经验全都来自具体的实践活动,因为他必须面对广大范围内不同人的情况,每种情况都在其自身的特征上是独特,每种情况都要求以其自身的方式来解决,每种情况都组织聪明人提出一种所有情况都有效、唯一的、标准的解决方式。必须考虑到经验性地决定的个人情况之不可化约的多样性。”那么这些基于个体产生并依赖于变化着的历史语境的特殊实在构成之间如何具有比较的可能?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引用了费耶阿本的人类学方法:对两种不同的社会或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并不需要一个客观的通约范式。“解釋者以细致耐心的工作面对他所操作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在进行这样的诠释活动的过程中,对异己社会他获得一种局部的和可更改的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中,他自己的社会也得到了更好的、更深刻的理解。”
齐柳利将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平滑的移到了普罗塔戈拉为首的“智者”群体面对外在世界,基于主体相对主义方式的认识路径上了:普罗塔戈拉的“聪明人”和他的“不满意的感知者”也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并谈论更好的或更糟的各种感知。人们也可以推测,聪明人和那不满意的感知者,通过他们相互碰面,都获得了对他们自己更好的理解。他们通过体会面对他人感知事物的不同方式是如何反应,二者都对他们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聪明人”与不满意的感知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后者改变了他对世界的倾向,并获得了更好的感知,那么,同一相互作用,通过让聪明人面对不满意的感知者的许多事例,从而使他变得有能力根据感知对不同个体的不同满足来分辨各种感知,增加的能力使他们可以成为像“医生”一样的角色,具有经验把握“感觉不好”的人,并且重塑这些人的“感知”,变成具有专业技术的“智者”群体。
《普罗塔戈拉篇》将这种相对主义扩展到了城邦的范围上,普罗塔戈拉认为社会依据属于那社会的“绝大多数”民众的反应,决定将一定的伦理规则用作它自己的伦理规则。一个社会决定将其用作它自己的伦理规则的那些伦理观念,似乎是表达了那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共识,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伦理法则。根据普罗塔戈拉的相对主义,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不同伦理法则的两个社会可能相互理解。在普罗米修斯的分配神话中,普罗塔戈拉的“技艺”概念的用法,表明了所有那些理性的和伦理的活动,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典型特征,从事这些基本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并不需要分享某种客观的理性和伦理观念,它处理的是可变的事物。这里的“技艺”实际上和人的实践有关,包括政治实践。
三、普羅塔戈拉的理论中的“功利”与“民主”色彩
在普罗塔戈拉伦理相对主义体系下,“有用”被当作了确定的东西。“我知道许多人对人不利的事物,食物、饮料以及许多其他事物,也知道一些有利的事物;一些事物对人既不是有利的,也不是不利的,他们对马或者是有利的或者是不利的,有些事物只对牛有利,有些只对狗有利,有些事物不对所有这些动物的任何一个有利,而是对树有利;有些对树根有好处,但对幼芽有害处。”当普罗塔戈拉在回应苏格拉底时说到这里赢得一片喝彩。他得出“善”是一种多方面的且易变的东西。在这样易变的对象中,“利益/有利”则会被当做人们主观判断的依凭。这是其相对主义倾向的哲学主张的世俗应用。
《普罗塔戈拉篇》中这个话题很快就被苏格拉底引到到对“快乐”的讨论中,如果从个人主观判断的利益/有利是“善”,那么人们以快乐为目的的追求会产生什么样行为?这是一个非常辗转的过程,苏格拉底论述至此时,他沿着普罗塔戈拉的“有用”性路径,“互换”立场以“美德”可教继续下去了这个命题。
苏格拉底比较朴素的享乐主义和计算享乐主义之间的冲突和选择的不同,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放置在时间的维度上,朴素的享乐主义选择即时的满足,并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是否会带来恶果,臣服于“陕乐”的控制。计算的享乐主义会在时间的维度里,突显出正确地选择快乐和痛苦的权衡一“选更多和更少、更大和更小、更远和更近[的快乐和痛苦】,生命的救助岂不首先显得是衡量过度和不足以及依相互‘比照来看的均等吗?旧苏格拉底非常关注于普罗塔戈拉在时间的维度上,通过“美德”可以给人们带来什么。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助这种相对性的“美德”构建的“知识”是否可以在未来带给人们认识上的“真知”。通过立场的互换,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将普罗塔戈拉没有坐实的“美德”与“未来”关联的实质内容指了出来——基于“有用”原则下的“相对主义”给未来带来的就是“权衡术”。
在韩潮《希腊思想中的技术问题》一文中,对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文本中techne概念的分析如下:1技术是从经验中发现的普遍判断;2技术是可以传授的;3技术追求确定性;4技术倾向于对事件给出个明确的解释性理由。他认为以上四个特征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寻求对偶然和不确定的控制。普罗塔戈拉所授之“术”反应了那时候的哲学家普遍把人类一切行动能力等同于技术,以技术来衡量人类实践的美德和智慧,因此,他们才主张美德是一种可以传授的技术。“美德可不可教”就成为了《普罗塔戈拉篇》全书讨论的核心问题。
“美德”在伦理相对主义的体系下就是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共识,它并非是需要去认知的“客观真理”,而是在形成过程中的“知识”,将这种“共识”规则教授出去,使得想要参与进入其中的人熟悉这些伦理规则,从而在政治空间与公共事务中运用,具备参政能力。如此对“美德”内涵的主张与实践的方法论与柏拉图基于“美德”之上建立的理想政治存在根本性冲突。普罗塔戈拉所授的以参政为目的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遵循社会的“共识”形成的伦理,即由多数人所决定的,这正是西方当代民主社会中“多数人”权力之所以得到至上推崇的内核。这种“共识”在贵族阶层中被广泛传播,又用作于公共事务处理的准则,渐渐为统治者建立了完善的价值体系。普罗塔戈拉“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中包含了“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雏形——天下大同的“普世价值”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