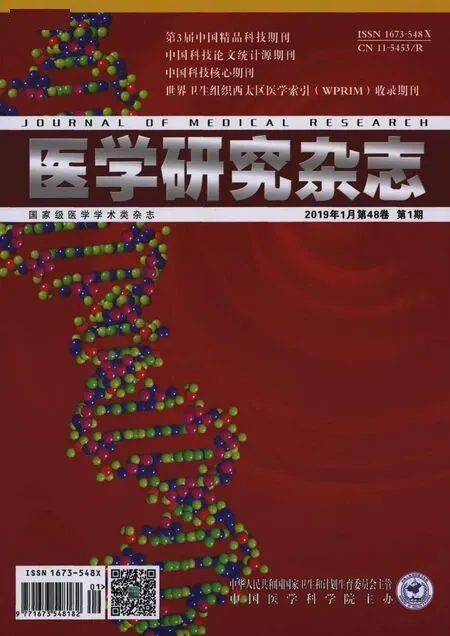PGC-1α在心血管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及机制
唐 楠 刘方圆 杨 振 樊 迪 邓 伟 唐其柱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激活子1α(PGC-1α),首先是在受寒冷刺激的棕色脂肪细胞中发现的一种蛋白,其与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相互作用,随后发现其通过刺激解偶联蛋白UCP1的生成而参与适应性产热[1]。此后,人们开始对PGC-1α产生兴趣,开展了大量研究实验,逐渐发现其生物活性远不止适应性产热,辅助激活的核受体远不止PPARγ,接受的刺激信号也远不止寒冷刺激。
早期很多实验均表明PGC-1α对于线粒体的生成以及氧化呼吸功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心脏过表达PGC-1α的小鼠线粒体生物合成明显增加,PGC-1α和PGC-1β双敲除的小鼠,在出生后不久即表现出了明显的的线粒体的形态学改变,如线粒体染色体的断裂或延长,线粒体嵴的坍塌,以及环状的线粒体,并出现心肌功能障碍[2]。PGC-1α在维持能量代谢平衡中也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调控了众多物质代谢过程中的关键酶的基因表达,参与调控呼吸链中的大部分酶,还调节Krebs循坏中的酶、脂肪酸β氧化中的所有关键酶,以及脂肪酸运输蛋白的基因表达。过表达PGC-1α的心肌细胞显著增加了脂肪酸的氧化。此外,PGC-1α还有促进血管生成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低氧刺激PGC-1α表达,而后PGC-1α与核受体相互作用,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分泌[3]。因此,PGC-1α还可以通过血管生成调节心肌细胞的能量状态。
实现上述功能,PGC-1α须辅助共激活核受体,介导目的基因的转录激活以完成对线粒体生成、能量物质代谢等的调控。PGC-1α 与多种核受体及转录因子相互作用,其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s)、核呼吸因子(NRFs)、雌激素相关受体(ERRs)等核受体是迄今研究较多的PGC-1α 作用靶点。大量研究证实,PGC-1α结合并辅助共激活PPARα,从而诱导产生许多脂肪酸转运和氧化相关蛋白。PGC-1α可通过辅助共激活NRF-1、NRF-2调节线粒体生成。线粒体生成不仅需要线粒体DNA的复制还需要线粒体自身基因组的转录,而联系核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需要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的介导,TFAM基因的表达正是由PGC-1α辅助激活NRF-1、NRF-2诱导的。ERRs是另一类重要的PGC-1α辅助共激活核受体,新生大鼠心肌中ERRα的过表达强烈诱导了很多基因的表达,糖利用相关蛋白如GLUT4,脂肪酸氧化相关蛋白,如CD36,氧化磷酸化相关蛋白ATP5b、CYCS,而ERRα 的mRNA的表达也受PGC-1α的诱导。有研究发现,Kruppel样因子4(Klf4)是ERR/PGC-1发挥作用所必需的,Klf4的缺失导致了线粒体生物起源受损和线粒体的成熟障碍[4]。大量其他转录因子也可以通过与PGC-1α相互作用而发挥生物活性,最新的研究发现线粒体丙酮酸酸载体(MPC)也是PGC-1α的作用靶点,其对于PGC-1α在线粒体呼吸和线粒体生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5]。
PPARs、NRFs和ERRs形成复杂的物质能量网络,而PGC-1α便是这复杂网络的一个调节者,通过整合各种体外刺激信号和体内神经体液信号,有序地维持着心脏组织的能量代谢平衡。PGC-1α可接受寒冷、饥饿、运动等细胞外刺激信号,从而增强PGC-1α相关信号通路的活化,很多生理信号能通过转录水平和转录后水平调节PGC-1α的活性,而这些作用机制也已被大量的研究证实。PGC-1α可由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信号分子和胰高糖素或是肾上腺素信号通路下游的的cAMP信号分子介导活化,这两条信号通路最终作用于PGC-1α基因启动子上一个保守cAMP反应元件(CRE),进而促进PGC-1α的转录。此外,PGC-1α基因表达还受很多信号分子的影响,如MEF2、钙/钙调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钙/钙调神经磷酸酶、AMP激活蛋白激酶(AMPK)、p53、一氧化氮。很多蛋白还可以通过翻译后修饰来调节PGC-1α的活性。PGC-1α蛋白的半衰期相对较短,很快就被泛素化,在蛋白酶体降解。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通过磷酸化PGC-1α的3个保守位点来抑制其降解。AMPK也直接磷酸化PGC-1α蛋白,促进PGC-1α的生物活性。相反,PGC-1α 被Akt激酶磷酸化后活性将被抑制。此外,GCN5乙酰转移酶通过乙酰化作用而降低PGC-1α 的活性,而NAD依赖的SIRT1型组蛋白去乙酰化酶使PGC-1α去乙酰化并增强其活性[6]。总之,PGC-1α表达受多种信号的影响,受细胞内代谢状态如ADP/ATP水平(AMPK),氧化还原状态(SIRT1)的影响,这些信号共同调节PGC-1α的活性,维持着机体物质能量代谢的动态平衡。
PGC-1α在线粒体基因生成、糖脂代谢及能量生成中有着重要作用,已成为目前备受关注的调控因子。PGC-1α主要表达于一些线粒体含量高和氧化代谢活跃的组织,如心肌、骨骼肌、肾脏、肝脏及棕色脂肪组织,而能量对于心脏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就其在心血管疾病中的重要作用及机制做一概述。
一、PGC-1α与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
很多实验观察到,脂肪酸运输和氧化过程在内的目标基因突变、高能磷酸盐的运输障碍、抗线粒体活性氧(ROS)的缺乏和线粒体DNA校正活动的异常,都会导致心脏功能不全。这些观察结果表明,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导致心脏病。线粒体是心脏能量的来源,占心肌细胞体积的40%,正常情况下,心脏中ATP生成量的60%~80%来自线粒体脂肪酸β氧化,心肌纤维中的线粒体严格地保持着ATP浓度,ATP稍有一定的减少就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而在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时,脂肪酸β氧化基因的表达明显减少[7]。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能量缺乏是心肌肥厚向心力衰竭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在人类心脏衰竭和啮齿类动物模型中发现许多线粒体蛋白的表达下降,而PGC-1α的表达在压力超负荷引起的心肌肥厚中下降,这提示PGC-1α因子可能发挥着某种作用。
此后,在很多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的动物模型中均发现了PGC-1α的表达下降。PGC-1α 敲除的小鼠早期即出现了心力衰竭症状,虽然PGC-1α敲除的小鼠心脏线粒体含量正常,但是ANP、BNP和β-MHC的升高提示心功能不全的存在。与此相一致,PGC-1α敲除后,心脏无法增加正性肌力刺激后的输出量,在主动脉横缩术后更是表现出严重的心功能障碍。这表明PGC-1α是维持心脏正常输出功能所必需的,对于维持心力衰竭后代偿状态也是至关重要的。ERRα敲除的小鼠在主动脉横缩术后表现出与PGC-1α敲除非常相似的表型:能量受损,包括磷酸肌酸和ATP水平降低,并逐渐发展为心脏衰竭,表明ERRα在PGC-1α的生物学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PE诱导的心肌肥大模型中,通过腺病毒转染心肌细胞,使其过表达PGC-1α,发现心肌细胞的肥大程度减轻,而用siRNA干扰PGC-1α的表达后,明显加重了PE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大。PGC-1α的这一保护作用是通过抑制钙调神经磷酸酶/NFATc4信号通路实现的[8]。近年来发现的microRNA-22也有致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的作用,其中一种重要的机制便是通过下调PGC-1α而减少PPARα和ERRα目的基因的表达[9]。而在T3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厚模型以及在体实验中发现,短时间的T3刺激导致一过性PGC-1α的降低,延长T3刺激时间,PGC-1α的表达上升并维持在高水平,这可能与之前的结论相悖,但值得肯定的是PGC-1α在T3所致的心肌肥厚中起到保护作用,实验中通过RNA干扰技术使PGC-1α弱表达,结果加重了心肌肥厚,而PGC-1α过表达则减轻了心肌肥厚,这一作用由p38 MAPK信号通路介导[10]。PGC-1α早相的降低可能提示在T3的刺激下心肌细胞已经出现了功能障碍,随后,T3致机体耗氧量的增加和ROS的增加可能代偿性引起PGC-1α的后相升高。
心肌病和心力衰竭中模型中还出现了底物使用的变化,在胎儿发育过程中,当氧缺乏时,脂肪酸水平较低,心脏主要消耗葡萄糖和乳酸;出生后不久,与心脏负荷的急速增加相对应,大量的脂肪酸运输和氧化的基因被诱导,底物的使用转变为脂肪酸为主;而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时,心脏的能量来源又转为以葡萄糖的消耗为主,而下调的PGC-1α及其辅激活受体 PPARα可能是这种不良代谢转变的原因[11]。在一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研究中发现卡维地洛的抗心力衰竭作用源于增加了PGC-1α的表达,从而增加线粒体的生成[12]。总之,这些研究表明PGC-1α在调节心脏的电子呼吸链的效率和脂肪酸的氧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因此影响着心肌肥厚和心力衰竭的发生、发展。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PGC-1α的心脏保护作用可能有一个阈值效应。在一些实验研究中,PGC-1α敲除的小鼠只在压力负荷过重时才加重心功能障碍,而并不影响在基础状态下的心脏输出,在压力超负荷的心肌肥厚模型中,维持生理量的PGC-1α的表达对收缩功能并没有产生影响,在过表达PGC-1α组,心脏射血分数和左心室舒张末压和线粒体氧化功能仍没有改善,但是却发现过表达PGC-1α组的VEGF显著升高,因此推测PGC-1α可能是通过ERRα介导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机制,起到保护血管,减少细胞凋亡,从而减少纤维化,降低病理性心肌重构而发挥保护作用[13]。因此,PGC-1α在心肌肥厚中的保护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若想成为一个治疗性的靶点,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实验研究。
二、PGC-1α与心肌病
在很多心肌病中也同样发现了PGC-1α的下调,大量证据表明糖尿病损害了心脏线粒体功能,增加了心脏的氧化应激,PGC-1α的下调与糖尿病有关,特别是PGC-1α基因上的一个单核苷酸位点Gly482Ser的多态性更是与糖尿病的发病密切相关[14]。因此,降低ROS,恢复线粒体氧化功能可以改善糖尿病心肌病的心脏收缩功能,后发现白藜芦醇可通过SIRT1/PGC-1α 信号通路增加PGC-1α相关基因的表达,降低心肌纤维的氧化应激,提高线粒体的氧化磷酸化而预防糖尿病心肌病[15]。另有研究发现,与运动行为相结合的褪黑素补充,可以通过上调PGC-1α增强机体抗氧化活性,改善高脂血症,从而缓解胰岛素抵抗,这为糖尿病心肌病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方向[16]。此外,大量研究证实了脂联素的下调增加了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病的风险,在糖尿病小鼠模型中,给予外源性的脂联素治疗,发现其通过激活AMPK使PGC-1α的表达上调,增加了线粒体的生成,降低了缺血性心脏病的发生[17]。还有研究发现,在铁沉积性心肌病中,脂联素显示出保护作用,而这一作用是通过PPARα/PGC-1α信号通路实现的,PGC-1α辅助激活PPARα,进而激活下游血红素加氧酶1( HO-1),减轻了心肌损伤[18]。在阿霉素诱导扩张型心肌病后,PPARα及 PGC-1α蛋白在模型组中的表达明显低于正常组,线粒体内高能磷酸盐含量和线粒体转运活性明显降低,心功能显著下降,而予 PPARα 激动剂预处理后,PPARα/PGC-1α蛋白表达增加的同时,明显改善了阿霉素心肌病小鼠线粒体腺嘌呤核苷酸转运体(ANT) 转运活性,对血流动力学指标也有改善作用,延缓了心力衰竭的发展,而抑制 PPARα/PGC-1α表达时则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加速了心腔扩张和心力衰竭的进展[19]。这些研究证实了PGC-1α在心肌病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心肌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思路,可能为心肌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策略。
三、PGC-1α与动脉粥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程复杂,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凋亡,平滑肌细胞增殖、迁移,单核、巨噬细胞浸润,脂质代谢异常和泡沫细胞的大量堆积仍被认为是其主要的病理特征。近来研究发现,PGC-1α作为线粒体合成和脂质代谢的主要调节因子,同样可影响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
内皮细胞通过调节物质交换、炎性细胞的运输来维持组织稳态,内皮功能障碍是慢性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特征,内皮细胞功能障碍通常与过量的ROS相关,因此抗氧化途径是保护内皮细胞免受伤害的关键。许多蛋白质可以降低活性氧,有的抑制ROS的产生,如线粒体解偶联蛋白(UCP2、UCP3)和腺嘌呤核苷酸转运体(ANT); 有的直接清除ROS,如锰超氧化物歧化酶(MnSOD)、过氧化氢酶、过氧化物酶(PRX)3、Prx5和硫氧还蛋白2(TRX2)。PGC-1α直接调节这抗氧化因子。诱导内皮细胞中PGC-1α的过表达,锰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Prx3、Prx5、TRX2和ANT均升高,同时过表达PGC-1α会使内皮细胞中的ROS水平降低,PGC-1α通过协同ERRα增加抗ROS基因的表达,减少ROS介导的线粒体毒性和细胞凋亡[20]。内皮细胞中ROS的下降也与趋化因子和黏附分子减少有关,包括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CAM)-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和NF kB,提示PGC-1α在内皮细胞相关的炎性中发挥着作用。PGC-1α另一重要作用是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介导的炎性反应,减少炎性因子的黏附,减轻TNF-α所致的细胞内和线粒体内ROS的升高,降低ApoE敲除的小鼠PGC-1α的表达后,发现粥样斑块中的炎性因子增加[21]。最近的一些研究还发现,PGC-1α基因缺乏的小鼠促进血管凋亡,这和增加的ROS、线粒体功能障碍以及端粒反转录酶的减少有关[22]。
在众多动物实验中发现,长期的血管紧张素Ⅱ可引起内皮功能障碍,同时可检测到乙酰胆碱的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作用降低,而在野生型小鼠中激活AMPK可逆转此内皮功能障碍,但在PGC-1α敲除的老鼠激活AMPK却没有出现此逆转现象,表明PGC-1α介导了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而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障碍被普遍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决条件。大量体内、体外实验结果显示PGC-1α改善了脂肪酸诱导的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障碍,在血管紧张素Ⅱ刺激的内皮功能障碍和高血压模型中,PGC-1α的表达下降,而内皮细胞过表达PGC-1α则减轻血管紧张素Ⅱ的这一不良影响,PGC-1α/ERRα诱导内皮一氧化氮合酶(eNOS)的生成,从而促进 NO的生物活性,改善血管舒张功能,抑制动脉粥样硬化[23]。
血管平滑肌细胞也参与粥样斑块的形成,而PGC-1α对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的ROS也有类似内皮细胞中的清除作用。还有研究发现,敲除巨噬细胞PGC-1α基因,共轭亚油酸不能抑制泡沫细胞的形成,相反,PGC-1α表达水平升高能明显抑制泡沫细胞形成,另外,氧化性低密度脂蛋白 (oxLDL)进入血管壁,会引发血管壁的氧化损伤和炎性反应,而PGC-1α可阻碍 oxLDL 进入细胞,因而可降低血管壁的损伤[24]。有研究发现,血管平滑肌细胞中PGC-1α过表达增加ATP结合转运体A1(ABCA-1)表达,进而增强胆固醇逆向转运能力增强,降低血胆固醇水平,从而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最近发现的可溶性豆荚纤维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而其很大一部分作用是通过增加SIRT1和PGC-1α 的表达而实现的。
四、PGC-1α与心肌缺血
ST段抬高的急性心肌梗死(STEMI)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死亡原因,临床上一直在改善灌注策略以减少缺血时间,进而提升STEMI患者的存活率。然而,许多患者在缺血再灌注后仍然有广泛的心肌坏死,因此,探究缺血后灌注的保护机制有助于为临床治疗心肌缺血性疾病提供依据。早年很多心肌缺血动物模型中发现PGC-1α表达水平下降,而使用PPARs激动剂以维持PGC-1α的表达水平可以减少心肌梗死面积和心肌细胞凋亡,有助于保护心室功能。诱导PGC-1α过表达已经在神经组织和骨骼肌缺血及激烈运动时表现出有利影响,另有其他研究表明,适度、短暂的PGC-1α过表达在应激状态下可以产生有益的影响。缺血后灌注(I/R)模型中,对照组棕榈酸的氧化以及乙酰辅酶A的产量明显下降,而缺血后用七氟醚预处理I/R组脂肪酸β氧化显著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是PGC-1α/PPARα的表达水平也升高, 因而推测由此增加的内源性甘油三酯的利用可能是促进梗死后心功能恢复的原因,而PGC-1α的表达水平升高与Sirt1的升高有关。类似的,硫化氢预处理心肌缺血模型后可以提高 Sirt1/PGC-1α的表达,降低心肌梗死面积和心肌酶(LDH、CK)的漏出,从而减轻缺血后灌注心肌损伤,改善心功能,Sirt1 特异性抑制剂 EX-527 的应用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作用。通过在再灌注起始采用缺血10s,灌注10s的6次循环的方法进行I/R的预处理,发现预处理组心肌的氧化损伤明显降低,这是通过调节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nNOS)发挥效用的,而nNOS的保护作用部分是通过增加磷酸化的AMPK,进而诱导PGC-1α的表达,达到抗氧化损伤的作用,这提示了PGC-1α在I/R中的保护作用。
一项纳入31例前降支STEMI病例的研究发现,患者入院时的PGC-1α的表达程度对心肌坏死的程度有明显的预测作用,入院时检测到血清中PGC-1α水平较高的一组在6个月的随访中显示出较高的心肌挽救指数,并且左心室重构较轻,收缩功能恢复得较好。然而,在STEMI急性期诱导PGC-1α的表达,发现其梗死面积增加,6个月的随访发现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加,虽然与对照组相比不伴有明显的收缩功能恶化,研究者提示这种有害作用可能与PGC-1α介导的腺嘌呤核苷酸转移酶(ANT-1)的增高有关,缺血事件后过度和持久激活PGC-1α对心功能的恢复有着不良影响[25]。最近的一项研究提示PGC-1α在动脉可塑性的维持及应对急性压力负荷时具有正面作用[26]。综合文献报道,PGC-1α在心肌缺血中可能具有保护作用,需要更多的实验来探究其具体机制,以期为心肌缺血的治疗提供临床方案。
五、展 望
PGC-1α在心血管系统的线粒体生物合成,物质能量代谢和抗氧化应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在心肌肥厚、心力衰竭、心肌病、动脉粥样硬化以及心肌缺血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能正是因为PGC-1α的下游分子之多,生理效应之广泛,调控之错综复杂,才会出现一些与主流观点相悖的观察结果,例如在动物模型中,PGC-1α的过表达出现心脏毒性事件,而其基因的缺失又会导致心功能不全;在临床研究中,关于心肌功能障碍时PGC-1α表达的上调或是下调也有互相矛盾的结论。但是,PGC-1α对于心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已被认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PGC-1α作用靶点为人们所发现,其调控机制也逐渐清晰。因此,PGC-1α的众多信号通路上的分子以及PGC-1α的剪接体PGC-1α4可能成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干预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