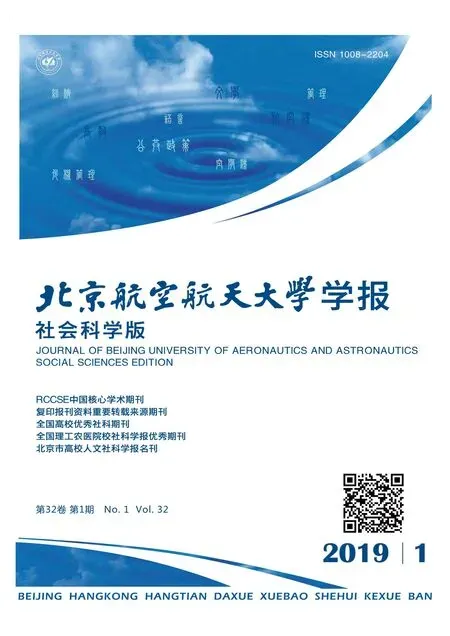跨媒介语境下《大都会》的身体符号认知叙事
杨 亭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一、引言
在西方文艺学与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的研究中,身份或身份认同命题,尤其是其中的混合身份认同在女权主义、后殖民等文学批评流派中的再现,使得文艺学研究中的阶级、性别、种族身份认同政治、狭义的主奴身份认同等意识形态论题变得不容遁避,也使得以下诸领域的研究均得以成为显学。譬如诠释学与哲学诠释学在文学、电影与文化史研究中论及的文化身份的建构的哲学传统问题,即文学通过所指性而获得意义的主张;批判与文化理论研究中的社会身份问题,即身体、心理、政治、意识形态、性和种族等因素在建构人们的身份时所起的重要作用问题;女性与权主义研究中的身份、人的身份、性别身份等问题;后现代性研究中的身份及其认同问题,如无产阶级及其异化,即工人阶级的特性与身份认同就属于去人性化和商品化;实验主义、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流派的小说文本中边缘人物的边缘化、身份政治、元话语、身份差别等问题;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先锋派艺术的视觉化艺术,尤其是电影艺术话语研究中的身份的根本性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中种族身份的确立问题,如对属下阶层、主子-奴仆、白人-黑人、驯化-顺从、主奴范式等的研究;他者建构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即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等的关系问题;以族裔文学批评为基石的离散理论研究中的身份政治、文化身份认同、种族身份等;性别身份与民族身份;身份认同与主客体;叙述者与受述者及其意识形态叙事;非自然叙事与女性主义叙事的关系;“可然世界”理论与身体叙事的关系;空间叙事、空间书写与主题和人物的关系;伦理、伦理批评与伦理叙事的关系等命题、论题,不一而足。[1—13]因此,有论者则诘问,“怎样才能恰如其分地从身份认同入手,重新解读文学文本,让那些在文本中掩压已久的历史、沉默的少数声音、扭曲的种族经验,以及各种边缘的身份问题一一解开面纱,从后台走到前台?”[14]465—474那么能否据此衍生出另一个母题,即叙事学研究中的(弱势)受述者[15—16]及符号学研究中的物种符号是如何以他者身份并借助其沉默的少数声音(文章意谓非自然叙述声音[17])分别通过从属、“非叙述”、自白以及身份、自我、物化了的身体、身份的符号化解构而获得其叙述地位的?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文本《国际大都市》(Cosmopolis,2003)与其视觉化文本的《大都会》(2012)就涉猎了此问题,从而实现了身份社会学问题的叙事学转向,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双跨媒介叙事中的忠实性改编问题。
二、原型类型与身体符号的述真语境
原型(archetype)既“是领悟的典型模式”[18],又是“一种文学性象征,或一系列象征。由于这些象征在文学文本中被反复使用而成为了一种惯例”[19];“原型可以是意象、细节描写、情节和人物四大类型。人物又可分为善恶两类……”[14]828—836,即语言学、哲学及文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二元对立模式。针对其中的人物类原型,文章称之为显性原型,把它类原型称为隐性原型;把主要人物(主角)和次要人物(配角)分别称为显性叙述者和隐性叙述者;把既非主要人物(主角)又非次要人物(配角)者称为极端叙述者。在跨媒介叙事研究中,读者与受众往往诉诸其眼光或曰视点,并通过文字和视觉的认知提示功能来实现凝视,并固定(anchoring)叙事认知形式、功能及叙述视角(文章采热奈特的术语“聚焦”)来探究书面与电影叙事的跨媒介叙事。读者与受众尤其对后现代作品中的非自然叙事声音充满好奇,因为应如何解构因人物(角色)的身份,尤其是其身份的阙如而呈现出的被符号学语境隐喻化了的政治无意识现象。具体而论,真实读者与真实受众或许会对《大都会》里身份阙如的女角在汽车里从事的性消费现象浮想联翩:他们之间是婚姻关系、正常关系、非正常关系或是婚外关系?[20]而隐含读者与隐含受众除作此联想外,他们可能还会思忖,作为非自然叙事声音的女角在汽车这一“可然世界”(possible world)里的行为应如何促使他们诉诸被认知叙事进程(文章意谓,小说文本在改编学方面所呈现的读者与受众对作者与人物和导演与角色的情感认知以及作者与导演的叙事与读者与受众在思维或心理方面的关系等)内化了的各种意象、细节描写、情节等隐性原型类叙事策略而在自己的大脑中映现出另一个故事世界(storyworld),并自问,在此种不同的世界里,既作为隐性叙述者又作为符号物化(reification)下的该女角是如何被作为身体符号叙事的?以上这些跨媒介叙事学议题就体现了《大都会》把身体作为符号叙事的后现代属性。此外,《大都会》的两种跨媒介叙述均借助文本对话与叙述对白等复调狂欢式的叙事策略,阐释了意象-镜头映射、细节-动作铺就、叙述者-角色塑造等情节构成要素在搭建整体叙事架构方面所呈现出的认知叙事性,即两种不同叙事媒介通过揭示处于三元对立之态的显性叙述者、隐性叙述者及极端叙述者的非自然身份或阙如的符号化现象,从跨媒介语境探讨了叙事学,尤其是认知叙事学的叙事构成要素、叙事形式及功能等诸多概念性范畴以及这种跨媒介叙事所具有的非自然认知属性,尤其是其中的身体叙事的认知属性。其次,所谓狭义身份认同的符号论,本文意谓,如何让《大都会》中那些沉默的、无名的及非自然的叙事声音,即人物(角色)—身体符号学意义上的行动者(actant),以其下层群体边缘化属性及阙如的叙事者的他者参与者身份走到前台,对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体系,包括其所处的阶级、所属的性别以及所具有的种族身份去中心化?因为后现代语境下的身份认同、身体叙述及其符号化的总体特征乃是去中心的,也因为当受众、隐含受众在没有阅读小说文本而去观赏或曰凝视该影片时,若只想通过文字和视觉的认知提示来辨明被边缘化了的群体人物的身份符号,那是很难把握电影叙事的叙述机制的,尽管受众的认知作用不容小觑。最后,从认知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本体论方面而言,《大都会》还涉及了人物(角色)的被符号化了的身份认同、身份政治及身体美学。身份政治及身体美学研究中的身体总是表征着人物、身份及其性别的物质属性。空间——“可然世界”的存在即可实现叙述者的身体修辞策略的本体论意义。既然身体有着物质属性,其美学意义在一定的层面上就有了关于身体的消费叙事,对于性的消费即是其中之一。受众,尤其是隐含受众眼中的身体符号、性别符号及人物符号均指向更高层面上的文化符号、权力符号及政治符号,这既是因为意义与关系、能指与所指、形式与功能、本体与认识、结构与解构等等的不在场才需要符号化的所指,又是因为“符号学只研究那些意指关系欠明确的现象”[21]19。《大都会》中的人物(角色)间的意指关系欠明确,符号与指称不能合一,即出现了所谓的述真(veridiction)语境现象。
三、叙事构成要素的形式与功能及其跨媒介表征的认知叙事进程
一般而论,无论是书面叙事还是电影叙事,其叙事构成要素可归纳为两种:第一种为一个或一系列事件,可呈现为线性的或非线性[22]177特征。
此种要素在书面叙事中具体表征为:一系列展示整体性和意义的关联性事件,由开始向中间和结束方向运动。而对于人物叙述地位的研究,可分为:仅有一个主要人物、有多个主要人物、有人物群体、有集体主角和无主要人物在对话中出现。[22]178
此种要素在电影叙事中则具体表现为:处在“一个整体的、叙事的、视听的话语之中”[23]22[24—25]。人物分配的研究主要以角色重要性与演员知名度的关系为依据,依靠电影对白再现。此外,电影叙事在宏观时间层面有未注明日期的叙事和注明日期的叙事;在微观时间层面有时序、时长及时频[23]140等诸范畴。
第二种叙事构成要素为借助语言再现这些事件。其一般表现为:第一,一个公开或隐藏的叙述者;第二,一篇或多或少带有特征的叙述;在叙事时间顺序里又包括倒叙和预叙;第三,一个或多个作为再现出发点的视点;第四,一个受述者及上述再现的观众。[22]203
第二种构成要素在书面叙事中具体表征为文本中所刻画的那个讲述者。可分为:(1)全知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多,即零聚焦;(2)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物之所见,即内聚焦;(3)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即外聚焦;(4)混合叙述者。[22]156
此种要素在电影叙事中则具体表征为一种机制:其特点为:(1)包括影像师、看不见的叙述者等;(2)电影有叙述但没有叙述者;(3)电影叙述者的构成元素之一是画外音[24];(4)传统叙述可分成远景、近景、特写和影像的交替蒙太奇,如正打与反打镜头[25];(5)有固定的内聚焦、变化的内聚焦或多重的内聚焦或泛视点、单视点及多视点[26]以及再现的观影者,即受众。
此外,在双跨语境下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中,有一些范畴显得至关重要。譬如,语境、认知模式、叙述视角、叙述声音及叙事空间等;电影叙事学的主要认知范畴可归纳为时间、叙述、视点、画面、声音及空间等。[27]而就叙事学本身而言,叙事一般被界定为“借助语言,尤其书面语言再现一个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22]4或“一个完成的话语,来自于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23]22或“由一个、两个或数个(或多或少显性的)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数个(或多或少显性的)受叙者传达一个或更多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表述。”[28]简言之,认知叙事往往关注如何直接或间接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跨媒介叙事认知进程即是揭示隐含读者与隐含受众如何在两种语境下实现对两种媒介的意义生成、各种表意手段及表意过程的认知的。[29—31]
四、《国际大都市》——《大都会》的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对话性复调狂欢在其“可然世界”里实现的身体符号语义关系
指号过程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的二元范畴论在语言学、符号学及叙事学等研究领域都有着其不可或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32]认知叙事学研究中的叙事进程在书面叙事和电影叙事的跨媒介叙事上就是以这种能指及所指的指称性建构借助聚焦法实现了人物-角色之间的认知符号关系的。《大都会》里的主要人物-主角的能指和次要人物-配角的所指即对能指的权力及所指的劳动-消费关系施行了异化叙述,对作为具有物质及社会属性的人物-角色的身体及其符号乃至生命等进行了符号化叙述,其实质就是对人及其身体、生命等实体实现艺术化的符号性叙写。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即是叙述艺术借助符号修辞,如符号隐喻及其变体等实现对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物的物化、符号化、片面化的任意消解。这也就造成了叙述艺术的符号学转向及后现代叙事的泛艺术化,即对经典的解构(续写、重写、改写、拼贴)、颠覆(戏谑、丑化、戏仿)乃至对文学场实行反乌托邦化(dystopia)。《大都会》中依次出场的各色人物都被物化与符号化了,成了符号化了的人物,即所谓的符号载体,只能等着真实读者与隐含读者[33—34]以及真实受众与隐含受众去感知和解码。那么,双跨语境下的《大都会》在刻画这些人物角色时采用何种技巧,又是如何通过描写、对话和行动把人物塑造出来[35]的?又是如何结合人物类型原型论实现人物之间的对话性复调狂欢并对人物的身体叙事进行符号学解码的?
2012年,加拿大著名导演大卫·柯南伯格把德里罗的Cosmopolis小说文本拍成了同名电影,中译名为《大都会》。(为了区分其与另一部名为Metropolitan《大都会》的电影,文章把Cosmopolis的小说名称译为《国际大都市》,电影名称仍采《大都会》。)在解读《国际大都市》——《大都会》的叙事时,有一种沉默的少数声音,即非自然的叙述声音,终于以其各种边缘的身份从后台走到前台,这种客体对主体、他者对自我、多数对少数等构成的二元模式的急遽对立在后者将被枪杀的刹那间达到高潮,也为读者——受众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也许“只有符号学才能解决小说与电影的沟通问题”[21]318。
若从叙事构成要素的第一个维度,即事件的时间序列方面而言,《国际大都市》的作者一开始就把事件的时间标注为2000年4月的一天,接着却并未使事件的时间安排呈线性发展,而是在第一部第一章的结尾处,通过闪回这一叙事策略,插入了次要人物本诺·莱文的自白一章,然后使事件接着呈线性发展;而叙事环境则主要被置于一辆在繁华的麦迪逊大道、第五大道、第六大道、第八大道、第十大道、第十一大道上缓慢行驶的一辆加长的白色豪华轿车里;具体时间是从叙述半夜失眠的他开始,到约莫当天“月亮……成了一弯淡淡的月牙”[36—37]时至;与之相照,《大都会》的导演则使事件呈线性展开,只是未在最初的镜头里就载明事件发生的年月;叙事环境被置于繁华大街上的一辆加长的白色豪华轿车里;时间是从上午至午夜的一个时间段。
若从叙事构成要素的第二个维度,即借助语言再现这些事件这个方面而言,书面叙事与电影叙事又是如何达到此目的的?
作为后现代叙事策略之一,电影视觉化叙事下的《大都会》打一开始就使受众如坠云雾之中。具体而论,若以主角-配角等二元人物论为肇始,该电影叙事的主要情节可概括如下:荧幕一开始,时间大约是上午,有若干辆白色加长的豪华轿车等候在一幢大楼前,随即两个都系着黑色领带的年轻人出现在这幢大楼前,一个说是要去理发,一个说是会出现交通拥堵问题,后来其中一人去找汽车,另一人坐进轿车里,此时的受众才意识到他俩也许是老板和下属的关系,即所谓的主奴关系。对此,若从认知叙事学的视角而言,该电影叙事机制和小说文本的书面叙事的文本提示的显著不同之处就是对配角的身份叙述,受众除了对似乎作为主角的那个青年人的身份,主要是通过其说话口气有所了解外,对其他后来依次出现在他周围,包括汽车上人物的身份,若从受众的凝视视域来看,都云里雾里。随着类似诸多插入性事件的发生,更多的身份认同的在场与阙如现象就出现在了受众们面前。若还按人物在影片里的出场先后顺序排列,可被分别所指为:一个坐在帕克的加长轿车,即所谓的“可然世界”里和他交谈的年轻人;帕克下车去见坐在一辆出租车上的年轻女人;另一个坐在帕克的加长轿车里的卷发年轻人;一个和帕克在那辆加长轿车里交谈的女人;一个在帕克的轿车外对着车窗提溜着一只老鼠的女人(即所谓的极端人物一);一个在车外锻炼、随后钻进帕克的轿车里的女人;一个叫印格兰的男医生;一个从帕克的车旁经过戴着墨镜的男人;书店里的一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另一个坐在帕克的轿车里的女人;书店里的那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在帕克的轿车里;和帕克一同在舞厅里观看跳舞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男人(即电影叙事里的极端人物二);进入汽车告诉帕克说唱歌手布鲁瑟·费斯死讯的一个不知名的黑人(小说及电影叙事里的极端人物三);一个攻击帕克的馅饼刺客(小说及电影叙事里的极端人物四);帕克的黑人司机;一个年长的理发师;以前那个从帕克的车旁经过的戴着墨镜的男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大都会》表现了显性叙事者与隐性叙事者的身体叙事的符号学修辞属性,即身体叙事的身份符号的提喻化现象。为什么此人要带着墨镜?墨镜喻指什么?在比喻学研究中,喻旨与喻体之间存在著一种映现关系。具体到对身体-身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作为喻旨的配角的身体-身份在《大都会》中如何被映现在具像化的喻体中?笔者认为,《大都会》中配角的身体-身份的喻体即是他们身体-身份的商品化现象,即可以被主角-老板肆意消费的配角们的身体及身体符号的转码(transcoding)。
总之,《国际大都市》与《大都会》的叙事构成要素及其具体表征可做如下归纳:
两者的叙事构成要素之一:从一连串的行动的维度而言,《国际大都市》的书面叙事是呈非线性的,即叙事有开始、预叙、中间和结束;而电影叙事的《大都会》亦是呈线性的,即有开始、中间和结束;若从人物的维度而言,《国际大都市》的书面叙事里有一个主要人物,即主人公埃里克·迈克尔·帕克及十几个次要人物,如安保主管托沃尔等(小说文本对他们的塑造及其获得的叙述地位,请见下文所述。)而电影叙事的《大都会》里有一个主角,即中心人物(但却不能称之为英雄人物,姑且称之为反英雄的)埃里克·迈克尔·帕克及十几个配角,如安保主管托沃尔等(电影文本对他们的塑造及其获得的叙述地位,亦请见下文所述。)从一个环境,即描写的维度而言,书面叙事主要是一辆豪华加长车;电影叙事主要是一辆白色豪华加长车及其内部设置;在从一个时间顺序维度而言,书面叙事在宏观时间层面是注明日期的叙事,即2000年4月的一天;而电影叙事在宏观时间层面是未注明日期的叙事,即事件发生的日期不详;但有推断叙事日期的基准点,如受众可通过人物的着装、乘坐的豪华加长车及车内先进的电子装置等,可推断电影的叙事时间为当代。
两者的叙事构成要素之二,即借助语言再现这些事件。若从叙述者的维度而言,书面叙事属于混合叙述者,即第三人称叙述者“他”埃里克和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本诺·莱文的混合;电影叙事,无叙述者的构成元素,如“画外音”等,故此部电影无叙述者;从叙述维度而言,书面叙事属于无标记叙述,同时又采用了预叙的叙述策略,即反面人物我(本诺·莱文,真名为理查德·希茨)提前讲述了后来才发生的“我”和埃里克的暴力冲突;电影叙事因为故事事件的情节发展属于自行展开,故该电影叙述属于无标记叙述的叙事;从视点维度而言,书面叙事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点与第一人称叙述视点相结合;电影叙事则属于零聚焦;从受述者或受众维度而言,书面叙事里有次要人物托沃尔等(对他们的刻画,详见下文所述);电影叙事里即为再现的受众。
此外,书面叙事的《国际大都市》(作为一种散文虚构作品)与电影叙事的《大都会》(作为一种视觉虚构作品)的叙事机制在叙事时间之维度,即顺序、时距和频率方面可做如下归纳:一般而言,叙事学在对书面叙事,尤其是对后现代作品的研究,就其人物塑造在叙事性方面的意义来论,亦是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对话和行动来实现的。而就电影叙事而言,(隐含)受众要实现的电影阐释一直被其中人物的身份问题困扰着。譬如说,在《大都会》的后半部分出现的那个举止古怪的人物为何要以其边缘化身份去对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的主体,即欲置主人公于死地呢?答案似乎可从后现代主义文化,尤其是福柯对权力、身份、自我等命题的哲学阐释中获得,因为“身份政治通常有意识地彰显边缘化身份,对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38]。此外,交际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发话者—受话者及其通过话轮[39]实现的对话而显现的叙事地位和叙述地位亦可解释这种身份的阙如现象,因为正是交际中语言的对话性复调狂欢彰显了对话对“事物的真理和真相的探讨”[40]。依巴赫金的复调叙事理论及对话狂欢叙事理论,不论是人物之间的公开对话或是内心对话,还是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元对话,人际之间进行交流时,对话必是在场的,可能伴随着停顿、沉默、结巴等副语言现象,并应该遵循某些原则,如诚信原则、公平原则、合作原则及礼貌原则等。其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对话的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及解释意义等符号意义可诉诸叙事视角、叙事聚焦及叙事角色来解读。下文即依此理论及跨媒介叙事对身体美学与身体政治的符号学形塑理论(configuration)依次对照列出《国际大都市》-《大都会》这两种叙事媒介对其人物的塑造及其获得的叙事和叙述地位。
(第三人称叙事视角/零聚焦/发话者)他(埃克·迈尔·帕克):主要人物(主人公/主角)/显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托沃尔的对话“我要去理个发”;“管他呢。我要去理发。我们要穿过市区”。电影叙事:和托沃尔的对白“我要理发。我们去城市另一边。”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学意指表现为:焦躁不安,颐指气使;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固执己见,专横武断。坚持去理发,结果被其公司解雇的前雇员枪杀。
(第三人称叙事视角/零聚焦/受话者)托沃尔: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去哪儿”;“总统正在市内”。电影叙事:和帕克的对白“去哪”;“总统来了”。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性格不够沉稳;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忠心耿耿,而又粗心大意。因保护老板不力,被老板借机枪杀于自己的枪下。这就是“符号撒谎论”的例证。
埃莉斯·希夫林/受话者: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我不能让你送。绝对不行。”电影叙事:和帕克的对白“不行。绝对不行。”书面叙事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善解人意,天真善良。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特立独行,又不失人妻风范。
迪迪·范彻/发话者: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我约过你吗。”和帕克的对白“我约了你吗。”书面叙事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善于出谋划策,讨人欢心;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工于心计,而又不失天真。
简·梅尔曼/发话者: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这么多的豪华轿车,我的天呀,根本无法分清。”电影叙事:和帕克的对白“天哪,这些豪华车,都长得一个样子。”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心直口快,消息灵通。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喜欢运动,有敬业精神。
维娅·金斯基/发话者: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我们要考虑一下挣钱的艺术。”和帕克的对白:“我们来思考一下赚钱的艺术。”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精于数字,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有经济头脑,精明能干。
肯德拉·海斯/发话者: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你做了运动。”电影叙事:和帕克的对白“算出来了吗。”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大胆前卫,敢于挑战。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自信十足,又温柔顺从。
易卜拉欣·哈马杜/发话者: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我们到了。”电影叙事:和帕克的对白“到了。”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自食其力,忠诚可靠。
安东尼·阿杜巴托/发话者: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你怎么这么久没来了。”电影叙事:和帕克的对白“怎么好久不见你来了。”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随和谨慎,世故老练。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和蔼可亲,与世无争。
(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零聚焦/发话者)我(本诺·莱文,真名为理查德·希茨):次要人物/配角/隐性人物及极端人物。
书面叙事:和帕克的对话“你在这里干什么。”电影叙事:和帕克的对白“你在这儿干什么。”书面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为人古怪,人格和生理都有问题。电影叙事里的身体符号意指表现为:贫困潦倒,报复心切。
此外,若从对极端叙述者的他者身份叙述的插入性叙事维度而言,两种叙事通过对此类人物的描写、对话—对白、行动等可概括为: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阿瑟·拉普遇刺;卖墨西哥炸玉米卷的男人;一个穿灰色弹力衣服的女人;工地里干活的建筑工人们;站在以色列银行外面取款机前的一个人;走在帕克桥车两边的两名保镖;参与电影拍摄的人群(电影叙事中未涉及此点,这就涉及到改编学问题);馅饼刺客安德烈·彼得雷斯库(具有双重身份,即隐性叙述者及极端叙述者);说唱歌手布鲁瑟·费斯;复仇者理查德·希茨(具有双重身份,即隐性叙述者及极端叙述者)等。
总之,通过上述的阐释可以得出,若对人物-角色身份认同或者阙如现象从身体符号学在书面叙事与电影叙事里的不同建构机制而言,主角—配角—辅角、主体—客体—它体、我者—他者(包括同性恋者、女性等)—第三者等等角色及其分配只有读者—受众通过叙事文本中的认知提示,并采取特有的认知策略,才能让各种边缘人物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读者的阅读及受众的凝视下的《大都会》里角色身份的政治化阙如、异化及其通过对话性复调狂欢实现的身体符号学叙事及其语义关系等等都与认知叙事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 、结语
从符号学意义上来讲,认知叙事学“在研究范围上是跨媒介的”[41],亦即戈德罗所谓的互介性问题。书面叙事的《国际大都市》和电影叙事的《大都会》即是如此。至于电影的改编学与改编研究[42]、电影对虚构散文改编的忠实原则等等问题,除了可以从“文字-影像”[43]的技术性转换,如台词设计、蒙太奇剪辑法、叙事结构的重组及光影技术的应用等、从文本化到视觉化、从静态叙事到动态叙事等方面给予探讨外,一般的观点是,影视导演可以对书面文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加工、创造。也许正因为如此,《大都会》的导演就把促使其主人公的金融帝国崩塌的国际金融市场及货币从东京及日元换成了深圳及人民币;把主角帕克的安保主管托沃尔从一个没有脖子的秃顶男人转接成了一个英俊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