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空间”: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的空间解读
艾志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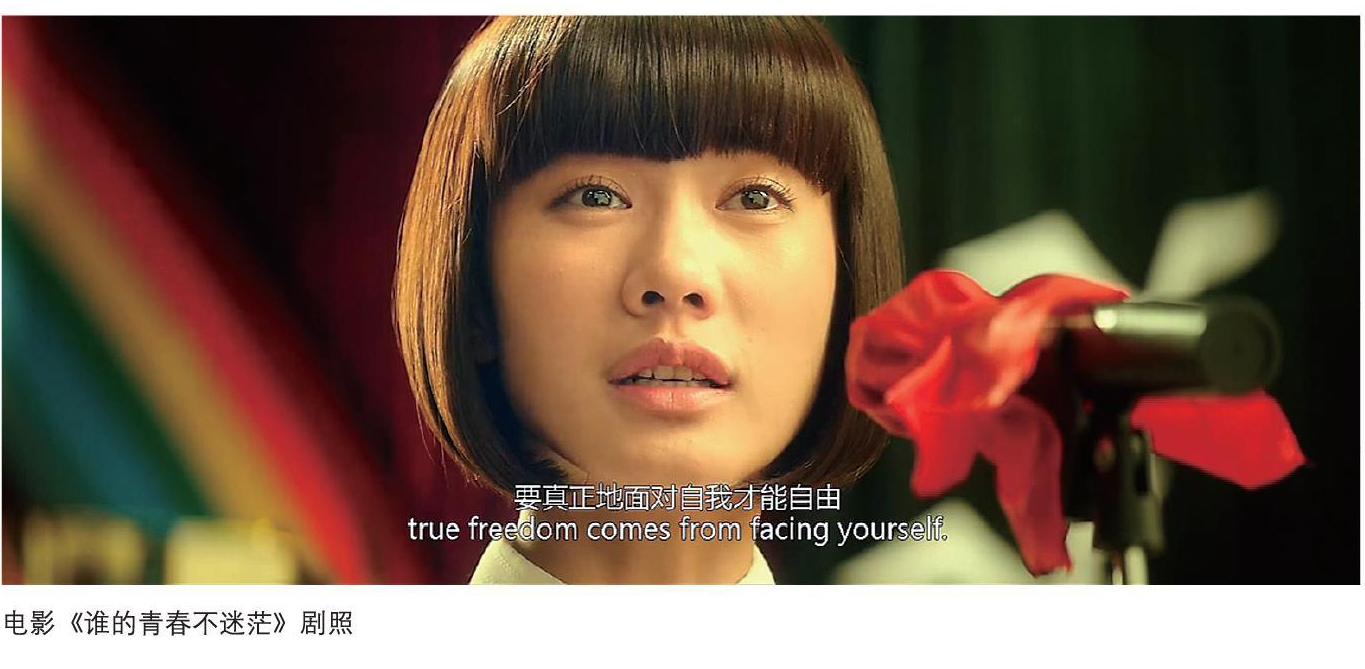
【摘要】 “家”“校园”和“异域”是青年人成长所经历的三个重要空间,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深入地表现了这三个空间的内在断裂性。“家”空间的温暖属性被置换成了不完整、布满裂隙的“压抑性装置”,校园空间失去“知识生产力”而成为青春爱情的历史见证者,异域空间由于不能实现青年人的梦想而变得像一座未知的现代性迷宫。这些电影通过空间的多维建构来重新审视青少年的生存环境、身份现实以及内心世界,从而彰显一定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关键词】 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空间;断裂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作为青少年生存状态和心理世界的艺术化反映,其优秀作品往往通过对家庭空间、校园空间以及异域空间的多维构造,展示与青少年有关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揭示他们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境遇,从而建构出丰富多彩的青春故事。尽管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出现了同质化、套路化、单一化等倾向,但客观地说,一部分作品对空间的挖掘和阐释具有一定的思辨性,并且秉承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展示青少年所处空间的内在断裂性,诸如本应温暖的“家”空间弥漫着分裂、压抑和焦虑,原本传道授业的校园空间服务于恋爱和谈情,充满机会和梦想的异域空间则成为了一座未知的现代性迷宫。这些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而是汇集了“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可知与不可知、重复与差异、精神与肉体、意识与无意识”[1]的混合体,从而让观众重新审视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和未来出路。
一、“家”空间:断裂的“压抑性装置”
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中的“家”空间主要呈现出家庭结构的断裂,这种“断裂”意味着“家”始终以一种“缺席的在场”状态影响着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父母不善于处理生存关系、爱情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等,形成贫困、离异和出走等一系列不良后果,破坏了家庭的完整性。《我和爸爸》中小鱼的母亲因为车祸去世,她被迫与几年未见的父亲一起生活。小鱼父母的离异关系使她整个青春期都处于单亲家庭,母亲的去世又让她进入另一个陌生的单亲家庭,家庭结构的失衡对她造成了双重伤害。好在影片采用了一种“温情”的叙事方式,父女间的爱最终缝合了“家”的缺口。而《悲伤逆流成河》中的易遥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从小就是别人眼中的“赔钱货”,她的母亲从事着难以启齿的职业,最终她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此外,处于这种断裂的“家”空间的青少年形象还有《地下的天空》中失去母亲音信的井生,《玩酷青春》中父母离异的何志鹏以及《狗十三》中母亲离家、父亲再婚的李玩等等。
平心而论,当这些断裂的“家”空间成为一种影像症候时,我们不仅要把它看做是弗洛伊德在探寻人类无意识时所讨论的关乎主体(青少年群体)焦虑、定位等问题的私人领域,而且还要将其视为更大的囊括历史性、社会性等范畴的文化场域,从而使作为独立单位的“家”空间联结成一个不再局限于书写个体经验的网状结构。弗洛伊德认为“家”在探寻主体无意识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把父亲、母亲和孩子组成的有血缘的三角关系类比成一种“压抑性装置”,在这种装置内,孩子受压抑、被拒认的无休止的欲望本能几乎成了无意识的全部内容。原生家庭的“压抑”往往是青少年成人过程中产生各种症候的根源,他们在焦虑情绪和错误定位中迷失自我。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正是通过断裂的“家”空间对这些主体无意识情绪予以影像观照。青少年群体的“焦虑”是他们在压抑的家庭状态中所产生的个体情绪的集合,譬如《青红》中青红因举家搬迁而经历的成长焦虑,《青春派》中居然因母亲拒绝早恋所引发的升学焦虑,《嘉年华》中小米和小文因家庭破裂所产生的女性焦虑,《过春天》中佩佩因家境贫寒而加入“水客”军团的生存焦虑,这些焦虑情绪严重抑制着他们的成长。如果说断裂的“家”所引发的焦虑情绪是一种短期状态的话,那么它给青少年群体所带来“错误定位”则是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左耳》中的张漾即在家庭的压抑性装置中失去自我,被母亲抛弃的他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报复者”,他通过黎吧啦让母亲的继子许弋身败名裂。他的报复行为造成了许弋、黎吧啦和李珥等一系列人物不可逆的结局。可见,他对自身“报复者”的身份定位是自孩童时期便形成的,直至成年都很难改变。
当然,断裂的“家”空间除了引发青少年群体的种种无意识状态之外,其本身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又带有某些历史性和社会性的隐喻意义。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变迁史实际上就是代际推演的人口发展史,其中“家”充当着文明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个体”则是“家”空间里的最小细胞。可以说,青春群体的变化史,实际上折射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史,在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我们也看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史,三者呈现出“中国变迁史—家庭史—个体成长史”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就历史演进来看,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中的“家”空间并非只是一个具有实体意义的能指,它更像是一种包含个体成长并指涉历史变迁的结构化的隐喻。另一方面,与“家”作为历史组成单位和个体成长空间所表现出的封闭性不同,社会的发展、资本的流通以及利益的交换要求“家”的敞开以及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流动。因此,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在着重表现主人公离家奋斗、成长和创业等故事时,对“家”空间的影像表达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温暖港湾,它可以是《孔雀》中平淡无奇的五口之家,也可以是《小时代》系列中争夺家产的豪门之家,更可以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谢训和高宝镜的农民之家,这些压抑的“家”空间恰恰为主人公“走出去”寻找自由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叙事情境。
二、校园空间:青春爱情的历史见证者
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電影中的校园空间往往不再是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读书圣地,出于故事性和可看性考虑,它被虚构成主人公纯真爱情的发源地,“爱情成为所有矛盾的救赎和终结,剧情也永远依靠爱情来收拢”[2]。一方面,在场景选择上,教室成为校园空间的主要场所,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消解了三尺讲台的威严凛然,教室逐渐走下神坛。以《同桌的你》为例,影片中的教室是林一和周小栀初次见面的场所,在那里,林一第一次看到周小栀迷人的笑,为她打抱不平、为她调换班级、为她努力学习,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周小栀。此外,像《分手合约》《匆匆那年》《何以笙箫默》等电影中的校园和教室同样也都成为了男女主人公相恋、相爱的必备空间,即使是像《全城高考》《少年班》等以“高考”和“学习”为主题的影片,校园和教室仍然是一种感性的浪漫空间,男女之情占据着相当大的叙事篇幅,从而为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建构一种美好的乌托邦想象。
另一方面,在院校设置上,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对校园的定位显得比较多元,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类、理工科类学校外,像《青春失乐园》中的法学院、《万物生长》中的医学院、《栀子花开》中的舞蹈音乐学院,这些专业院校的背景设置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主人公的情感叙事与成长叙事,不仅为青春故事的讲述增添更多新鲜的元素,而且以更加生活化的方式吸引受众的眼球。《青春失乐园》中来自法学院的程小雨等人的故事则完全架构在了“打击犯罪分子”的情节之上,既讲述女孩们的成长故事,又讲述程小雨和汪小菲之间的爱情故事。《万物生长》中的解剖室则成了秋水的“泡妞神器”,他带柳青参观各种泡着福尔马林的骨骼和器官,阴森恐怖的解剖室在电影中完全被建构成一个充满情欲、令人好奇的场所。《栀子花开》有意模糊了校园的具体信息,看似只有音乐和舞蹈两个专业,主人公们的故事则主要围绕“跳芭蕾”这件事展开。因此,校园背景的多元定位给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提供了更多新鲜的元素,“对正处于青春进行时的90后群体来说,童话般的爱情故事通常又会带来移情式的精神仿像”[3],从而让故事更易被观众所接受。
如果说在空间层面上校园空间是主人公爱情萌芽地的话,那么在时间层面上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中的部分校园空间则被置于历史的洪流中,让主人公们的情感体验与宏大的历史叙述紧密结合、共同演进,从而成为主人公青春故事的历史见证者。电影《十三棵泡桐》对校园的历史化建构是通过教室墙壁上广播的同期声来完成的:“申请加入世贸,不仅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在全世界面前像醒狮般地站起来了,更意味着炎黄子孙五千年来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这标志着我们经济将完全抛弃计划经济的模式,走向市场经济的轨道,这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影片第一次通过校园广播定位时空,让观众知道这个发生在泡桐树中学的青春故事大致发生在“申贸”前后。而这个简单的历史叙述与主人公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样的严肃历史背景之下,泡桐树中学的“炎黄子孙们”呈现出一种懒散、嬉闹、不学无术的状态。讽刺的是,中华民族如醒狮般地崛起,青春群体却如枯枝般地萎靡;经济效益在走上正轨,文化发扬却在坠入深谷。这既是对青春群体成长过程中迷失、迷惑、失序状态的真实写照,又是对青春群体现实成长状态的深刻反思。到了《同桌的你》,电影则完全按照历史时间来顺序叙述,从1996年开始,影片用时间线串联起了男女主人公长达数十年的爱情长跑,校园空间则成为他们爱情的见证者。影片以广播、电视和历史事件等一系列手段来强化特定的历史时空,如中国加入WTO的广播信息、天津卫视播放的“我的校友是明星”、“911事件”和非典事件等,这些符号真实地还原了主人公的青春时空,最重要的是,它们参与叙事,成为推动爱情故事发展的必备条件。如在“911事件”中,林一和周小栀不顾班主任的反对,翘课去参加校外游行。抗议之声、此起彼伏,林一在1995年5月9号那天第一次拉住周小栀的手。人潮涌动、摩肩接踵,林一和周小栀被迫松手,颇有点战火中爱情的感觉。可见,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中的大部分空间建构都在为主人公的青春故事服务,校园空间则失去“知识生产力”,转而成为青春和爱情的历史见证者。
三、异域空间:未知的现代性迷宫
如果说正青春期的“家”空间和校园空间展示的是主人公情感秩序的话,那么后青春期的异域空间则更多地展示了主人公所身处的理性的社会秩序。他们终将离开家和校园,踏入另一个异域空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目前这个时代也许基本上将是属于空间的年代。我们置身于一个共时性的年代,我们身在一个并置的年代,一个远与近的年代,一个相聚与分散的年代。”[4]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即展示了这样一个空间并置与空间流动的年代,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主人公都发生着物理空间的位移。从表现形式来看,这种位移通常有“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从原乡到异乡”等;从行动目的来看,主人公通常有升学、打工、创业等几类目的;从发生时间来看,这种空间迁移通常发生在主人公成年后的后青春期中。例如《半碗村传奇》中的书立前往北京读书,《谁的青春不迷茫》中的高翔前往非洲追求自己的梦想,《七月与安生》中的安生离开南方小城前往北京打工。
不难发现,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中的空间置换与地点迁移已然成为一种叙事常态,这不仅是为了给主人公的核心行动建构合理的叙事情境,而且也是通过空间的打开来丰富电影的叙事艺术。然而,异域空间本来应该是主人公寻找梦想、实现自我的乌托邦圣地,但事与愿违,他们的情绪被再次压抑,他们的行动依旧受到限制,这个空间实际上成为了一座充满困顿、失望以及不确定性的现代性迷宫。
由于断裂的“家”空间对主人公造成的压抑心理,使得他们不能真正体验异域空间的敞开性和自由性,他们看似越过了围城,实则仍旧因无法融入异域空间而被再压抑。这种再压抑性主要通过异域空间的景观来建构。一种是街道,“街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体现了城市的流动性、匿名性、混乱性特征”[5],《我是路人甲》中的街道报纸横飞、路灯静默、人影稀疏,繁华熙攘的影视旅游基地被强力解构,而在视觉上展现了一个与孤独的青年群众演员相契合的现代化都市想象的另一个“真实”维度。《同桌的你》中美国的街道川流不息,白种人行色匆匆,而林一孑然一身,站在街道的中央等红灯、吃汉堡、看监控(他与周小栀曾希望一起对着美国街头的监控拍照),街道的“闹”与主人公的“静”形成鲜明对比,更显空间对个体的压抑。另一种是城市底层景观,当电影镜头游走于底层景观时,北京、成都、上海、纽约以及洛杉矶等大城市的光鲜的一面便被层层遮蔽,暗示青春群体的压抑状态。电影《后来的我们》中以见清和小晓的视角展示了“北漂”所处的底层文化景观,拥挤简陋的群租房、鱼龙混杂的手机卖场、摆满光碟摊位的地下通道,都给青年人的城市生活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印记,从而让观众看到青春群体在异域空间中的真实生活状态。
青年群体在异域空间中遭遇情绪压抑的同时,也在行动上受到诸多限制。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中的主人公离开原初空间而到往异域空间的行动目的多种多样,有创业、有圆梦、有疗伤(感情受挫)、有逃避,当他们再度归来时,或许西装革履,或许长发及腰,或许功成名就,或许爱人拥怀,但是在异域空间,他们的行为仍旧受到种种限制。《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陈孝正由于受到非绿卡持有人身份的限制,而与不爱的美国女人结婚;《中国合伙人》中的成东青等人所办的留学培训机构受到美方的控告;《观音山》中的南风难以摆脱原生家庭,不能在城市中自如生活。陈孝正的“留学梦”、成东青的“创业梦”、南风的“城市梦”,众多拥有梦想的主人公在走出正青春的出口时,都曾经想当然地以为离开被感情牵绊的青葱校园时空便能进入一个独立自主的现实时空,可走了一圈下来,冰冷的现代社会却让他们拘囿于另一座未知的迷宫。
结 语
总的来说,青年人是一个不稳定、流动性较强的群体,他们“同时被视作‘社会倒退的危险信号和‘未来的最好希望,并在二者之间不断流动、倾轧和被协商”[6]。面对瞬息万变的成人世界,他们缺乏独立的经济条件,也缺乏温情的家庭关照,亦缺乏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能力。所以,他们在断裂的“家”空间中陷入压抑与焦虑,在有幸结识异性的校园空间中不学无术,在充满未知的异域空间中找不到出口。所以,創作者所要思考的问题是:青年人在成长的各个空间中该如何正视自己?就新世纪中国大陆青春电影来说,如何抚慰青年人的情感创伤和精神压抑,如何重塑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如何让青年人在所处环境中接触的青年亚文化逐渐向主流文化、精英文化靠拢,这些将成为电影创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爱德华·索杰. 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2]梁君健,尹鸿.怀旧的青春:中国特色青春片类型分析[J].电影艺术,2017(3).
[3]聂伟,杜梁.国产青春片:基于供给侧创新的类型演进[J].电影艺术,2017(3).
[4]张颐武.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陈晓云.街道、漫游者、城市空间及文化想象[J].当代电影,2007(6).
[6]何谦.致青春:作为另类历史、代际经济与观看方式的美国青春片[J].电影艺术,20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