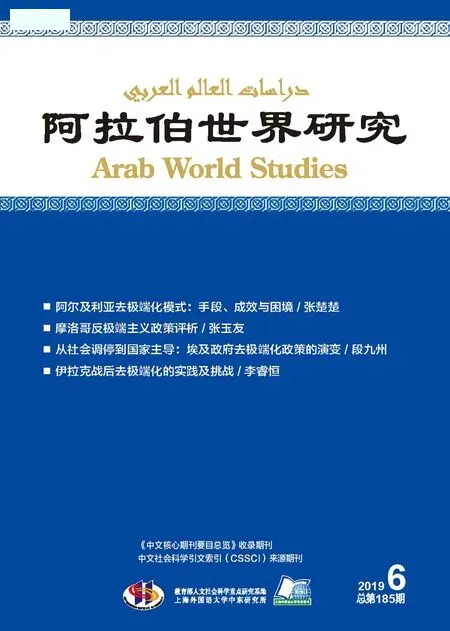阿拉伯国家“东向”外交的动因、目标及意义*
包澄章
进入21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逐渐转向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理上位于阿拉伯世界以东的亚洲国家,这一政策转向通常被学界称为“东向”外交(Look-East Diplomacy)(1)“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最早由印度于1991年提出,旨在借鉴东南亚国家发展经验、深化与东南亚国家战略关系、谋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政策。进入21世纪后,印度加快了“东向”政策的步伐,不断拓展外交空间和融入亚太区域合作进程,其战略导向、地缘范围和议题领域均发生了转变。参见张贵洪、邱昌情:《印度“东向”政策的新思考》,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4期,第90-103页;赵干城:《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及意义》,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8期,第10-16页。或“向东看”(2)有学者认为,“向东看”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重要国际现象,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印度等东方新兴国家的崛起及其发展经验的关注和重视,尤以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向东看”最为明显。关于中国学者对中东与非洲国家“向东看”现象的专题论述,参见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13(2010-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取向经历了从冷战后的“向西看”到21世纪以来“向东看”的转变(3)安惠侯:《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第3-9页。,这既是阿拉伯国家受到西方国家疏远和压力的结果,也是亚洲新兴国家崛起及其发展经验对阿拉伯国家产生吸引力的表现(4)杨光:《从经济视角看中国对中东国家的重要性》,载杨光主编:《中东非洲发展报告No.13(2010-2011)》,第44-53页。。“东向”外交本质上是阿拉伯国家为适应国际体系转型、国际能源结构调整,转变外交方向以满足国内发展需求的政策取向,拓展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关系、加强互补合作和实现外交平衡是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 阿拉伯国家实施“东向”外交的动因
阿拉伯国家自21世纪以来不同程度地加强了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关系,其中尤以海合会国家寻求与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国深化能源和经贸合作最为典型。“东向”外交本质上是阿拉伯国家受到国际体系转型、国际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寻求拓展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合作、增加经济互补性和实现外交平衡的政策转向。
第一,世界权力结构变动与国际体系转型推动阿拉伯国家通过发展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平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在行为体、体系结构和国际规则三个层面经历了深刻转变。在行为体层面,尽管民族国家仍是当前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当今世界还远未脱离国家体系,也远未达到世界体系状态”,但随着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乃至市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并日益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影响因素,“行为体多元化和主权原则松弛化在全球层面已经显现”。(5)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页。在体系结构层面,冷战后世界格局经历了从两极格局瓦解到“一超多强”格局形成,再到近年来充满争议的“两超多强”格局(6)“两超多强”是指以中美两国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参见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第14版。初显的转变。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也是以物质力量的增长改变国际格局和权力分配结果。(7)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19-20页。在国际规则层面,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使得各自对国际规则的态度发生转变。新兴国家崛起后,对调整现行规则体系中不平等、不公正的权力分配的诉求日益上升。与此同时,处于实力相对衰弱阶段的美国“无力继续承担世界霸主在单极世界中的财政重负,却不能坐视其主导地位因新兴国家的崛起而被削弱”(8)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12期,第88页。。为实现以最小的物质投入来领导和治理世界,美国“更加倚重规则对国际秩序的塑造能力,通过调整运用国际规则的战略目标和策略,继续主导全球/地区规则网络”。(9)同上。新加坡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指出,在过去2,000年中的1,800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直是中国和印度,近200年美国和西方对世界的主导只是“一段刻意制造的历史时刻”(artificial moment of history),至2050年或更早,世界前三大经济体将依次是中国、印度和美国;(10)Serge Schmemann, “The Seesaw of Powe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3,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6/24/opinion/global/24iht-june24-ihtmag-nye-36.html; “Asian Century Is Here to Stay: Kishore Mahbubani,” AsiaOne, August 1, 2016, https://www.asiaone.com/business/asian-century-here-stay-kishore-mahbubani, 登录时间:2018年11月12日。“中国和印度恢复它们的地位很正常”,届时“所有的失常状态(aberrations)都会自然而然地结束”,“当尘埃落定,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印度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两国将不再袖手旁观、被动地接受美国为世界制定的每一条规则”。(11)Ibid.
大国力量的消长推动世界格局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全球经济和战略重心逐渐转向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在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参与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意愿不断增强。21世纪的前十年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先后发动两场战争,虽然战争本身并没有导致美国实力明显折损,但伴随战争和美国强推“大中东民主计划”而兴起的地区反美力量尤其是极端主义势力,却成为日后牵制乃至耗损美国全球战略资源的主要因素。至奥巴马时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使其主导中东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同时下降,并成为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的主要动因。美国试图通过签订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和加快从中东“抽身”,却加深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崛起的担忧,这导致奥巴马时期沙特、以色列两个地区盟友与美国关系龃龉不断。同一时期,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较21世纪初已实现大幅增长。海合会国家认为,伊朗拥核和地区军备竞赛可能会动摇海湾作为持续增长的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寻求中国帮助以重新塑造海湾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中国的“一带一路”途经海合会国家海上通道,这为双方发展更深层次的关系提供了动力。(12)Theodore Karasik, “The GCC’s New Affair with China,” MEI Policy Focus, No. 6, February 2016, p. 3, http://www.mei.ed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Karasik_GCCChina_PF6.pdf, 登录时间:2019年1月17日。
第二,从国际能源结构来看,美国对中东能源需求整体下降、亚洲主要经济体对能源需求日益增长、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共同推动了阿拉伯能源生产国在开展对外合作时转向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能源消费大国。
首先,美国能源自给率的提高导致其对中东能源需求持续下降。自2003年以来,美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间曾出现过小幅回升,但伴随页岩油技术的进步,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下降趋势已难以发生根本性逆转(见下表)。

美国从沙特原油进口量(单位: 千桶)
*注: 2019年数据统计至当年6月。
资料来源: “U.S. Imports from Saudi Arabia of Crude Oil,”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EIA), https://www.eia.gov/dnav/pet/hist/LeafHandler.ashx?n=PET&s=MCRIMUSSA2&f=M, 登录时间:2019年9月15日。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和美国页岩油开采等因素的影响,阿拉伯产油国尤其是海合会成员国的经济持续放缓,财政状况一度恶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6年海合会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1.7%,较2015年3.4%的增长率下降了一倍;(13)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conomic Prospects and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GCC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26, 2016,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6/102616b.pdf, 登录时间:2019年3月9日。海合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超过1,530亿美元,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21.3%,经常项目状况恶化,总体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6.6%。(14)Santhosh V. Perumal, “GCC Budget Deficits Could Cross $153bn in 2016,” September 27, 2016, Gulf Times, http://www.gulf-times.com/story/515306/GCC-budget-deficits-could-cross-153bn-in-2016, 登录时间:2017年2月7日。
其次,经济高速增长助推了亚洲主要经济体对能源消费的巨大需求。从能源消费国的角度来看,2015年中国和印度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分别为62%和79%(15)Zhijie Zhang and Wanli Xing, “Overseas Oi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ased on Crude Oil Trade Flow Analysis,” IOP Conference Serie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 p. 2, https://iopscience.iop.org/article/10.1088/1755-1315/153/3/032046/pdf, 登录时间:2019年2月4日。,日本和韩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接近100%(16)Bo Kong and Jae H. Ku, eds., Energy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 39.;中国和印度对中东的原油依存度分别为50.7%和58.3%(17)Zhijie Zhang and Wanli Xing, “Overseas Oi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ased on Crude Oil Trade Flow Analysis,” p. 3.,日本和韩国对中东的原油依存度高达86%和83%(18)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and 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Japan’s Energy 20 Question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nergy Situatio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May 2018, https://www.enecho.meti.go.jp/en/category/brochures/pdf/japan_energy_2017.pdf; EIA, “South Korea Energy Profile: Heavily Dependent On Imports — Analysis,” Eurasia Review, January 22, 2017, https://www.eurasiareview.com/22012017-south-korea-energy-profile-heavily-dependent-on-imports-analysis/, 登录时间:2019年3月8日。。从能源生产国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主要能源生产国的油气产品收入占出口收入比重依次为伊拉克(99.8%)、利比亚(97.7%)、阿尔及利亚(96.7%)、科威特(94.2%)、苏丹(90.9%)、卡塔尔(88.7%)、沙特(87.4%)、阿曼(82.5%)、阿联酋(64.8%)、巴林(64.1%)。在国家经济对能源出口的依赖度方面,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苏丹属于单一型能源出口国(90%以上);卡塔尔、阿曼和沙特属于极高依赖型能源出口国(80%~90%);阿联酋和巴林属于高度依赖型能源出口国(60%~80%)。(19)除利比亚(2010年)、苏丹(2011年)、阿联酋(2008年)、巴林(2012年)外,其余国家数据均为2013年数据。Marek Dabrowski, “The Impact of the Oil-price Shock on Net Oil Exporters,” Bruegel, November 24, 2015, http://bruegel.org/2015/11/the-impact-of-the-oil-price-shock-on-net-oil-exporters/, 登录时间:2019年1月5日。对经济极易受到能源价格冲击的阿拉伯能源生产国而言,确保国家稳定的能源出口收入是实现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它们与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亚洲能源消费国之间在经济和贸易结构上的高度互补性,为互相之间开展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
最后,21世纪以来,伴随非中东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和产量的增加,全球石油供应板块出现了中东、北美和拉美、中亚和俄罗斯、非洲等多个中心。在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全球能源供应格局的转变为能源消费国实现原油进口多元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反过来加重了经济结构单一的阿拉伯产油国能源出口的压力,迫使其在外交上转向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亚洲能源消费大国。从数据上来看,在2018年世界原油进口量最多的五个国家中,亚洲国家占了四席,中国(20)2017年,中国超越美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2018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美国、印度、日本和韩国原油进口量的全球占比依次为20.2%、13.8%、9.7%、6.8%和6.8%。(21)Daniel Workman, “Crude Oil Imports by Country,” World’s Top Exports, April 15, 2019,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crude-oil-imports-by-country/, 登录时间:2019年4月10日。国际能源供需格局的变动,使得以海合会国家为首的阿拉伯能源生产国意识到,只有与亚洲主要能源消费国开展长期且稳定的能源合作,才能确保其国内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为阿拉伯国家实施拓展与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关系的“东向”外交注入了动力。
二、 阿拉伯国家转型背景下“东向”外交的目标
在美国逐渐实现能源自给的背景下,海湾国家将能源出口重心从西方市场转向亚洲新兴市场。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亚洲主要经济体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为海湾国家的能源出口提供了稳定的市场,致使海湾国家对亚洲市场的依赖日益增加。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加快国家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推进社会改革已成为多数阿拉伯国家解决发展困境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尽管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推出了国家转型计划或远景规划,但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深层次问题远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腐败蔓延、裙带关系丛生、法治观念缺失、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青年失业率高企、政府补贴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价值体系混乱等问题依然严重。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秩序变动引发的阿拉伯国家政权不安全感伴随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加剧。
第一,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契约亟待更新和改革。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东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实行由国家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粮食和燃油补贴以及公共部门职位的制度已经接近极限,这种被学者形容为“威权主义的讨价还价”(authoritarian bargain)或社会契约存在的弊端日益凸显(22)Shanta Devarajan and Lili Mottaghi, “Towards a New Social Contract,”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Economic Monitor, April 201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 12,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2171468299130698/pdf/956500PUB0REVI020150391416B00OUO090.pdf, 登录时间:2017年8月10日。,不仅对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的政权造成严重冲击,还引发了巴林、摩洛哥、约旦等君主制国家的民众抗议浪潮。阿拉伯国家统治者依靠基于高额政府补贴收买民心、压制民众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来维持政权稳定,但其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和私营部门工作岗位的现实,反过来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隐患。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阿拉伯威权政权的垮台,并未从根本上实现民众所要求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甚至约旦、巴林、摩洛哥等相对稳定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近年来也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民众抗议活动。“阿拉伯之春”打破了阿拉伯国家“以国家向民众提供高福利来换取民众出让政治权利”的旧社会契约(23)田宗会:《“食利契约”与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福利社会》,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81页。,而新的社会契约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尽管表面上阿拉伯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指标有所改善,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进展,但经济结构性缺陷并未得到“根治”,高失业率、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机会的缺乏等问题仍引起了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愤怒和不满。(24)Adnan Mazarei and Tokhir Mirzoev, “Four Years After the Spring,” Finance & Development, Vol. 52, No. 2, June 2015, p. 55.
第二,推动经济多元化成为海湾产油国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近年来,国际油价持续低迷造成海湾产油国财政收入锐减,迫使海湾国家政府启动了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的大规模经济改革计划。沙特和阿联酋自2018年起开始征收5%的增值税,旨在实现政府财政收入的多元化,对冲过去几年低油价对本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培育新的私营部门,进一步降低本国经济对石油部门的依赖。在国际石油市场需求增加、欧佩克成员国联手俄罗斯等国增加原油生产等因素的影响下,2018年海合会国家的石油生产剩余产能得到充分释放。油价上涨和石油增产带来了充裕的流动资金,短期内缓和了海合会国家此前因低油价而受到冲击的经济形势,同时也部分抑制了这些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动力。任何旨在促进私营部门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改革一旦迟滞,都可能会削弱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的经济多元化努力。(25)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November 18, 201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 6,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MECA/Issues/2018/10/02/mreo1018, 登录时间:2019年5月1日。
第三,阿拉伯地区资源匮乏国家的经济挑战日益严峻。尽管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下跌使阿拉伯地区的资源匮乏型国家获得了短期收益,但从长期看,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过去十年间,埃及、摩洛哥、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等资源匮乏国家的经济只在基础设施、卫生和初等教育、商品市场效率、技术准备和市场规模五个领域有所改善,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在大部分时间都停滞不前”,尤其是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令人失望”。(26)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Arab World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pp. 5, 7.阿拉伯地区资源匮乏型国家的经济挑战除失业率高、收入分配不公、投资政策透明度低等传统问题外,也深受中东地区局势和海合会国家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因地区战乱造成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加重了黎巴嫩、约旦等国力有限、经济基础脆弱国家的经济压力,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以约旦为例,自2018年初以来,该国政府多次上调燃料和生活物资价格,引发民怨,大批约旦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治理不力。约旦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因愿意接受低薪资和长时间工作进一步挤占了约旦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约旦民众和境内难民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埃及、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约旦等资源匮乏国家的民众,都寻求去待遇更好的海合会国家务工或寻找发展机会,海外劳工汇入国内的侨汇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例如,在外打工的约旦劳工汇入本国的劳务储蓄占该国GDP的10.3%,其中近一半来自沙特。(27)“Top Remittance-Sending Countries, 2014,” in World Bank Group,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book 2016, 3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6, p. 31.然而,海合会国家近年来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实行就业本土化和提高税收的政策,对在这些国家务工的外籍劳工的就业机会和实际收入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汇入原籍国的侨汇呈现下降趋势。新旧问题的交织,进一步加重了阿拉伯地区资源匮乏国家的经济压力,为其国内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第四,人口结构年轻化加重阿拉伯国家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压力。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中东和中亚地区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国家需要实现7%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将人均收入提高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并在中期内将当前失业群体和新增劳动力吸收进劳动力市场。(2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p. 20.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已对地区国家的经济转型与改革构成重要挑战,这不仅与地区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趋势直接相关,还受到地区国家教育制度、经济结构和传统社会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据2018年数据统计,当前中东地区人口年增长率达1.7%,高于世界1.3%的平均水平。2000年至2015年,整个中东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了1.21亿。(29)UNICEF, MENA Generation 2030: Investing in Children and Youth Today to Secure a Prosperous Region,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October 2018, p. 16.预计到2050年,中东地区人口规模将从2000年的3.38亿增加至7.24亿,其中24岁以下青少年人口将达2.71亿,(30)Ibid., pp. 16, 40.这表明地区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阿拉伯地区15岁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达22.2%,其中女青年失业率高达36.5%,(31)Ibid., p. 48.这些数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海合会国家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公共部门、私营经济发展滞后等问题,进一步阻碍了青年进入私营部门就业的渠道。更为关键的是,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教育体系仍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方法以及过时的课程体系和教材,难以适应当前地区国家推行大规模经济社会改革对劳动者就业技能和终身学习能力的要求,使得地区国家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教育系统为学习者提供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是导致地区国家青年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从雇主的角度来看,青年就业者普遍缺乏创造力、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人际沟通等关键技能,也是其失业的重要原因。(32)Ibid., p. 49.此外,阿拉伯地区盛行的父权制社会导致的性别不平等,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阿拉伯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就业机会。
第五,地区秩序变动加剧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不安全感。阿拉伯地区权力重心的“东移”和传统威权政体的崩溃动摇了地区旧秩序的基础,突出表现为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及其引发的国内政局动荡,导致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传统领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并助长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野心。近年来,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负面效应、地区力量对比变化导致的权力格局变动、超国家政治和宗教力量的崛起挑战国家政权和秩序规则、地区矛盾呈现多点并发态势等,加速了地区旧秩序的解体。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的数年间,一种地缘政治双层博弈结构在中东地区逐渐形成,这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美俄之间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博弈,在地区层面则表现为从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博弈逐渐扩大为沙特、伊朗和土耳其之间对地区领导权的三方博弈。而美国对中东秩序的支配性主导地位同时受到来自俄罗斯和域内国家的挑战和侵蚀。此外,阿拉伯地区整体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治理体系的低效也使其极易受到政权不安全感的冲击而陷入动荡(33)[英]蒂姆·尼布洛克:《政权不安全感与海湾地区冲突的根源析论》,舒梦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1期,第4页。,而地区秩序变动进一步放大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不安全感,并成为贯穿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上述背景下,“东向”外交的目标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已不再是简单的稳定能源出口和分享亚太地区经济红利。“阿拉伯之春”的经验教训表明,社会治理失当易使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权安全。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提升国家综合治理能力已成为阿拉伯国家实现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重要考量。阿拉伯国家对改革、发展与安全需求的整体上升,使得“东向”外交的战略意图出现了新变化,通过合作带动国家整体转型、平衡美国地区影响日益成为阿拉伯国家巩固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关系的现实需求。
首先,亚洲国家可以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经验。21世纪初,埃及学者马哈茂德·阿卜杜·法蒂勒在对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发展模式进行考察后指出,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对阿拉伯国家的启示在于,经济和社会复兴不仅是技术和物质进步的过程,更体现在制度安排、文化和价值观体系、社会组织、个人和团体日常行为等方面。(34)[埃及]马哈茂德·阿卜杜·法蒂勒:《阿拉伯人和亚洲经验》(阿拉伯文),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00年版,第240-241页。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中东地区的改革一旦缺乏稳定和资源,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阿拉伯世界必须同时“向东”和“向西”寻找有效改革的经验,而亚洲地区表现出色的经济体可向阿拉伯国家提供经济增长和经济韧性方面的经验教训。(35)King Abdullah, “The Road to Reform: The Arab World Must Look Both East and West for Lessons on Effective Refor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December 2004, Issue 145, p. 73.在安全与稳定、转型与改革的多重压力下,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正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迷茫状态,亟需寻找替代性发展模式。(36)田文林:《地区格局变动中的中国特色中东外交》,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52页。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模式。约旦学者萨米尔·艾哈迈德指出,阿拉伯国家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崛起、借鉴中国的“非模式化”发展经验,通过借助未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摆脱外部世界长期以来对阿拉伯复兴事业的阻碍。(37)[约旦]萨米尔·艾哈迈德:《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刘欣路、吴晓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3页。《阿拉伯人》杂志主编苏莱曼·阿斯卡里教授则认为,阿拉伯国家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亚洲国家发展经验的客观比较和辩证研究并使阿拉伯社会从中受益的基础之上。(38)[科威特]苏莱曼·阿斯卡里:《阿拉伯人向东看?》(阿拉伯文),Sulaiman Al-Askari,2011年1月1日,http://www.sulaimanalaskari.com/ar/,登录时间:2019年2月16日。
其次,在重构地区秩序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已开始意识到亚洲国家在平衡美国地区影响方面的独特作用。伊拉克战争后,伴随地区反美力量的兴起,很多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一度恶化,这使其在对外合作上开始转向亚洲国家。以沙特为例,无论是阿卜杜拉时期,还是萨勒曼时期,沙特国王在登基后的首次出访都未将欧美大国作为访问对象。2006年1月继任王位仅半年的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首次出访时,将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四个亚洲国家作为目的国,杰弗里·格雷什(Geoffrey F. Gresh)将此访视为沙特外交在21世纪的“战略转向”(39)Rafiullah Azmzi, “GCC ‘Looks East’: Saudi Arabia’s Engagements with India,” India Quarterly, Vol. 62, No. 4, 2006, p. 149.。2017年3月萨勒曼国王登基后首次出访时,除俄罗斯外,依然选择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作为访问目的国。格尔德·纳尼曼(Gerd Nonneman)将这种应对外部霸权、寻求与大国发展多元外交、增加国家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外交模式称为“管理多重依赖”。(40)Gerd Nonneman, “Saudi-European Relations 1902-2001: A Pragmatic Quest for Relative Autonom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7, No. 3, July 2001, p. 635.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后,海湾阿拉伯君主国持续加强与欧亚和东亚地区新兴国家的关系,开始适应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崛起。(41)Geoffrey F. Gresh, “The Gulf Looks East: Sino-Arab Relations in an Age of Instability,” Sociology of Islam, Vol. 4, No. 1-2, 2016, pp. 149-165.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向”外交正使阿拉伯国家在重构地区秩序过程中引入新的外部变量,试图通过发展与中国等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关系来平衡——并非取代——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
最后,阿拉伯国家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正从传统的低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适度拓展。以沙特为例,近年来该国不断展现出同亚洲国家加强防务关系的意愿,2013年2月、2014年2月、2016年9月和2017年3月,沙特先后同韩国、印度、日本和中国签订防务协定,开始在军售、安全培训、反恐、去极端化等领域开展合作。这标志着沙特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正在从能源和经贸等传统低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适度拓展。但需要指出的是,沙特的目标是在维持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沙特与欧洲国家军事关系的基础上,使本国的对外安全合作呈现更高程度的多样性,而非寻求替代美国作为其主要安全盟友的方案。(42)Matteo Legrenzi, The GCC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Gulf: Diplomacy, Security and Economic Coordination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London: I.B. Tauris, 2011, p. 151.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在海湾既定的区域安全框架内寻求能源的稳定供应,而非承担改变地区安全架构的成本,更加符合亚洲国家的最佳利益。(43)Makio Yamada, “Saudi Arabia’s Look-East Diplomacy: Ten Years 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2, No. 4, p. 132.
三、 “东向”外交背景下提升中阿整体关系的战略意义
从1998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首次倡议阿盟成员国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44)1998年9月16日至17日,阿盟第110届理事会呼吁“阿拉伯各国发展与中国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关系,以实现双方共同利益,支持阿拉伯各国在中国各层次的存在”。参见《第三部分 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关于与中国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决议》,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http://www.arableague-china.org/chinaese/araborchina/araborchina3.htm,登录时间:2018年12月8日。,到1999年中国和埃及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关系”,再到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实现了整体提升。这既是阿拉伯国家努力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寻求更加平衡外交的体现,也是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和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结果。在阿拉伯国家“东向外交”的背景下,提升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整体关系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致力于通过加强中东外交服务周边外交战略。中国中东外交的对象主要是西亚北非地区的23个国家,其中阿拉伯国家有19个。(45)外交部西亚北非司主管西亚和北非地区23个国家的双边事务,即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沙特、科威特、阿曼、巴林、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也门、摩洛哥、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南苏丹、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吉布提和科摩罗3个阿拉伯国家由外交部非洲司主管。西亚与中国周边的中亚在地理上直接相连,两个地区同属于伊斯兰文化圈,具有宗教和文化的相似性,在信仰层面与中国西北地区联系密切。历史上,中国和中亚、西亚之间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实现贸易往来和文明交流,中国古代的“西域”概念不仅在事实上主要指中亚和西亚地区,在观念上也反映了中国周边观的整体性,“西域”在历史上并没有今天中亚、南亚、西亚等局部地区的区隔。(46)刘中民:《中国周边学:大周边视野下的中东》,载《中国周边学研究简报》第24期,2018年。中国中东外交的定位是“中国周边战略的延伸和大周边战略的组成部分”(47)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15页。,中东国家实际上已被纳入中国的大周边战略框架中,成为中国拓展周边战略的政治资源。2005年伊朗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都体现了中国将中东国家纳入周边视野、运筹周边外交的战略考量。阿拉伯国家是中东国家的主体,中国利用其“向东看”的政策转向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有利于中国通过大周边战略资源的跨区域互动来运筹大国外交。
第二,伊斯兰国家是未来世界格局变动的重要变量,阿拉伯国家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全球穆斯林人口将从2010年的16亿增长至2050年的27.6亿,占全球人口的近三成(29.7%);至207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将超过基督徒人口,全球超过六成(61.6%)的穆斯林将集中分布在十个国家,即印度(3.1亿)、巴基斯坦(2.7亿)、印尼(2.6亿)、尼日利亚(2.3亿)、孟加拉(1.8亿)、埃及(1.2亿)、土耳其(8,932万)、伊朗(8,619万)和阿富汗(7,219万),届时印度将超过印尼成为全球穆斯林人口第一大国。(48)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 2010-2050,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 2015, pp. 8, 14, 16, 74, https://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1/2015/03/PF_15.04.02_ProjectionsFullReport.pdf,登录时间:2019年1月2日。伊斯兰国家无疑将成为未来世界格局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49)“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包括: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文莱、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摩洛哥、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和也门。集中分布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非地区。其中,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的西亚阿拉伯国家,位于“一带”与“一路”的交汇地带。阿拉伯世界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内部发展极不平衡的地区之一,阿拉伯国家可以成为中国实践新发展观、亚洲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和文明观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推进未来世界格局重塑和国际体系转型必须倚重的政治力量。
第三,阿拉伯国家所在的中东地区是中国牵制美国的重要战略区域。“9·11”事件以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先后发动了两场战争,在地区推行霸权政治,消耗了大量战略资源,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21世纪前十年的战略机遇期。“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控制意愿和控制能力逐渐下降,奥巴马政府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伊朗缓和关系并促成伊朗核协议的达成,试图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至中国周边地区。但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以及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危机加大了美国从中东抽身的难度,美国逐渐陷入了与俄罗斯在中东冷战化、阵营化的对抗态势。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实践中表现为依靠地区盟友在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方面增加投入和承担责任,其本质上仍是奥巴马政府“离岸平衡”政策的延续。从美国中东政策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主义”的政策取向具体表现为:降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风险,即在维护中东安全和反恐方面进一步收缩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力量;注重运用经济杠杆来强化美国与地区盟友的经济关系,打压地区反美政权或敲打与美国意见不合的地区国家;在涉及地区政治和安全重大问题的政策制定上,漠视国际准则、全球舆论、外国政府的意见以及美国国内建制派的批评。(50)参见George Friedman, “The Trump Doctrine,” Geopolitical Futures, July 11, 2018, https://geopoliticalfutures.com/the-trump-doctrine/; Ross Douthat, “The Trump Doctrin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9,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1/29/opinion/trump-doctrine-venezuela-afghanistan.html,登录时间:2019年3月5日。从影响来看,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极大地加深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裂痕。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美俄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博弈、美国与地区国家关系的紧张,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战略掣肘,这在事实上部分牵制了美国战略转移的步伐,同时也为中国提升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提供了机遇。
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整体关系具有坚实的基础,其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价值观三个层面。近年来中阿整体关系的深化,亦是“一带一路”与阿拉伯国家“东向”外交良性互动的表现。
第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间的整体关系经历了从新型伙伴关系(2006年)到战略合作关系(2010年),再到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的整体提升,这符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阿拉伯国家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先后与阿尔及利亚(2014年11月)、埃及(2014年12月)、沙特阿拉伯(2016年1月)和阿联酋(2018年7月)四个阿拉伯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卡塔尔(2014年11月)、苏丹(2015年9月)、约旦(2015年9月)、伊拉克(2015年12月)、摩洛哥(2016年5月)、阿曼(2018年5月)和科威特(2018年7月)七个阿拉伯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战略”一般是指“合作层次更高或者着眼点更高,双方从整体上、全局上、核心利益和未来发展趋势上都具有一致性”(51)孙敬鑫、林剑贞:《伙伴关系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0期,第36-37页。,在中阿关系上则表现为双方在“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52)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2016年1月21日,开罗),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3版。方面具有共识。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给予中国坚定支持,使得双方间的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如阿拉伯国家2016年集体支持中国南海问题立场(53)2016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多哈宣言》,该宣言强调阿拉伯国家支持中国同相关国家根据双边协议和地区有关共识,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议问题;强调应尊重主权国家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参见王雪、孟涛:《中阿合作论坛第七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多哈宣言>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立场》,新华网,2016年5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6-05/13/c_128979165.htm,登录时间:2019年1月3日。、2019年积极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54)2019年7月10日,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22国发表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公开信,对中国的新疆治理进行粗暴指责,将新疆去极端化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污蔑为“大规模拘留场所”。联署的22国还要求将这封信列入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届会议正式文件,并刊登到人权高专办的网站上。7月12日,俄罗斯、巴基斯坦、沙特等37国常驻日内瓦大使联名致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积极评价中国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和反恐、去极端化成果,支持中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其中的阿拉伯国家有阿尔及利亚、科摩罗、索马里、叙利亚、沙特、埃及、阿曼、卡塔尔、阿联酋、巴林、苏丹和科威特。等。
第二,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经济互补性强、发展战略契合度高。摩洛哥“经济起飞计划”和“2014~2020工业振兴计划发展战略”、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2030工业发展战略”、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巴林“2030经济发展愿景”、埃及“2030愿景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威特“2035新科威特”、阿曼“2040愿景”等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都致力于解决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化发展滞后、青年失业率高等当前困扰阿拉伯国家的“治理赤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中国的优势产能与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和资源红利互补性强。阿拉伯国家所在的中东地区已成为中国全球资本和产能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铁路、电信等众多行业的中国企业大量进入中东市场并融入当地竞争。(55)郑一晗:《以和为贵 共谋福祉——中国智慧助力中东和平发展》,新华网,2015年4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4/08/c_1114906376.htm,登录时间:2019年1月3日。2018年7月发布的《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强调,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消除隔阂、促进区域经济融合,为实现发展、繁荣提供内生动力,并保障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56)《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8年7月13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agx/gjydyl/t1577010.htm,登录时间:2019年1月3日。该行动宣言也是首个中国与地区组织签订的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文件。“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地区对安全类公共产品和发展类公共产品的刚性需求更加迫切,“一带一路”确立的“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这对辩证关系,打破了传统上西方将发展与安全二元对立(57)李伟建:《“一带一路”视角下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体系》,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88页。的思维定势,将解决阿拉伯地区“发展缺位”和“治理赤字”作为实现地区普遍安全的重要前提。新时代的中国中东外交要求中国对中东问题的认识从过去强调“冲突和矛盾”转向突出“治理和发展”(58)同上。。
第三,中阿文明和价值观具有互通性。从文明体系的角度来看,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体系和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的伊斯兰文明体系,在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文明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和从属地位,从而造成了文明有高低优劣之分的错觉和成见。(59)朱威烈:《“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构建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载朱威烈:《学思刍议:朱威烈文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328页。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阿关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成为论坛的常设机制之一。中华文明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是推动世界文明体系向平等和包容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60)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中阿双方“都不赞同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而是主张文化多样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61)《王毅: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是引领中阿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l_675049/zyxw_675051/t1162627.shtml,2017-06-10。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将文明和宗教交流作为中阿人文交流的首要内容,不仅提出“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还开创性地提出要“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62)《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体现了中方对阿拉伯地区宗教与文明特性和当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深受“伊斯兰恐惧症”“文明冲突论”和极端主义困扰等现实的深刻认识。
从外交角度来看,中阿交往的价值观基础使得阿拉伯地区成为中国践行大国外交理念的重要区域。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持续震荡,地区秩序严重失衡,大国在中东博弈异常激烈并逐渐陷入僵持状态。经历了数年动荡的阿拉伯地区,已从“阿拉伯之春”初期狂热的街头政治逐渐转到解决民生问题、加快经济发展、推进社会转型、实现安全与稳定的正轨。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演讲中强调“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坚定了中国在中东“以发展促和平”的外交理念,明确了中国在中东地区建设和平、推动发展、助推工业化、支持稳定和促进民心交融的角色定位。(63)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方提出要“尊重每个国家的国情差异和自主选择,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域外力量应该多做劝和促谈的事,为中东和平发展提供正能量。要摒弃独享安全、绝对安全的想法,不搞你输我赢、唯我独尊,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64)习近平:《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8年7月10日,北京),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第2版。。正如《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指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65)《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中阿合作论坛网站,2018年7月13日,http://www.chinaarabcf.org/chn/zagx/gjydyl/t1577010.htm,登录时间:2019年1月3日。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指导中国中东外交的同时,中国中东外交的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和检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阿拉伯地区正日益成为中国践行大国外交理念的重要舞台。
四、 结 语
“东向”外交是阿拉伯国家适应国际体系转型、国际能源结构调整转变外交方向以满足国内发展需求的政策转向,主要表现为阿拉伯国家积极拓展与亚洲国家合作关系、加强互补合作以实现外交平衡。“阿拉伯之春”的发生打破了阿拉伯国家旧的社会契约,在转型动力和改革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深受“发展赤字”困扰的阿拉伯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而亚洲国家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和在平衡美国地区角色方面的独特作用,为阿拉伯国家深化与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提供了机遇。阿拉伯国家的政权不安全感也使其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开始从传统的低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适度拓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整体关系的提升,表现为双方间日益增强的政治互信、合作需求和价值观交流,这既是中国拓展周边外交战略、发展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和部分牵制美国战略转移的现实需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与阿拉伯国家“东向”外交良性互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