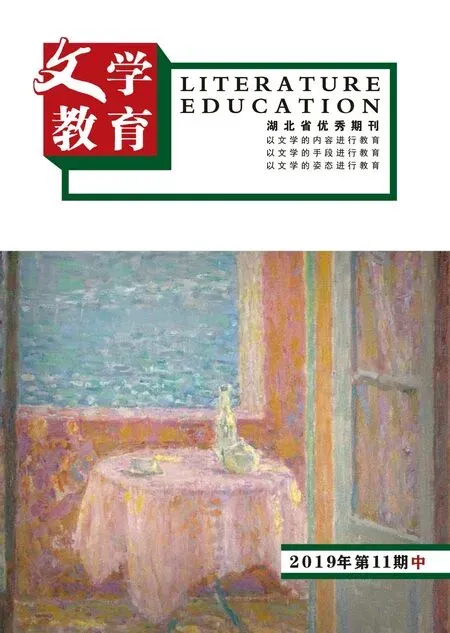论艺术家的社会处境:《饥饿艺术家》解读
袁筱凤
《饥饿艺术家》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作家卡夫卡于192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它是卡夫卡的自画像。卡夫卡试图勾勒出一个衰老的、渐渐失去影响力的艺术家复杂的角色图[1]53。
一.观众与艺术家之间的鸿沟
小说中,叙述者始终以一种讽刺的口吻讲述饥饿艺术家的行为和他狂热的好胜心。小说的第一部分叙述的是饥饿艺术家事业的鼎盛期,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也“不满足”,因为人们虽然观赏他的表演甚至发出赞叹,但是这种肯定并不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理解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观众几乎全都怀疑饥饿艺术家在表演过程中偷吃东西;第二,没有人了解饥饿对于他来说有多么容易;第三,经理每次最多只让饥饿艺术家表演四十天,因而没有人相信他能饿得更久。
所有的观众都认为饥饿艺术家的表演是以欺骗为前提的。由于他们自己不能长时间地压抑自己的食欲,他们便把这种判断强加于饥饿艺术家身上,认为他也不能。所以大家选出了看守,“日夜监视饥饿艺术家,以防他通过某种秘密的手段进食”。紧接着叙述者又转为从“知内情者”的角度介绍,其实饥饿艺术家“即使受强迫也不会吃一丁点东西,为了维护艺术的尊严,他不能这么做”。[2]335这句话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即使是这少而又少的“知内情者”也不真正了解饥饿艺术家,正如小说末尾所交代的那样,他不进食与维护“艺术的尊严”毫不相关,而只是因为他没有食欲。没有一次表演结束饥饿艺术家是“自愿离开笼子”的,但没有人相信他。
经理的存在加深了饥饿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鸿沟。他是真正的欺骗者,观众加给饥饿艺术家的罪名本应属于他。他既欺骗了饥饿艺术家又欺骗了观众,因为他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剥夺了前者“继续饥饿”从而“超越自己”的权利,同时让后者以为已经看到了艺术家的极限。最让饥饿艺术家不能容忍的误解是,在他企图通过愤怒来回应人们的误解时,经理居然在观众面前将他的行为归结为“因饥饿引起的”“过分敏感”,并用照片反驳饥饿艺术家的“雄心壮志”,言下之意是他能饿四十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这种饥饿艺术家虽然司空见惯、却不断使他伤心丧气的歪曲真相的做法,实在使他难以忍受。这明明是饥饿表演提前收场的结果,大家却把它解释为饥饿表演之所以结束的原因!”[3]63这种将因果颠倒的做法使饥饿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误解达到了极致。
在第一部分结尾处叙述者站在饥饿艺术家的角度感叹道:“反对这种愚昧行为,反对这个愚昧的世界是不可能的。”[2]342饥饿艺术家与观众的关系始终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不理解。马戏团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多数普通人观看稀有的人或动物的场所,这种观看行为以猎奇为目的,而不以理解为基础。笼子不仅仅是饥饿艺术家的表演场所,还具有将二者归入两重世界的象征意义,暗示二者之间交流和理解的困难甚至是无望。文中全知的叙述者既客观地叙述外部事件,又进入饥饿艺术家的内心,从他的角度生发议论和感慨,同时还把观众的心理展现出来,这样就一览无余地挖掘出对立的二者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观众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受到限制的强制性表演,而并不关注饥饿艺术家到底可以饿多久——当经理把表演时间限制在四十天时,“全城的人都在关注饥饿艺术家”“随着饥饿的天数增加,关注度越来越高,每个人都想每天至少看一次饥饿艺术家”[2]333,尽管他从未达到挨饿的极限;而当“转变”发生后,他终于可以像梦想的那样不受时间限制地挨饿时,他的笼子却无人问津了,没有人欣赏他的艺术,就意味着他被剥夺了存在的价值。“饥饿艺术家没有欺骗大家,他在诚实地工作,但世界骗取了他的报酬”[2]348。最后荒谬的结局是,饥饿艺术家向观众对他的艺术做出的判决提出异议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献身他的艺术。
二.作为殉道者的艺术家
策划表演的经理把饥饿的上限规定为四十天,原因是超过这个期限观众的兴致就会下降。这一出于经济角度考虑的规定与《圣经》中多次出现的数字四十不谋而合——《旧约》中的大洪水持续了四十天;摩西在锡奈山上等待上帝颁布写有律法的石板等了四十天;尼尼微城进行了四十天的忏悔;以色列人在沙漠中行走了四十天;耶稣受洗后斋戒了四十天,复活后在门徒中间显现了四十天。其中耶稣受试探前的四十天斋戒与《饥饿艺术家》的内容尤为接近,也是关于饥饿的。在描写经理将饥饿艺术家抱出笼子时还有这样一句话:“(经理)仿佛是邀请上苍来观看这稻草堆上的杰作,这位值得同情的殉道者,饥饿艺术家也的确是一位殉道者,只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2]340卡夫卡仿佛有意要把饥饿艺术家与耶稣作对比,把他写成一个殉道者,只不过他之所以成为殉道者不是因为他必须饥饿,而是因为他不能无限期地表演饥饿,而且得不到世人的理解。他不仅想“成为史上最伟大的饥饿艺术家”,而且还要“超越自我,直至不可思议的境界”;而经理在这里与《圣经》中的魔鬼相反,扮演一个“反试探者”的角色,因为他通过强制性的食物阻止饥饿艺术家超越四十天的饥饿期限。这让对《圣经》的影射有了戏仿的成分,导致饥饿艺术家的绝对要求多了一分滑稽,少了一分悲剧性。将艺术家作为追求绝对高度的殉道者,是20世纪初许多艺术家小说的共同主题,同样以此为题的还有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克勒格尔》和格里尔帕尔策尔的《可怜的游吟诗人》等,但与格里尔帕尔策尔对耶稣受难故事“严肃认真”的化用方式不同,卡夫卡的化用带有“讽刺”色彩。
三.艺术家的社会处境
在小说的结尾处,艺术家慷慨激昂的呼喊“试着给人们解释一下饥饿艺术吧!谁不亲身体验,就无法理解。”使人联想到《浮士德I》当中浮士德短促的叹息:“如果你们不感受它,就无法追求到它”。[4]25汉堡版的注释将该句解释为“艺术家对理性主义者的回答”。这种影射进一步体现了饥饿艺术家的要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表达了他对与他对立的普通市民的无奈。他在临终前道出饥饿的真实原因时,反倒更没有人能理解他了——看守“用手点点额头”,示意其他人“饥饿艺术家的状态”。
如果说观众不理解饥饿艺术家,那么饥饿艺术家对观众也存在误解,他们之间的误解是双向的。艺术家通过观众的存在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并对观众抱有一种带有错误期望的依赖性。他的表演不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不能”,但他却企图利用这种固有的局外人身份强迫社会接受他,并把他摆在一个受人膜拜的位置上。他请看守吃早饭的时候免不了表现出一丝自负。他不仅要求观众钦佩他,而且必须是由于他所规定的原因——饥饿对他来说是最容易的事——而钦佩他,不能是处于别的原因。而这一点观众是绝对做不到的。
看守怀疑饥饿艺术家偷偷吃东西,暗喻人们对于艺术家的怀疑和流言蜚语。观众去观赏表演不是出于对艺术的欣赏,而是受猎奇心理的驱使,并企图用自己狭隘的经验来解释艺术家的行为,直到新奇的事物成为习惯,不再吸引他们的眼球,他们对艺术家渐渐产生厌恶。艺术家作为社会上的少数,他们的行为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受众在观赏艺术的同时会感到自己普通的生活方式遭到了质疑,就像正常饮食的人看到饥饿艺术家禁食时产生的感觉;而在充满生机与力量的豹子身上,观众才找到了自我认同感。临死前,饥饿艺术家认为世人不应该钦佩他,却没有放弃饥饿艺术本身,完成无限饥饿的使命对他来说比获得荣誉更重要。他不再需要他人的肯定,把自己当成唯一能够评判他的艺术的人,呼应了“只有他自己才是对他能够如此忍饥挨饿感到百分之百满意的观众”这句话[3]60。这种断念可以看成是受排挤的艺术家进行唯我论的自我评价,将艺术家和欣赏者合二为一,从而摆脱了对受众的依赖,从被孤立走向解放和自立。最后故事为何以豹子在笼中的场景而不以饥饿艺术家的死结束,文学研究中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可以看到的只是,艺术与生活,文明与自然,艺术家与普通市民依然之间依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饥饿艺术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中艺术家的处境。“饥饿”既象征艺术家独特的存在形式和创作方式,又象征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状况。卡夫卡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肤浅的、被间离、被异化的世界,一个被社会孤立的、绝望的艺术家、和一群对艺术的本质和高度缺乏理解的观众。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存在的只是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