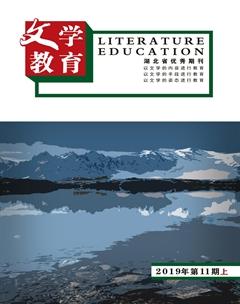“忽逢幽人,如见道心”
“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概念,为《诗经》“六义”之一。一般谈新诗,很少论及新诗的“兴会”问题。其实,中国古典诗学中的“兴会”传统与西方诗学中的“象征”多有相似之处。谈新诗常常重象征而忽略“兴会”,是一种偏见。华清曾在其诗学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论及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李白《将进酒》、曹操《短歌行》等古代经典名篇,对于传统诗学中的“兴会”之义心领神会。从华清的各种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兴会”有多种层次的理解。低层次的含义,亦即通常所理解的情景交融、托物言志。深层次的理解则包括了心与万象之间的神秘对应关系,类似于西方象征诗学中的契合理论。上升至这一层,我们会发现他将“兴会”这一诗歌生成机制的根源和特点认知得相当深刻。由于“善诗之人,心含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合我晦明”(虚中《流类手鉴》),则其诗兴触发必“与敏感的情绪、非理性的意绪有关”,所以华清有将“万古愁”或“灵敏”作为中国诗歌的精神的精妙之论,并且认为应当“对中国的传统语言,古典诗歌和现代诗,以及现代语言之间建立起一种血肉的联系,建立一种内在的气息、贯通古今的理解,因为它既充满思想,血脉相连,也无限地保有了其固有的本质——灵敏。”有鉴于此,我们便很容易理解,为何华清能在其诗中将“兴会”手法运用的灵活自如了。华清的诗歌既有效地传达了类似于“万古愁”的情绪,又显豁地体现出了诗的灵敏精神。当然,对于写作主体而言,这种“灵敏”可能是无形的,它深深地植根于诗人的骨子与灵魂当中。这是内在的质地,但却常常以感性的形式发挥作用,与写作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又难以言传的隐秘关系。
华清曾指称其最早对诗歌的痴迷源于对文字和图画之间构成的意境,他“爱上了语言,爱上了语言的游戏”,受诱惑于“形而上学的诗”,对于诗词意境和韵味的追求已成为他难以摆脱的本能。其大量的诗歌写作皆有这方面的体现。首先,华清尽量采择那些带有典雅、清奇、温婉、纤秾、瑰丽等色调的意象入诗,如尘埃、舷窗、鲸鱼、驿道、柳絮、华盖、春梦、蝴蝶、芦荻、桃花、枯井、夜枭、洪荒、西风、白雪、画舫、寒蝉等,衬托出了古典诗歌以“清”为核心范畴的审美风格;其次,在诗歌中,他借助“秘密经验的敏感通道”和各种表现手法来大力经营深沉、柔软、唯美的诗歌意境,映照出了他对李商隐、李煜格局的欢喜。如《枯叶》《春梦》《春光》《枯坐》《看客》《德沃夏克:寂静的森林》等即是如此。更为难得的是,诗人对诗中意境的“忘我”营造,其语言的清澈和灵性生长,让很多人都陷入了美妙的镜中。《枯坐》写一个人梦见自己“干枯”的过程,以第三人称作为叙述的视角,展现其在特定时间、空间中实体渐变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整首诗虽然一直以“静—动”交叉的视野在布局人的存在,然而从客观的角度看,这里呈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自在之物”的化境。在这个化境之中,人枯坐着,而内外的世界气象万千。《二十四诗品》的“实境”品云:“忽逢幽人,如见道心。”华清在《枯坐》中就是设置了这样一位类似的幽人,透过他的“半倒半立”我们也仿佛见证了某种“道心”。
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对于“兴会”“韵味”“意境”“兴趣”这些古老的诗歌特质早就弃若敝屣。而华清对这些“祖传秘方”却似乎情有独钟,这说明他诗歌的血脉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这其中就包括道家思想——如“玄之又玄”、“道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言不尽意”、“不落言荃”“物我两忘”等影响到中国诗学中的“形而上学”“自然”“含蓄”“幽冥杳渺”“妙悟”“理趣”“神韵”“恬淡”“虚静”等理论观念。而华清对道家思想与诗歌的关系也有独到理解:“‘诗歌的最高形式应该接近老子所说的‘道。”并且对“形而上学”的诗歌十分痴迷:“另一个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诗歌,这是无形的、永恒的作为理想的诗歌。……永远在诱惑和‘毒害着我,让我为文本狂想、激动、发自灵魂地颤栗。”这无疑从理念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他还曾经高屋建瓴地以“上帝的詩学”——即“生命本体论的诗学”作为诗歌的最高原则,将司马迁、雅斯贝斯的宏论进行有效对接,以实践“伟大诗篇”与“人格”的相互辉映,体现出一种纯正的格调和非常宏大的格局。这种诗学建构独创性地融合了中国古典诗学与中西现代诗学,其意义是重大的。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