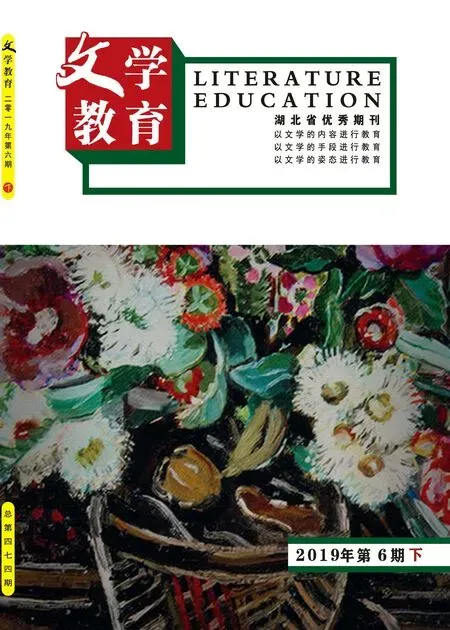火野苇平战争观批判
林彦汝 孙立春
一.战时:“忠君爱国”的圣战呐喊者
1938年2月,火野苇平的《粪尿谭》获得了第六届芥川奖。当时的火野苇平正作为杭州警备部队一员驻守在杭州,为此军部还特地派遣小林秀雄从日本专程来到杭州进行颁奖。这种超乎常规的授奖方式无疑是对火野苇平的一种鼓励与隐形的要求,为之后火野苇平在火线上从事战争的宣传与文学活动埋下了铺垫。同年4月,火野苇平就被派往华中派遣军报道部,5月随军参加徐州会战,并以徐州会战为题材创作了其代表作品《麦与士兵》,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紧接着同年11月以杭州湾登陆为题材发表了《土与士兵》,12月以杭州警备留守为题材发表了《花与士兵》。之后陆陆续续辗转战场,先后参加了汉口作战、安庆攻克战、广州攻克战、海南岛作战,并以不同战场为题材发表了《海与士兵》(后改为《广东进军抄》),《东莞行》,以及《海南岛记》等等作品。之后,《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这三部作品由改造社分别出版单行本,火野苇平总称为《我的战记》,评论者则称为“士兵三部曲”,这三部便是火野苇平的侵华文学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作品的大量发行给当时日本国内喧嚣的军国主义气焰推波助澜,鼓励着全民加入这场不义之战中。“对这种不义之举,竟然有的评论家还坚持认定火野苇平的作品与一般颂扬侵略战争的文学有别,更有评论者认为火野苇平在某些地方表现了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表现了对战死的中国士兵的怜悯之情,而认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人性的”,甚至是“人道主义”的。”(王龙,2015:89)但遗憾的是这种“辩白”无疑是荒谬的,在处于一个受军国主义驱使,人人身陷战争狂热的年代下,身为军人兼从军作家双重身份的火野苇平也沉浸在为“报效祖国,效忠天皇”的迷乱氛围中,成为宣传军国主义的文字工具。
火野苇平曾自白过自己作为作家的身份从获奖的那刻起就已经定格。而火野苇平作为作家定格的那个昭和10年代却是片冈良一所说的“……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右翼、以及诸如此类词语将昭和十年代染上卡其色的时代。也是无法忘怀的最坏的时代。”(田中艸太郎,1971:30)在那个年代日本国内早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法西斯热潮,军国主义风行,言论和思想都受到了严酷的控制。一批又一批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者在日本政府的残酷镇压下纷纷“转向”,宣布脱离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阵营,为日本法西斯政权服务。仅剩下少数还顽强抵抗的拒转向者,要么流离失所,要么遭到严刑拷打致死。1935年前后,日本国内左翼作家或无产阶级文学的反战文学几乎销声匿迹,日本文坛就此步入了“最坏”的黑暗时代。在这样一个政治高压与严酷思想控制的时代,火野苇平也迅速被卷入这场黑暗潮流的漩涡之中,与日本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摇身一变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呐喊者,成为侵华战争的帮凶。
在前线,火野苇平一手握钢枪,一手持笔杆书写着战争的谎言,以掩饰日军的恶行,达到宣扬“圣战”的目的。关于战时火野苇平对侵华战争的态度,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他以战场为题材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来探讨。
(一)日军形象
身兼军人与作家的双重身份,给了火野苇平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与其他走马观花式的从军作家,切身经历枪林弹雨的火野苇平对战场、士兵的描述则更“真实”且令人信服。在《士兵三部曲》中,首先就对日军形象进行了塑造,在他的笔下,日本士兵都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在艰苦的行军环境下他们会为了报效祖国而咬牙坚持,在生死离别的战场上他们会依依相惜,在异国他乡也会油然生出思乡之情,他们都是一群“真实”的普通人。在《麦与士兵》中,作者描述日军在漫无边际的麦田里行军,黄沙尘土和跋涉的汗水染黄他们的衣服和毛巾,散发出阵阵臭味,然而没有替换的衣物只能将就。“不停的行军路使脚底生出了水泡,忍痛涂上碘酒,踩烂水泡,像虐待自己的双脚一般继续行军。双脚已站不住般的剧痛,觉得快不行了,但咬咬牙又继续坚持了下去。……我看着士兵这些又脏又烂的脚,感受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东西。”(尾崎士郎,火野葦平,1968:350)诸如此类描写战场上生活条件的艰苦,体现士兵“吃苦耐劳”形象的描述在《士兵三部曲》中多次出现。此外,还通过美化日军,塑造出“忠君报国、正义高尚”的高大形象。比如,在《海南岛记》中面对中国军队发出的招降宣传,日军的态度是“……支那军队拼命的呼吁,却招来日军的反感,反而加强了日军满腔燃烧的爱国心。”。在《土与士兵》中,“为了祖国而奋勇前进,这比什么都简单而又单纯。也是最崇高的事情。为此,我们前进。在战场上,被枪弹打中将要死去的时候,大家嘴里只知道喊出‘大日本帝国万岁’”。(王龙,2015:106-107)“看到好几个抬着负伤的战友逃跑的敌人,日本人果真是不行呀,该说是多性情呢还是说容易心软,看着这些敌人,还要开枪射击这种事实在是令他们感到厌恶……”,这些本是侵华战场上杀人如麻的日本士兵在火野苇平的笔下,却被塑造成富有“人情味”、朴实真诚的正义形象,充满着“庶民”的色彩。有人指出“庶民性”正是火野文学的特点之一,这些表现庶民性内容描述也体现了火野苇平作品中带有“人性的”色彩。但这些所谓的庶民性就如进藤纯孝所说、“不过是基于‘与历史的发展方向一致’、基于‘在狂热军国主义的驱使之下’而产生的事实。”(前田角蔵,1983:21)很明显,火野苇平在战时俨然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拥护者,在这种基础上创作出的战争文学又何来“人性”,更谈不上“人道主义”。在这些作品中,民众只能看到“忠君爱国、正直高尚”的日军的美好形象,却看不到掩盖在美好光环下那罪恶的行径。
(二)中国军民形象
与日军“高尚”的形象相比,中国军民就显得很“不上档次”。在《麦与士兵》中有一段借一个中国老太太的嘴,说到:“中国军队每到一处,米、钱、衣服、姑娘、什么都洗劫一空。日本军队什么都不拿,非常好。”(王向远,2015:201)面对“友好、正义”的日本军队,中国人民都表示热烈欢迎,还会自制太阳旗,看到日军更是笑脸相迎,摇旗呐喊。在沦陷区家家户户都插着太阳旗,到处都贴着“欢迎大日本”、“欢迎亲华胜利大日本”的红纸。中国老百姓还会自己端上茶水,拿来鸡蛋等食物送给日军。但是,面对中国老百姓这种讨好的举动,日军还表示出不解与轻蔑。例如,“我们日本军队每占领一个支那城镇的时候,留下来的支那人就到我们的驻地来,面脸堆笑地和我们套近乎。这种作法我们是无法理解的。我想,这如果是在日本,敌军攻来的时候,不是军人的国民谁都不会讨好敌人,连小女孩也会同仇敌忾地反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直到以死相拼。所以,我们对“萝卜”、“咸菜”(作者对两个汉奸的称呼——引者注)为代表的支那人,单个的人觉得亲近。但对这整个的民族,置本国失败的命运于不顾,为了个人的性命而向敌人献媚,是感到轻蔑的。用我们士兵的话说就是:都是些没有廉耻的东西。”(王向远,2015:201)《海南岛记》中面对沦陷区的居民如往常一样开市做生意的情景时,“光是当地的居民非但不逃跑反而留下来这种事就足够令人惊讶,占领不久后就呈现这样一种状态更是让我感到不知所措,难道这里的人都是傻瓜吗?我不禁这样想到。”(火野葦平,1939:107)不仅如此,对于中国老百姓这种“愚弱、唯唯诺诺”的性格,火野苇平还得出了一个所谓“合理”的解释: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时常处于动乱的政治环境与强权的压迫下,逐渐形成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更荒谬的是将其用来解释战争的正当性,“当然,将他们从这种桎梏之中解放出来,是我们当下的使命。”(火野葦平,1939:107)可以见得,这些描述无非是让民众们相信日军的到来是为了“帮助”和“拯救”中国人,美曰其名多亏于“皇军”的庇护与帮助,中国老百姓才得以脱离苦海,安居乐业。面对愿意“出手相助”的日本军队,中国民众应该协助他们共同实现“大东亚繁荣”。此般黑白颠倒,将这场不义的战争硬说成为光荣的事业的火野苇平,宣扬“圣战”的企图无疑昭然若揭。
(三)作者的内心独白
姑且不论火野苇平的作品是否有体现对侵华战争或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光是以他当时作为一名侵华日军报道部成员的身份来看,写出反战的作品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火野苇平深知这一身份对他的写作意味着什么,军部政府对作家创作的内容也有十分明确且具体的规定与限制。在火野苇平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条限制:“不能写涉及战争中所必然出现的罪恶行为”,仅看这一条规定就知道,这些在军部授意与掌控下的作品是不可能会出现描写日军焼杀奸掠的真实情况,更不可能奢求其会表现出反战的情绪的描写。
此外,也有人认为这些侵华文学作品是火野苇平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写下的产物,并不是出于其本人的意志。理由是火野苇平在《士兵三部曲》中面对被杀害的中国士兵,也有体现出内心的不忍与怜悯的描述,这便是火野苇平的“人道主义”,作品中充满“人性的”证明。但事实上,加入日军报道部成为皇军的“御用作家”这条路是火野苇平自己的选择。前田角藏也认为踏上这条路并不是火野苇平在没有选择余地下的无奈之举,当初派遣他到中支部派遣军报道部时,他完全可以以没有自信承担重任为由拒绝,但他却没有。同时,火野苇平在自叙里也说到,当时作为分队长且担任伍长一任的他起初并不想离开现在的队伍,还向他的战友表明自己会好好回绝上级的好意继续留在队伍里。但最终火野苇平还是选择加入报道部,作为一个军队作家为军国主义效命。并且即使军部对写作内容有规定和限制,火野苇平仍然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不出风头,但他却在没有任何人强制命令的情况下主动创作出了一系列的战争文学。这一来他站在军国主义的阵营,宣扬“圣战”为皇军效力的态度早已不言而喻。火野苇平的言行与内心活动也不经意地暴露出他对军国主义与天皇的“忠心”。例如他在给孩子的书信中写到:“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像岩见重太郎(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武士——引者注)那样。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王向远,2015:196)要去杀中国人这种残酷冷血的话却能作为向孩子炫耀的资本,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还有面对共产党对日军的“污蔑”,火野苇平这样为其申辩:“……一切对日本的诽谤,说是帝国主义,又或是资本家和军阀的走狗的等等这些言论,这些企图分裂日本国民,制造内讧的行为对日本人来说都是没用的……对这些武士来说,左翼公式主义的呼喊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日本的军队只管杀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火野葦平,1939:62-63)
显而易见,战争下火野苇平早已被军国主义的狂热氛围所感染,沦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在他眼里侵华战争是一场“拯救中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光荣“圣战”,日本军队是忠君报国的“伟大军队”,在炮火硝烟的前线上勇敢顽强的奋斗着。就这样,通过文字火野苇平竭尽全力向日本国内人民群众传递“圣战”的丰功伟绩,使得越来越多的刽子手纷纷投入侵华战场。
二.战后:“百口莫辩”的文化战犯
1945年日本战败,在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文件的支持下,日本文学界也开始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进行揭发和追究,作为战争中积极协助鼓吹军国主义的主要人物,火野苇平被定为“战犯作家”。1948年被逐出“文笔家”之列,解除公职,其战争责任受到严厉追究,日本的《赤旗》杂志将他指定为“第一号文化战犯”。(王龙,2015:112)1950年火野苇平的处分解除,1955年受邀来中国和朝鲜进行访问旅行,并以途中的见闻为题材,写下了游记《赤色国度的旅人》。1959年,以战败前后的经历为题材写下生涯中最后一篇长篇小说《革命前后》,次年,服下100片安眠药自杀,死前留下了遗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战败,无疑对火野苇平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战败后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心情激愤的火野苇平就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小说《悲伤的士兵》,并表示放弃文学创作。小说中写到“如今,我依旧忘不了八月十五日的痛哭”;“战败的耻辱与现实”;“为了皇军,无数的人献出生命……”;“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日本人是好战的民族是最大的误解”;“这才是作为臣民响应圣断(天皇的旨意)的唯一之路”。这些言论足以体现出火野苇平难以接受战败的事实,同时也证明了他战时鼓吹军国主义这一不争的事实。然而,收录在1959年发表的《革命前后》中的《悲伤的士兵》,虽然大体上与初次发表的内容一致,但删去或修改了如上文中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文字。对于这一修改,我们是否可以像田中艸太郎所说,从善意的角度来推测,战后经历14年的岁月使得火野苇平的“国家观”和“天皇观”发生了改变,他自己无法忍受这些赤裸裸地带有国粹色彩的文字而主动要求删去,这是他对侵华战争所犯下罪行的某种忏悔。然而,回顾战后火野苇平的作品,却发现他反省侵华战争罪行的作品实际上寥寥无几。唯一一部对战后中国进行访问所写下的《赤色国度的旅人》,十多年后重新踏上曾经侵略蹂躏过的土地,火野苇平表示:“当初征服中国时的骄傲与兴奋心情多愚蠢,现在后悔也没用,谢罪也晚了吧。”(火野葦平,1955:118) 这些虽然看似流露出对战争的反思,但实际上不堪战败的心情占更多。这是面对新中国的友好与进步表现出的一种怀疑与疏离感,而不是真诚的赞许与接纳。文中多次描写他身为一个“战败国”的人来到战胜国中国是一种接受拷问时复杂、苦闷心情,尽管在新中国受到友好的接待,但他却表示“不想迎合中国人”。并且在新中国的治理与规范下以前脏乱差环境得到改善,乱收费、街头乞丐、性工作者等不良风气也消失。面对这些积极的转变火野苇平却持有怀疑的态度,表现出更怀念“曾经的支那”,自顾认为这好现象是专制体制下对自由的束缚,认为新中国是追求真正自由与和平人士难以居住的地方。在这部游记的最后,火野苇平写道:“无论新中国如何如何迅速建设起来,作为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在这个国家呆着。”(王向远,2015:291)相比之下现在的好情形,侵略战争时沦陷的中国才是“王道乐土”,这自相矛盾,尖酸刻薄的言语更暗含他不甘战败的内心。
火野苇平对日本的失败一直耿耿于怀,战时被捧为“国民英雄”荣誉归国的他,然而战败后却被判为“第一号文化战犯”,受到解除公职的严厉处分。更令人讽刺的是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也是火野苇平的长篇小说《陆军》原定出版的日子,呕心沥血的作品转眼就成为没有价值的废纸,不言而喻,想必他内心充满了愤慨与苦闷。面对战败后国内情势的迅速转变,战争归还后的士兵包括火野苇平都成为了国民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对象。对此他内心感到不平,指责战败的真正原因是日本国民“道义的颓废、节操的欠缺”。(火野葦平,1939:404)一直“据理抗争”坚持忠君爱国的士兵是无罪的,火野苇平在为日本军队开脱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抱不平,这一点在《赤色国度的旅人》中也显露出来。文中火野苇平面对新中国随处可见指责侵略战争、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宣传海报和标语中出现的日军形象和称呼表现出十分敏感,并一直强调自己被说是“日本鬼子兵”,在意中国人说“日本鬼子”。观看话剧时,看见活跃在舞台上,饰演为祖国不惜性命的中国人民军队,火野苇平的竟将这正义的形象与侵略战场上日军相提并论,认为两者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那活跃在舞台上的人民军士兵和曾经的日本士兵是如此的相似。不,两者完全就是一样的。那份爱国心、那牺牲的精神、那艰苦、那勇气、还有那勇敢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并且还委屈地认为,“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军人是英雄,而日本的军人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爪牙下的鬼子兵 。’”(神子島健,2012:295-296)可见火野苇平是为自己申辩,对侵华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还在依依不饶的讨价还价。除了为自己开脱还在为天皇“喊冤”,“……曾经在战场上,如果被子弹击中倒地之前,我会高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在《麦与士兵》、《土与士兵》等作品中我也是这样写的。我是个笨蛋,从来没把这场战争当作是侵略战争,只是一心坚信祖国处于危机,祈祷祖国的胜利。为此,自己也要竭尽所能去战斗,我的爱国心背后有天皇陛下的影子一直如影随形。为了陛下去死——直到现在想起来也感受到一种纯粹的感动。”、“日本战败,天皇开始受到国民痛骂的时候,我对谩骂天皇的浅薄国民感到憎恨。在绝望中,在战败下充分反省的同时,我丝毫没有对天皇产生痛恨的心情。”(神子島健,2012:211-212)这些自白充分暴露了火野苇平的真心,显然这根本不是对战争的忏悔。
无论如何,火野苇平都应该承认战时他作为一个军队作家,炮制了大量的侵华文学的责任与罪行,而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反过来抱怨战争本身,为自己诉苦和开脱。对于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有人说,战时他们也许是因为受军国主义的政权的驱使,不得已才协助战争。对于这些辩护,王向远先生认为“既然这样,那么照理说,战后他们有着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凭着他们的良知把他们在战争中不敢说的话,不敢写的东西说出来,写出来。写出‘反侵华文学’,‘ 反侵略文学’,以正视听,以挽回他们炮制的侵华文学所造成的的恶劣影响”。(王向远,2015:291)然而,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火野苇平不仅没有写出反省侵华战争罪行的作品,还一直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开脱,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反战”,不如说是“反对战败”。经历处分和诘问,却仍然冥顽不灵,不愿真心实意地去忏悔去反省,显然对侵略战争所应承担责任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火野苇平的一生充满了戏剧化色彩。浮生若寄,造化弄人。如果火野苇平当初没有被授予芥川奖的话,或许他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象。但无论如何,火野苇平对侵华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战时作为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炮制侵华文学,为帝国主义摇旗呐喊的不义行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战后的火野苇平虽然在访问新中国时流露出一种自责,但这微不足道的反省念头比起他应承担的罪行还远远不够。他更多表现出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为自己的责任与罪过开脱,显得诉苦有余而反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