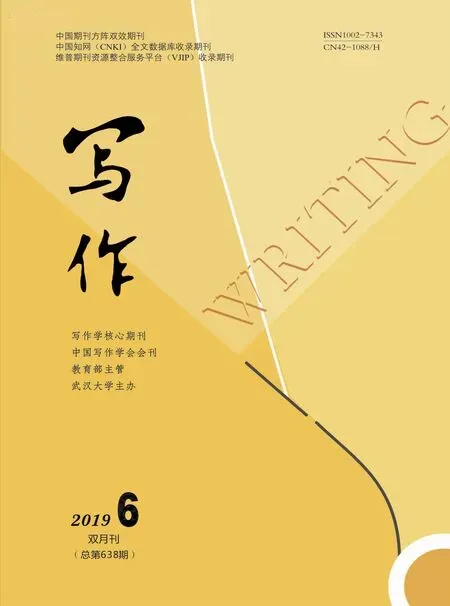从玄言诗的历史评价论文学接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邓 娟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最强音。相对来说,优秀文学作品的产生大多在承平日久、社会发展相对繁荣稳定之时,然而却没有哪种文学作品如同玄言诗一样,仅仅流行一个朝代(还同这个朝代一样短命),日后少被提起或是被提起时多被批评甚至诟病——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玄言诗素来地位尴尬,前有建安风骨,后有山水田园,更为盛唐诗歌的光辉所掩。近年来虽有研究者试图从积极的一面来解读玄言诗,但是多数也是从思想根源来解说玄言诗语言的简朴性。这种“强说”使得玄言诗在整个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更像一块需要掩饰的伤疤。
一、时势造“英雄”:玄言诗流行
诗歌的创作往往反映着时代,是当时生活的直接反映,对社会思潮有着强烈的观照作用。玄言诗从萌芽到蓬勃发展,兴衰过程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下文人的思想变化。对于玄言诗的定义,目前学界依然莫衷一是:“给玄言诗定义难,是因为它作为我国诗歌演变史上的有机一环,本身有着最大的特殊性: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阶层在特殊思维下形成的特殊文学,其存亡兴衰与时代人文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①王澎:《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因此对玄言诗时代划分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有人把仲长统的诗歌算作是玄言诗的滥觞,有人则把正始时期何晏之辈所作看成开山之作:“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彼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②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有人觉得陶渊明的诗歌应该看作是玄言诗:“陶渊明从本质上说也还是一个玄言诗人,因为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在玄学精神指导下的人生。”③孙绿江、孙婷:《中国古代诗歌结构演进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有人认为谢灵运的部分诗歌也反映着玄学妙思,应当划入此类。争议颇多,不在此一一列举。王锺陵先生认为:“玄言诗的远源可以追溯到汉末建安之时,而其孕育阶段则主要在西晋。虽永嘉时玄言诗风已兴起,但玄言诗作为一个文学史阶段,则应以郭璞为正式起点;许询、孙绰之时为玄言诗的鼎盛时期;谢混之时,则为玄言诗这一文学史阶段之终点。”④王锺陵:《玄言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目前关于玄言诗比较统一的观点是:玄言诗是反映玄学思想、玄学旨归的诗歌;东晋时期是玄言诗的兴盛期。本文讨论的重点不在为玄言诗定义和划分时代,也不争论其诗歌品第的高低,只以东晋时期玄言诗的兴盛与它在文学史中的尴尬地位进行对比,分析时代特征对其题材、内容、传播效应的影响,通过观照这种影响,进行创作反思。
(一)社会现实促成了玄言诗的发展壮大自汉末宦官与外戚祸乱开始,社会一直动荡不安。没有了强大的皇权,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官员不断发展自身地方势力,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逐渐形成一定武装力量,在自身势力范围内起到维持社会基本安定的作用。当这种封建宗法性大土地所有制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宗法封建性世族大地主阶层不断攫取权利,并且试图保有这种权利,将其发展为世袭制,从而把自己变成特权家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世族既要与皇权斗争,也要控制平民的上升通道,避免皇权与平民的相互联结,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汉末,察举制已经被高门控制,魏晋初始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对豪门士族起到一定限制,但后来也沦为了门阀贵族的工具。举荐制、考试制,这类平民得以上升的主要渠道,在两晋时代根本难以形成,平民阶级必然地走向了消沉。“整个官僚系统都主要被世族控制,平民士子被压制于底层,皇权文化与平民文化联系的道路被阻隔,传统两极政治文化结构中的一元化权力被分散到世族高门手中。”⑤何光顺:《玄响寻踪》,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7页。随着皇权的衰微,士族的兴起,皇族也不过算是众多世家当中较大的一个,甚至不如某些家族势力——在评定世家时,某些士族的排名甚至高于皇族——唐太宗李世民改定世家排名谱系,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士庶之间的天壤之别使得资源分配极度不均衡,在给世家士族带来了极大利益的同时却给皇权带来了极大冲击,让中国原有的两极型结构(皇权与平民)转化成了三极型(皇权、世家、平民)结构(两极文化结构是指自西周萌芽,而秦汉完全形成的皇权文化和平民文化二元共生结构;三极文化结构是指魏晋时代形成的皇权文化、世族文化、平民文化的三极鼎立结构)⑥参见何光顺:《玄响寻踪》,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封建文人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在这一时期基本行不通,低级士族以及平民阶层与其寻求失势皇权的赏识,倒不如依附于顶尖的士族大家,得到他们的认可。东晋时期的王、谢之家,号称“与马共天下”,是当时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
汤用彤指出,魏晋玄学的“无为”主义实际是一种“虚君”主义,并认为其来源有二:“1)天无言而四时行——人君法天;2)‘无为而无不为’之一种新解释。”①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在皇权不够强硬、难以与顶级世家争锋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表面的和平,不得不倡导黄老学说——“清静无为”,既为皇家示弱之举,表明自己不会实施皇权集中制,减轻皇家面对世家时的压力;亦是压制世家的一种手段,既然崇尚“无为”,醉心于“清谈”,那么汲汲名利、一心想立事功者往往会被嘲讽、鄙弃。甚至于桓温的北伐、谢安的“东山再起”,都曾被时人诟病过——这种诟病事实上是害怕这两个家族分得更大的利益而从舆论上对他们进行牵制。皇权文化控制下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与平民文化潮流下物质性的文学作品在此阶段都极少流行。脱离了皇权控制,又不用困于世俗物质的泥沼,世族子弟精神上更加自由,能够达到“为艺术而艺术”的境界,表现在思想上,是对人生终极问题的考虑;反映在文学上,玄言诗就应运而生——“世族文化的兴盛是玄言诗作者与读者群存在于魏晋这个特定时空的深层文化背景。世族文化的消退及平民文化传统崛起之后审美旨趣与品位的转向,则是玄言诗作者及读者消隐的深层历史原因。”②何光顺:《玄响寻踪》,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二)社会思潮引领玄风兴盛,玄言诗成为宠儿当上层建筑发生变革之时,社会思潮也会受到冲击和影响。两汉时期,儒学发展到极盛阶段。当它成为官学并被“独尊儒术”捧上神坛之后,逐渐物极必反,走向僵化与繁琐,成为思想束缚。到了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弄权,朝廷黑暗腐败,皇权岌岌可危、世家权势日上,大一统时期建立起来的儒家思想体系已经完全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起不到维系社会纲常的作用,因而受到严重冲击,不断被质疑、被挑战。战乱、瘟疫、割据……在这样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儒家学说既解释不了强权的无耻和生命的无常,频繁变换的政权也不再需要儒家这块遮羞布。在质疑和挑战中,思想禁锢松动,新的思潮渐渐成形,试图调和儒家在现世中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黄老之说此时对于痛苦中的文人无异于一针强心剂。“有”“无”之说缓解了朝不保夕、命如飘萍的问题,越名教而任自然更是一种别样的反抗,清静无为则成了政治避祸的有效手段。玄学就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矛盾下的产物——“我们可以说,魏晋玄学是以老庄(或者说《易经》《老子》《庄子》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儒家经学中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思潮。”③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7页。
诗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超越当时的政治、思想、现实去生活。玄风盛行,整个学术家、文学界自然都会受到影响,更何况当权者还是玄风的吹捧者呢?有晋一朝,由于玄学的泛滥,占据高位的世家认为官场充满了俗尘,多数身在其位却不谋其事,实务就由低级士族或庶族执行。这些有机会执行实务的人要想脱颖而出,也避免不了追随玄学的脚步,先让自己有出头的机会。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诸闲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得到谢尚赞赏之后,袁宏(即袁虎)“自此名誉日茂”。虽不能说袁宏是为了能有出头的机会而学玄谈玄,但是玄风之盛此中可见。
又如《晋书》卷四十三所记:
(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因谈玄清言而得名人赏识自此走上仕途者比比皆是,社会风尚可想而知。
二、“大梦终觉醒”:玄言诗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失势的必然
(一)写作理念旨归不同,不符合中国诗歌传统的审美观第一,诗言志。中国的诗歌自开篇起,无论是“献诗、赋诗、教诗、做诗”①参见吴梅、朱自清、闻一多:《诗词十六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其最终目的都是言“志”——“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②吴梅、朱自清、闻一多:《诗词十六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然而东晋时期是个人觉醒的时代,个体更多注重是的个人的生存体验,重视自我,深入挖掘个体感悟,没有怀抱天下的雄心,惟有感怀生死的思考。沉溺于个人体玄悟道的玄言诗显然不符合政治教化的标准。加之东晋偏安一隅、不思收复失土,救万民于水火,却用玄言清谈来装点门面,更有为扮作高人韵士而丑态百出者: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才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夫古人谓通达者,谓通于道德,达于仁义耳,岂谓通乎亵黩而达乎淫邪哉!③葛洪:《抱朴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317页。
如此种种,不仅为当世有识之士所不齿,更为后世所难容。即使可以把玄言诗看作是个人之志的表述,它也没有把个人怀抱与天下兴亡联系在一起——“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于儒家这种重视实践道德的学说基本占据纲常地位的中国来说,玄言诗是一个异类。
第二,诗缘情。既不能述诗之大志,那么玄言诗在“缘情”这一方面又当如何?一样是失败的。“玄学影响玄言诗并不是直接创造出了玄言诗这一‘诗体’,玄言诗不是体裁概念,而是风格概念。玄学影响诗的过程就是逐渐地渗透、拿来或改造某些现有的诗歌种类,通过嫁接使之开出无色、无味、无香的玄理之花来。”④王澎:《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版,第112页。这种玄理之花大异于陆机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也有悖于钟嵘所认可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玄言诗要消解的恰恰就是这种悲喜之情引起的心灵震荡:“它有着普遍一致的审美追求,趋向于一种统一的审美风格,这就是平淡。平淡具体表现为语言的落尽华彩和言说方式的不事雕琢,而归根结底则是诗人超脱的生活态度和超越的人生境界的体现。也就是说玄言诗的平淡是由玄学的精神所预设和规定了的。”⑤杨合林:《玄言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版,第35页。表现出来就是情感淡然、语言无味,这样才能达到东晋士人们所欣赏追求的世外之美,沉入玄虚妙境,获得恬淡安然的心境,达到平和忘情的精神境界——“它化情感力度的表现为精神高度的呈示、精神境界的演示,以淡泊虚静,而非词采华茂作为美学特征。”⑥伍晓蔓:《“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
总之,玄言诗言的是纯粹个人之志,无关生民;说的是高蹈世外之情,平淡无味。虽有“托意”,却在“玄珠”;“兴、观、群、怨”几乎没有,赋、比、兴的手段难得一见;选词寡淡、文采逊色,完全不符合中国文学传统主流的审美趣味,难以引起共鸣。
(二)处于尴尬的“过渡期”,几无立足之地建安风骨继承了《诗经》及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又抒发了个人治国平天下的伟大志向,是玄言诗所无法比拟的。玄言诗“为艺术而艺术”,追求的是哲学思想上的虚静,一旦对比就显得过于抽象,过于干瘪。玄言诗除了直陈玄理的诗歌外,还有通过山水悟道之类,这类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山水田园诗的前身。比如题为《兰亭诗》和《三月三日诗》的这类玄言诗,多是玄学家们流连山水时的体悟之作。虽然不能说没有玄言诗,就生长不出山水田园诗,但是玄言诗为山水田园的题材做了大量的铺垫。陶渊明的诗歌中不乏体玄悟道之作,谢灵运的诗歌中也有一些可以看作是玄言诗,但是这二位都“转型”成功,在后世备受赞誉。他们生长于东晋晚期,作品创作上吸取了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成就也更大一些。
玄言诗的尴尬之处不仅在于它在建安风骨和山水田园的夹缝中出现,更在于它处于中国语言发展的一个变革期。仅从词汇上来说,这一时期正是双章节词语取代单章节词语成为主流之时,对诗歌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原有的四言诗那种一反一复的舒缓节奏在双音节词汇发展后显得单调呆板:“四言诗对称、平衡的节奏与形式正是原始初民在生活中缺乏秩序与规则,缺乏稳定与平衡,也就是缺乏安全感的心理追求的结果。”①孙绿江、孙婷:《中国古代诗歌结构演进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东晋士人的人生,生命的无常感时时侵袭,他们的生活缺乏的也正是稳定感与安全感,所以他们就会在文学中去追求、创造这种平衡感——不少玄言诗就采用了四言诗形式,如孙绰的《赠温峤》《赠谢安》等诗,还有兰亭诸人之诗也有不少是四言诗。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音乐的发展,五言诗在东汉末年发展已经趋于成熟。五言诗句式更富于变化,表达也更加自由且有韵律感,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其风靡势不可挡:“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钟嵘《诗品·序》)试图用四言诗来寻求心灵平静的东晋玄言诗人,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无论如何挣扎,最终只能走向消亡。
(三)玄言诗理性其辞,淡乎寡味其一,玄风高涨,玄言诗受其影响,“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②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3页。,从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③钟嵘:《诗品·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9页。玄言诗最为诟病的一点,便是其语言的淡乎无味。这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④鲁迅:《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2卷第2号。经历了各种丧乱,魏晋士人躲在一个个“坞壁”中假装歌舞升平,用玄学来麻醉自己,于是作品就显得平和、平淡;其次,陈词滥调,几乎有些词语必然会在玄言诗中出现,如“大道”“大化”“太上”“太玄”等等……这些“照魏晋人看,文章的最上乘,乃‘虚无之有’、‘寂寞之音’,不如此则不足以为‘至文’。”⑤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90页。在后世读者看来,却是极为枯燥无趣的措辞;最后,有些诗人为了表现自己融入“大道”,能够“忘情”,在写作时有意地使用平淡地语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彰显自己世外高人的形象,这种刻意愈发地使玄言诗味道淡漠,既无深情,又无诚意。“自刘琨、郭璞相继去世以后,玄言诗泛滥了将近百年,除了王羲之、孙绰、许询、殷仲文、谢混等二三流诗人外,没有出现真正有成就的大家。”⑥陶文鹏:《诗歌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其二,物化的玄言诗泛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息息相关,当社会风尚决定了某一类文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学,而且当权之人本身亦是士林领袖时,文学必然物化。东晋时期三极结构并不稳定,皇族与士族不断斗争,士族之间也相互倾轧,庶族中有能之士不愿久居人下,试图跻身于权力阶层,那就需要高级士族的援引,玄学和玄言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成为他们的晋身之道。时风如此,诗风自然会受影响。不管是否对玄学有着深刻的理解,也不论是否真正有所体味才有所作:“……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玩其形,而不究其神,故遭雨巾坏,犹复见效,不觉其短,皆是类也。”①葛洪:《抱朴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660页。这种全民皆追捧的情形导致了脱胎于对玄学理解和表述的玄言诗的机械化、庸俗化。高品质的作品愈发少见,正如梁先生所说:“凡是一种风尚,每每有其扩衍太过之处,尤其是日久不免机械化,原意浸失,只余形式。”②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三、沉默的螺旋:从文学传播和接受上论不利于玄言诗流传的因素
任何文学作品的流传,都需要传播,也需要受众。王兆鹏先生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要考虑六个层面的问题: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以及传播效果③参见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首先从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以及传播对象来分析,玄言诗只要脱离门阀制度这一政治温床,就会走向衰亡:它既不能满足受儒家之影响而形成的“托意言志”那一派所欣赏的温柔敦厚、微言大义的评判标准,又不能达到受道家之影响所形成的“直观神悟”的一派所追求的诗歌整体的精神和生命,从而唤起心灵深处的一种共鸣与契合。而这两派又是中国说诗的两大主流④参见叶嘉莹:《迦陵谈诗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两部重头之作——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它们对玄言诗评价不高,这基本上就给玄言诗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两部作品没能脱离他们的时代影响,对于华辞丽藻有着钟爱之心,所以对于言辞较为质朴的作者评价难免有失公允。“一个在某方面享有声誉的人比无声誉的人总能引起更多人的思想与态度的改变。”⑤彭军辉:《社会信息传播视野下的唐诗宋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倘若谢灵运没有李白这位诗仙推崇,陶渊明没有苏轼这位“迷弟”的追捧,恐怕他们的诗歌也还在历史的卷册中寂寞地存放。以东晋高级士族为传播主体的玄言诗,是官方政治推崇的产物,也是特殊时期人情心理的反映,只能在东晋一朝风靡一时。过了这一时期,它的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人复存在,它传播环境也特别不友好,没有缺少接受和消费者,又哪来的传承者,更遑论生命力?
其次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效果来看,受建安风骨的影响,两晋甚至六朝时期,诗歌的主要传播方式还是口头传播,包括配乐歌唱、徒歌、吟诵等几种方式。玄言诗的口头传播方式究竟如何,现在基本无据可考。配乐歌唱的作品多具有娱乐性和世俗性,这是玄言诗极力规避的特点,也是它无法在皇权阶级(东晋时不够集权的皇权阶级例外)和平民阶级受欢迎的原因;徒歌主要在民间流传,就像现在的民歌或者童谣之类,实在不符合玄言诗高冷的风格;吟诵则在魏晋文化雅士中颇为盛行⑥参见吴大顺:《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根据流传下来的算作玄言诗的作品来看,这些诗歌一般是朋友赠答和亲友聚会时的产物,在这样的场合下,吟诵应该是玄言诗口头传播的重要方式,如上文所举袁虎夜间咏诗之例,在东晋文献中记载良多。这三种传播方式相比较而言,最能够广为接受、快速流传且能流传时间更长的,自然是配乐歌唱,徒歌次之,吟诵又次之。现存的玄言诗能够流传下来,有赖于文本传播。吴大顺将文本传播分为石刻、题壁以及传抄这几种,其中“书写传抄的传播形态更为普遍和流行,石刻、题壁传播还是相当有限的”①吴大顺:《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兰亭集》就是这一传播方式的成果。
综合而言,没有真正的公众传播思想指导,追求“得意忘言”“高蹈世外”的精神境界的玄言诗,传播主体凋零,传播内容不能贴近传播对象,传播方式缺乏技巧性……这一切都不利于玄言诗的传播。其后的南北朝又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火之下文学作品的保存困难重重,“近时王士祯极论其品第之间多所违失,然梁代迄今,邈逾千祀,遗篇旧制,十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残文定当日全集之优劣。”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39《诗文品类·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94页。玄言诗本身的传播效应也局限了它在这种损毁中留存的可能性。文本数量达不到,文本质量高低就更加难以评定。
四、结语
玄言诗成于时代,也败于时代。离开它所在的时代,就成为文学史上一缕幽魂。如果作品能够在当下流行,这也未尝是件坏事;但是如果作品只能在当代流行,而于后世饱受诟病,作品本身的质量肯定值得商榷。
习近平总书记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伟大的作家可以高于时代,却也脱离不了时代的影响;好的读者能够排除个人偏见,给予作品公正的评价,却也局限于风尚和潮流的审美养成。“传播信息越是接近受众的,就越能引起受众的普遍关注,其价值也就越大,其可视、可听、可读性也就越高。因此,可以更为具体地说,信息传播的接近性指的是因所传播信息中的事实同受众在地理上、年龄上、性别上、职业上和心理上等的距离对于受众能够产生的吸引力。”③彭军辉:《社会信息传播视野下的唐诗宋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作品能否流传且受到欢迎,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质量是否过硬,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的锤炼。一时的主流并不意味着永远的主流,倘若仅为跟风而做的题目,势必被大浪淘沙,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唯有那些能够感动人心、贴近受众心理的作品,才能持续给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好的影响,才能经久不衰。当然,好的作品能够更加广泛地传播也需要作者本身具有良好的传播意识,借助于一定的传播手段——能够从读者的方向来思考作品的创作,这样的作品大抵是不会被民众抛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