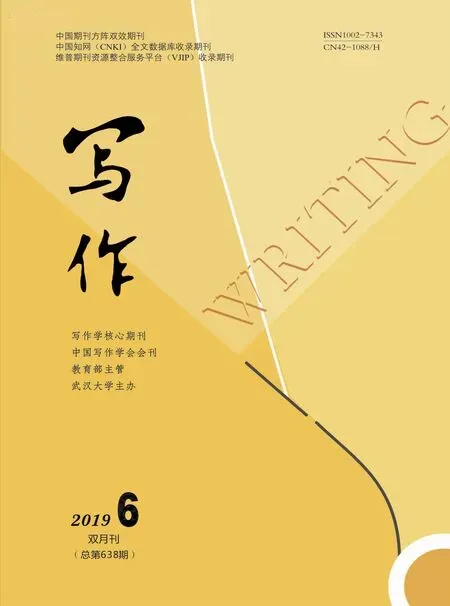论王晓明的文学批评写作
——以《“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为例
李 樵
很多人肯定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多年前读到过的东西印象深刻,甚至曾让你激动、震惊,也许这些东西还对你产生了某种知识或情感的启蒙,但是多年后或者过不是特别长的时间,回头再读,那种震惊和激动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到了。但是,有的文字却恰恰相反,它们总似乎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气质,有一种可以持久唤起和维持震惊与感动的能力,让你感到欣喜、焦虑,让你恋恋不舍、蠢蠢欲动。好的文字应该有这样的素质:它总有些更为内在的精神或情感性的东西激荡着你内心最深处的波澜,那不是转瞬即逝的浪花,而是泉眼潭底深沉不息的涌动。在笔者看来,王晓明的文学批评就是这样的“好文字”。
一、精神:拒绝“世俗意识”
第一次读到王晓明,是他的《所罗门的瓶子》,那种惊人的细致和丝丝入扣到现在都记忆犹新;现在再一次读他的文章,这种震动的感觉更为强烈。那么这种震动的感觉因何而生,它究竟来自于哪里,我们通过《潜流与漩涡》中《“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一文具体分析。
这篇文章分析的是曾经作为一个文体家的沈从文是如何寻找、遭遇并最终失落自己的“文体”的。王晓明从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感受出发,通过对作者的心理分析来推测、判断,勾画出这一寻找、遭遇和失落的线索,并挖掘出沈从文作为一个文体家的悲剧性命运的根源。
这个根源就是:世俗意识。
按照王晓明的考察和分析,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的时候,所捕捉到的只是一些“世俗的情感”,它们“并不能真正深入地撼动他那诗人的灵魂,也就唤不起那种殚精竭虑去穷尽它们的形式意味的冲动”①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2、122、127、130-131、131页。;沈从文自己内心深处和灵魂深处的那种独特的情感记忆和生命感受尽管在发出召唤,但是它们这时候只是些“混沌感受”,这是逼迫沈从文最终创造属于自己的那种特殊文体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压力,沈从文在这一阶段仅仅通过《山鬼》《船上岸上》《连长》《雨后》《参军》等热情描写湘西风俗环境,刻画湘西人朴素天性的小说与这种 “混沌的感受”维持着联系。直到1929年5月发表的 《灯》,作者开始将对湘西理想的自然和人性世界的刻画与面对现实人生时的“深长的忧郁”联系了起来,并创造了一个“突转的”“悲音”式结尾形式,这时,沈从文“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个人文体了”②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2、122、127、130-131、131页。;及至《边城》“出世”,成为这种文体的“集大成者”,作为文体家的沈从文也建立了起来。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文体呢?王晓明用诗化的语言这样描述道:“它不但体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节奏,更暗含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叙事结构;不但能对读者造成强烈的撞击力,更能把他们引入动人的朦胧心境,仿佛是重游故地,满怀惆怅的抚今追昔,又好像是置身在明亮的余晖之中,却清楚地感觉到暮色正从背后悄悄地围拢过来,一种对造化无情的迷惘油然而生,它身后更紧随着那种对人世间容不得美物长存的朦胧的预感。”③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2、122、127、130-131、131页。
然而《边城》作为这种文体的集大成者,却同时也是这种文体失落的开始,沈从文变得“力不从心”了,他开始为观念所累,为湘西现实的愚昧、腐败以及面对这种现实时的厌恶所累,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开始步入城市的上流社会和绅士阶层,智识者圈子的压力迫使他要对这现实做出解释和态度反应,原先那种“发自心底的朦胧深广的忧虑”变成了“另一种有明确的针对性的相当切实的愤慨了”④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2、122、127、130-131、131页。,1930年代中后期以及到40年代的作品里,“讽刺笔调”和“嘲讽的口吻”开始难以抑制地流露出来。在1946到1947年间的《赤魇》《雪晴》《巧秀与冬生》等涉及悲惨和伤痛的短篇小说中,沈从文的愤怒和讽刺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陌生的局外人式的冷漠:他的文体变了,他的“整个审美感受”也变了。这种“变”按照王晓明的说法,就是沈从文已经彻底地“绅士化”了,从那个初入城市“被沉重的记忆压得坐卧不宁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位温和、沉静,面呈淡淡忧色的中年教授”,“世俗生活逐步改变了他的审美趣味,成年人的理智渐渐消解了天真的童心,城里人的冷漠挤开了乡下人的热忱,总之一句话,他置身的现实环境差不多完全收复了他”⑤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2、122、127、130-131、131页。。王晓明在这里尖锐地指出了“世俗意识”对于艺术创造的巨大腐蚀作用。他说:“艺术创造是和世俗意识格格不入的,就是再富于诗情的作家,一旦他过分热衷于世俗的生活理想,太孜孜于实际的功名目标,他心中对诗意的敏感就必然会大大减弱,不是萎缩,就是变质。”⑥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22、122、127、130-131、131页。
托尔斯泰直到80多岁去世之前还创作出了不朽的皇皇巨著,那种蓬勃旺盛的创造力一生都汩汩滔滔激荡不止,老而弥坚,相比较来看,为什么近现代以来我们民族的作家的创造力却是如此的贫瘠、单薄?曹禺23岁便写出了《雷雨》,中老年以后创造力却急剧衰退,最后郁郁而终据说很大程度也是因此之故;曾经创造出当代最具“史诗品格”的经典的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后再也找不到新的创作动力和灵感,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沉寂;还有张贤亮,这个曾经以深刻的痛苦和决绝的孤独打动读者的优秀作家,后来成了一位财大气粗、志得意满的地产和影视大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笔者总在想,到底中国的作家缺少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导致他们的才华和创造力过早萎缩,是缺少内心里一种深刻、持久的痛苦?灵魂深处的挣扎和搏斗?还是缺少面对灵魂痛苦的勇气?或者宗教式的博大深沉的悲悯和虔诚?
王晓明在《所罗门的瓶子》中曾批判过张贤亮,缺少那种作为“历史感的核心”的“尊重过去的诚意”和“正视自己的勇气”,其实这是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批判,他们缺少一种直面自己内心痛苦和灵魂不安的勇气,缺乏独立、勇敢的内省精神,总是企图在喋喋不休的“理智的解释”中平息自己真实而痛苦的情感冲突。而这一点正是导致中国作家缺少艺术持久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最重要原因,因为真正的文学是源于灵魂深刻的痛苦和生命固有的疑难。在《“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里,王晓明又提出了另一个潜在的腐蚀性因素,那就是“世俗意识”,这种世俗意识从作家深层的心理体验开始发生作用,进而影响作家的情感感受和审美品位,让他很容易就丧失那种“深广的忧愤”和朦胧的诗意化的心境,这种极具腐蚀性的世俗化意识是如此的普遍又是如此的残忍,“它竟能从一个已经建立起个人文体的小说家手中,硬把那文体生生地抢夺走”①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12页。。在这里,王晓明显示了一个批评家所应该具备的深广的忧愤。批评家不是躲在自家书房里自我陶醉的收藏家和鉴赏者,批评家对于作家、读者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即便面对作家的不屑和读者的讪笑,批评家也不该后退,他们可以因为自己的粗疏和浅陋而脸红,但不可以因为对自己责任和使命的无知而自轻自贱甚至缴械投降。好的批评家应是美的发现者,同时又是勤奋而深刻的思想者,他能够向作家和读者指出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各种“潜流与漩涡”,就像王晓明说的,从他自己对新文学作家创作心理的分析角度,探寻“现代中国人精神变迁的深层奥秘”②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并且将那些诚挚、深刻,渗透着批评者真切的生命感受的文字财富积聚成全人类的文明遗产。笔者觉得王晓明的批评最主要就是在这一点上打动人心,即他的那种诚挚、深刻、尖锐让人感动。诚挚,是说无论面对怎样的作家和作品都不脱离实际须臾溢美,都不随意谩骂指责;深刻,是说其所灌注的独立思考和不断追问、持续发掘的探索精神;尖锐,说的是其从不暧昧不明、一团和气,从不见风使舵、人云亦云。正是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让笔者看到了一个优秀批评家的良知和责任感。
二、方法:用感受提问
当然不仅仅是良知和责任感,就像心地良善有着美好构想的木匠没有好的手艺和工具同样无法造出像样的家具一样,好的批评家当然要有好的批评方法。王晓明的批评方法,笔者觉得可以简要概括为:用感受来提问,用设身处地的心理体验来推析。
无论是《所罗门的瓶子》还是《“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作者都忠实于阅读作品的第一感受,并且从这种感受出发来提问,这得益于其敏锐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力是如此敏锐,以至让人觉得他就像童话故事中那个“豌豆公主”一样,再微小的“不适”也逃不脱他的感觉,感觉了“不适”,他就非要把那颗硌在九层被子下的豌豆给找出来不可。他从不放过任何一点感觉上的龃龉,那种“执拗”劲儿在文章中表现得非常鲜明。比如阅读沈从文早期的那些小说的时候,他感到沈从文的笔法是“相当杂乱”的,带着很多模仿他人的痕迹,但《副官》《船上》《槐化镇》《传事兵》等几篇小说却是例外,它们“笔调淡漠”,“也看不到有什么精心结构的痕迹”,他感到沈从文讲述这些故事时候的“自我克制是非常明显的”,这和其早期的大多数作品明显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王晓明发问道:“为什么面对昔日军人生涯的记忆的时候,他不愿意再像记述童年趣事那样纵情挥洒了呢?”③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12页。他敏锐地抓住极其细微的感觉,提出疑惑和不解,然后再进行心理推析与解答。再比如,作为沈从文独特文体集大成者的《边城》创作出来之后,王晓明便感觉到沈从文有点“精疲力竭”了,这种感受也是来源于他阅读时敏锐的感受,他说“《边城》竟是沈从文所能奉出的最后一位出色的产儿,因为那母亲自己精疲力竭了。这疲倦甚至在《边城》里就已经表现出来,譬如在描绘地方上风土人情的时候,作者多次直接插话,表示热烈的赞叹”①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3、117页。。不是将情感融入叙述当中,而是在叙述当中插入直接的抒情或者议论,这是沈从文文体失落这场“索命”之疾微乎其微的前兆,它被王晓明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作家不断用自己的称赞来加强他对某样事物的描绘,这是否说明他在捕捉对那事物的诗意感受上,多少有点力不从心了?”②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3、117页。读到这里,笔者忽然想,如果沈从文晚生几十年或者王晓明早生几十年就好了,当然假如王晓明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会有一种“身在庐山中”的隔障让他无法作出现在这样清醒明晰的批评,或许他现在的批评确实有“事后诸葛”之嫌,但是他所显示出来的精细和敏锐的感受力对今天的作家们来说已经算是一笔足够值得珍惜的财富了。这样的批评家多了,是同时代作家们的幸运。
在感受力之精细方面,王晓明就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敏感而又苛刻,哪怕感觉上有丁点儿的裂缝都不被其放过。强烈的问题意识,来自其作为一个批评家应有的良知与自觉。感受上的龃龉,促使他追问,他必须面对并且解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个过程显示出王晓明良好的心理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且这种心理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并非用多么高深的理论来支撑和装饰,而是呈现以设身处地的心理体验,同时结合作家的实际创作情景和创作环境,对作家创作时的心理背景进行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推理,最终使问题涣然冰释。在这个推理分析的过程中,他就由女孩子变成了一丝不苟的老太太,一针一线、从容不迫,把那些感觉上的裂缝一一缝补。其心理体验之深入和贴切让人印象深刻。在谈到沈从文那种“地方志式的抒情描写”使得自己与那种独特的文体渐行渐近时,他同时感觉到这些作品有些“矫情”,尤其以《雨后》和《阿黑小史》为代表,前者“一味渲染原始人情”,后者暴露出强烈的“渲染自然性爱”的“意图”,以致人物心理刻画极其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是刚刚进入大城市的沈从文内心“深藏的自卑感”和“受挫者的沮丧情绪”在作怪。王晓明是这样分析的:“城市对他的轻慢就不只是煽引起思乡的情绪,更激发了他一种向别处去寻找精神支柱的迫切愿望。只有服膺于一套足以与城市的价值标准相匹敌的另一种标准,他才能毫无怯意地走进城市……而从他当时的意识范围来看,恐怕唯有对家乡的记忆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柱,只有从湘西的风土人情当中,他才能提取出与都市生活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③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23、117页。,正因为这样,沈从文才会这么过分热情地渲染那种牧歌情致,以致于显得“矫情”。
这部分作品中的“矫情”暗示着一种坏的倾向,因为这种“矫情”来自于自卑带来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它可能将沈从文引入肤浅、矫饰的歧途,幸好沈从文并没有这样继续下去。王晓明在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卒伍》《阙名故事》等作品中读出了一种“深长的忧郁”和“沉重”,而且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让人“说不清”。那么为什么会“说不清”呢?王晓明抓住了这一点——这显示了他敏锐的感受能力——接着通过对这一点丝丝入扣、步步进逼的分析,让笔者看到了正是这“说不清”才让沈从文最终收获了他那独特的文体。对故乡湘西世界人情风俗描写与对野蛮和愚昧的暴露相结合,对故乡的回忆、赞美与面对野蛮、愚昧的痛苦和憎恨相混杂,这就造成了作品朦胧、模糊的独特韵味,不回避现实的苦难和人生的残忍却又无法真正切近这残忍和苦难,摆在自己面前的究竟是什么,连沈从文自己也“说不清”,然而这正好成全了他。
为什么会“说不清”?这是问题的关键,王晓明结合了沈从文的身世经历加以解释。“他出生于在湘西特别受人尊敬的军人世家,虽说家道日衰,童年毕竟还相当富足;以后离家入世,又是当的军人,而在那个时期,军人称得上是湘西最自在的一类人”①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这便决定了沈从文面对苦难和残忍,即便是受到了刺激,也还是“隔了一层”。但是随着年龄经历还有知识的增加,理智能力应该让他能够对那些原始的感受进行整理,使之变得清晰。但是,王晓明分析到,大城市受冷遇后的思乡情绪使得他先急着去重温童年欢愉,无暇也无心去整理对苦难、残忍的感受和记忆,“等到他终于回忆起这些阴暗故事的时候,眼前早已经挤满了对于牧歌图景的记忆:依然是隔了一层”②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分析看起来应该到此结束了——就是这种朦胧感让沈从文真正走进了那种独特的文体。但是没有,文章接下来更加精彩。王晓明像一个导游又像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总能在山穷水尽处转手一指便给你又一处洞天,他问:“一个人发现他所向往的美满世界中依然存在着不幸,而他对这不幸又看不清楚,他会怎样呢?”,他告诉我们有三种情况,一是“豁达地一笑”,“继续弹奏热情的颂歌”;二是“勃然大怒”,“睁圆了眼睛要把那不幸查个明白”;三是“介于这二者之间”,“因为不愿意放弃原先的向往,他反而对整个世界发生了怀疑”。王晓明说:“在我看来,沈从文的反应就近于第三类。”③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接下来的分析充分体现了王晓明的精细、深切:“他原就不是那种真能够达观的高人,好像也缺少洞悉不幸的眼力,而更重要的是,他毕竟是一个来自偏僻地方,正受着四面的轻蔑,偏偏又那样敏感多情的人,你甚至可以说他对湘西的神往本身就有几分病态。他越是虔诚的描绘牧歌图,就越说明他对这图景的信心并不牢固。因此,倘若在他眼前冒出来的仅仅是一块边沿明确的污迹,那就是再大也不要紧,他可以绕开它另外再画;可他遇上的恰恰是那样一团隐隐绰绰的阴影,谁也不能说它一定就不会遮没整个世界:请想一想,如果你落入这样的处境,会不会绝望地丢开画笔?”④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300页。
沈从文放不下这支画笔,那些故事时时刻刻啃噬着他的心。朦胧的情绪化成一种“人生无常”的感伤,这种情绪模糊又充满了诱惑力,同时又让他发现那些以前记忆里熟知的景象变了样子,这让他欲罢不能,他抑制不住要用新的笔法把那图景画下来。这样,沈从文终于向着那种独特的文体走了过去。
三、语言:重朴素的感悟
王晓明的批评似乎是有一点刻意排斥理论的。他从来不使用那些时髦的概念和艰涩的理论,总是力图用朴素而富有诗意的语言把问题说清楚。对此他曾经解释说:“许多特定的词,尤其是名词,都是和特定的认识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因为感知和理解方式发生变化,有了许多新的感受,用原有的词汇却无法表达,人才会创造和接受新的名词。如果你没有获得新的感受,或者这种感受可以用原来的词汇来表达,你是不会对新名词产生真正兴趣的。”⑤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300页。这样的态度确实是一种朴素的态度,透露出淡泊宁静的心态,反映在文字上便是同样的朴素而富于诗意。这样的文字当下已不常见,纯印象式的批评早已不是文学批评的主流,朴素似乎也不再是文化界的美德,对那种一味注重感悟而轻逻辑体系的批评文字,批评界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反思,并且表现了足够的厌倦甚至轻蔑,反思是必要的,但厌倦和轻蔑就不好了。感受性的东西和理论不是不能结合起来,朴素也不等于不深刻,王晓明在这方面即使不是做得最好的,也至少是在努力尝试,而且效果不错。
和那些用理论来图解作品,用作品来演绎理论的批评相比,王晓明的批评完全从作品感受出发,又不满足于获得些许灵感式的顿悟,作一点即兴的引申和发挥,他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的发现都来自于他敏感和尖锐的感受力,但对问题的分析和解答却又不仅靠感受,它需要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相当的理论素养。王晓明不缺少这些,只是在他的文字里,理论和学养没有成为知识的炫耀,没有成为情感枯竭感受力匮乏的遮羞布,而是作为一种内在的推动力深隐在了对问题的思考和推析之中。比如对沈从文丧失掉文体家过程和原因的分析,他结合考察了沈从文的身世经历,更为精细地推测和分析了这种身世处境对其心理状况的影响和作用,这不仅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还有具体层面的作家创作心理的探知,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推理分析过程中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严密和严谨的思维能力。不管什么样的理论,说到底,主要还是一种思维的训练,在人文学科领域,很少有像理工科那样可以不加论证直接拿过来加以运用的公理和公式,对于文学来说,任何理论必须和实际的经验感受,和第一手的作品材料相结合才具有说服力,理论必须解决了作品在阅读感受中产生的问题才算发挥了效用。所以理论作为一种思维的训练比作为一种纯粹的凭据和佐证要重要得多;同时,作为凭据和佐证的理论也必须与经验感受、作品材料真正地渗透融合。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批评,需要理论所提供的逻辑思维能力,在这一点上,王晓明的批评虽然拒绝了时髦的概念和空洞无着的理论,但理论所带来的严谨细密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对作品材料的宏观驾驭能力却深深地渗透在其批评中。其对沈从文作品阶段性整体特征的归纳就体现出良好的宏观概括能力,对这种整体性特征中那些异质性特征因素导致的“裂缝”的感受和分析,又充分体现出其令人惊叹的微观透析能力。
刘西渭(李健吾)曾经说过:“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需要外在的提示,甚至于离不开实际的影响。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却不是某部杰作或者某种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①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王晓明拒绝了时髦的概念和唬人的理论,将批评落实到自己的生命感受和思考中,正是这种生命感受和思考,显示了他“自己的存在”,其批评也成为可以单独存在的艺术品。这种生命感受和思考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他对沈从文的批评,最主要的挖掘角度是心理的角度,心理的分析最需要做到设身处地,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感同身受才行,否则根本无法推测他人内心的幽微曲折,更何况所要面对的是沈从文这样一个敏感忧郁的心灵。挖掘沈从文内心深藏着的自卑和受挫感对早期创作和处境改变(步入城市乡绅行列)之后创作的影响,能充分显示出王晓明对那种自卑和受挫心理精微的感应和体验,没有同样敏感和细腻的生命体验做不到如此精细深切;其次,他的批评里充满了“随时随地”的体悟,比如分析沈从文早期处于模仿阶段的创作中为何会有那些比较独特(或者说个人化)的作品时,他说:“我们常说人与人在感情上能够相通,那其实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你刚刚注意到自己的一种情感记忆的时候,也许会觉得它和别人的某些情感差不多……可一旦在这情感中沉浸得深入一些,你立刻就会看出它其实是那样的与众不同……”②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这种体悟其实是一种普遍化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这样的体悟经常如晨露般点缀摇曳于其批评文字当中,同时也参与构筑着文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第三,在其貌似温和徐舒的文字背后藏着深广的忧愤,有学者早就指出他的批评着眼点并非创作心理学,而是文化心理学,在作品、作家的背后他力图挖掘出的是文化心理的积垢,就我们所讨论的这篇文章来看,这种深广的忧愤不仅表现在通过沈从文揭示出世俗意识对作家创造力的腐蚀,而且还不时浮现在文章的角角落落,甚至注释里——其注释很有特点,它们大多不是告诉我们引文出处,或提供给文章以阐释和佐证,而是基于自己的感悟做出的一种引申和发挥,夹杂了其个人化的思考和体会。比如提到人对世界的理智(或观念)解释往往有很大的被动性,人常常是用各种现成的逻辑范畴和价值标准,依照现实环境规定的方向来进行解释,也就是说人依据现成的观念和理智判断解释的时候,常常为观念所累而缺少一种独立性和主动性,对此他这样做了注释:“那些特别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当然是例外;但可惜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文学家一般都不属于此例。”①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0页。这是对文学家的批判,更是对所有独立自由理性精神匮乏者的批判,很能体现掩藏在文字中的那种深广的忧愤。
批评的风格是多样的,王晓明只是代表了一种,或者说只是属于他自己的一种,当然这种批评(尤其是其批评方法)还存在争议,但从他的批评中我们确实可以获得很多启发:源于知识分子良知和责任感的忧愤和批判精神,深刻敏锐的问题意识,精细严密的推理分析能力等。他非常注重批评的“真诚”,甚至觉得真诚比学识修养和批评文章的科学性还要重要②王晓明:《潜流与漩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0页。。我们应该承认,王晓明的批评对帮助克服当前学界如批评精神的失落、批评话语的滥用、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跟风等诸多不良批评倾向,对促进文学批评事业的良性发展确实有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