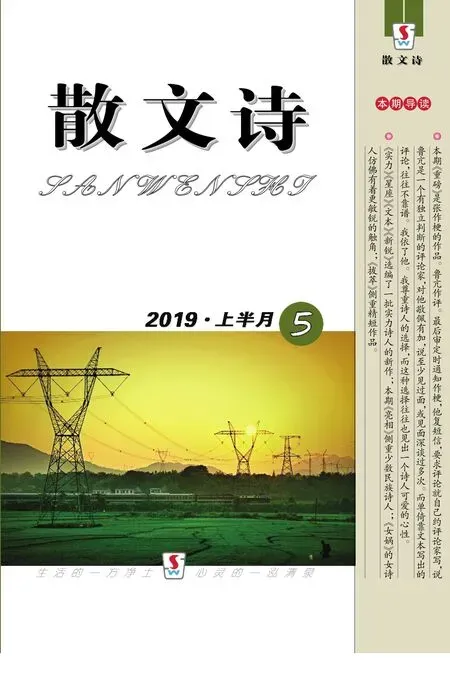马岭散章
天津◎青槐
燕子
转过山坳,世界消失了……
一房老屋停在春天的额头,是世界的源点。燕子绕屋三匝,穿窗投入梁下的旧巢。昨天的体温,还暖在巢沿。
此时,人间是一扇虚掩的窗。源点与终点,都栖在窗棂上。
屋外,鹑鸠在枞树林里唱歌,土鸡在啄食,柴犬在篱笆下跑来跑去……一切都是昨天的样子,有着理所当然与怡然自得的表情。
风收敛翅膀像燕子收敛归程,穿越窗棂如同燕子穿越千里。
燕子梳羽,看着母亲啼啾,它的喜悦能把整个春天填满。
这讨厌的燕子,总是抢先一步到达
母亲的微笑。
清明
鹑鸠的歌声从沿江公路跑到伍家院,用去了一秒的时间。刚好等同父亲在檐角,眯着眼睛认出从山坳边走出的我。
爱唱歌的鹑鸠,在梅山到处乱窜,它与刚睡醒的映山红一样,总是比桃花更早拥抱春雨,拥抱老牛叔经年的风湿与湿漉漉的咳嗽,拥抱山峦间烟雨迷蒙的清明,也拥抱我:一个差点分不清鸲鹆与乌鸦的远乡人。
席菜沿着山路,曲曲折折地绿着,像大多数山民的心肠,给点春雨就发芽,蘸点春风就开花。禾苗茂盛时,它就与叔爷爷一起,在路边站成草。
唯有金樱子,用体内的针尖挑着雨丝,挑着父亲的檀香与纸钱,轻轻地敲打着清明。
祖传的纸幡在山坡摇曳,它们在乡亲的缅怀里,从一朵花落看到一万朵花落,从一朵花蕾看到一万朵花开……
生与死,被同一竿纸幡飘展,随山峦流淌,渊默如光阴。此时,我的山峦哟,死亡如此澎湃又如此安宁。
此时,鞭炮禁燃,群峦胸怀静寂。
那么多庞大的出生,漫山遍野地跑,在花瓣里一一打开。
此时,生与死都是一场春雨。
我抬头,看见每一座山峰都正襟危坐
像不苟言笑的祖坟。
花椒凤蝶
在老椿村下看岩烟氤氲是一种幸福。
山崖边,金钱松脱光衣服用影子在资江里游泳,岩烟再高三尺,便可以淹没它锁骨上的鸟鸣。
屋后的田垄里,禾苗在抽穗。更远处的荒田里,稗草因抽穗太少正惭愧地低下了头。
老牛叔在唱歌。
他的瘦脖子伴着山歌的节奏伸缩,像啄食的鸭子。音节嘹亮之后,满山峦都是郎与妹的应和。
“上山能挑百斤担,下田能摸水田螺。”
花椒凤蝶从丝瓜藤边闪出,掠过老牛叔
就像掠过一朵花。
长喙天蛾
“一辈子只爱一朵花是可耻的。”
长喙天蛾不说话,它在苦瓜花前悬停,内心的甜蜜,只说与花朵与清风。悬空的翅膀,只为下一朵花扇动。
独自一人将孩子养大的孙婆婆看着长喙天蛾,就像看着亲人。
七十多岁的她洞悉马岭隐秘,知道不是每一朵花都会有甜蜜的果实,知道凋零与绽放总是互为背景,知道时光里行走,就是寻找每一朵花,往死里爱,将落日爱成朝阳,泪水爱成花蜜。
“总有一天,我终将替流水死去。”
长喙天蛾飞过孙婆婆的咳嗽,它看见老屋后的小溪,蛇一样爬进了草丛,也爬过老屋与不远处别墅的影子。
——此时,孙婆婆的眼里群峦如染,山花烂漫。
长喙天蛾在花蕊里,吻上了小溪
长着花香的透明体重。
冬桔
最后一枚桔子黄在树上,寒风穿过它,就像穿过秋天的句号。
凛冽的风摇着翠绿的桔叶,仿佛随时都会递出白色的桔花;随时都会摇落桔子金黄的倒影与虚无的鸟鸣;随时都会摇落父亲的咳嗽与母亲的浅笑……
此时,整个桔林都是它的:比它高的天,比它低的草,以及夹在高与低之间的我与几声狗吠。
此时,坐在树上的桔子与我对视,风吹着它就像吹着孤独。
孤独有多大,内心就有多甜。
在冬天
在冬天,满地的绿草个个都在代言我的家乡。
冬寒菜内心圆滑,掌心有小火苗,穿绿衣,风一摇,影子里便滴落鸟鸣。
蜈蚣草见缝插针,每一根骨节都伸出一双手,它知道小人物的大情怀就是拥抱身边所有的事物。阳光甜,石缝辽阔,一捧泥土也可以爱成祖国。
风吹唐竹,细碎的声响恍若秦朝。
傩歌用丘陵的形状起伏,唱土地(1)的人,嗓子里养着一条叫资水的河,黄尾鲷模样的颂歌,逐水凌波……
鸡鸣是软的,狗吠也是。
一只大鹅追着我咬,仿佛我是它的仇人
就像我追着时光咬。
注:(员)唱土地:老家的一种风俗,春节前后,会说唱的人就会挨家挨户地登门,以说唱的形式送上祝福的颂歌,换取报酬。颂歌节奏明快,词语吉祥。
寒霜之后
大雪落下——除了时光,有什么不一夜白头呢?
寒霜吻在雪上,它不知道:在马岭,太庞大的爱,容易令青春变色。鸟鸣在寒霜里暗淡,满园子的蔬菜从绿转枯。
干枯的还有昨日的稻茎,一茬茬像祖先的断骨,在田垄里固执地等待春分。
冬天仍然走不出二十年前的记忆:燕巢干巴巴的,守着燕子的南归梦。白头翁啄着苦楝子,啄着啄着歌声便掉落下来。
没有花朵,烟雨比人情冷漠;没有父母,家乡比天涯遥远……
阳光还是四十年前的样子,母亲垫着影子摘菜芯,摘着摘着,微笑便也滴落了下来。
老屋前的松树林,在母亲的微笑里
越长越像,一声鸟鸣。
摸黑回家
在羞涩的乡村公路上摸黑回家,犬吠比灯光温暖。
寡妇滩下,资江瘦成一弯冬月。
篱笆边,池塘黝黑,它的暗语唯有抱蕾的枇杷与母亲的唠叨懂。
路宽一米,天地便晴朗十分。太阳能路灯是新的,檐灯也是。
这个春节,小村禁燃炮竹之后,父亲每一声咳嗽,都能咳出
一大片宁静
一大片安恬。